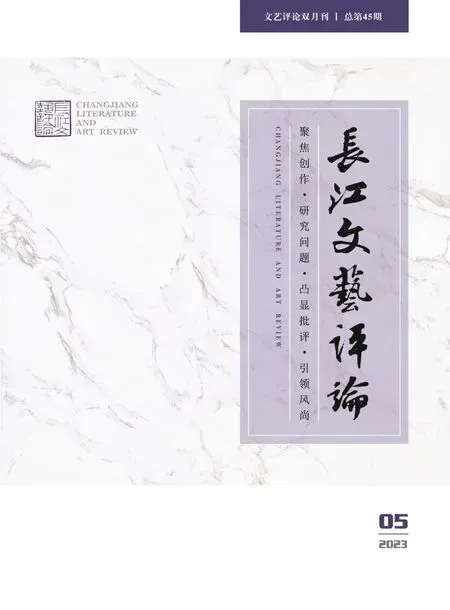起源、介入與方法:論“大地”與新時代的文藝創作
◆楊光宗 鄭雪禮
一、“大地”的多重意蘊
從文學的發展演變史來看,作為人類生存家園的“大地”因承載著諸多人類活動而顯得實在又深邃,實在意味著人能夠在物理意義上腳踏實地,進行各種人類活動;而深邃則更多地來源于“大地”所能夠容納的人類活動及人類從歷史事件中進行的哲學思辨與經驗總結。隨著時代的演進,“大地”得到更多的闡釋,其意蘊也共占豐富與深刻兩端,體現為一種堅實的精神屬性。
(一)從“大地之母”原型到道家“天”“地”“人”一體的自然意蘊
在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基于原始農業與家畜飼養的出現,以及原始農具的使用,人類對土地的崇拜與日俱增,上古時期關于女媧與后土的神話佐證了這一點。女媧以華夏民族人文先祖的創世神的姿態出現,仿照自己摶土造人,其子女的骨架與肉身均取材于大地,而女媧后來的補天救世,也是出于對洪水肆虐,淹沒人類耕地的不忍;后土則執掌陰陽生育、萬物之美與大地山川的秀麗,對大地予以適當的變化使之適應人類的耕作,是基于土地給予人類福祉的女性神。女媧與后土均有著“大地之母”的稱號,在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中,她們與大地的緊密關聯使其稱號均具有了原型色彩,是中國古代社會人類與大地長期存在深厚情感的映照。存在于上古神話傳說中的大地以物質形態存在,深刻影響中國先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各類文化活動。
在道家原典中,常有將天、地、人以一體論之的論述,它們不僅說明了人類在衣食住行等物質層面對大地的依賴性,同時也從精神層面講述了大地對人類藝術空間的介入。老子言:“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這就意味著,天、地作為人生存的根本,對萬物的出現與生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雖然“地法天”直述了地之于天的第二性地位,但是“人法地”說明了大地對人類的承載之恩與人的行為效仿大地、依賴大地的合理性,是對人類與大地間親緣關系的合理說明。如此看來,道家強調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不無道理,從“命系天,根在地”的樸素哲學觀,到莊子基于自然對人的塑造作用提出的“與人為善、與物為春”的生存要義,均顯現出道家哲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關注。拋卻大地的物質屬性,其形而上的色彩也在道家哲學中十分明顯。天地與藝術空間、藝術精神相聯結,人類能夠通過精神的升騰與超脫,運用種種語言和符號,打破物理世界的時空,進入“精神縱橫馳騁、靈活自由翱翔之空靈領域”[2]。莊子承載著出世的睿見,不拘泥于有限的現實世界,主張將精神化為大鵬,扶搖而上以背青天,最終上達精神世界的至高點——“寥天一”處,進而達到“天地與我共生,萬物于我為一”的境界,此即“提其神于太虛而俯之”,能“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當實現藝術升騰的人類從凌云之處俯視人間,便可頓覺自然之美麗,而現實世界的種種焦躁與虛浮在這一過程中煙消云散。在象征世間一切事物運行規律的“道”的統攝下,天、地、人三者交錯勾連,“大地”之于人類的重要作用在哲學層面得到奠基。
在工業革命深入發展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農業文明的發展不斷加深著人類與土地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夠先進的勞動資料、單一的勞動對象,均導致承擔社會發展重任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不得不時刻感受自然帶來的壓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為了交往半徑受限的人類的常態,這就使得“大地”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存在同樣顯現出了與自然的親緣關系。以“大地”為基礎的自然書寫始終是古代文人的難以割舍的創作核心,據民俗學家孫作云先生統計,《詩經》305篇中共記載了動、植物252種,涉及到的山、水、草、木、鳥、獸、蟲、魚不勝枚舉,這些頗具靈性的自然事物存在于天地間,以“象”的身份滿足了詩文創作者抒發情感的需求,也為接受者提供了會“意”的可能,在《詩經·王風·君子于役》中,有“君子于役,不知歸期”,從地理角度反映出男子從軍的路途遙遠,又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從農業生產的角度展現了生長于天地間的自然萬物供人取用的生活現象,兩者均是“人法地”的結果。陶淵明棲身南山、采菊種作,以魏晉名士獨有的隱逸生活彰顯“大地”之上的閑情雅致,至于后來陶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則也說明了延誤農時、不擅耕作只會無限擴大土地對人類限制,進而導致“大地”僅能夠存在于文人的抽象表達中。對自然的渴求并非是魏晉文人的專屬,在整個封建時代,士大夫階層的文人往往對庸俗繁雜的社會生活感到困倦,并將“大地”之上的自然萬物作為調節情緒、陶冶情操的有效工具,由此,出游宴飲、尋山問道、農事耕作等活動在文人群體內風靡,結伴出游如“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親近農事如“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麥苗漸長天苦晴,土干確確鋤不得”,貶謫自慰如“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古代文藝創作者不斷以他者的視角嘗試將“大地”融入到文藝實踐中,體現為借自然物象以抒情言志,反映天、地、人三者的合一。
(二)從“家”“國”合一到“扎根生活、服務人民”的社會意蘊
不同于中國古代社會中“大地”概念顯現出的自然色彩,“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大地”與中國人民的家國情懷結合得更加緊密。魯迅對故園、鄉土及生長于其間的生命有著深刻的思考,在小說《補天》中,他以地母女媧為原型,書寫她煉石補天、哺育人類的辛苦與疲倦,展現出對祖國大地極具歷史感的深厚情愫。魯迅也在《故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調用羅漢豆、烏篷船、菜畦、桑椹、蜜蜂等多種意象,在對故鄉的回憶中塑造家園的溫馨。魯迅將故鄉的風景、人物與風俗融為一體,將其塑造成為那個外憂內患的時代中國獨特的鄉土“大地”。沈從文則在《長河》《邊城》等作品中借湘西地區自然景觀與風土人情,塑造了滿滿、天保、儺送、夭夭、翠翠等純粹又美好的形象,勾勒出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湘西“大地”。在戰亂年代,家與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魯迅、沈從文從“家”著手,描摹了中國美好的鄉村“大地”,給予遭受多重打擊的“國”以精神力量,也有蕭軍《八月的鄉村》與艾青《我愛這土地》等作家作品在中國人民如火如荼地投入抗日戰爭的背景下,以積極抵抗的個體及其感觸為核心,直接表達對“家”被破壞的痛惜與對“國”將奮起的真切期盼。毛澤東同志在其創作與講話中同樣展現了“大地”所具備的家國情懷,他在早年寫就了氣勢恢宏的《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直擊靈魂的一問,凝結了毛澤東本人對中華民族走向何方的憂慮與思考,也展現了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與追求,帶有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毛澤東為團結抗擊侵略的一切力量,建立文藝統一戰線,對黨的文藝工作作出了“扎根生活、服務人民”指示,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在生活與人民間扎根,譜寫祖國大地上的華章,并催生出了一批服務于社會現實的優秀文藝作品,如杜鵬程的《保衛延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賀敬之的《回延安》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鼓勵藝術領域“百花齊放”,郭沫若的《蔡文姬》、楊沫的《青春之歌》、老舍的《茶館》等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就此產生,報告文學、雜文、散文、詩歌等多種體裁的作品走向繁榮,極大地豐富了建國后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
近十年來,不論從文藝政策的引導還是作家的創作上看,對“大地”進行闡釋已經成為了一種頗具規模的共識。第一,在文藝作品數量激增與文藝表現形式逐漸多樣的背景下,“大地”被視為創作者釋放藝術想象力的根基,許多具有極高文學素養,并已創作出優秀文藝作品的藝術家獲得了正本清源、創造新時代文藝精品的動力,而他們的創作需依靠的,便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能夠推動人民文藝發展的“大地”。第二,中國文學在海外漸受關注,莫言、余華、殘雪的創作使得外國讀者獲得了觀察中國、了解中國的契機,而“大地”在此形勢下也成為了文藝塑造中國形象、傳播中國聲音的生長土壤。
綜上所述,文藝創作意義上的“大地”具備雙重意蘊:一是生發于中國上古時期神話傳說與道家自然感物觀的自然意蘊,既包括能夠承載人類衣食住行的物質形態的“土地”,又包括實現精神擢升的人類在藝術空間中“看到”的、根據自身生活經驗想象出的“大地”,帶有一定形而上的意味。賦予“大地”自然意蘊的哲學家、藝術家們要求創作者“心在物外,身與神游”,盡力實現精神的升騰,體味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美麗;二是在百年中國近現代史中呈現逐步發展狀態的從“家”“國”合一到“扎根生活、服務人民”的社會意蘊,反映了先進知識分子在愛國主義引領下,對人民及其生活進行高度關注并總結書寫的全過程,關涉不同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狀態。這要求文藝創作者能夠順應時代的發展,在當下合理使用媒介技術輔助創作,對現實生活加以觀察與總結。“大地”的雙重意蘊并未在文藝實踐的歷時性發展中被割裂,古代文學中的“大地”同樣具備社會意蘊,如“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萬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晉英雄”等詩句中便展現出了作者興國安邦的夙愿以及對個人與集體力量的辯證看待;現當代文學中的“大地”也顯現出了自然意蘊,如魯迅、沈從文、汪曾祺等作家借家園的美好對地方風土人情進行的記錄式敘寫。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藝作品是時代的產物,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以農業生產為主導,自然以其原生的面貌介入人類的生產生活,此時的“大地”之于人類處于第一性地位。而近代以后,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日漸增多,“人法地”在過去存在的諸多不便得到緩解甚至消除,“大地”在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中不再具有絕對的獨立地位,而成為人類自然書寫在文化與社會領域的延伸。
二、“大地”構塑新時代文藝創作的重要性
(一)“大地”是文藝作品成為精品的養料
中國進入新時代以來,以“大地”為依托進行的文藝創作與批評成果斐然,按照創作主題與內容進行劃分,這些成果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對直接提及“大地”的既有文藝精品進行的文藝批評,如對賽珍珠的《大地》,艾青的《我愛這土地》,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范穩的《悲憫大地》等作品的批評;其二,對當代作家作品進行的文學批評,并指出了該作品在書寫過程中的“大地”特性,如被稱為“書寫鄉村大地回聲”的莫言,熱愛土地的“大地之子”海子,“于大地上書寫”的路遙等;其三,對“大地”相關的文藝理論進行的研究與闡釋,如對海德格爾“大地”理論的解析與應用,又如對“大地”進行的符號學闡釋;其四,對國家在推行文藝方針政策時所論述的“大地”相關內容進行整理與解析,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問題。這四個部分并非呈現各自獨立的割裂狀態,而往往存在一些交叉甚至重合的部分,對“大地”涵義的闡述與其對文藝創作的重要作用便體現于此。
以“大地”為依托進行的文藝創作與批評成果斐然,究其根源,第一,在于“大地”本身意蘊的豐富性,既包含作家在創作時對自然的描繪或在字里行間體現出的對自然的深厚情感,也包括作家筆下的那些受社會影響頗深的地域與在其中生存的人民;第二,在于作家與“大地”間存在不可分割性,他們或生長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黃土高原,創作風格極盡粗獷豪邁,或生于皇城相府,在京味的喧囂中展現時代的風云變幻,亦或久居于江南小鎮,在陰雨綿綿中書寫邊城情話。人不能脫離他所生長的環境,作家更需要在其生活經驗中提煉出可供言說的精品。
(二)“大地”需要新時代文藝精品的反哺
“大地”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近十年來,互聯網不斷發展,人類逐步數字化地生存于社會中,作為與文藝創作有著強關聯性的“大地”逐步向虛擬化的數字平臺靠攏,為公眾提供“喧嘩”的機遇。“喧嘩”對于“大地”的建構是雙向的,一方面,創作者的泛化使得不同審美情趣、不同創作水平的作品大量產出,如當下在各個網絡平臺泛濫的網絡小說和以個人拍攝為主、作品內容受時長限制的自媒體文藝作品等,其審美的積極性、內容的專業性都值得商榷,需要接受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就對“大地”的時代性轉化產生了阻礙;另一方面,在“喧嘩”中也有理性聲音的存在,不排除諸多具有正確價值觀導向與一定專業性知識的個體創作者創作出了具備相當程度審美性的文藝精品,他們深諳網絡運行規則,是“流量密碼”的破解者,也是“網絡爆款”的制作人。與此同時,部分專業作家也加入到了數字平臺的創作中來,他們或對自己書籍進行進一步的闡釋,或借由網絡對其作品的改編進行宣傳,以促成文藝作品的最大化傳播。文藝創作的數字化趨勢實質上是對“大地”概念的充實,使其不僅具有對“家”“國”發展的殷切期盼,還有對個體生活在數字化潮流中產生的變動的反饋。
新時代的文藝創作者們無法離開網絡,他們的生長環境是虛實結合的,既有對現實或深或淺的介入,又以網絡沖浪的方式便捷化地接受在現實中難以接觸的信息。所以,新時期的“大地”不能停留在自然與社會等實體的范疇,還應對虛擬空間的文藝創作表示歡迎。
三、“大地”構塑新時代文藝創作的方法
緊貼“大地”是一種創作選擇,也是創作者在時代影響下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創作立場。從方法的視角來看,“大地”對文藝創作的構塑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努力,即關注個體與集體經驗、平衡文藝作品與媒介技術、塑造中國故事中的中國形象。
(一)從“大地”的人民屬性出發,關注“具體的人”與“集體的事”
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人民在文藝實踐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人民既是歷史的親歷者,也是歷史的創作者,他們并非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文藝創作若以人民為中心,便不得不關注“具體的人”與“集體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試圖洞悉人類內心世界時感慨道:“我愛人類,但我對自己實在大惑不解,我越是愛整個人類,就越是不愛具體的人,即一個一個的人。”[3]所謂“具體的人”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的,可以被真實感受到的,時而顯現人性的美好,而永遠存在瑕疵。當下社會在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彩中飛速前進,諸多非理性的、反傳統的文藝創作成為了現代社會的文化景觀,如講述世界在病毒中毀滅又重建的末日題材作品,塑造超級英雄懲惡揚善、拯救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作品,均基于宏大視角展開敘事,而主角身邊小人物的生存與死亡、個人價值的凸顯均被納入一場視覺狂歡的背景板。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古老中國在近百年來的發展中歷經坎坷,而人民有著對于時代發展最為直觀、最為深刻的體驗,他們是社會變遷中的“具體的人”。創作者只有立足人民生活的土地,開展廣泛的田野調查,觀察農人、手工業者、農民工、城市新銳們的生活并與之交流,總結個體經驗以反映群體狀態,給讀者以感同身受的激烈美感。不少當代作家會采用關注“具體的人”的方法來反映時代風貌,他們在對人民不同視角的觀察與書寫中顯現出對人性的深刻洞見。當代中國主流文學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給予了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以相當力度的支持,從全景式表現上世紀末中國城鄉社會生活的《平凡的世界》,到以“延津”為“大地”,展現兩代人失去與追尋故事的《一句頂一萬句》,再到書寫“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的《人世間》,作家不拘泥于人民生活的現實表象,而憑借自身的生活經驗,以真摯的情感與筆觸表現時代變遷與人事糾葛的切膚之痛,于表象間展現深邃,于平凡中鑄就經典。
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4]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社會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但生產力水平受限,大量勞動人口只有聯合起來參與農耕才能滿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集體主義傳統在這種農耕文明的影響下起源并發展,個體行為逐步與小農經濟時代最重要的“集體的事”,即農耕相結合,個體的價值也在與集體的強關聯性中得到凸顯。直至2020年,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貧困問題,自然經濟生產力的提升與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集體的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文化作為社會前進的支柱之一,成為了一項需要群策群力的事業。從宏觀層面講,“具體的人”需要有“宏觀的事”作為指向,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目標,國家以增近民生福祉為基礎,對法律法規、醫療保障、生態環境、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等多方面“集體的事”進行了規劃,也為未來十年中國的文藝創作提供了指向與豐富的素材。諸如取材于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的《姜子牙》《白蛇傳·情》,以歷史典籍為基點進行創造性改編的《中國奇譚》《長安三萬里》,都是國家“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號召下的產物。從微觀層面講,“集體的事”也需要“具體的人”的大力支持,“具體的人”始終是文藝的敘事主體與對象。在城市化迅速推進的當下,大量農村勞動力選擇遠離故土,去往城市從事手工業、服務業;部分優異者經過篩選考入大學,經過進修后在城市獲得了一席之地;還有響應“青年下鄉”政策的下鄉創業者,為鄉村帶去新的面貌,他們都是“集體的事”的親歷者與講述者,也是文藝創作應當關注的對象。諸如反映時代交替中農民與工人生活的影片《三峽好人》《山海情》《隱入塵煙》,又如講述大學生返鄉參加建設工作的作品《秀美人生》,也有再現城市新銳的奮斗生活的作品《人生第一次》,均顯現了為“集體的事”奮斗的個體形象。
(二)從“大地”的創新屬性出發,平衡文藝作品與媒介技術
“文章和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藝作品的創作與改編在形式與方法上應當與時代發展帶來的創新性技術相結合,在主題與內容方面則要切合當下時代的主旋律,任何固步自封的與過于超前的文藝作品都難以形成文學經典應具備的固定接受者群體。
在電子媒介被廣泛使用以前,在西方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才應運而生的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媒介技術,對文藝的介入微乎其微,文字在文藝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文藝創作選用不同的書寫對象,以散文、小說、詩歌等不同書寫建構不同的故事,但在書寫與傳播的媒介上沒有根本性的進步——均以物料、紙張等實體物品為主體,這也使得文藝創作僅能從靜態的文字、圖像或動態的語言、講演中刺激讀者的感官,而無法給予讀者一種持續的、直觀的感受。所謂“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古代文人對文藝作品“意境”的理解與闡釋實際上也是接受者感官與藝術作品間存在隔膜的表現。而當互聯網的發展進入新階段,數字媒介依托于多種創新性技術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文藝作品的表現形式得到了聲音、圖像、影像的全方位拓展,文藝創作也擁有了更多具備可行性的選擇,包括攝影、電影、電視在內的電子媒介開始運用自身在復制、儲存、傳播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創造出更多文藝類型,同時拓展了文藝邊界。于是,當下時代的創作者不得不關注到創新性技術對文藝創作的強大輔助作用,圖像化、影視化、電子游戲化的文藝作品均是二者相結合的產物,如古代文學經典的改編紀錄片《中國》《書簡閱中國》,電子游戲《黑神話:悟空》《全面戰爭:三國》等;還有諸多當代文學精品的影視化作品,如《活著》《紅高粱》等。在技術的加持下,文藝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續,并留下了更加廣闊的闡釋空間。
技術對藝術的輔助有時會演變為二者間此消彼長的博弈,而長期以來高居藝術殿堂主位的文字通常是受到壓制的一方,正如本雅明所言:“將來的文盲是不懂得攝影的人,而不是不會書寫的人”[5]。圖像與影像“殺死了”過去那種純粹的藝術,并不斷蠶食文字具備的意義生產權力,本身就不具備大量閱讀興趣與能力的讀者不再是文字閱讀的潛在客戶,轉身就投向了此類看似同樣具備強大文化屬性的文藝奇觀,沉淪于新技術的聲色犬馬而不自知。人類從當代高科技媒介手段中獲取方便與舒適的同時,與世界直接獲取連接的能力卻遭受弱化,接受者像是被隔絕在電子孤島上的哲學家,總試圖以絕對理性評判新生的文藝作品,卻在孤寂的生活方式中喪失感性的能力。綜上,文字依然需要占據文藝創作的主體,文藝作品依舊需要主導媒介技術的使用。
(三)從“大地”的時代屬性出發,塑造中國故事中的中國形象
在中國的文化資源得到進一步挖掘的趨勢下,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可愛、可敬中國形象成為了新時代文藝發展的要求。中國形象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而中國形象的“可愛”,則是在向世界傳遞中國走和平發展路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望。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傳統,從文化典籍中拔擢而出的中國形象數不勝數,并于近代在海商與藝術家的共同努力下踏上享譽世界的征途,有從歷史中挖掘出的真實形象,如忠肝義膽、義薄云天的“關公”關云長,忠孝兩全、替父從軍的巾幗英雄花木蘭;也有從神話中發源的虛構形象,如拒斥成規、百折不撓的“斗戰勝佛”孫悟空,斧劈華山、一心救母的沉香;還有在當下,為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而創造的新形象,如北京冬奧會的“冰墩墩”與“雪容融”,這些中國形象依托于其背后的故事,為新時期的文藝創作提供了素材與經驗。值得注意的是,居于民族共同體內的中國形象是自構的,能夠得到廣泛的肯定與贊譽,而跨區域、跨民族的中國形象存在他構的現象,其形成與傳播造成的危害極大。1913年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在其《傅滿洲》系列小說中創造了身體瘦削、面部狹長、眼露兇光的“傅滿洲”形象——一個集天才與邪惡于一身的科學家,它集中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妖魔化想象,是“黃禍論”最直接的體現。直至今日,“黃禍論”雖然不再像百年前那樣被西方人廣泛認同,但隨時代的發展,它依舊為中國人留下了許多諸如“體型瘦削,雙眼狹細”“凝滯呆板、缺乏創新”的刻板印象。
中國形象來自于不同時代自然與社會發展下的文藝“大地”,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就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再現與闡釋,也是對“大地”自然與社會功能的彰顯。文藝創作作為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的必要手段,必須發揮自構的作用,對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進行影視化改編,從性格到外貌對其進行全方位的審視與重構,既要符合原著的人物形象,又要盡量貼合大眾的審美趣味。經此過程,文藝創作對“大地”的介入才能深化,新時期的中國形象才能隨中國故事一起進入當下時代的“大地”的范疇。
結語
“大地”首先是一個多重的概念,它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自然的,又是社會的。它從“大地之母”的神話中發源,在道家自然觀中得到哲學闡釋與理論總結。以此為基礎,近百年來的文藝創作者及黨的領導人在對現實的觀照中不斷挖掘“大地”的社會意蘊,并分析出了“大地”蘊含著的愛國主義情愫與人民意旨。其次,“大地”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而不斷充實自身,并在對文藝創作的介入中取得了文藝創作與批評方面的豐碩成果。最后,文藝創作者憑借對人類、技術和符號三方面的關注,促使文藝創作向“大地”靠攏,從方法論的視角闡述了新時代文藝精品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