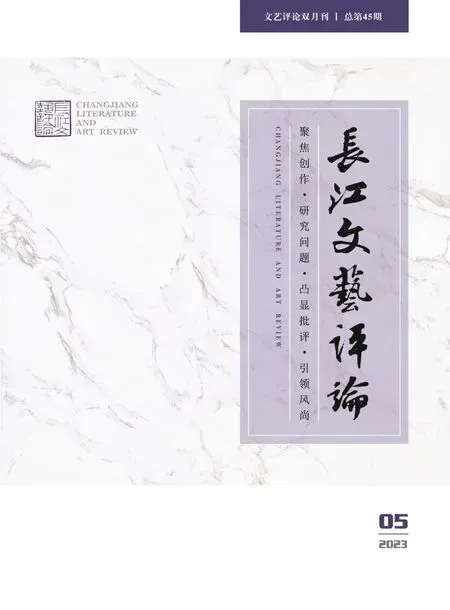互文·隱喻·反諷:論東西《回響》的敘事策略
◆顏同林 王太軍
作為東西繼《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之后推出的第四部長篇小說,《回響》依然是一部聚焦現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的作品,延續了作家長期以來對復雜人性的持續關注和反復書寫。小說肇始于一樁殘忍的兇殺案,沿著破案緝兇、追查真相的敘事主線,借“推理偵破”之名,行“心理挖掘”之實,傳達了東西對于情感、倫理、道德、人性等形而上層面的深入思考。自《回響》面世以來,其文本張力和思想意蘊引發眾多知名評論家撰文“回響”,王彬彬指出《回響》是“在人性的平面上表現人性之種種不確定的小說”[1],吳俊認為《回響》“呈現出一個具有生活經驗性真實的隱喻文本”[2],張莉表示《回響》“切實寫出了當下時代人內心的情感危機”[3]……這些獨到的評論,佐證了《回響》的文學價值。
盡管《回響》是一個具有多重闡釋可能的文本,但不確定性應該是作品中比較直觀且值得推敲的一種意義指涉。小說借助刑警冉咚咚破獲“大坑案”的緝兇路徑和與丈夫慕達夫婚戀破滅的情變過程,揭示出現代人其實生活在一種不確定的情境里,人的語言、認知、情感、心理乃至生存境遇、精神狀態,都處于不確定之中,從而鋪陳出人生、人心、人性的不確定性。那么這種不確定性是如何力透紙背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呢?這就涉及東西小說創作的敘事策略了。互文、隱喻、反諷的敘事策略,在東西的創作中屢見不鮮。以長篇小說為例,如果說《耳光響亮》書寫的是“后革命時代的悲喜劇”,那么《后悔錄》則上溯至革命時代“個人被誤置的歷史”,而《篡改的命》下啟物質主義時代“人的身份的喪失”[4],作家使用互文、隱喻、反諷的敘事策略,將當代歷史次第呈現在讀者眼前。長篇新作《回響》拆解生活真相和心理真實,探究當代人人心人性的幽暗變化,在敘事上同樣采用的是東西最為得心應手的互文、隱喻、反諷的寫作策略,因而無論是主題上,還是敘事上,都與前三部恰好構成一個序列,體現著作家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編年史書寫的宏圖壯志。以下將展開討論《回響》中互文、隱喻、反諷的敘事策略對于文本不確定性意義的生成過程。
一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互文是一種修辭手法,有“參互成文,合而見義”之義。而在西方文論中,互文是一種文本理論,強調的是文本之間的互涉關系和邏輯生成,使文本從自我封閉的狀態轉向開放的意指實踐。互文的豐富指涉,使之既成為東西組織敘事、建構情節、塑造人物的具體敘事策略,也成為我們認知、闡釋《回響》的一種研究視角。
閱讀《回響》文本,首先令人矚目的便是雙線并置的敘事結構。小說共有九章,其中第一、三、五、七章以刑偵推理為敘事主線,講述刑警冉咚咚偵破“大坑案”的過程;第二、四、六、八章以婚姻愛情為敘事核心,講述冉咚咚與丈夫慕達夫婚姻走向離散的情感際遇;第九章則雙線合并,給予案件和情感一個看似明確且圓滿的結局。這兩條敘事主線既獨立行進,又彼此交織,以互文的方式巧妙實現了把案件部分生活化、把生活部分案件化、像偵破案件一樣偵破愛情的敘事意圖。聚焦小說里兇殺案的偵破進度與兩人情感婚姻的離散程度,可以看到,兩條敘事主線正是通過情節性關聯形成互文的,每當在案件有了重大進展或轉向時,冉咚咚與慕達夫的婚姻關系也會出現相應的波折起伏。如冉咚咚因為調查受害者夏冰清身份而調閱藍湖大酒店資料時,意外發現了丈夫慕達夫的兩次開房記錄,由此在心中埋下懷疑的種子,且一發不可收拾;而此后每當兇殺案偵破遇阻陷入困境時,冉咚咚和慕達夫總是發生激烈的爭吵,關系愈加變得疏遠。這之外,兩人約定的離婚日期以案件告破為界限,雖然理性承諾的約束力遠遠比不上感情破裂的速度,但等到案件真相大白,冉咚咚終于坦然面對了自己的內心情感。可見,奇數章的案件推理始終與偶數章的情感糾葛緊密纏繞在一起。東西在《回響》的“創作談”中明確地指出:“奇數章專寫案件,偶數章專寫感情,最后一章兩線合并,一條線的情節跌宕起伏,另一條線的情節近乎靜止,但兩條線上的人物都內心翻滾,相互纏繞形成‘回響’。”[5]這種兩條主線相互纏繞形成的小說結構層面的“回響”,即是互文的敘事策略所達成的。
《回響》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征是“推理小說”的敘事模式。推理小說是通俗文學的一種亞類型,從這個角度講,東西借助通俗文學的寫作方式展開了嚴肅文學的社會分析,將思想的觸角伸向文學的某種本質——對于幽暗人心、復雜人性的探尋和詰問,從而實現了符合自己純文學作家身份的強烈現實關懷。這里無意強調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區別,只是想要引出東西對于當代人情感世界的深入分析與道德層面的透徹解剖,也即對于人心、人性不確定性的思考。評論家王春林指出:“《回響》盡管有著足夠充分的推理小說元素,但卻仍然不能被歸類于推理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文本中那些以冉咚咚的情感世界為主要關注對象的偶數章的存在。更進一步說,整部小說藝術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包括冉咚咚在內的若干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精神分析。”[6]的確如此,雖然小說以命案偵破為敘事的內驅力,情節緊湊、邏輯嚴密而頗有看頭,但文本的敘述重心仍在偶數章的心理勘探與人性剖析之上。冉咚咚和慕達夫作為小說的核心人物,東西在圍繞兩人夫妻關系從恩愛到破滅的敘述中,大量使用了刻畫人物心理細微波瀾的筆墨,纖毫畢露地呈現出冉慕二人內心的微妙狀態和幽暗變化。具體如冉咚咚在愛情面前的懷疑、糾結、軟弱、焦慮不安和慕達夫在婚姻面前的含糊、猶疑、妥協、無能為力,切實寫出了當下時代人們內心的情感危機。此外,隨著案情的逐步展開,不同人物相繼出場,仿佛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人物牽扯出另一個人物,像與案件相關的夏冰清、徐山川、沈小迎、吳文超、徐海濤、劉青、易春陽等人,以及摻雜進冉慕婚姻的貝貞、洪安格、邵天偉等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經過了作家心靈的拷問,赤裸裸地揭示了關于物欲、倫理、道德、精神等方面的“病態”癥狀,直抵人性最真實的幽深處。由此,案件推理與情感推理在敘事內核上也緊密勾連起來,形成小說內容層面的互文。
在小說的敘事結構、內容之外,《回響》的互文性還體現在對其他經典文本的引用、吸收、移植上。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的法國批評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認為,“任何文本的構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文本是一種文本置換,是一種互文性:在一個文本的空間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種陳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7]這種文本之間彼此吸收轉換的互文性,體現在《回響》的字里行間,古今中外許多經典文藝作品被作家別出心裁地嵌入了篇章之中,在輔助敘事的同時,也生發了文本的多層意義指涉。這里隨手擷取幾處略作例證,比如《回響》與《紅樓夢》的互文,在冉咚咚詢問慕達夫怎樣愛自己的時候,慕達夫回答稱:“就像《紅樓夢》里的賈寶玉愛林黛玉,你喝藥我先嘗苦不苦,若有好玩好吃的第一個想到的是你,你要是生氣,我就求爺爺告奶奶地哄你。”[8]聯系文中慕達夫與冉咚咚相處的日常,前者確如賈寶玉對待林黛玉一樣小心翼翼地呵護、照顧著后者的情緒和生活。又如《回響》與魯迅小說的互文,在慕達夫回答之所以能夠將冉咚咚出差的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條時,“他說就像寫文章,設身處地,把我當成你,就像魯迅寫阿Q的時候把自己當成阿Q,寫祥林嫂的時候把自己當成祥林嫂。”[9]這種不起眼的話語細節悄無聲息地凸顯出慕達夫的細膩與用心,也流露出他對冉咚咚的關懷和在意。再如《回響》與卡夫卡作品的互文,在冉咚咚出差之后,慕達夫一個人躺在床上,“他想象自己是卡夫卡《變形記》里的那只甲蟲,因翻不過身來而不得不這么躺著。他就想躺著,覺得做一只甲蟲沒什么不好。”[10]這里引入《變形記》的“甲蟲”,憑空為慕達夫的處境渲染上幾分虛無、孤獨、落寞的氣氛。這些之外,類似文本間的互文還有很多,像與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卡波特《冷血》、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司湯達《紅與黑》、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契訶夫《小公務員之死》等,以及與電影《泰坦尼克號》《煤氣燈下》《阿甘正傳》《楚門的世界》等,都形成了一組組的互文性關系,籍此使得《回響》的文本生成了獨特藝術張力和多層話語空間。正如有學者所講的那樣:“這些文本的嵌入,使得《回響》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穩定的結構,相反,這些文本就像多種聲音的交響一樣,演繹成一個多聲部的、對話性的復合結構,從而展現出交響樂般的不確定性和多元性。”[11]應該指出的是,《回響》中這些信手拈來的文學典故,幾乎都出自身為大學教授的慕達夫之口,顯然,這是作家出于對慕達夫身份確認的有意安排。
東西在回顧《回響》的創作時說:“這么一路寫下來,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對應關系:現實與回聲、案件與情感、行為與心靈、幻覺與真相、罪與罰、疚與愛等等。李叔同說‘念念不忘必有回響。’由此引申,小說的奇數章便是主人公的‘念念不忘’,偶數章就是她的‘必有回響’。心靈是現實的回音,善惡愛憎都有呼應。”[12]東西提到的“對應關系”和所謂的“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正是對互文敘事策略的透徹表達。經由互文,《回響》才在結構層面與內容層面實現了案情推理與情感推理的相互勾連;也經由互文,《回響》才成為具有豐富意義指涉的開放性文本。
二
隱喻實質上是一種由此及彼的引申方式,指兩種現實現象所能表達的意義在一定基礎上有著相似相通的地方,因而可以從一個現實現象引申出其他相似的現實現象加以闡釋。它既是一種表達手段,也是一種認知事物的思維方式。隱喻用之文學創作,“不僅是寫作者在特殊語境中遭遇言意困境時的一種書寫策略,也是他們進行終極意義探尋的一條必由之路。”[13]東西就是一個極擅隱喻的作家,他的不少小說文本在意義增生與消解、價值生成與解構等方面都使用到了隱喻這一敘事策略。小說《回響》也存在大量的隱喻,伴隨著敘事的推進或隱或現地呈現在文本之中,增強了文字的表達效果,延展了作品的意蘊空間。
小說從一樁名為“大坑案”的兇殺案展開,“大坑”案名即是隱喻。因為被害人尸體被發現的地方是“西江大坑段”,所以這一支撐整個敘事框架、貫穿整個故事始末的兇殺案便被正式命名為“大坑案”,自此一語成讖,“大坑”的陰影籠罩了全文。在冉咚咚將案件命名為“大坑案”的時候,文本中的表述頗有意味:“助理邵天偉舉手反對,說坑太大會填不平。她說填不平就跳進去,我們不能為了好聽而改地名吧,假如取個‘一帆風順’你不覺得別扭嗎?說完,她的腦海迅速浮現一個巨大的坑口,深不見底。”[14]這里的“坑太大會填不平”“填不平就跳進去”“巨大的坑口,深不見底”便是一組組隱喻,小說的后續讓人明白,案件、婚姻與潛藏于兩者之后的人性,對于冉咚咚來說,就是一口深不見底的大坑,她宛如掉入深坑的困獸一般,不得不面對“坑里”的殘酷與絕望。因此在這個層面上,“大坑”至少有著三重隱喻,分別映射著夏冰清被害的兇殺案、冉咚咚與慕達夫的婚姻、幽暗難言的人性深處,下面稍稍展開。
冉咚咚偵破“大坑案”的過程并不順利,從徐山川、沈小迎、徐海濤到吳文超、劉青、易春陽,再到夏冰清父母、卜之蘭等人,幾乎每一個與兇殺案相關的人在接受審訊調查時,都出于各種原因而隱瞞了真相,他們編造謊言、虛構口供,每次所謂的交代皆有所保留,前后接連的口供都不一致,使得案件始終處于團團迷霧之中,幾度陷入中斷。案件真相掩埋在嫌疑人的層層謊言之下,被包裹得密不透風,為了得到真相,冉咚咚不得不“撕裂”每一個人表面的掩飾,直面所有人心底的秘密。案件的偵破屢屢遇挫,印證了“大坑”案名的第一層隱喻。在調查夏冰清身份時,冉咚咚發現了丈夫的開房記錄,由此牽扯出了兩人的婚姻愛情,相較于兇殺案在迷霧重重之后柳暗花明、峰回路轉,冉咚咚和慕達夫長達十一年的婚姻卻徹底走到了盡頭。在冉咚咚決心以偵查案件的方式偵查自己的婚姻時,慕達夫便陷入了一種無論如何也說不清道不明的情境里。就開房事件而言,慕達夫先后用和朋友打牌、請按摩女服務的理由向冉咚咚辯解,但冉咚咚以朋友可以作偽證、按摩女出勤記錄上顯示無服務為由,反而加深了對慕達夫的懷疑。之后,貝貞小說《一夜》中所描述的曖昧故事、卜之蘭情戀穆姓老師等,均在冉咚咚的聯想下,與慕達夫建立了聯系,慕達夫因為無法取信于冉咚咚而始終百口莫辯。懷疑的種子一旦生根,原本熱烈的恩愛便開始支離破碎,冉慕二人的婚姻因為懷疑而掉入了永遠也說不清楚的“大坑”里,這印證了“大坑”案名的第二層隱喻。無論是案件偵破過程中所牽扯出的受害者與加害者,還是冉慕二人婚姻危機中出現的各類人物,都經過了作者翔實縝密的心理分析,讓讀者直面了人心深處的錯綜復雜。以夏冰清為例,在與徐山川的交往中,她從一開始的被強迫、不情愿,到之后的心甘情愿、渴望與徐結婚,再到后來一切破滅后開始反抗、想要討回公道,夏冰清悲劇的人生既令人哀其不幸——從始至終被徐山川欺騙、玩弄于股掌之中,又令人憤其不爭——沉淪于徐山川的金錢物欲攻勢之下。串聯起夏冰清的點滴人生,她既單純、驕傲、輕信,又隨波逐流、貪戀物欲,性格十分矛盾,但與之相比,表面上云淡風輕而暗地里工于心計的沈小迎、始終不愿面對自己內心真實情感的冉咚咚,其實性格更為復雜。作家借助書中人物的行為抉擇,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心理,揭示出了人性不可直視的幽暗地帶,由此印證了“大坑”的第三層隱喻,即人心之大坑。
在解讀完“大坑案”命名隱喻之后,回到案件本身的偵破方式上來。冉咚咚何以從枝蔓叢生的紛亂線索中順藤摸瓜地揪出真兇?依靠的就是自身強烈的共情或同理心。小說開頭交代說局領導之所以指定冉咚咚作為“大坑案”的負責人,是因為“局領導相信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尋找兇手更有把握,而且女性之間容易產生共情或同理心”[15],這里的“共情或同理心”即隱喻了冉咚咚接下來的破案方式。每當刑事偵查進行到一定階段,冉咚咚總是憑借自己女性的共情能力,與一個個同案件相關的人物建立起同理心,揣摩不同人物在各自身份、立場與情感關系中,會如何去做出應對,從而一次次“屢試不爽”地獲得了關鍵性的破案信息,也因此牽引出人心深處最幽暗的、最隱秘的角落。比如冉咚咚最開始接觸到兇殺案時,就迅速與死者夏冰清建立了“共情”,所以才在緝兇過程中堅持己見,一步步逼近真相,并且執意要將罪魁禍首徐山川繩之以法;同時,也正是與沈小迎、黃秋瑩、卜之蘭等建立“共情”,所以冉咚咚才能攻破徐山川、吳文超、劉青等人的心防,了解案件真相,獲得有力證據。不獨是偵破方式,這種共情和同理心也隱喻了冉咚咚為人處事、對待外界的方式。就情偵來看,依靠共情和同理心在刑偵中無往不勝的冉咚咚,卻在婚姻愛情中遭遇了“滑鐵盧”。她因為與夏冰清等人建立起的共情,將徐山川的所作所為“同理”到丈夫身上,認定丈夫出軌,從而導致與慕達夫的婚姻一步步趨于崩碎。這之外,共情或同理心也讓冉咚咚陷入了一種矛盾糾結的“疚愛”情緒之中。小說結尾處寫道:“她沒想到由內疚產生的‘疚愛’會這么強大,就像吳文超的父母因內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蘭因內疚而重新聯系劉青,劉青因內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陽因內疚而想要給夏冰清的父母磕頭”[16],這一連串的因果關系都是因為“疚愛”情緒,而冉咚咚的共情能力又使之對慕達夫產生了“疚愛”,因此故事的最后雖未明示,但顯然她已經不可能順從本心、與自己心生愛慕的下屬邵天偉開啟新生活了,只會啟動心理防御機制,陷入“疚愛”的情緒中無法自拔。
此外,小說里一些細節上的隱喻也隨處可見。比如在冉咚咚搜查吳文超辦公室時,發現了隱藏于電腦三層目錄下的黃秋瑩懷抱吳文超的照片,“懷里的吳文超還是嬰兒,嘴里嘬著小指頭仰視母親,母親微笑俯視他的臉龐,溫馨溢屏,就像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畫家達·芬奇的那幅《圣母與圣嬰》。”[17]這里將母子相親的照片隱藏起來,并與達·芬奇畫作進行聯系的情節,實際上隱喻了吳文超對于母親表面怨恨、內心依戀的復雜情感,與后文在母親黃秋瑩的勸說下選擇自首形成呼應。再比如在冉咚咚與慕達夫情變的過程中,冉咚咚飯店里向邵天偉索吻,慕達夫請求邵天偉幫忙開導冉咚咚,以及離婚后慕達夫第一時間告知邵天偉結果等情節,初讀起來似乎有些突兀,好像沒有任何先兆,本來存在感不強的邵天偉突然“插足”了冉慕婚姻。直到后來冉咚咚直面內心對邵天偉的情感時,才讓人恍然大悟,原來早先的情節是為后文冉、邵二人互相欣賞所做的鋪墊,所以邵天偉的“亂入”其實就成了冉慕兩人婚姻早已千瘡百孔的前置隱喻。這之外,較為明顯的隱喻還存在于慕達夫分享給冉咚咚的《故鄉》一詩里。冉咚咚在埃里村等待真相的時候,慕達夫分享了一首名為《故鄉》的詩給她,詩中寫道:“故鄉,像一個巨大的鳥巢靜靜地站立/許多小鳥在春天從鳥巢里飛出去/到冬季又傷痕累累地飛回來”“有的一只手臂回來,另外一只沒有回來/有的五個手指回來,另外五個沒有回來”[18]。這是一首描寫春去冬返、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詩歌,隨著真相浮出水面,易春陽暴露在讀者視野里,這首詩也具備了隱喻的功能——前半段隱喻殺人兇手是一個失意的農民工,后半段隱喻兇手殘忍切斷了夏冰清的手臂。類似細節上的隱喻還有很多,多數情況下為后續故事的發展變化指明了方向,這里不再一一展開。這些由此及彼、相互輻射的隱喻情節,一方面讀起來饒有興味,另一方面也昭示出作家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敘事技巧。
作為小說《回響》的重要敘事策略,很多時候,隱喻并沒有明確表明本體和喻體之間的關系,像“大坑案”的命名、共情的破案方式等,都需要讀者在閱讀前后文之后去慢慢體味和感知,由此讀者便自覺參與到了文本意義的建構之中。這種作者、文本與讀者的互動,形成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自然導致了作品多重話語維度與多層意義空間的衍生與發展,也就生發出作家關于不確定性的意義建構。
三
與互文、隱喻一樣,反諷也是一個意義指涉相當廣闊的概念,既指一種語言修辭技巧,也指隱含在敘事中的與正面描述意義相悖的暗示或對照,體現為表面含義與內在含義的沖突。東西小說中的反諷,其實更接近于一種藝術效果,讀罷他的作品,現實的荒誕感、人生的虛無感、命運的悲劇感會在悄無聲息間慢慢滋生,令人百感交集、欲言又止。有學者直白地指出:“東西小說給人的另一個最大的感受是反諷,通過對現實結果與目的的悖反;語言表層含義與深層含義的對立;主題與內容不協調達到以形式對抗現實的目的。”[19]《回響》同樣使用了反諷的敘事策略,無論是刑偵主線中一眾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口供、作案手法,還是婚姻主線中冉咚咚、沈小迎、卜之蘭等女性幽暗難明的情感心理,抑或是文本中不同階層人物身份、道德的錯位,都具有反諷的性質,給讀者閱讀黑色幽默小說一樣荒誕不經的體驗。
首先來看《回響》刑偵主線中在講述嫌疑人犯罪動機、口供和作案手法上使用的反諷敘事策略。回顧整個案情,謀殺夏冰清的罪魁禍首是與之長期保持情人關系的徐山川,直接兇手是易春陽,但徐山川與易春陽之間并無直接聯系,而是通過徐海濤、吳文超、劉青三人,層層轉嫁、委托,最終達成了謀殺的閉環。從犯罪動機來看,作為罪魁禍首的徐山川為了逃離夏冰清的糾纏而暗示徐海濤“解決”夏冰清,但夏冰清對他的糾纏其實是徐山川一手促成的,他一開始強迫、傷害了夏冰清,又用金錢腐化、籠絡了夏冰清,而當夏冰清情系于自己之后,徐山川又想要擺脫與夏冰清的親密關系。對比徐山川前后的所作所為,作者諷刺的筆鋒直指憑借金錢、權勢、地位而胡作非為的資本階層。相較徐山川,作為直接兇手的易春陽,犯罪動機“單純”得出人意料。作家安排與夏冰清素不相識的農民工易春陽來充當最終兇手,他殺人看似是屈從于金錢之下,實則是出于對劉青欣賞自己詩歌的感激,甚至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想要夏冰清的手臂,如此一來便徹底消解了夏冰清之死的意義,使得整樁兇殺案變得荒誕和戲謔。從警察審訊時獲取的口供來看,面對公權力機關,嫌疑人并無敬畏之心,他們用謊言掩飾真相、用借口為己開脫,不斷推翻前一次的供詞,并且每一次的證言都有所矯飾,每一次的回答都不夠完整,但偏偏每一次被審訊都能自圓其說、有理有據,以至于屢屢騙過文本中的警察、文本外的讀者,使得整個案件撲朔迷離。僅從口供內容來看,除了徐山川之外,主動或被動參與作案的其他人似乎都“情非得已”且“情有可原”,但在被殘忍殺害的夏冰清尸體面前,所有的推諉借口、脫罪理由都顯得蒼白無力,如此讀者再面對他們口是心非的辯詞,便陡然只剩下希冀他們早日伏法的心思了。再從兇手的作案手法來看,夏冰清被易春陽殘忍殺害,并被冷血地切下了手臂,究其原因,是因為易春陽沉迷于“被愛妄想癥”的精神疾病之中,他由暗戀之人缺失手臂而聯想到維納斯雕像的斷臂,幻想著送給暗戀對象一只完美的手臂,而夏冰清的手臂恰好符合了他的心理期待。由作案手法聯想到犯罪動機,或許導致夏冰清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一個精神病人對完美手臂的癡迷?如此一來,小說反諷的意味便不可謂不濃厚!
有必要梳理一下犯罪嫌疑人之間存在著的金錢關系:徐山川為了逃避夏冰清的糾纏,特意“借給”徐海濤二百萬元“買房”;徐海濤找吳文超策劃夏冰清遠離徐山川的方案,愿意支付五十萬元(實際支付的金額是二十五萬);吳文超又將這件事情委托給了劉青,先后兩次共付款十萬元;而劉青以一萬元的代價將解決夏冰清的事情委派給了易春陽,于是便有了兇殺案的發生。因而事實上,夏冰清青春靚麗的生命,在逐層剝離、“分包”之后,竟然“貶值”到區區一萬元,令人感到十足的戲謔與諷刺!這之外,這個殘忍詭譎的兇殺案,在一眾施害者眼中,竟然只是一單被層層分包的生意,文中寫道:“冉咚咚想他們都把做這件事當成做生意,徐海濤是這么說的,吳文超也是這么說的,每個人都說得輕描淡寫,好像夏冰清的命是一件商品。”[20]活生生的人的生命被金錢量化,成為一件供人挑選的商品,這段冷酷到極點的話語所折射出來的人性冷漠程度與沉淪程度可見一斑,由此小說反諷的意味更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其次再來看情偵主線上在剖析冉咚咚、沈小迎、卜之蘭等人真實情感心理時使用的反諷敘事策略。在選擇以刑偵方式偵測感情之后,敏感多疑的冉咚咚不斷地尋求證據來證明丈夫出軌,她先是懷疑慕達夫兩次與情人開房幽會,接著篤定慕達夫與女作家貝貞有染,最后又試圖證明慕達夫與卜之蘭發生過戀情。但實際上,慕達夫自始至終都深愛著冉咚咚,從頭至尾都不曾有過不忠于婚姻的行為,反而是冉咚咚自己早早就精神“出軌”了邵天偉,只是囿于道德良知的約束,刻意掩飾住了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所以想著轉嫁責任,將變心的過錯安置在慕達夫身上。從結果回推過程,冉咚咚在一力推動與慕達夫離婚的過程中,愈是義正辭嚴地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表現出一副情感潔癖的模樣,也就愈顯得她色厲內荏、方寸大亂,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因為小說主要沿著冉咚咚的視角展開敘述,所以讀者下意識地會將冉咚咚當作了可靠的敘述者,于是很容易同冉咚咚一起對慕達夫生出了懷疑之心,但到了小說結尾卻發現原來可靠的敘述并不可靠,反而歪曲了真相、顛覆了認知,這就陡生出一股反諷的意味,既有對掩飾自己變心真相的冉咚咚的反諷,也有對輕信于作者敘事話語的讀者自己的反諷,還有對當代人婚姻愛情忠貞性、唯一性、神圣性的反諷。
相比于壓抑真實情感的冉咚咚,沈小迎身上的反諷意味更重。沈小迎一開始是以婚姻受害者身份出現的,作為徐山川的妻子,她為了孩子成長、家庭完整,不得不忍受徐山川在外面花天酒地、沾花惹草,并且還要經常幫助丈夫處理“桃色”后事,應對找上門來的諸如夏冰清一類的丈夫情人,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賢內助”。但這樣一個外表“佛系”、對丈夫無可奈何的可憐女子,背地里卻一直在報復徐山川,她不僅與健身教練保持親密關系,還生下了別人的女兒,并且一直監聽丈夫、錄下丈夫的犯罪證據。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家庭關系中,沈小迎看似柔弱順從逆來順受,處于絕對弱勢地位,但實則內在一直在反抗,并在關鍵時刻迸發出了摧毀一切的能量,這一人物形象前后、表里的巨大反差和割裂使得文本生發出極大的藝術張力。如此再來回想徐山川為了維護家庭關系而決定除掉夏冰清的犯罪動機,似乎顯得更加的可笑又可悲!
如果說從冉咚咚、沈小迎身上讓讀者看到了當代人的婚姻危機,消解了婚姻關系的忠貞與神圣,那么從卜之蘭身上則讓人體會到了婚姻的前置關系——戀愛的不可靠。在劉青眼里,卜之蘭是一個完美的戀人,美麗、浪漫、深愛著自己,即便是中間不告而別,也在命運的安排下重新回到自己身邊,挽救自己于平庸生活之中。但事實并非如此,劉青只是卜之蘭報復心愛之人的替代品,她最開始醉心于穆姓教授,與劉青的高調戀愛是愛而不得之下刺激穆姓教授的舉動;中途離開劉青的三年時間也是因為穆姓教授的召喚,選擇以助理身份追隨左右;而重新回到劉青身邊則是出于對穆姓教授給不出婚姻承諾的失望,以及傷害劉青后滋生的“疚愛”情緒。文中寫道:“她說劉青傷沒傷害夏冰清我不確定,但我傷害劉青是事實,所以我會用一輩子的愛來彌補他”[21],這里“用一輩子的愛來彌補他”即是“疚愛”,但“疚愛”是愛情嗎?畢竟“疚”在“愛”之前。美麗的謊言一經拆穿,丑陋的真相便立刻浮出地表,讓人難以直視。東西《回響》中的女性人物似乎都存在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和“往事”,作家依靠對人心、人性最隱秘角落的逐層剝露,實現了對當代人婚姻愛情關系和情感心理世界的解構與反諷。
最后再來看《回響》在描寫不同階層人物身份、道德錯位時所使用的反諷敘事策略。如果從財富程度來劃分人物階層的話,小說中的徐山川、易春陽正好對應了貧與富兩個不同的階層,這里以兩人為例,簡要分析一下身份與道德的錯位關系。徐山川作為一個財力雄厚、家境殷實的資本家,本來家庭幸福、生活美滿,但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欲,多次出軌女下屬,甚至為了擺脫麻煩鋌而走險。在得知自己陰謀敗露的時候,徐山川第一反應不是認錯、不是懺悔,反而是滿腔怨憤:“他恨得咬牙切齒,說早知道沈小迎監聽我,出賣我,那我做掉的就是她而不是夏冰清。我想過跟她離婚,娶夏冰清為妻,但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沒有離,我當初怎么會愛上這么一個狠人?”[22]可見徐山川對于殺害自己情人一事從未后悔過,人性的酷烈惡毒竟然如斯!無怪乎小說里冉咚咚從一開始就對徐山川抱有強烈的懷疑與敵意,并且全程矢志不渝地要他認罪伏法,這除卻是出于同情夏冰清遭遇和刑警多年直覺的原因,未嘗沒有作家著意安排的成分在,由此折射出作者對資本社會和金錢物欲的批判。處于社會底層的易春陽是書中十分悲劇的一個人物,他掙扎在貧困線上,患有精神疾病,為了一萬塊錢就敢于殺人,似乎是一個窮兇極惡的罪犯。但實際上呢?易春陽熱衷于詩歌創作,親近美好的事物,重視、珍視愛情,還是一個努力贍養父母的孝子,甚至最后還想要向夏冰清父母下跪來表達自己的懺悔。對比徐山川與易春陽,一個身居高位但品性卑劣,一個雖是底層卻心思單純,這種貧與富、德與位的參差令人瞠目之余,頗值得反思,籍此小說也引申出了貧富分化、城鄉有別的社會命題。
在反諷的敘事策略之下,謊言與真相、起因與結果、表面與內在、想象與現實、意識與潛意識,乃至于富與貧、城與鄉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關系,被作家置于悖反的情境之中,使得彼此之間的界限極為模糊,從而生成一片具有含混意義的話語空間。在《回響》所營造的含混意義空間中,我們一度篤定無疑的事物都被無情地解構、祛魅,比如真相,比如婚姻,比如現實,比如人心,而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我們唯一能夠證實的,只能是萬事萬物的不確定性。
結語
不確定性是現代科學與哲學的本質屬性之一,從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到沃納·海森堡發現的量子世界不確定原理,再到香農的信息論,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混沌理論和復雜性理論,都表明我們生存的世界是一個復雜、混沌、動態、相互聯系的系統,不確定性才是世界的常態。[23]在我們還在本能追尋“確定性”的時候,東西已經借助自己的小說創作為我們展示了一個“不確定性”世界。在《回響》中,東西憑借互文、隱喻、反諷的敘事策略,使得文本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一走向多維,從而衍生出了豐富的指涉意義,造成文本的多義性、文體的豐富性,向讀者傳達出包括現實與情感在內的萬事萬物不確定性的哲思。在這個意義上,《回響》不愧是當代的優秀之作,既有對現實世界里人心、人性的深刻詰問,也有對抽象世界里不確定性哲學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