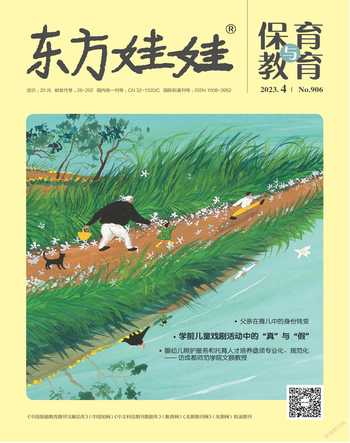班級環境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策略初探
張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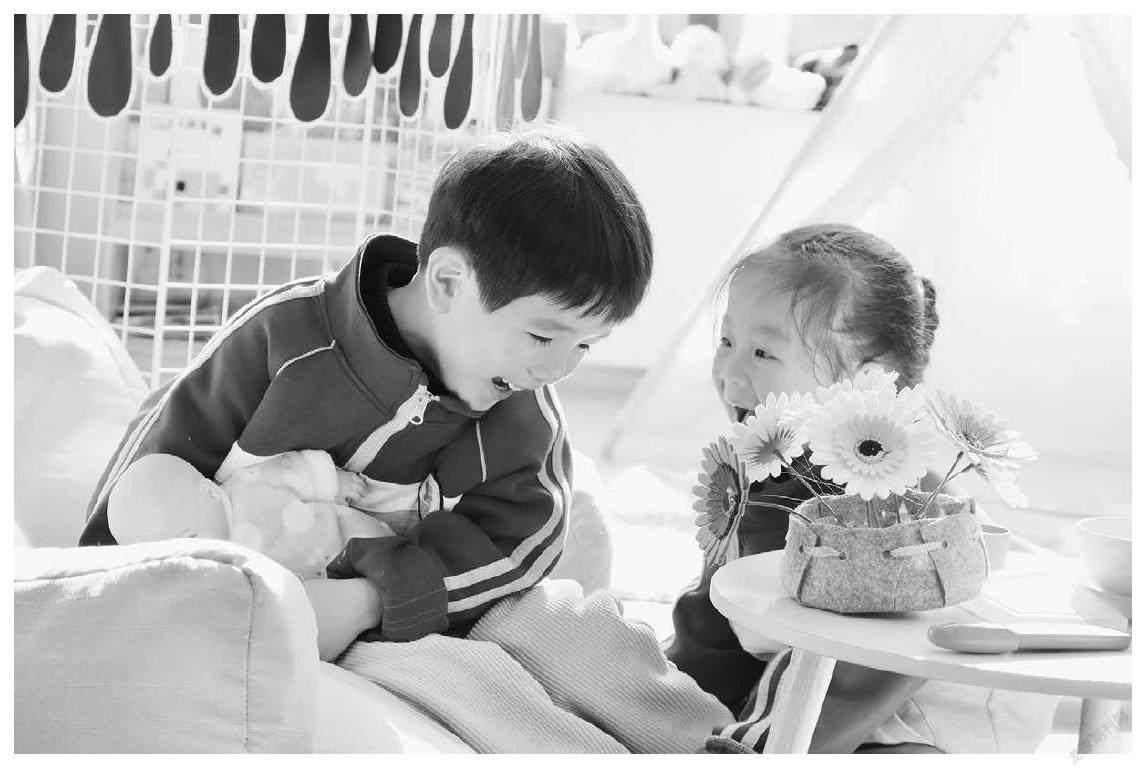

環境是重要的教育資源,幼兒通過與學習環境的積極互動來實現自身發展。那么,幼兒園目前的學習環境能否提供給幼兒深度學習的機會,能否激發幼兒深度學習的動機,能否為幼兒的深度學習搭建支架呢?我們從調查入手,了解班級環境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尋求解決路徑。
一、研判:班級環境創設現狀
1.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環境基礎略顯單薄
筆者隨機對蘇州高新區某公辦園8個班級的16名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了解班級環境創設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教師認為自己班級區域中的游戲材料都非常豐富,班級的環境一般以學年為單位進行規劃布局。83%的教師直言班級環境是根據自己的想法而設計的;68%的教師認為幼兒活動的實際發起者是教師,班級環境大多結合幼兒的年齡特點與活動需要進行創設。各區域的材料從種類和性質上來看,具備了開放性和多樣性的特點,為幼兒的深度學習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然而,幼兒深度學習的環境應是由物質材料、空間、時間、人際氛圍、師幼及同伴關系等要素共同構建,是一種多元的、交互的、立體的、開放的環境,僅材料的支持無法完全滿足幼兒深度學習的需要。
2.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發生場域需要拓展
隨后,筆者對這16名教師進行了訪談,并對小、中、大班幼兒游戲做了觀察,發現教師支持幼兒進行深度學習的行動并不顯著,幼兒高階思維的發展需持續助推。從教師的訪談結果來看,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行為基本發生在區域活動中,而在所有區域中,建構區和美工區是重點區域,顯然他們認為在這兩類活動中,更容易引導幼兒進行深度學習,支持策略也更容易掌握。從對幼兒的游戲觀察來看,教師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策略有言語提醒、創設情境、引導觀察探究、鼓勵多次嘗試等。這使幼兒在活動中表現出應用高階思維的傾向:遷移經驗解決新的問題、積極主動地探究生活中的現象等。但這種表現一般發生在特定的活動中,教師的有意識引導并非常態。
由此可見,教師對環境支持幼兒深度學習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常態化、多情境促進幼兒深度學習的意識和能力有待提高。
二、探究:環境支持幼兒深度學習有哪些“攔路石”
1.教師——從意識到能力的缺乏
(1)對班級環境的認識略顯狹隘
通過對幼兒園16名教師的調查發現,在大多數教師看來,環境指向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活動材料。他們試圖通過提供更為多樣的活動材料來促進幼兒的發展,如某班級美工區的材料多達48種。第二方面是班級布局。他們會根據一些原則來規劃班級區域,以便為幼兒提供適宜的環境,如美工區靠近水源、閱讀區遠離建構區并保證光照等。第三方面是區域環境。他們會在區域中創設適宜的墻面環境和過程性環境,以此來提高幼兒與環境互動的頻次及質量,從而促進幼兒的發展。可見,教師對促進幼兒學習的環境創設局限于靜態物理環境,而對同樣可促進幼兒發展的其他環境,如可變的空間、彈性的時間、師幼的互動等有所忽略。
(2)嫁接幼兒深度學習和環境創設的能力仍需提高
在幼教課程改革的不斷推進中,教師對如何立足兒童本位、創設有助于幼兒深度學習的環境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在實踐中,教師創設環境的主要方向依然放在主題環境和區域環境中。雖然有些教師能夠關注交互性環境的創設,但仍會存在師幼互動“人到心不到”、把握不住幼兒深度學習的契機、忽視生活環節中深度學習的發生等現象。對于如何提供適宜的材料促進幼兒的深度學習、如何把握幼兒深度學習時教師“介入”的度、如何辨別幼兒深度學習支持策略的有效性等問題更是充滿困惑。
2.園所——從設施到管理的雙重被動
該園幾乎所有班級的格局在學期初規劃后,一學期甚至一學年都不會變化,如統一規格的實木柜和6人一組的長條桌,它們比較笨重,不易移動,在大多數班級是雷打不動的“標配”,教師甚至從未想過對它們有所改造。事實上,6 人一組的長條桌便于有序組織餐點,但其實用性不如尺寸小、易組合的桌子,無法很好地滿足幼兒的游戲需要。
從園所管理的角度來看,受限于諸多方面的要求和區域規劃的一般規律(如美工區靠近水源、閱讀區靠近窗戶),管理者往往希望各班教師在多重因素的考量下盡量統一布置,所以留給教師在班級規劃上發揮的余地尚且不大,更不論加入幼兒的班級規劃意愿了。
三、調整:創設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班級環境
1.開放空間和材料,為幼兒的深度學習奠定基礎
支持幼兒的深度學習,就要鼓勵幼兒與外界環境充分交互。開放的空間一方面能促使幼兒做環境的主人,發揮自主性,打造自己的游戲空間;另一方面也支持幼兒在環境中自由走動,自主決定游戲內容、自我選擇游戲材料。
我們嘗試提供不同規格的游戲柜、為游戲柜安裝滾輪、將長條桌換成小方桌,將空間控制權還給幼兒,鼓勵他們充分討論,根據需要布置班級區域,決定游戲柜、游戲桌、工具、材料等的擺放。我們還引導幼兒在實踐→反思→再實踐的循環探索中不斷優化班級空間布局,實現幼兒對班級空間的把握,提高他們的班級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深度學習的發生奠定情感基礎。教師給予幼兒充分的信任和鼓勵,引導幼兒在審視中發現問題,并在幼兒遇到“疑難雜癥”或“沖突膠著”時進行破冰引導。
如:幼兒自選材料進行“卡片建構”,遇到了卡片因桌子不穩而總是坍塌的難題。在幼兒無法解決而將要放棄時,教師提示他們選擇合適的場地進行搭建。幼兒選擇了在空地上搭建,但同伴的來回走動容易把“卡片建筑”碰倒,教師便鼓勵幼兒分析問題所在——因為沒有設置區域界限,同伴路過時會誤闖進這一場所碰到卡片。隨后幼兒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用長條積木建起了區域界限,提醒同伴不能走進,成功地為游戲設置了“安全空間”。在這一案例中,幼兒實現了對游戲空間的自主,通過教師的鼓勵和引導,在觀察、分析和思考中表現出了自主性、創造性,以及在反思中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無疑是幼兒深度學習的表現。
2.靈活的時間安排,為幼兒的深度學習創造條件
在課程游戲化理念下,作息時間彈性化已成為對教師實施一日活動的基本要求。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作息時間卻是模式化的,主動權也在教師手中。顯然,教師對“彈性作息”的理解不夠深入,落實“彈性作息”的能力也有待提高。而對于認知發展水平處于前運算階段的幼兒,他們的深度學習是主動探索、發現問題、產生認知沖突進而采用策略解決問題的過程,也就是說,“幼兒深度學習”需要時間的保障。如果幼兒只有半個小時的游戲時間,他還未進入游戲情境,就被迫結束,這種情況下很難發生深度學習。這就要求教師自己先沉下心,花時間、精力去陪伴幼兒、觀察幼兒,發現他們偶然的好奇心,支持他們的探究,并鼓勵他們通過協商、合作、調查等途徑,找到問題的解決思路和方法,從而促進其深度學習的發生。
在實踐中,我們一方面需要通過培訓和學習,轉變教師“重視教、輕視學”的教育理念,增強教師觀察與支持幼兒的意識,在提升教師對幼兒行為的觀察、分析等能力的基礎上,把握好幼兒自主與教師控制之間的度;另一方面,需要嘗試通過環境(材料、游戲空間等)的支持將時間還給幼兒,讓幼兒在與環境的充分互動中產生更多的可能,獲得高階思維的發展。在這里,教師往往會有一個極大的困惑:如何把握支持幼兒個體活動和集體活動的度。比如:區域活動中當大部分幼兒已經完成探索,小部分幼兒仍興致勃勃時,該如何取舍,是“收”還是“不收”?如果“收”,是不是就打斷了小部分幼兒的活動?如果“不收”,那無疑是在浪費大部分幼兒的時間。那么,我們何不支持小部分幼兒繼續他們的探究,同時帶領大部分幼兒轉入其他活動呢?
再如木工活動中,幼兒自找伙伴、自選材料進行創作,當大部分幼兒完成自己的創作時,制作椅子的小組才完成了一半,此時教師陷入了兩難:是讓這一小組暫停,留待下次活動再繼續,還是不打斷,讓他們繼續完成作品?教師在觀察了幼兒的操作狀態,又征詢幼兒的意愿后,選擇由一位教師帶其他幼兒回班級,另一位教師留下陪伴他們繼續制作。在這一事例中,當教師發現大部分幼兒的游戲已接近尾聲,但個別小組仍在操作探究時,常規做法往往是引導幼兒保留半成品,放在“未完成”區,留待下次活動時繼續制作。但當時教師觀察到幼兒的操作熱情正濃,同伴間對制作時發現的問題討論正酣,意識到如果按以往的方法處理,大概率會打斷他們的思維,阻斷他們與材料進一步互動的可能。于是,在充分尊重幼兒自主的情況下,選擇讓這一小組的活動時間延續下去,這無疑為幼兒深度學習的產生創造了重要條件。
3.溫馨的師幼關系,為幼兒的深度學習搭建鷹架
作為幼兒園教育的基本表現形式,師幼互動存在于幼兒一日生活中。它表現在幼兒園教育的各個領域,對幼兒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要轉變自己的兒童觀、教師觀、教學觀,將開放的教育理念逐漸內化為無意識的師幼互動行為,營造溫馨的師幼互動氛圍,鼓勵、支持幼兒的深度學習。
目前,有些教師總是在班級中制定各種公約、區域規則等,要求幼兒服從,對幼兒的情感性需求越來越冷淡,而較多地關注幼兒認知、交往能力上的發展。由此造成了師幼關系較為疏離。要促成幼兒的深度學習,就需要改變這一現狀,創設開放的班級心理環境,讓幼兒在包容、溫暖、自由、自主的氛圍中感受到自己是被看見、被認同、被信賴的,而不是被束縛、被拒絕、被冷落。教師一方面應信任幼兒,給予他們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與時間,鼓勵他們通過對周圍的環境的積極探索去獲得各種經驗;另一方面應在確保“到場”的前提下,持續了解、傾聽幼兒,鼓勵幼兒的觀察、思考和探索,不斷提高師幼互動實效,提高幼兒深度學習的可能。
比如:在調整班級公約前,教師調查了解幼兒的想法,很多幼兒認為傳統的“點名”活動太無聊,不想再喊“到”了。教師對此進行了反思:一成不變的點名模式使思維固有化,難以調動幼兒的興趣;點名活動看似零散隨意,實則是幼兒在園生活的重要一部分。那么,如何將“點名”的主動權交到幼兒手中呢?教師以問題為支架,組織幼兒進行討論,鼓勵幼兒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過程如圖1所示。
在確定好新的點名方式后,經過3天的實踐,大家又發現了如下問題:如果把點名任務都交給小組長,小組長就沒時間玩了,一直在等小朋友;點名和天氣記錄表都在門口,離時鐘很遠,不方便看時間;雖然寫上時間了,但也看不出來誰遲到誰沒遲到;雖然自己打鉤很方便,但這樣只能知道小組里來了哪些人。
于是,教師組織幼兒進一步討論,并提供幼兒所需要的支持,如:在大門口放上時間顯示器,省得再進去看時鐘;在記錄紙中每組后面留空格,以便統計今天來了幾人;提供兩種顏色的水筆,一種顏色表示在規定時間內來了,另一種顏色表示遲到了,等等。
在這一事例中,教師尊重幼兒對班級中“約定俗成”做法的質疑,與幼兒建立了一種鼓勵和包容的師幼互動關系,幼兒的任何一種想法都能得到支持,都可以去大膽嘗試。在幼兒產生不同想法時,教師沒有設“一言堂”,而是鼓勵幼兒以小組為單位協商,選擇其中一種點名方式進行嘗試;在幼兒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實踐后,教師又為幼兒搭建平臺,讓幼兒通過分享、比較、評判等方式不斷審視自己的實踐過程,判斷并調整自主點名的方法,在反復嘗試中優化自主點名的內容和方式。這就告訴我們,在開放的師幼互動背景下,即使是生活中不起眼的一小點,也能誘發幼兒的深度學習,從而促進幼兒高階思維的發展。
綜上,教師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行動,需要創設開放性環境,充分發揮環境這一課程資源的教育價值;而經過優化的開放性環境,又能促進幼兒與環境的交互,從而進一步支持幼兒深度學習的發生。開放性環境與幼兒深度學習,在互促共進中不斷推動著幼兒高階思維的發展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