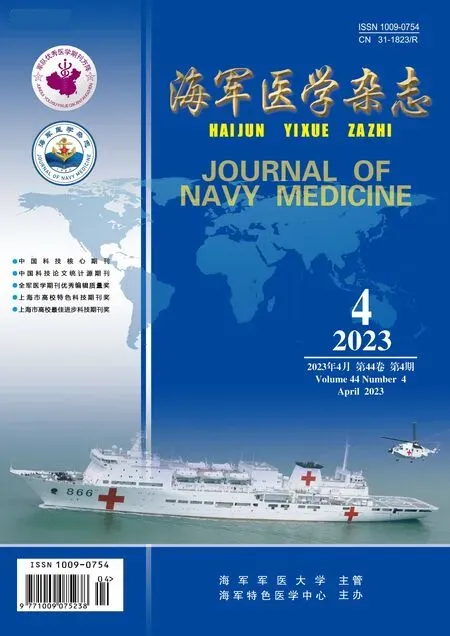自我效能感和軍人智能手機成癮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文靜,宋相瑞,邵小琴,董薇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手機是民眾上網的最主要設備,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已達99.7%[1]。智能手機集社交、生活資訊、娛樂等功能于一體,且體積小、便于攜帶。這些優點給大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問題,智能手機成癮(smartphone addiction)便是其中一種。智能手機成癮是指個體過度使用且無法控制過度使用智能手機的行為,并導致一系列心理和行為問題[2]。智能手機成癮不僅與頸椎病、視力下降等器質性病變有關,還會影響個體的睡眠質量、執行功能、心理健康水平等[3-6]。既往有研究者對某部340 名官兵進行調查,發現手機成癮檢出率為6.47%[7]。軍人由于職業的特殊性,需時刻保持機敏與警惕,智能手機成癮可能會擾亂正常作息,降低專注度,對軍人作戰能力造成不良影響。但現有研究多關注青少年群體智能手機成癮狀況的影響因素,較少關注軍人群體。因此,對軍人手機成癮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于自己能否完成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念[8]。自我效能感較高的軍人對自己有正確的認識,與自我效能感較低的軍人相比,會采取更加積極向上的方式達成目標[9]。特定網絡成癮理論認為,個體的核心特征和個性(自我效能感等)能夠預測具體的認知,并導致不同類型的網絡成癮[10]。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可以負向預測成癮行為[11],在學生群體智能手機成癮的研究中也發現學生的學業自我效能感越高,越不容易手機成癮[12]。因此,自我效能感更高的軍人可能更少通過智能手機成癮逃避現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自我效能感能夠預測軍人智能手機成癮。
根據個體-環境交互作用模型[13],個體行為受外部因素和個體自身因素共同影響。因此,智能手機成癮除自我效能感(個體因素)外,還受到家庭、社會等外部因素影響[2],個體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程度也可能與智能手機成癮行為有關。社會支持指個體的各種社會聯系對個體所提供的物質等客觀的、實際的支持和情感等主觀支持[14]。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較高者樂于幫助他人,積極與外界交流,能夠獲得較多的社會支持[15]。也有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手機成癮具有負向預測作用[16]。自我效能感較高的軍人可以從社會關系中獲得更充足的支持,不需要依靠手機建構的虛擬世界獲得精神滿足,即自我效能感可能通過社會支持影響軍人的智能手機成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軍人的社會支持在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間起中介作用。
焦慮是影響軍人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17]。個體行為不僅受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情緒的影響。即使有充分的社會支持作為支撐,但當個體感到焦慮時,依舊有可能通過手機成癮行為來試圖緩解[18]。相關研究表明,焦慮與自我效能感[19]、社會支持[20-21]呈負相關,與手機成癮呈正相關[22],但尚無研究綜合探討焦慮在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手機成癮中的作用。軍人作為特殊群體,探討焦慮情緒對其智能手機成癮的影響很有必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焦慮可調節軍人自我效能感與手機成癮間的關系。
本研究擬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探討社會支持、自我效能感和焦慮如何影響軍人手機成癮,研究假設模型見圖1。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軍人智能手機成癮的影響因素及內在機制,對維護和促進軍人群體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圖1 本研究的理論假設模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某部共5 304 名軍人作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1)納入標準:年齡18 歲以上;意識清晰;對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參與。(2)排除標準:未完成答卷者(100 名),如錯填、漏填選項等情況。最終共有5 204 名軍人納入研究,問卷回收有效率98.2%。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23]該量表由10 道題目組成,屬于單維量表。量表采用Likert 4 點評分形式,每個條目均為1(完全不正確)~4(完全正確)評分,10 道題目的平均分為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越強。該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樣本計算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93。
1.2.2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ore,SSRS)[24]該量表分為客觀社會支持(3 題)、主觀社會支持(4 題)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 題)3 個維度,共計10 道題目,10 道題目的總分為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個體的社會支持度越強。該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樣本計算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22。
1.2.3 智能手機成癮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SV)該量表為Kwon 等編制的智能手機成癮量表簡版[25-26],由10 個題目組成。量表采用Likert 6 點評分形式,每個條目均為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評分,10 個條目的總分為量表得分,男性得分高于31 分,女性得分高于33 分,表示存在智能手機成癮[27]。該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樣本計算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03。
1.2.4 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28]該量表分為抑郁(7 題)、焦慮(7 題)和壓力(7 題)3 個維度,共計21 道題目,可以同時測量被試者的抑郁、焦慮、壓力狀況。量表采用Likert 4 點評分形式,每個題目均為0(完全不符合)~3(非常符合)評分,分量表分值越高則表示越存在該情緒。本研究選取該量表中的焦慮分量表進行研究。該分量表信效度良好,依據本研究樣本計算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43。
1.3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或百分比(%)表示。采用Harman's 單因素檢驗方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來檢驗共同方法偏差;采用相關分析探索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智能手機成癮和焦慮間的關系;采用Hayes 編制的SPSS PROCESS 宏程序的簡單中介模型Model14 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的檢驗,檢驗標準α=0.05。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s 單因素檢驗方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29]來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以特征根大于1 為標準,共析出39 個因子,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18.52%,小于40%為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某部軍人手機成癮狀況
5 204 名軍人中共有515 名手機成癮者,占總人數的9.90%。分別以是否獨生子女、手機主要用途、日均上網時間對手機成癮量表總得分進行分類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某部軍人手機成癮的人口學統計
2.3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感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P<0.01),與智能手機成癮、焦慮呈負相關(P<0.01);社會支持與智能手機成癮、焦慮呈負相關(P<0.01),智能手機成癮與焦慮呈正相關(P<0.01)。見表2。

表2 某部軍人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智能手機成癮和焦慮的相關分析(r 值)
2.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選用Hayes 的模型14(本研究的理論假設模型與該模型一致,因此可直接進行檢驗)[30],在控制是否獨生子女、手機主要用途、日均上網時長的情況下對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檢驗,以自我效能感為自變量,智能手機成癮為因變量,社會支持為中介變量,焦慮為調節變量。見表3。自我效能感可負向預測智能手機成癮(β=-3.03,t=-16.10,P<0.001),支持了假設1。自我效能感可正向預測社會支持(β=1.76,t=21.83,P<0.001),社會支持可負向預測智能手機成癮(β=-0.35,t=-9.69,P<0.001),因此,社會支持在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設2。將焦慮納入模型后,可看到焦慮對智能手機成癮的影響不顯著(P>0.05),但社會支持與焦慮的交互項對智能手機成癮的影響顯著(β=0.05,t=3.65,P<0.001),說明焦慮的調節作用顯著。為更清楚地解釋焦慮在社會支持與智能手機成癮之間的調節作用,將焦慮水平按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進行分組,并做簡單斜率檢驗。結果表明,高焦慮者的社會支持對智能手機成癮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β=-0.194,t=-4.754,P<0.001)。見表4。隨著焦慮水平的降低,社會支持在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關系中的中介效應呈上升趨勢,支持了假設3。低焦慮者的社會支持對智能手機成癮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且與高焦慮者相比,其負向預測作用更加明顯(β=-0.35,t=-9.69,P<0.001)。綜合以上結果可知,自我效能感通過社會支持對智能手機成癮產生影響的中介作用受到焦慮的調節。

表3 自我效能感對智能手機成癮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表4 不同水平焦慮對社會支持的中介效應情況
3 討論
3.1 軍人手機成癮狀況低于學生群體,但不容忽視
本研究中,5 204 名軍人手機成癮總分為(21.08 ± 8.25)分,手機成癮者占總調查人數的9.90%,檢出率低于既往研究報道的學生群體[31-32],但略高于王梅等[7]對某部官兵手機依賴的調查結果。這可能是因為部隊日常管理嚴格,思政教育和手機教育較多,因此本研究手機成癮程度更低,但情況不容忽視。人口學統計結果顯示,獨生子女中手機成癮者更多(11.66%),可能是因為獨生子女從小獲得更多愛和關注,有更多的情感需求。當他們來到部隊后,如果無法獲得充足的情感支撐,較易通過手機獲取情感補償[33]。此外,手機用途為游戲的軍人更容易手機成癮(13.57%);手機日均使用時間越長,越容易造成手機成癮,其中手機日均使用時間為8 h 以上的軍人,占手機成癮者的25.28%。這可能是因為手機日均使用時間較長的軍人自控力和戒斷力較差,與領導及戰友的溝通較少,易沉迷于手機,造成惡性循環[34]。
3.2 軍人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呈負相關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呈負相關,說明自我效能感較高的軍人會更少地出現手機成癮行為,支持了既往研究[35]。也有研究發現低社會自我效能感是網絡成癮的原因之一[36],這可能是因為自我效能感較低的軍人更難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對于克服困難的信心較低,因此會沉迷于手機以逃避壓力。該結果提示管理者可以通過提高軍人的自我效能感來預防智能手機成癮。
3.3 軍人社會支持在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相關性分析及中介效應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感與社會支持呈正相關,社會支持與智能手機成癮呈負相關,社會支持在自我效能感與智能手機成癮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這說明自我效能感能夠提高個體的社會支持,從而降低智能手機成癮行為。該結果提示管理者應重點提升軍人的自我效能感,從而提升軍人的社會支持水平,降低智能手機成癮行為。軍人平時的管理較為嚴格,生活方式單一。有研究發現積極心理團體活動與正念認知療法能夠有效增強自我效能感[37],改善手機依賴者的注意偏向[38]。“間接互惠理論”提出利他行為是可以傳遞的[39],軍人在相互交流中的互惠行為越多,被關照的人越會傾向于采取同樣的態度和行為感恩個體[40],進而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和正向情緒體驗。因此,管理者可以定期組織活動,以健康向上的軍營文化豐富官兵業余生活,增加面對面交流,幫助軍人通過合理方式宣泄情緒,提升自我效能感,促進互相交流。此外,管理者還可以為軍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質及精神上的支持,這些關懷能夠使軍人以更積極的狀態踐行使命[41],獲得更多深層次的滿足和愉悅,從而減少智能手機成癮行為。
3.4 焦慮在軍人社會支持對手機成癮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焦慮調節了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智能手機成癮這一中介過程的后半路徑。具體來說,當焦慮程度更低時,社會支持對智能手機成癮的影響更強,高社會支持者更不容易出現手機成癮行為。根據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buffering hypothesis),社會支持能夠緩沖不良情緒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焦慮情緒對高社會支持者的沖擊更小,更不容易手機成癮[42]。該結論進一步提示管理者需注重軍人的社會支持,同時也需關注其焦慮情緒。可以通過增進與官兵的日常交流,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關愛與支持。部隊也可定期開展心理篩查工作,一旦發現官兵出現焦慮情緒,及時進行疏導。此外,也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心理彈性訓練,促進官兵形成健康的心身狀態,減少焦慮產生[43]。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僅考察某部軍人某一時期的智能手機成癮狀況。今后可使用交叉研究的方式,從宏觀上分析整理軍人的手機成癮行為變化及影響因素。第二,本研究中男性軍人居多,女性軍人僅有一小部分。男女比例失衡使本研究無法分析軍人手機成癮狀況的性別差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既往研究已揭示性別因素對手機成癮行為的調節作用[44],今后的研究可做好性別平衡,使結果更具普適性和說服力。第三,本研究僅探討焦慮在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智能手機成癮這一中介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未將抑郁、壓力等密切相關的負性情緒納入研究。今后研究可考慮納入更多的負性情緒因素,使結果更為豐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