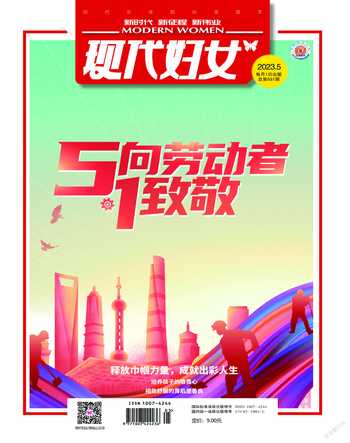徐穎:可否不叫我“北斗女神”
李晨陽 徐可瑩

徐穎被叫作“北斗女神”,是從2016年開始的。
那年徐穎33歲,她站在一個公益講壇上,僅16分鐘的講座,她的講述流暢得像首敘事詩,把北斗導航系統(tǒng)的故事講得絲絲入扣。超過2000萬的視頻播放量,一夜之間把她從幕后推向臺前。
2017年,徐穎和“航天英雄”楊利偉、“嫦娥之父”歐陽自遠院士等人一起,被評選為“科普中國”形象大使。她還榮獲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wù)隆?/p>
每一次她獲得榮譽,媒體上都會掀起一陣“北斗女神”熱。
北斗:當時只道是尋常
2020年,我國成功發(fā)射第55顆北斗導航衛(wèi)星,完成了北斗三號全球衛(wèi)星導航系統(tǒng)的全面部署。自此,中國自主建設(shè)、獨立運行的全球衛(wèi)星導航系統(tǒng)——中國北斗終于正式開通,登上世界舞臺。
1999年,徐穎剛滿16歲,就考上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的通信工程專業(yè)。讀大學前,她一直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雖成績不突出,但學得也不吃力。填報志愿的時候,她聽說“21世紀一定是通信的世紀”,便一拍腦袋,選了通信專業(yè)。
2004年,她在北京理工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導師著手做北斗二號一期接收機的課題。由于之前有過類似的研究經(jīng)驗,徐穎便自然而然地轉(zhuǎn)入了北斗課題組。
那時徐穎想不到,“北斗”二字,日后會貫穿她的生命。
徐穎說:“我讀過一篇散文,說改變你命運的那一天,在日記上總是沉悶而平凡的,‘當時還以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這就是我回顧那個人生選擇時的感覺。”
當時只道是尋常。
時至今日,徐穎和北斗已經(jīng)相伴十幾年。作為彼此的“老朋友”,徐穎已經(jīng)習慣了和北斗較勁兒死磕。
交互、發(fā)射、入軌、報文、組網(wǎng)……這些世人矚目的閃耀時刻,對徐穎來說,更像在茫茫答卷中跋涉時,偶然遇到的句點,而非慷慨激昂的感嘆號。
在中國青年五四獎?wù)碌南嚓P(guān)簡介里,這樣介紹徐穎的成就:“主導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北斗,全球?qū)Ш叫l(wèi)星系統(tǒng)(BD/GNSS)電離層監(jiān)測接收機,支撐構(gòu)建了當前國內(nèi)最大的電離層閃爍監(jiān)測網(wǎng)絡(luò),填補了中國氣象局電離層應(yīng)急移動監(jiān)測能力的空白。”
即便如此,徐穎仍然說:“我還不配被稱為一名科學家,最多是一名工程師。”轉(zhuǎn)而想到,一輩子與衛(wèi)星打交道的孫家棟院士也說過幾乎一樣的話,她又補上一句自嘲:“那我大概連工程師也算不上吧。”
科普:無心插柳柳成蔭
《來自星星的燈塔》這則主題演講,是徐穎走向大眾視野的起點。“我當時沒想那么多,只是接到一個邀請,去參加中國科學院舉辦的一個活動。”
誰也沒想到,她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簡單幾個起承轉(zhuǎn)合,就吸引了聽眾的注意。
“通常衛(wèi)星發(fā)射只有延遲,沒有提前。但是,北斗試驗星必須提前發(fā)射,這在我國航天史上是罕見的。”徐穎在演講中說。
“雷電和恐怖片更配哦,那么雷電和什么不般配呢?不錯,就是衛(wèi)星發(fā)射。”她說,“北斗第9顆衛(wèi)星發(fā)射時也是一個電閃雷鳴的天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北斗研發(fā)中的艱難與挑戰(zhàn),北斗人的勇氣與智慧,盡在娓娓道來中。但她最想講的,還是為什么要用北斗,怎么用北斗。
“不敢用、不想用,這才是制約北斗發(fā)展的重要原因。”當初的演講已經(jīng)過去6年,這仍然是她心之所系的癥結(jié)。
“北斗是要用起來的——這是我做科普最直接的目的。”她說,“如果大家都不了解它,又怎么去用它呢?”
在徐穎的講述里,北斗無處不在,又潤物無聲。
“即使其他系統(tǒng)不能用了,北斗還在。”徐穎斬釘截鐵地說。這才是他們?yōu)橹畤I心瀝血的原因——為祖國打造一份高懸星空的安全感。
在徐穎看來,每個青年科學家都應(yīng)該嘗試一下,把自己的工作講給不懂專業(yè)的人聽。她說:“先講得正確,再講得通俗;少列個公式,多講個故事。”
“通過科普,讓公眾知道我們在做什么,知道科學能為大家做些什么,是科學家永不過期的社會使命。”徐穎說,“哪怕只有一個小朋友,聽完后萌生了對科學的興趣;哪怕只有一個人,聽完后覺得北斗未來可期,我就感到自己又貢獻了一點分內(nèi)的力量。”
成名:也無風雨也無晴
對徐穎來說,一朝成名純屬意外,她說:“我一開始是很開心的,但不久便意識到,它是一把雙刃劍。”她至今都不太適應(yīng)“北斗女神”這個稱呼。
“我不喜歡這個叫法,可不可以給我改成‘北斗青年科研工作者?”面對媒體采訪,徐穎冷幽默地說,“趁現(xiàn)在我還能用‘青年這兩個字。再過兩年,你們就只能叫我‘北斗中年科研工作者了。”
當被問到:“北斗就像您的孩子一樣,您怎么看待這個孩子?”
徐穎反應(yīng)迅速:“它不是我的孩子,它是幾萬北斗人共同奮斗的結(jié)果。不過你也可以這么理解,我們所有人在參與一個‘云養(yǎng)娃的過程。在我們建設(shè)完成后,它會在遙遠的云端繼續(xù)成長成熟,不斷地發(fā)揮更完善的作用。”
徐穎總結(jié)自己的青春:“時代的發(fā)展,國家的發(fā)展,技術(shù)的發(fā)展,北斗的發(fā)展,造就了一批成長起來的人。作為其中一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幸運。”
40歲到來的前一年,徐穎榮獲中國青年五四獎?wù)隆T谶@個特殊的節(jié)點上,她對“青春”和“青年”的理解別有滋味。
“二三十歲的時候很清苦,但很快樂。因為年輕是一個不斷得到的過程,你知道自己在走上坡路。”徐穎說,“但到了40歲左右這個階段,你會有焦慮,不知道未來的路是上坡還是下坡。”
但徐穎想通了,“要像面對科學的未知那樣,面對人生的未知。”她說。
漫漫長天,北斗高懸,為全世界指引著方向。從“而立”走向“不惑”的徐穎,也在科技的浩瀚星空里,尋找著自己歸屬的位置,閃爍著自己獨特的信號。
她清醒,勇敢,還有點酷。
(摘自《中國科學報》)(責任編輯 史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