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郭鴻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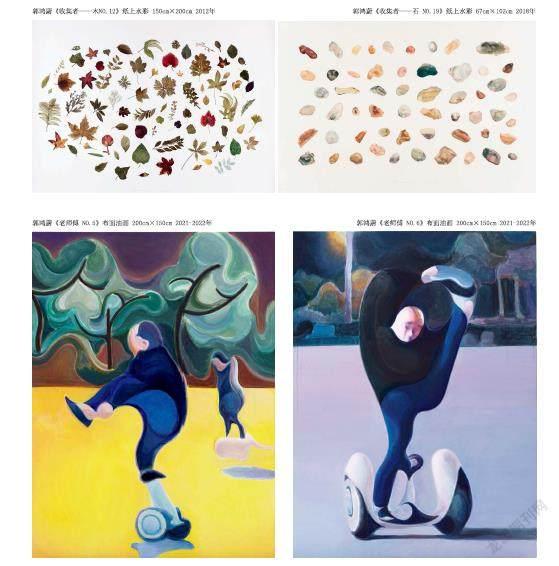
我現在還經常想起很小的時候跟著她去文化宮上課的情景。我們會簡單吃點晚飯,通常是四川小吃,有時候是打包,然后去教室。我會坐在最后一排,似懂非懂地聽著老師教大寫意。在講授結束開始動筆的時候,她的同學大多都會來摸摸我的頭。我能感受到學習繪畫帶給她的快樂——一種單純的快樂,她也把這份藝術帶來的快樂傳遞給了我。
當然,做藝術不能只憑這種快樂,還需要堅韌,不斷學習、思考,讓自己變得自信等必須有的特質。幸運的是,這些特質都是她的光芒,這些光芒也照耀著我。我相信這些光芒也會照耀著她的學生。過去她學習繪畫,如今她教授繪畫,但我始終看到她謙卑的一面,既是對他人謙卑,也是對藝術謙卑。我時常記得她說傳統藝術的偉大,如何從中學習和吸取精華。我更時常記得她說,只有踏實沉穩,不驕不躁,才能從幼苗長成參天大樹。
我總不想用太日常普通的言語去表達我和她之間的聯系,因為我總企圖把這種聯系全部放在藝術中。我們站在不同角度,看見了藝術的不同模樣,又能彼此默契地交流。這看起來比那種日常生活中的母子對話要有營養得多。但事實卻是,這遠沒有每次我從北京回到成都進家門的一句“回來啦”有溫度,也沒有我們呆在電視機前心照不宣的家常有質感,更沒有在我坐進去機場的出租車前的擁抱有愛。藝術似乎只是這種感情的外化,平平無奇卻又彌足珍貴——這不正是一種最高級的藝術嗎?
所以,你可以把生活中的矛盾理解成藝術上的摩擦,把日常里的拌嘴理解成藝術上的爭辯,我們得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即篤信又尊重,洋溢著不被觀點沖昏頭腦的包容。因為我們之間有著這樣的共識,當然這個共識可能就來自于她對我的教育——有一種存在于我們之間的感情是不會被觀點和立場所左右的。
我和一些藝術家朋友常常會談起選擇學藝術的時候,我們的父母對此的態度。我總是很自豪地講起關于她的一個故事。當我決定大學去學藝術時,他們無比的支持。也許因為源自他們對藝術的渴求,我的父母覺得一生從事這樣的事情是美好的。但是我的高中學校并不愿意放我去藝考,因為我的文化課并不差,這會讓他們損失一個上線名額。她到學校據理力爭,她說,文化課考五百多,專業課考三百多,加起來快九百分了,你們其他學生考滿了都到不了七百五,為什么不放?她的強勢是這么的可愛,再官僚的教導主任也抵擋不住她的進攻,也只好放我自流了。我覺得,這應該是我藝術之路上最具決定性的時刻了。
我們當然也是朋友,這是現在比較主流且西化的親子方式,但我們的關系遠不止此。我們在傳統和現代、西式和中式中找到一種近乎不可能的微妙平衡。我們既保留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又對新事物充滿著好奇。我們敬畏自然,心懷慈悲,思想開放。在我們眼中,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并不是二元對立,世界是復雜、多邊、分形、混沌的,這是超越人造的自然之美。
最后,母親節到來,愿我為您帶來更多的創作靈感,就像您帶給我的一樣多;愿您畫出更多偉大的作品,就像您對我的愛一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