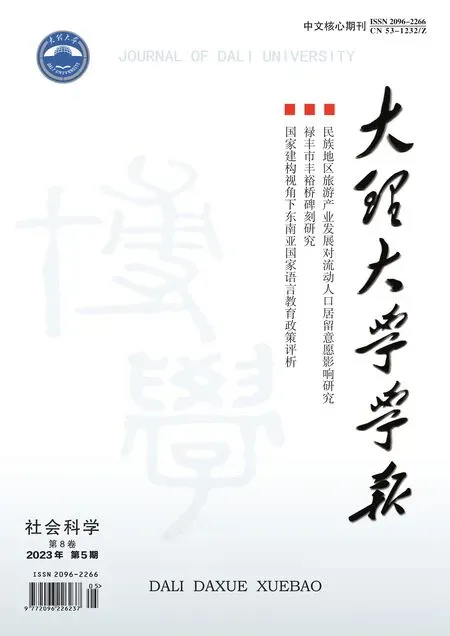祿豐市豐裕橋碑刻研究
趙志宏,黨紅梅,楊朝霞
(大理大學,云南大理 671003)
祿豐市位于云南省中部,隸屬楚雄彝族自治州,東臨昆明市富民縣、安寧市和西山區,南接玉溪市易門縣和楚雄州雙柏縣,西倚楚雄市、牟定縣,北連元謀縣、武定縣。因境內發現世界最大規模的祿豐恐龍化石(距今1.8 億年)和臘瑪古猿化石(距今800 萬年),被譽為“恐龍之鄉”“化石之倉”“人類搖籃”“亞洲人類發祥地”和“天然的自然博物館”而蜚聲海內外〔1〕。祿豐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交通區位優越,素有“扼九郡之咽喉,實西迤之鎖鑰”之稱,自古即昆明通往滇西方向的必經之地,是南方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境內重山疊翠,河谷縱橫,龍川江、星宿江、沙龍河縱貫其間。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古已有之。勤勞、勇敢、智慧的祿豐先民,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不斷地修路建橋,為后人留下了為數眾多、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豐裕橋便是其中之一。
一、豐裕橋的地理空間與歷史
豐裕橋,又名飛鳳橋、飛虹橋、利濟橋,俗稱羅次河橋,位于祿豐市金山鎮城北菜園村旁,橫跨羅次河之上。橋呈南北走向,始建于明天啟四年(公元1624 年),清康熙、雍正、咸豐年間屢次被洪水沖塌,屢次重修。其中,從咸豐初年被沖毀后至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 年),雖多次由民眾及過往鹽商集資重修,但皆因工費浩大、多有虧蝕而數十年未成。光緒十六年,黑鹽井提舉司提舉鄒馨德主持重修,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 年)修復,沿用至今〔2〕。橋長116.55 米,高9.5 米,橋面凈寬7.6 米,兩旁人行道各寬0.5 米,4 墩5 孔石拱橋,單孔跨徑12 米,拱券縱聯砌筑。橋面建有石欄,高0.8 米,寬0.4 米。橋北雙獅昂首,橋南對象臥立,中孔拱頂東、西兩側分別雕刻有龍頭、龍尾,寓“神龍治水,永固橋基”之意,其余各孔拱頂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石刻浮雕。橋南原有樓閣一座,1958 年被拆除。橋北建有石牌坊一座,高5.5 米,寬5.8 米,重檐斗拱,中檐三層,側檐二層。六柱五門,柱聯三對,門鑲五碑〔3〕。該橋規模宏大,工程精良,雄偉壯觀,是云南古代橋梁的杰出代表之一。
祿豐境內的黑井、瑯井、元永井、阿陋井,原系滇中重要的產鹽之區。豐裕橋古為黑、瑯、元永、阿陋四井運鹽至省會昆明之重要橋梁,關系國計和民生。據傳,因橋北石牌坊上有“豐課”“裕民”之匾額,以及碑文中有“鹽豐課裕”之說,故名“豐裕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豐裕橋變為縣城通往附近村鎮之公路橋。1973 年,豐裕橋被祿豐縣人民政府評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3 年12 月,豐裕橋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為云南省第六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013 年5 月,豐裕橋和星宿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
2021 年7 月,“南方絲綢之路云南段交通碑刻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到楚雄彝族自治州祿豐市進行田野調查。在豐裕橋北橋頭,尋訪到碑刻遺存5 通,保存基本完好。但由于年代久遠,日曬雨淋,加之碑石材質紅砂石易于風化,5 通碑石的下角及底部已現風化、皸裂、分層翹腳現象,部分碑刻的文字已不同程度受損。碑刻遺存具有與古代典籍同樣重要的文獻價值,亟待社會和學界的保護與關注。
二、豐裕橋碑刻研究現狀
(一)學界關注不多
據文獻查閱,關于祿豐豐裕橋,《中國橋梁技術史》《云南省志·卷33:交通志》《云南省公路交通史》《云南名勝古跡詞典》《云南名勝大全》《云南文物古跡大全》《云南古橋建筑》《云南導游基礎知識》《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辭典》《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志》《祿豐縣志》《祿豐縣文史資料》等文獻中,或多或少皆有相關記述。但幾乎都是關于豐裕橋的地理位置、建造歷史、橋梁規模、保護情況等的簡單介紹和說明,間或有文獻涉及豐裕橋碑刻者,不過只言片語。毋庸諱言,學界雖已關注到了豐裕橋,且相關記述散見于各種文獻中,但對于豐裕橋的碑刻遺存卻研究關注不多。
(二)系統研究缺失
據實地調查,豐裕橋碑刻遺存共計5 通,除“修建羅次河豐裕橋記”被《楚雄州交通志》在該書“附錄”中輯錄為“豐裕橋碑記”〔6〕425-426外,其余4 通未見文獻記載。況且,《楚雄州交通志》所載“豐裕橋碑記”一文,只是單純的碑文輯錄,并無更多深層次的探究。經對照原碑校勘發現,該錄文存在諸多衍、脫、錯、訛等,不利于學界參考。再查《楚雄歷代碑刻》,以及祿豐市、楚雄州、云南省等出版的金石錄、碑刻集等文獻資料,依然未見相關輯錄或記載。種種跡象表明,學界對于豐裕橋碑刻遺存,尚無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或專題研究,實乃憾事。
三、豐裕橋碑文簡介
受篇幅限制影響,原碑文無法詳盡呈現。現依由右至左的順序,將豐裕橋5 通碑刻的基本情況簡單介紹如下。由于原碑中有4 通無碑名,為便于研究,暫以各通碑刻上方的橫匾作為碑名進行概述。
(一)永奠碑
碑存豐裕橋北橋頭,位于石牌坊右一。紅砂石質,高230 厘米,寬84 厘米。碑文楷體陰刻,文12行,行5~50 字,計454 字。碑身四周紋飾環繞,碑頭有石匾,楷體陰刻“永奠”2 字。光緒十八年立,鄒馨德撰文。
碑文可分為兩部分,1~6 行(含第7 行前部)為第一部分,乃黑鹽井提舉鄒馨德向上級稟請嘉獎橋工紳董一事的呈文。呈文細述了豐裕橋為黑、元永、瑯各井運鹽必由之要道,但因工費浩大,加之歷任官員虛報,故籌修數十年而不成。光緒年間,時任黑鹽井提舉鄒馨德捐資倡首,選派勤廉耐勞之井紳鄧芝、張文林、王釙等監督修理,不日功成,工堅費省。為示嘉慰,特稟請上級賞給橋工紳董鄧芝、張文林、王釙等匾額、頒發獎勵之事。7~12 行為第二部分,系上級對鄒馨德稟呈事項的回文。回文刊載了上級對鄒馨德捐資倡首、帶頭修橋的充分肯定,并飭令鹽法道會同善后局遵照指示辦理。
(二)裕民碑
碑存豐裕橋北橋頭,位于石牌坊右二。紅砂石質,高265 厘米,寬91 厘米。碑文楷體陰刻,文17行,行4~68 字,計約850 字。碑身四周紋飾環繞,碑頭有石匾,楷體陰刻“裕民”2 字。光緒十八年立,普津撰文。
碑文可分為兩部分,1~12 行(含第13 行前部)為第一部分,記載了光緒年間黑鹽井提舉鄒馨德稟請修理豐裕橋的詳細經過,修理該橋之款項借墊、提撥等情況說明,以及稟請同意委派黑井紳董鄧芝、遠灶生王釙、元永井灶紳張文林隨同監修之事。13~17 行為第二部分,刊刻了云南省鹽法道普津對以上稟請給予的批示,以及責令認真修理豐裕橋、嚴禁侵蝕虧短款項、從嚴懲治違紀等方面的告示。
(三)功資砥柱碑
碑存豐裕橋北橋頭,位于石牌坊正中。紅砂石質,高300 厘米,寬98 厘米。碑文楷體陰刻,計4行。碑身四周紋飾環繞,正中楷體陰刻“豐裕橋”3個大字,1、2 行列其右,3、4 行列其左。碑頭有石匾,楷體陰刻“功資砥柱”4 字。光緒十八年立,鄒馨蘭題并書。
碑文簡要記述了時任永昌知府鄒馨蘭,光緒十六年冬往返省會昆明公干、光緒十八年四月赴昆明任職,途經豐裕橋時的不同感受,記載了豐裕橋由木易石的歷史以及橋名的由來。
(四)豐課碑
該碑《楚雄州交通志》有輯錄,碑名為“豐裕橋碑記”,但錄文有錯訛。碑存豐裕橋北橋頭,位于石牌坊左二。紅砂石質,高265 厘米,寬91 厘米。碑文楷體陰刻,文16 行,行9~97 字。碑身四周紋飾環繞,碑頭有石匾,楷體陰刻“豐課”2 字。光緒十八年立,鄒馨德撰文。
碑文可分為三部分,1~4 行為第一部分,記載光緒年間鄒馨德蒞任黑鹽井提舉,積極整頓鹽務井政,修路建橋,修廢舉墜之事。5~10 行為第二部分,記載修建豐裕橋的經費籌措、工程時間,橋梁的規模,經費收支等情況。11~16 行為第三部分,記述了修建豐裕橋之始末,作者撰寫碑記的緣由,以及漏敘事項的補記。
(五)利安碑
碑存豐裕橋北橋頭,位于石牌坊左一。紅砂石質,高230 厘米,寬84 厘米。碑文楷體陰刻,文8行,計175 字。除第1 行與第8 行外,2~7 行分上下二欄鐫刻。碑身四周紋飾環繞,碑頭有石匾,楷體陰刻“利安”2 字。光緒十八年立,羅森、鄒炘書丹。
碑文刊載光緒年間修建豐裕橋橋工經事人員之姓名,如監修人員、經理橋工人員、書丹人員、工匠等,以及大北廠王姓、棠海沖希姓捐山采石之事。
四、豐裕橋碑文解讀
(一)黑鹽井的鹽運與豐裕橋
據《滇南志略》記載,云南的鹽井主要散布于云南府、楚雄府、大理府、麗江府、普洱府、景東直隸廳、武定直隸州、鎮沅直隸州等八個地區。其中,普洱府有鹽井區8 個,楚雄府6 個,麗江府3 個,武定直隸州2 個,鎮沅直隸州2 個,景東直隸廳1 個。單從鹽井數量來說,楚雄府是云南境內鹽井分布較多的地區之一,僅次于普洱府。楚雄府的鹽井,主要分布于姚州、廣通縣、定遠縣三地。姚州有白鹽井,廣通縣有阿陋、元興、永濟三井,定遠縣有瑯鹽井、黑鹽井。從每年煎額鹽數量來看,黑鹽井10 131 026斤,位居全省第一;白鹽井8 739 300 斤,位列全省第二;元興、永濟二井5 485 300 斤,居全省第三;瑯鹽井1 486 808 斤,居全省第六〔7〕。不難看出,無論從數量或產量上而言,楚雄府無疑是清代云南鹽井重區之一,而黑鹽井則是楚雄府鹽井之重中之重。
黑鹽井,地處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祿豐市西北部,山高谷深,溝壑縱橫,林深木密,荊棘叢生,地形復雜。由于河道淺隘,水流湍急,不通舟楫。加之層巒疊嶂,危巖壁立,往來全賴牛馬和人力。千百年來,雖交通不便,轉運維艱,但通過先民的不懈努力,由黑井發端的鹽運古道依然四通八達。“井在萬山中,路不止一處也。由土主廟下南行者,往瑯井路也;由龍王廟右西去者,由白衣庵下西去者,往姚安路也;過龍溝北去者,往元謀路;過五馬橋上山東去者,往武定路也。”〔8〕其中,由黑井往省會昆明(即武定方向)的道路是黑鹽井最重要的鹽運道。明清至民國初期,黑井至祿豐段計為兩站,長約80 公里。歷經五馬橋、三河橋哨、水臺坡、羅武關、老王坡(瑯井入省鹽運道交匯處)、高栗哨、花箐、小板橋、羊毛關、小石橋、章喜哨、沙矣舊(黑井入省、元永井入省鹽運道交匯處),此為第一站,約35 公里。再由沙矣舊、惠遠橋、鸚哥哨、秧草地、大莊科哨、小莊科哨、稗子溝哨、章公橋、刺桐哨、白沙哨、寶泉村、廟山哨、小河橋、石灰壩、科甲村、大北廠、飛鳳橋(豐裕橋),直入祿豐縣城,此為第二站,約45 公里。到達祿豐縣城后,匯入古滇洱大道,再經楊家莊、祿膿、安寧等地直達省城〔9〕。
(二)豐裕橋橋名溯源
《新纂云南通志》載:“飛虹橋,俗名羅次橋,在城北門外里許,通黑、瑯井大路。明天啟間,邑紳王錫袞建石橋三硐。”《明大學士王文毅公事紀略》載:“王錫袞,字龍藻,號昆華,一號仲山,又號念昔,別號素齋。世居祿豐縣城北大北廠,先代及公塋墓在城西蓮花山。”王錫袞,祖籍陜西華陰,先祖王仲寬,以軍功授右衛冠帶總旗,屯田祿豐,子孫遂占籍于此。《知我府君行述》載:“吾家世為陜之華陰人,始祖仲寬,以良家子從穎川侯克滇,功授右衛冠帶總旗,屯田祿豐,子孫遂家焉。”明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王錫袞鄉試中舉。天啟二年(公元1622 年),中進士。不久因其父病故,回家守喪。《王氏家譜·王錫袞傳》載:“守制在里,民病涉,新建飛鳳石橋三硿。”又《啟明橋碑記》載:“吾邑在滇池右,合武定、羅次,達于沉而入于交,溢悍馳迅,不減兩津。凡為橋者三:曰星宿,西環邑治者也,邑令向君成之;曰飛鳳,東環邑后南達金沙者也,予奉先大夫命,合鄉人成之;曰啟明,則東拒邑前,南聯省會者也,方伯木君成之。”在家鄉祿豐為父守孝期間,天啟三年(公元1623 年),王錫袞見村旁鹽運驛道所跨羅次河無津梁可過,即捐資倡首興建跨河橋梁,次年建成三孔石墩木橋,取名飛虹橋,又名飛鳳橋。后來,橋被洪水沖塌,其子王咨翼繼承父志續修完工,《王氏家譜·王咨翼傳》載:“王咨翼……重建飛鳳石橋,鼎建古林書院。”〔10〕
《楚雄州交通志》《明代云南文學家年譜》《文化楚雄·祿豐》等文獻均有“天啟年間,王錫袞回祿豐為父守孝期間,建成三孔石墩木橋,取名飛虹橋,又名飛鳳橋。后來該橋被洪水沖毀,其子王咨翼續修完工,取名豐裕橋”〔6〕371之說,但“王咨翼續修之后,取名豐裕橋”這一記述卻與《功資砥柱碑》所載有出入。
《功資砥柱碑》載:“洎壬辰四月,赴首府任鴻爪重經,則橋以巨石砌成,嶻然改觀,履若坦途。周歷審視,工程浩大,當費帑金巨萬。問所出,則皆由井鹽價內籌集。問其工,則三井紳灶所鳩督。問其地,則屬祿豐乃予之轄境也。予喜曰:‘是橋之成,不僅先得我心之所欲,實為鹽務所不可緩。’從此駢牢墆鬻,商旅暢行,不又愈見鹽豐課裕之庥乎。昔漢武得鼎,名年歐陽。予喜雨名亭,是不可無以名之也。爰泚筆而名之曰:‘豐裕’。黔東鄒馨蘭題并書。”據上述碑文可知,光緒十八年,時任永昌知府鄒馨蘭奉命赴省城任職(昆明知府)再次經過祿豐,親見鄒馨德所修之橋“則橋以巨石砌成,嶻然改觀,履若坦途”,有感于當地“商旅暢行”“鹽豐課裕”之繁榮景象,欣然“泚筆而名之曰:‘豐裕’”。是故,我們認為豐裕橋之名應始于光緒,源于鄒馨蘭。
黔東鄒馨蘭何許人也?鄒馨蘭,名位揆,字循陔,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 年)生,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縣長吉鄉長吉村人,乃鄒馨德之胞兄。晚清附生,歷任云南永昌知府、昆明知府、蒙自道員、云南按察使等職。法國、英國吞并越南、緬甸之后,經常在云南邊境制造邊界事端,鄒馨蘭被朝廷委任為中法(滇越)、中英(滇緬)劃界專使。他精選熟悉疆土掌故的屬員,攜帶歷代輿圖、志書和檔案資料,在與法、英代表談判時,據理力爭,寸土不讓,使劃界得以勝利完成,為保護國家主權作出了貢獻。惜返昆途中病故,壽終68 歲。朝廷嘉獎其功績,追贈為內閣學士,賜其子為一品陰生,陰知州,從優撫恤。旨諭貴陽城治喪,貴州三司主持喪儀,葬修文縣扎佐大壩〔11〕。
又《豐課碑》載:“國初,鹺使檄飭黑井提舉,措款興修,名曰‘飛虹橋’,年久被水沖圮,行人病涉。其遺址在今橋下數武,嗣經民間修成矮墩四座,架木為梁,以濟往來,每夏秋水潦輒至漂失。”由此碑文可知,天啟年間王錫袞所建之飛虹橋,不僅橋名發生了改變,而且其最初的橋址也并非如今豐裕橋之所在。
再據《道光云南通志稿》記載:“飛虹橋,在城北門外里許,通黑、瑯兩井大路。明天啟間,邑紳王錫袞建石橋三硐。康熙十一年傾圮,鹽道郭廷弼捐修,易以木橋。四十六年,水泛沖斷,鹽道李苾捐俸,知縣黃樞督修,后復壞。五十二年,黑井提舉沈懋價重修。《云南府志》俗名羅次橋,邑紳士王咨翼重修。祿豐縣采訪:雍正五年,被水沖坍,夏秋造船濟渡,冬春建木為梁。”〔12〕咸豐初年,該橋再次被沖塌后,雖多次多方集資重修,但因種種原因直至光緒十六年皆未成。光緒十六年,黑鹽井提舉鄒馨德主持重修,光緒十八年建成為4 墩5 孔石拱橋,并名之曰“豐裕橋”,沿用至今。
(三)黑鹽井提舉鄒馨德與豐裕橋
鄒馨德,字寅臣,名位寅,又名亮清,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 年)生,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縣長吉鄉長吉村人。因軍功升任都司、副將,后以知州銜赴滇供職。云貴總督劉長佑知其擅長理財,委任其為云南黑鹽井提舉司提舉,專司鹽務。
修路建橋,是云南高原地區、深山密林之處交通順暢的重要保障。《裕民碑》載:
卑職于十二年冬月二十五日到任,整頓井務,按照抽收遵□飭提撥此款,先修運鹽道路;抽解省城敬節堂公□,續經修建衙署、行署貳所造報。至十五年□□余存銀陸百柒拾捌兩零捌分肆厘,除稟奉詳定以十六年續抽之款修建□財神祠及大使儒學兩署外,其十七、八、九等年所抽專供修橋之用,限年落成。茲經領到借墊銀□千兩,卑職業于三月初一日募齊匠役人等,踩山取石,開工興辦。惟工費浩繁,一手一足,期年所能成事。
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 年),鄒馨德被委任為黑鹽井提舉司提舉。他深知“橋興則路暢,路暢則鹽運興,鹽運正常則鹽業興,鹽業興則國泰民安”的道理,到任后立即著手整頓井務、興修鹽路,工作主次分明,先后有序,使黑鹽井的井務、鹽路逐漸恢復正常并獲得長足發展,“滇南鹽井有八,黑居第一,蓋八井課價,黑井過半焉”。
又《永奠碑》云:“卑職有鑒前車,特選派勤廉耐勞之井紳鄧芝、張文林、王釙等,稟請札委監督修,限年落成。由卑職隨時稽查,如有侵蝕等弊,稟送嚴究。倘卑職從中染指,亦許該紳灶等揭稟,以期力挽積弊。”《裕民碑》曰:“月給薪水,由卑職就款酌發。其勤支工糧等銀,仍由卑職隨時稽查,認真督率修理,并請給示張貼曉諭。倘有侵蝕虧短等弊,由卑職稟送究辦。如卑職從中染指,即仰該紳等指明揭控,務期工歸實洽,款不虛糜,庶可早日告成,以副各憲籌劃謞諭之至意所有。”
橋梁的建設與發展,是鹽運能夠恢復正常、鹽業復興的決定性因素,也是清朝國家政治、經濟、交通的重要命脈。因此,鄒馨德高度重視豐裕橋的重建工作,不僅“有鑒前車”,還“特選派勤廉耐勞之井紳鄧芝、張文林、王釙等”負責主持工作,并“稟請札委監督修,限年落成。由卑職隨時稽查,如有侵蝕等弊,稟送嚴究。”鄒馨德不但親自監督、稽查,防止“侵蝕虧短等弊”,而且還稟請上級“給示張貼曉諭。倘有侵蝕虧短等弊,由卑職稟送究辦。如卑職從中染指,即仰該紳等指明揭控,務期工歸實洽,款不虛糜,庶可早日告成,以副各憲籌劃謞諭之至意所有。”字里行間彰顯了鄒馨德廉潔奉公、勞心勞力、盡職盡責的崇高品質和風清氣正的工作作風。其任職8 年,共解繳鹽課28 萬兩,創下黑鹽井歷任提舉解繳鹽課最高紀錄。
另《永奠碑》“合無仰懇憲恩,書給該紳鄧芝、張文林、王釙匾額各一方,頒發獎勵,以資觀感。”父母官鄒馨德拳拳為民之心、愛民之情躍然石上。此外,在黑鹽井任提舉期間,鄒馨德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和培養地方人才,積極籌資創辦“萬春”“鷲舉”兩書院,并帶頭捐資助學,重金聘請外地名士講學,讓書院聲名遠揚。因政績卓著,升任云南省鹽法道員,負責全省鹽法事務。后歷任順寧府知府、云南府知府。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 年),改任云南鹽法道、兵備道、糧儲道和迤東道員等職。辛亥革命后,馨德告老還鄉,1916 年6 月病逝于貴陽寓所,葬大西門水磨河邊〔13〕。
(四)重修豐裕橋的時代背景
豐裕橋,位于祿豐縣城北門外二里許(今祿豐市金山鎮城北1 公里處),橫跨羅次河之上,其時為楚雄府黑井、瑯井、元永井、阿陋井四井運鹽至省會昆明之重要橋梁。《功資砥柱碑》載:“羅次河距祿豐北門二里許,為黑、元、永三井運鹽要道。”《永奠碑》曰:“竊祿豐縣城北門外羅次河豐裕橋,為黑、元永、瑯各井運鹽必由之要道。”《裕民碑》云:“伏查羅次河豐裕大橋,距祿豐縣城北門外二里許,為井鹽運銷省城各屬要道。”《豐課碑》記:“查是橋距黑井二站,距元永井一站,距祿豐縣城北門僅里許,為黑、元永、瑯各井鹽運必由之要道也。”
然而,咸同之亂致使云南包括鹽業生產在內的社會經濟受到重創。《豐課碑》記載:“光緒丙戌冬十一月,予捧檄蒞任黑鹽井,以兵燹之后,承敗壞之余,鹽務井政幾于不可收拾。”受動亂之害,饑餓橫行,瘟疫肆虐,民不聊生,祿豐境內部分鹽井被起義軍控制,鹽業遭受重創,黑鹽井的鹽務、井政等亦難幸免。此外,“而井政中如硔、鹵硐、關卡、橋梁、道路,以及祠廟、學校、衙署,諸事未遑規復,目睹情形,時覺耿耿。”頻繁發生的戰亂,導致鹽礦、關卡、橋梁、道路等受到破壞,甚至祠廟、學校、衙署等概莫能外,黑鹽井的鹽路、鹽運等皆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百姓死傷過半,部分灶戶為躲避戰亂而四下流竄,導致制鹽人員流失,黑鹽井百廢待興。“下車后勤求利弊,首將煎辦銷征諸要務設法整頓,苦思焦慮,積弊始清,期年報解照額,自后遞有加增。”戰亂平息后,在地方官員的不懈努力下,鹽業生產逐漸得以恢復。但關卡、橋梁、道路等交通要害的重修卻并非一日之功。
有清一代,“滇南大政,惟銅與鹽”〔14〕。 毋庸置疑,鹽運暢通、鹽課豐裕不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充裕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成了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重修豐裕橋,已成燃眉之急。
(五)重修豐裕橋的經費籌措
重修豐裕橋,不僅“工程浩大”,而且“當費帑金巨萬”“羅次河橋工需款甚巨”,經費成了首要難題。《豐課碑》載:
請將自光緒十二年冬到任起,至十六年底止,照征橋工經費二分項下提款,逐一修理。逾年始克,次第告成。惟羅次河橋工需款甚巨,除提款及奉文提解省城敬節堂經費外,所余無幾。其自同治辛未年起,歷任征獲二分橋工經費之用,已成烏有,分毫無存,始擬請以十七、八、九等三年,應征經費專供橋工之用。而鹽運攸關,工須急就,是以稟請:前護鹽憲陳昆山觀察咨由藩庫預借墊銀肆千兩,……是役也,計需銀玖千捌百陸拾陸兩肆錢玖分玖厘,除庫借及收獲經費外,不敷銀貳千捌百捌拾捌兩肆錢壹分伍厘,由予捐廉以蕆其事。除前捐外,又捐置廟田銀壹百柒拾兩。前后共捐銀叁千伍拾捌兩肆錢壹分伍厘,馨德再記。
據碑文所載可知,重修豐裕橋的經費來源主要如下:一、征收橋工經費二分項下提款;二、奉文提解省城敬節堂經費;三、擬請連續征收光緒十七、十八、十九共三年應征經費,專供修橋之用;四、稟請上級由藩庫(即省庫)預借墊錢;五、鄒馨德捐廉補充不足;六、鄒馨德捐置廟田銀補充不足。如此多樣的資金籌措方式,特別是專項經費的籌集及提出,在云南古代官方主持修建的古橋中實屬鮮見,這既是黑鹽井提舉鄒馨德勤政為民、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真實反映,也是其足智多謀、有膽有識、聰明睿智的具體體現。
其中,“惟羅次河橋工需款甚巨,除提款及奉文提解省城敬節堂經費外,所余無幾。”尤其令人過目難忘。敬節堂,清代收養貧苦寡婦的場所,或稱清節堂、恤嫠會、永安局、濟孀會。云南的敬節堂,與咸同之亂息息相關。光緒九年(1883 年),云貴總督岑毓英、巡撫唐炯,為了收養在戰亂中死亡的清軍將士守節遺孀,在昆明錢局街的大井巷建立敬節堂。宣統末年,敬節堂附設女子職業學堂,學員都是“節婦”,教她們學裁縫、織布、織草帽等技藝,同時也開設修身、國文、算術等課程〔15〕。豐裕橋的修建,需要提解昆明敬節堂的經費,不難看出當時地方財政由于戰亂所遭受的重大影響,以及橋工經費的捉襟見肘。
又“除庫借及收獲經費外,不敷銀貳千捌百捌拾捌兩肆錢壹分伍厘,由予捐廉以蕆其事。”“除前捐外,又捐置廟田銀壹百柒拾兩。”等碑文,清清楚楚地記載了“鄒馨德為重修豐裕橋,心甘情愿以捐俸祿、捐置廟田銀的方式承擔入不敷出的部分”的史實,其清正廉潔、克己奉公、大公無私、為國為民之心天地可鑒。同時,也從側面印證了豐裕橋在當時當地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六)重修豐裕橋的地方社會狀況
清代,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國家對滇鹽開發的重視和推動,滇鹽的井區、產量及其課稅均超過了以往,云南鹽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鹽井不但解決了井地偏僻、崇山密林中當地民眾的生計問題,而且增加了地方和國家的財政收入。鹽井的開發,促成了以鹽井為中心的聚落的產生;井鹽的生產、運輸、銷售、交易等,增進了人口流動、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推動了聚落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等的發展和繁榮。鹽業的日新月異,最終成為黑鹽井、白鹽井、瑯鹽井等行政中心產生的重要因素。清初,朝廷即在黑鹽井、白鹽井和瑯鹽井設立了鹽課提舉司,鹽課提舉司設提舉一人,駐在井地,輔助鹽法道管理所屬井鹽鹽務。其下又設有鹽課司,鹽課司設大使一員,負責管理監督井灶生產和督催鹽課〔16〕。
行政中心、管理機構的設置,官員的選派、制度的完善,以及先進技術、文化的輸入等,致使楚雄府境內以黑鹽井為代表的云南鹽礦區,社會風氣清正,民眾教化良好,民風淳樸,百姓安居樂業,勤勞務實。《康熙黑鹽井志》有云:“井自有明三百年,訖國朝六十七年,生齒日繁,風氣日開,教化大行,文章漸著,人物氣象,卓有可觀。”〔17〕
《永奠碑》“黑鹽井提舉鄒馨德稟請,賞給橋工紳董獎勵事”,時任地方官員有感“勤廉耐勞之井紳鄧芝、張文林、王釙等……雇匠、督工、采石、備料,不辭勞怨,無間風雨,故能工堅費省而成功甚速,洵屬竭急”,特向上級“仰懇憲恩,書給該紳鄧芝、張文林、王釙匾額各一方,頒發獎勵,以資觀感”。《裕民碑》“茲查有黑井紳董鄧芝、遠灶生王釙、元永井灶紳張文林,勤正耐勞,素知急公好義”。《豐課碑》“當采石維艱之際,復得祿邑王、希二姓捐山采石,藉成厥工,永為鹽運百世之利,詎不幸哉”。《利安碑》“大北廠王姓、棠海沖希姓捐山采石”等,是以鹽井為聚落的地方社會各族人民凝聚力、向心力的體現,也是祿豐官民一家親,民眾同心同德、自愿出錢出力積極參與橋梁工程建設的真實記載。這些第一手原始資料,一方面彰顯了地方官員黑鹽井提舉鄒馨德的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另一方面體現了祿豐民眾民風淳樸、崇善向善的優良品質;第三方面,從側面反映了清朝政府富有成效的邊疆治理方略和卓有成效的治理方式。以上種種也正是豐裕橋從咸豐初年屢毀屢修而數十年未成,后光緒年間鄒馨德主持重修,雖工程浩繁需巨款卻不日即成的重要原因。
五、豐裕橋碑刻的價值
碑刻遺存是豐裕橋的歷史見證、歷史記載和原始實物資料,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文物價值
豐裕橋是云南古代橋梁的頂尖杰作之一,是云南古橋建筑成就和技藝的集中體現。碑刻遺存是豐裕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祿豐先民留給后人的珍貴的文化遺產,是祿豐各族人民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
(二)史料價值
碑刻遺存共計5 通,刻立于光緒十八年,距今已130 余年,歷時久遠,其中《永奠碑》《裕民碑》《功資砥柱碑》《利安碑》未被文獻記載。新搜整的這些實物資料,是全面、系統、深入研究豐裕橋歷史、地理、演變、發展等的重要新發現,不僅有利于彌補已有文史資料對豐裕橋碑刻記載之不足,而且有利于豐富和完善學界對豐裕橋的相關研究,對研究楚雄州、云南省古橋及其碑刻,社會歷史發展、生活變遷、民族風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18〕。
(三)學術價值
碑刻刊載了豐裕橋在清代楚雄府鹽業發展、鹽業運輸、增課裕民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黑鹽井提舉司整頓井政、鹽務,恢復鹽業生產、鹽運、銷征,重修關卡、道路、橋梁等系列措施;大量的官職、名銜、人物,如云南通省鹽法道、前護鹽憲、布政司史、井員、滇南榷鹽使者長白普津、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黑鹽井提舉鄒馨德、都司職銜武生張文林、提督銜升用總兵前貴州永安協副將鄧芝、特授瑯鹽井儒學訓導羅森、云南前先補用從九品鄒炘等等。這些歷史記載,對清代云南地區的鹽井歷史、鹽業發展、鹽產運輸、食鹽課稅等;楚雄鹽井地區的民風民情,地方官員的廉潔自律,以及西南邊疆的區域治理等;職官體系、名宦、名人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四)科研價值
豐裕橋碑刻記載的內容多樣,內涵豐富,年代久遠,涉及豐裕橋的歷史、地理、工程建設、資金籌措、經費收支、工程時間、橋梁規模、功德芳名等方面,這些珍貴的原始資料,為我們厘清豐裕橋的歷史沿革,研究楚雄古代橋梁文化、橋梁工程建設與發展,乃至云南省的橋梁史、建筑史、交通史、科技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
(五)文學價值
豐裕橋碑刻中,《永奠碑》鐫刻了黑鹽井提舉鄒馨德稟請上級獎賞勤廉耐勞之井紳鄧芝、張文林、王釙等橋工紳董的呈文;《裕民碑》刊刻了欽命督理云南通省鹽法道加十級紀錄七次普津為修建豐裕橋而出的告示。這些碑文從表面上看只與修建豐裕橋有關,其實關乎國計和民生,碑文中的“稟、札、準、遵、照、批、委、飭、令、批示、特示、曉諭”等,對于研究清代公文的文體、行文規范等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