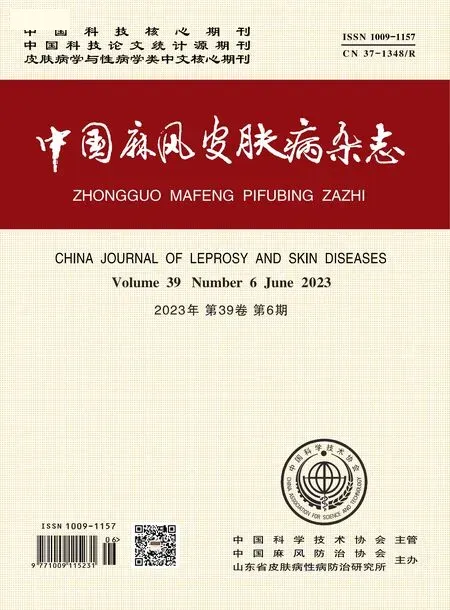抗PD1/PD-L1免疫治療誘發的大皰性類天皰瘡的機制及診療進展
黃銳婷 姜福瓊 胡齡予
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昆明,650101
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也稱為CD279(分化族),是一種免疫抑制分子,主要分布在T細胞膜表面。配體程序性死亡蛋白配體1(programmedcell death ligand 1,PD-L1)表達于人體多種細胞的細胞膜上,使其能躲過免疫系統的攻擊。腫瘤細胞膜也表達PD-L1,其與T細胞表面的PD-1結合后抑制T細胞的增殖、活化、細胞因子的產生和其他效應器功能,最終抑制抗腫瘤免疫反應[1]。PD-1/PD-L1單克隆抗體免疫療法已證實可治療許多實體腫瘤及血液系統惡性腫瘤。但隨著越來越多PD-1/PD-L1單克隆抗體免疫療法的使用,使得免疫相關副作用(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也越來越常見,其中皮膚不良反應最常見[2]。在一項回顧性研究中,使用該免疫療法超過1/3的患者都出現過皮膚毒性表現,其中大皰性類天皰瘡(Bullous pemphigoid, BP)為少見類型[3]。因irAEs在臨床工作中越來越常見,這種皮膚毒性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患者腫瘤的治療策略,因此,本文復習文獻,為使用PD-1/PD-L1引起的BP的診療提供最新總結報道。
1 抗PD1/PD-L1免疫治療誘發的大皰性類天皰瘡的患病率與發病機制
據目前的報道,抗PD1/PD-L1免疫治療后引起大皰性類天皰瘡的患病率比較低。在一項853例的回顧性研究中,在使用PD-1/PD-L1治療后有7例(0.8%)出現BP[4]。另一項3825例接受抗PD-1治療的患者和556例接受抗PD-L1抗體治療的患者當中<1%患者出現BP[3]。抗PD1/PD-L1免疫治療后治療如何誘發大皰性類天皰瘡的發病機理暫不清楚,可能的機制:(1)“共享抗原理論”。 腫瘤細胞表達了基底膜帶的某些抗原,機體對腫瘤細胞產生免疫反應時,共同抗原可能誘發機體出現免疫反應產生抗體,進而攻擊基底膜帶,導致BP發病[5,6]。(2)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亞型的過度表達。研究提示特定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亞型的過度表達可能導致BP的發病,其中HLA-DQB1*03:01尤甚[7]。(3)“T細胞耗竭”的恢復。PD-1受體位于活化T細胞、B細胞、單核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上,PD-L1配體位于腫瘤細胞和一些上皮細胞上[8]。腫瘤細胞通過表達PD-L1消耗T細胞,出現免疫逃逸,抑制機體對腫瘤的免疫力,并出現“T細胞耗竭”[9]。PD-1/PD-L1抑制劑主要通過增強機體免疫反應治療腫瘤,在這個過程中T細胞耗竭情況逐漸恢復,活化的T細胞增殖和炎癥反應細胞因子釋放,使人體原有免疫耐受被打破引起自身免疫反應,導致BP。(4)B細胞活化。B細胞表面也表達PD-1, PD-1抑制劑可能通過上調濾泡調節性T細胞(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Tfr)的數量間接激活B細胞,或者直接促進了非T細胞依賴途徑的B細胞活化,活化的B細胞分泌的針對基底膜帶的自身抗體BP180或BP230可能會誘發BP[10]。
2 抗PD1/PD-L1免疫治療誘發的大皰性類天皰瘡臨床特征
抗PD1/PD-L1免疫治療后引起大皰性類天皰瘡與傳統的藥疹不同,其臨床特征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瘙癢;二是延遲反應;三是皮疹持續。在出現特征性的水皰、大皰前,大部分患者曾出現過非特異性皮膚表現,最多的是瘙癢,另伴或不伴有丘疹、斑塊的濕疹樣皮疹[4,11,12]。在一項58例PD-1/PD-L1所致BP回顧性研究中,治療開始和初始皮損發展之間的中位時間為21周(范圍1~88周)。67.2%的患者(39/58)觀察到瘙癢,發生在治療開始后26周(范圍1~104周)的中位延遲。51例患者(87.9%)出現水皰[12]。臨床中皮疹的分布和嚴重程度各不相同,皮疹主要累及患者四肢,其次為軀干[13],但也有少數患者出現粘膜受累[4],且出現黏膜受累較特發性BP更多見[13],匯總如表1。且有報道提示多種免疫抑制劑使用較單一免疫抑制劑使用更容易使患者皮疹出現時間縮短[11]。但BP的發生可能與用免疫療法治療的惡性腫瘤的良好結果有關(反應率較高)[14]。PD-1抑制劑治療后出現皮膚irAE時間范圍很廣,在一項回顧性觀察中,皮膚irAE延遲發作(≥3個月)很常見,同時,PD-1抑制劑相關的皮膚irAE可能在治療中斷后發生[15]。有研究證實PD-1抑制劑具有持久作用,即使在停止治療后,腫瘤反應仍具有高度持久性[16,17]。有研究表明43.6% 的停止免疫治療的患者在初始皮膚毒性后的20周內被診斷出患有BP[12]。持續性免疫再激活和腫瘤靶向相關的長期腫瘤反應,可能是導致在停止治療后仍然出現皮膚毒性反應的原因。

表1 人口統計與臨床數據匯總表
3 抗PD1/PD-L1免疫治療誘發的引起大皰性類天皰瘡的診斷
由于缺乏特異的血清學標記物和實驗室檢查指標,目前關于PD-1/PD-L1所致BP暫無特殊的診斷方法,在既往文獻報道中,主要還是依據病史詢問和特發性的BP診斷標準。病史詢問中要注意抗PD-1/PD-L1藥物的服藥史、藥物使用與皮疹嚴重程度間的相關性以及藥物誘導期可能數月甚至更長。其診斷需要結合臨床特征、組織病理、直接免疫熒光(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DIF)、特異性皰病抗體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和間接免疫熒光(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IIF)。(1)臨床表現:在非大皰期,出現瘙癢、紅斑或蕁麻疹斑片、斑塊,還可能觀察到濕疹樣環形、靶形紅斑、結節,之后在外觀正常或紅斑基底上出現緊張水皰、大皰,尼氏征陰性,口腔、生殖器黏膜損害輕或無。(2)組織病理:新鮮水皰取材可見表皮下水皰,水皰中含有纖維蛋白網、嗜酸粒細胞和/或中性粒細胞,并伴有主要由嗜酸粒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在真皮淺層浸潤。在非大皰期,組織病理學檢查結果可能是非特異性的,可能僅觀察到表皮下裂和嗜酸性海綿樣增生。(3)DIF:新鮮水皰周圍1 cm內正常皮膚或紅斑處取材,基底膜帶IgG和/或C3線狀沉積,少數患者有IgA、IgE線狀沉積。(4)IIF:以正常人皮膚冰凍切片為底物,患者血清中存在識別基底膜帶的IgG自身抗體,呈線狀分布。鹽裂IIF以正常人皮膚為底物,1 mol/L氯化鈉溶液作用后表皮和真皮分離,IgG抗體呈線狀結合在表皮側。(5)特異性抗體檢測:ELISA檢測到血清中抗BP180和/或BP230 IgG抗體水平升高,抗體水平多與疾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
在既往的回顧性研究中,組織病理學分析顯示71%-81%的病例有表皮下水皰,82%~85%有嗜酸粒細胞浸潤。DIF有71%~79%的病例IgG沉積和71%~95%的C3沉積呈陽性[4,6,13],IIF陽性率為60%~83%。血清免疫學中,BP180和BP230抗體滴度分別在61%~83%和13%~50%的病例中升高[5,13,18]。
4 抗PD1/PD-L1免疫治療誘發的大皰性類天皰瘡的治療
在已發表的病例報告中,局部、系統使用糖皮質激素已成為抗PD-1/PD-L1 相關BP短期水皰控制的主要治療方法。對于輕中度BP患者,每天使用強效外用糖皮質激素(丙酸氯倍他索乳膏)40 g 或每天10~30g的劑量已被證明與全身性潑尼松龍同樣有效,對于重度BP患者,需用系統性糖皮質激素治療(潑尼松 0.5 mg/kg·d)治療[19]。另有美國癌癥協會推薦當皮疹面積在10%~30%時即可外用強效激素聯合系統激素治療(0.5~1 mg/kg劑量的強的松),皮疹面積>30%時,系統使用潑尼松龍(或等效物)1~2 mg/kg·d進行治療[20]。然而,一項針對成人BP的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多西環素在短期(6周)水皰控制方面不劣于口服潑尼松龍,并且在52周時對嚴重、危及生命和致命事件的安全性顯著提高[21]。在Lopez等發表的病例報告分析中,5例使用多西環素治療BP,其中1例僅使用多西環素聯合煙酰胺治療BP,大皰可消退[11]。綜上,對于短期控制可選擇局部、系統類固醇,若要長期維持治療,可以優先考慮四環素類藥物,皮疹少于30%的皮疹初始可使用高效的局部類固醇和多西環素聯合或不聯合煙酰胺治療[4]。對于糖皮質激素難治性抗PD-1/PD-L1相關BP,建議使用利妥昔單抗,由于其對致病性B細胞的靶向抑制,該藥物應優于T細胞消耗性免疫抑制劑(硫唑嘌呤、嗎替麥考酚酯)[22]。另外,奧馬珠單抗、度普利尤單抗也被成功用于治療抗PD-1/PD-L1 相關BP[23,24],在糖皮質激素難治、糖皮質激素副作用強烈或嗜酸細胞、IgE升高的患者中可考慮使用上述藥物。
在既往病例報道中,是否需要停用抗PD1/PD-L1藥物取決于BP的嚴重程度,若依據常見不良事件評價標準(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等級≥2,患者皮損面積大于10%體表面積時暫停使用抗PD1/PD-L1藥物[25],治療后視皮疹改善情況逐步恢復原免疫治療藥物。如果水皰覆蓋體表面積 >30% 并伴有相關的體液或電解質異常,則應永久停用PD-1抑制劑[20]。
5 小結
由于抗PD1/PD-L1免疫治療后引起大皰性類天皰瘡具有延遲性,有的患者皮疹不典型,因此抗PD1/PD-L1免疫治療后出現皮疹應及時轉診皮膚科,進行診斷評估和適當的治療,以防止BP進一步惡化后免疫治療的長期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