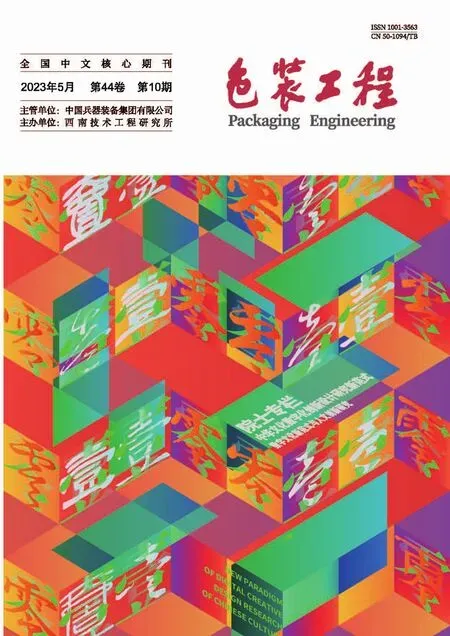建構中國漢字設計史理論體系
陳楠
【特別策劃】
建構中國漢字設計史理論體系
陳楠
(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
立足設計學的研究視野,從傳播學、美學等跨學科視角,梳理兼具信息傳播與藝術審美雙重功能的漢字文化發展歷程,旨在建立新的漢字設計史觀,將漢字從純粹的美術學或文字學中獨立出來,形成相對獨立的設計研究體系,為漢字設計教育與設計實踐提供更為系統完整的理論依據與學術支撐。采用文獻調研法、對比研究法、實證研究法等多學科研究方法,厘清漢字設計相關學術概念,梳理漢字形態與呈現載體的演變以及漢字文化與國計民生的邏輯關聯,全面、系統地考察漢字發展中的設計問題。將漢字形態與設計形式的歷史演變作為橫向發展軸線,挖掘其中潛藏的文化脈絡;將漢字設計思維、依托技術載體、實踐應用作為縱向發展軸線,探索漢字發展中內在邏輯要素間的關系。首先鮮明地提出“中國漢字設計史”的學術概念,其次從橫向與縱向梳理漢字設計史的主體結構,在設計學的視角下建構史論體系,最后將漢字設計智慧與方法運用于藝術設計教學與具體的設計實踐之中。以“漢字設計史觀”發掘漢字中蘊涵的中國傳統文化深厚的設計智慧與文化內涵,提升其在藝術設計教育與設計實踐領域的文化價值,拓展漢字設計的理論研究空間和實踐創作場域,為構建中國漢字設計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及話語體系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撐。
漢字;漢字設計;設計史;設計學;設計教育
2021年筆者撰寫的《中國漢字設計史》一書正式出版發行,2023年在清華大學率先開設了同名公共通識選修課,也是該課程在國內首次開設。從理論研究、教學實踐兩個層面初步建構起了中國漢字設計史的研究體系。本文即是在此基礎上撰寫的,目的是解決以下問題:
1)厘清、明確與中國漢字設計史相關的學術概念、定義,并對邏輯脈絡系統進行梳理,進一步明確如何從設計學的視角對漢字文化進行深入研究。
2)對中國漢字設計史龐雜的歷史資料所講述的重點內容與研究方法進行強調與提煉,形成較為清晰的知識結構與理論框架。
3)強化了相關論述觀點:(1)面對不同維度的漢字設計形式,明確漢字設計史的發展進程絕非單一的正體字主線,進而挖掘多條并行發展的線索,采用不同的設計評價標準和態度,避免用正體字的字形標準討論創意字體設計的問題;(2)一直存在的對設計功能與裝飾美學的爭論是影響當下藝術設計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命題,什么是設計、設計功能是否包括技術功能與心理功能等,漢字設計的歷史涉及大量具有此類問題的案例分析;(3)進一步強化科技發展對漢字設計的影響與促進,從19世紀中葉英國工藝美術運動以來,就凸顯了科技進步對設計形式的深刻影響,面對這種影響設計師群體存在積極迎合與反思抵制兩種不同的態度,中國漢字設計史也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提供了可參考的歷史事件案例與設計批評的依據。
4)強化了對中國漢字設計史宏觀思維結構體系的理解,通過直觀可視化的論述,使受眾免于陷入對具體設計案例形式的糾纏,可以在更加宏觀的視角清晰地看到設計的發展流變。
5)近年來,涌現了眾多從創意形式到視覺表現都非常優秀的漢字設計作品,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顧漢字各種書體構型原理與文化傳承隨意扭曲變形、連筆斷筆、增筆減筆的現象,以及違背文字學基本規律、基本原理的各種問題。中國漢字設計史為此提供了漢字設計發展的文化邏輯和學術脈絡的必要參照。
1 對“中國漢字設計史”相關學術概念的梳理
對于“中國漢字設計史”學術概念的確立,有必要按照相關概念的邏輯進行必要的梳理,作為本文論述觀點的概念基礎。
1.1 西方文化語境的“設計”概念
設計(Design)源自拉丁文“de-sinare”,意為“記號、徽章”[1]。從構詞法看“design”是復合詞,即由前綴“de”和詞根“sign”兩部分構成,前者含有“向內、向下的實施、計劃、制作等動詞性語義,后者則具有符號、記號、標記、方案、構思等更為廣闊的含義。”1824年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團的《柯林斯英語詞典》按詞性對其進行了解讀:作為動詞,當制定一項調查、政策或制度時,所做的計劃和準備。作為不可數名詞而言,是指規劃和繪制某物詳細圖紙的過程和藝術,以及被計劃和制造的方式。作為可數名詞而言,可以指為了展示、建造或制作某物而繪制的圖紙,也可以指用來裝飾某物的線條或形狀的圖案,還可以指在做事之前腦海里的總體計劃或意圖[2]。1857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字典》指出:設計源自16世紀意大利語"designare",具備更有指向性的“以草圖的方式表達藝術家心中的創作意圖”,也就是通過線條等手段將隱藏在藝術家心中的構思、想象等以圖形的方式現實化。由法語單詞"désigner"加強而來,意為“指定”。主要包括:一是指對某物的不同部分的總體安排,如建筑物、書籍、機器等;二是指通過繪制計劃、制作計算機模型等來決定事物外觀、工作方式的藝術或過程;三是指可以用來制作某物的圖紙或計劃——作為裝飾的線條和形狀的排列;四是指計劃或意圖[3]。18世紀末,英國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三版)將“Design”限定在藝術范疇之內并定義為:藝術作品平面、立體、結構、輪廓的線條、形狀在比例、動態以及審美方面的協調[4]。直到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催生了“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現代設計”概念的產生,設計的概念才打破了美術、藝術的限定而具備更為寬廣的含義,材料的性能、加工方法等都被納入考量之中[5],逐漸形成了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現代設計體系”。20世紀中葉可持續發展戰略進入人們的視野,生態設計、綠色設計進一步拓展了設計的邊界。21世紀以來數字媒體、人工智能(AI)重塑了設計的定義,正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在《人工科學》中認為的“凡是以現存情形改變成向往情形為目標而構想行動方案的人都在搞設計[6]”一樣,“設計”一詞具有了更廣闊的文化屬性。
綜上,從設計詞匯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專業的事實來看,它確實是在工業革命現代機器生產推動下誕生的近現代社會的新事物,這也就使人們形成了“設計”一詞只屬于現代社會的刻板印象。但事實與之相反,設計活動、設計思想始終隨著人類造物史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設計法則、設計體系和設計文化。
1.2 中國傳統文化語境的“設計”流變
“設計”在我國始見于《說文解字》:“設,施陳也,從言從殳;殳,使人也。”“計,會也,筭(算)也,從言從十[7]。”意為:陳列、布置、安排、計算等。191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中關于“設”“計”的釋義和《說文解字》基本相同,二者皆有“使人、計謀、陳設”等意思[8]。在1928年出版的《辭海》中解釋為:設計是指“根據一定要求,對某項工作預先制定圖樣、方案,如服裝設計、廠房設計”。這里的“設計”更傾向于“Project”,并非由藝術設計獨享,特別是指工程類的方案、計劃,即通過一定的物質手段制造具有實用價值的物品的計劃與構想。但也有另一個解釋是:“造型藝術術語,意為廣義的一切造型活動的構思計劃、實施方案[9]。”在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中既有廣義的含義——“在做某項工作之前預先制定的方案”,也有狹義的含義——“記號、徽章,或根據一定要求對某項工作預先制定圖樣”[10]。這種廣義的設計蘊含著人類活動的文明成果,具有“泛概念”的特征。
雖然對“設計”一詞的近現代梳理具有當下語境的時代含義,但這種設計行為也可以通過許多其他詞匯加以表述。《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11]。以“器”表達“開物”的設計內涵。《孫子兵法·謀攻篇》“欲攻敵,必先謀”,“謀”開始具備了謀劃、規劃,設下“計謀”或“圈套”的意思。繼而設計的內涵向“計謀”“圈套”“裝飾”“營造、經營”“工藝美術”“圖案”[12]等領域進行延展,具有某種“泛設計”的概念。《詩經·大雅·靈臺》的“經始靈臺,經之營之[13]”進一步明確了建筑和繪畫中“意匠”“經營”的含義和地位。“裝飾”源自《后漢書·逸民傳·梁鴻》:“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意為打扮、修飾、裝潢、點綴、裝點、裝飾品等[14],既是造物設計的手段,也是美化器物的方法,是中國古代造物的重要內容。南齊謝赫[15]在《古畫品錄》中提出“經營·位置是也”;北宋郭熙[16]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將設計的地位提升到造物過程的首要位置。而后元代的《蜀錦譜》、明代的《髹飾錄》《天工開物》、清代的《小山畫譜》等著作將“經營”推廣到更加廣闊的應用領域。1920年蔡元培先生在《美術的起源》中提出:狹義的美術專指建筑、造像(雕刻)、圖畫與工藝美術(包裝飾品)。而廣義的美術還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等[17]。“圖案”是20世紀30年代由陳之佛、李叔同等從日本引入的。陳之佛在1937年出版的《圖案構成法》中認為:“圖案”是日本人的譯意,并在中國普遍使用。同時,諸葛鎧在《裂變中的傳承》中認為:“漢語中的動詞‘設計’大約與‘圖案’同時出現[18]。”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圖案”在龐薰琹、雷圭元、張仃等前輩的努力下,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了圖案的系統化、本土化,促使了中國圖案學的誕生,培養了一批批設計人才,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工藝美術設計事業。此后,“工藝美術”的內涵和范疇逐漸縮小,成為“手工藝”或“特種手工藝”“工藝品的美術加工”的同義詞[19];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設計構成”(德語為Gestaltung,形態)從日本經中國香港引入內地,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設計的發展主線[5]。
綜上,不難發現中國“設計”及“設計思想”歷史悠久、內涵豐富,蘊含著中華民族的設計智慧和文脈基因,“工”“藝”“工藝美術”“造物”“計謀”“經營”“意匠”“圖案”“裝飾”都具有某些“設計”的特征。一些外來詞匯甚至因為不同時期的不同翻譯,漸漸形成了超越各自本身的概念含義。因此,研究中國傳統設計問題不能被這些不同時代不同翻譯的詞匯所累,將設計行為相對統一的概念認知作為研究中國漢字設計史的歷史觀依據,需要在滿足目標和約束的前提下,全面考慮美學、功能、經濟及社會政治因素與特定環境下的設計形態的相互作用,進而展開設計和研究。
1.3 設計史與中國設計史
設計史是設計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正如前文所述,盡管設計行為從人類文明早期便已經產生,但作為專業概念詞匯的“設計”卻是在近代工業革命背景下創造出來的,設計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喬治·瓦薩里(Giorgio Vasari)、約翰·溫克爾曼(Johan Joachin Winkelmann)以及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藝術史基礎上的,雖然藝術與設計同根同源,但16世紀瓦薩里將藝術納入歷史研究范疇的時候,設計就并未納入藝術的考察范圍,導致與設計有關的手工藝未能進入藝術史研究的序列中,即使英國美術史協會主席尼古拉斯·佩夫斯納(Antoine peusner)的《社會美術史》《現代運動的先驅》以及《塘鵝美術史叢書》中以符號學的方法討論神話并利用設計的方式進行傳播,那也僅僅算是對設計史研究的前期探索,20世紀50年代的工藝史還是處于被忽略的歷史地位[20]。直到戈特弗里德·桑佩爾(Gottfried Semper)強調工藝的重要作用和威廉·莫里斯將“工藝”與藝術提到同樣的位置上,才揭開了現代設計史的研究序幕[21]。1977年英國成立設計史協會(Design History Association)以后,設計史才從裝飾藝術史和應用美術史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學科門類[22]。
國際上關于設計史研究模式與方法也在不斷演變,傳統的西方設計史在書寫體例上以編年體和人物史為主,以喬納森·伍德姆(Jonathan Woodham)的《20世紀的設計》為代表,推動了西方設計史的研究,主要關注日常生活、社會關系、經濟消費中的設計問題[23],維克多·馬格林2015年出版的《世界設計史》則進一步將設計史的研究視角放大至更寬廣的范疇[24]。現代設計史研究從英國設計師協會成立至今只有四十余年,關于設計史大量的學術概念和設計問題還尚待進一步解決。
20世紀70年代現代設計概念進入中國后,國內開始了設計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藝美術史、裝飾藝術史等,雖然針對中國古代“設計”是否納入設計史的研究范疇在學術界存在不同意見,但也出現了廣義設計史觀的學術成果,如李立新的《中國設計藝術史論》、胡光華的《中國設計史》、高豐的《中國設計史》等。
1.4 漢字設計與中國漢字設計史
漢字不僅是記錄漢語言的書寫符號,也是記錄與傳播中華文明重要的載體之一,其本身也是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漢字設計的內涵可以依據設計的概念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是指運用設計思維圍繞文字形式、創意方法以及實用功能開展的對文字大小、筆畫結構、排列、裝飾、賦色等方面的字體設計。而廣義是指依據漢字發展的規律,考慮和形成更合理的漢字形態,綜合考量漢字設計發展中的科技因素,厘清其與漢字發展的互為關系,挖掘其中蘊含的漢字設計思維與方法,并結合少數民族漢字文化圈、東亞漢字文化圈傳播中的漢字設計文化等相關問題開展的綜合設計及研究。目前漢字研究的學科體系包含:漢字學概論、傳統文字學、漢字語言學研究、現代漢字研究、漢字文化學與漢字美學等。其中漢字美學以書法、篆刻、美術字為研究對象,研究漢字及漢字使用中的美學規律,一般局限于具體漢字的字體分類、設計方法的講解,這為漢字設計實踐及研究提供了更為寬闊的場域。
中國漢字設計史是指系統研究漢字設計的歷史,在這一命題中強化“中國”的定語,目的是立足學科特色和時代背景,深入理解和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探索新的研究視角,建構漢字設計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首先,從學術概念上擺脫“現代設計”對漢字設計行為、設計思想等的局限和限制,立足于中國設計文化視野,將“裝飾”“營造”“經營”“工藝美術”“圖案”等概念蘊含的設計文化納入漢字設計的研究范疇,以宏大的歷史文化觀審視漢字發展歷程的設計現象、設計本質和設計規律。其次是以廣義的漢字設計為指導,將漢字發展歷程中形態演變的政治因素、科技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其設計思維與方法、文化傳播與設計等納入漢字設計史的整體研究,更加全面、宏觀地建構中國漢字設計史的研究體系。
1.5 中國漢字設計史的結構體系
中國傳統史書的編寫體例有通史、斷代史、編年體、紀傳體、國別體等類型,其中通史、斷代史與編年體都是按照一條總的時間線索對歷史資料加以編輯的,而紀傳體和國別體則是根據并行的多個單位概念自身的時間進程編輯相關歷史事件的。近代中國開始使用的章節體是引入西方史觀與體式的產物。西方史論較為普遍的體例是史料編輯與理論分析相結合,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整理敘述,以比較個人的史料處理方法,用偏文學與哲理思辨的手法處理歷史材料,體現作者獨立的思考與學術立場。笛卡爾在方法論中首次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指出研究問題的原則之一就是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要盡量避免魯莽和偏見,只要沒有經過自己切身體會的問題,無論是什么權威的結論都可以懷疑[25]。1902年,梁啟超首創了章節體的學術史新體裁,其主要特點是按所要論述的問題性質分章立節,并且與史論結合,用論述敘述史料,用史料證明論述。著名經學大師劉師培1905年發表的學術史研究論文《周末學術史序》是中國學術史上首次運用現代學科分類法[25]。在此啟發下,“中國漢字設計史”的理論體系采用的是章節體與傳統體裁相結合的綜合性體例,不在一條貫穿始終的時間軸上組織漢字設計的歷史資料,而是分為不同的問題概念單位,在每一個單位內部再依時間線索組織歷史資料。既關注漢字設計的形式美學、表現語言,又重視漢字設計的實用功能,基本包括四個主要部分:(1)其中字形的發展被分為正體、快寫、注音、裝飾四條并行的主線并加以敘述闡釋;(2)科技的發展也是影響漢字設計進程的關鍵因素,探討在不同歷史階段漢字如何與工具材料、呈現載體、傳播方式等相適應,從而煥發新的設計活力;(3)從文化傳播的視角梳理不同歷史時期受漢字影響的少數民族文字書體,并將研究場域擴大到東亞漢字文化圈,發現漢字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價值為漢字設計創新提供了靈感與啟發;(4)研究潛藏于漢字設計形式背后的思維與方法,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厚的設計智慧。
漢字設計史理論研究力求從漢字的起源、演變脈絡、材料工具、實用方法、編排組版、代表人物、裝飾處理以及字體創意七個切入點,多維度、全方位地去講述漢字的設計發展,梳理了正、草、音、飾四條發展主線,歸納了影響漢字設計發展的因素,深入探索漢字在不同文化圈中傳播和發展的基本狀況和內在規律,研究不同歷史階段科技發展對漢字文化發展的影響,挖掘不同角度文化傳承的設計思維與方法,分析當下漢字設計所處的形勢,使大眾更加清晰、全面地了解中國漢字設計發展史,突出了研究理論的體系性以及對經典文本的設計闡釋,著力于探索研究型的漢字設計之路。
2 漢字設計四條并行的發展線索
2.1 第一條主線——標準化、規范化的正體字
漢字設計的標準化與規范化被視為第一條主線。這一主線描述了歷代官方推廣使用的標準“正體字”字形的演變過程,見圖1。作為記錄歷史的載體,文字是傳遞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治理和對外交流的重要工具,代表著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形象。漢字形態結構的演變不僅是漢字匠人的智慧,還反映了管理者的美學與功能需求。在文獻記載中,倉頡、沮誦、史籀等人以及后來的李斯、蔡邕等重臣都推動了漢字字形設計的發展。
甲骨文和金文是了解漢字起源的兩個重要坐標。相對于手刻的甲骨文,鑄刻的金文更加精細、完整且更具圖畫感、裝飾性。據此可知,金文更接近官方標準字體。族徽與銘文的儀式感和紀念性也說明了金文比甲骨文更具完整性、裝飾性和設計感。青銅器的鑄造是一個較為精細的工藝過程,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可以更好地還原文字筆畫的弧線轉角等細節。工藝與技術的進步使金文具有了圓潤的弧線,因為是通過鑄造模具制作文字,所以基本上都采用等寬的線條、等距和豎式的編排形式。這種秩序與甲骨文有許多相似之處。現存最早的具有秩序規劃的編排設計案例是西周的散氏盤,見圖2。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方便國家政令通達和事務管理,通過統一文字實現了“書同文”,對大篆進行簡化后,規范設計的小篆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通行全國的標準字體。漢代以后,從隸書發展而來的楷書成為官方文書碑刻的標準字體。而“篆體”被神圣化,主要在璽印、碑額以及書籍封面標題中出現。在推行統一的小篆的同時,嬴政又采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因縑帛、竹簡的使用和紙張的產生,漢字書寫形式和方式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隸書在漢代逐漸成為官方的主要用字。楷書又名“真書”,是楷模文字、真正文字、標準書體的意思。至唐代,這種規范漢字標準書體的書寫水準發展到巔峰。宋徽宗趙佶將畫意入字創立了新的楷書書體——瘦金體,書寫過程富有節奏感,字體金鉤銀劃,而且大開大合,筆跡瘦勁至瘦而不失其肉,風姿綽約。這是楷書字體設計中重要的案例,對后世字體設計的創新具有啟發性。明太祖推崇書法致帖學大盛,在科舉取士中皆用楷書答題。橫平豎直,整整齊齊,寫得像木版印刷體一樣,稱為“臺閣體”。《明史》曰:“度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清代稱為“館閣體”,這是一種因科舉制度而生,廣泛應用于官場的專用字體,非常具有正統性。可見,楷書就是漢晉至唐代碑刻、文書中的正體字標準形,后來宋刻本中的楷體、明代的宋體、近代的仿宋體和黑體都是楷體的變化,它們至今仍是正體字的主流字體。

圖1 正體字設計的發展歷程

圖2 西周散氏盤的文字編排設計
2.2 第二條主線——漢字簡化、草化的快速書寫形式
漢字簡化、草化的快速書寫方式,一直以來都是與規范標準字體并行發展的[25]。在甲骨文、金文時代,大篆時期的簡牘字體和古隸體是為快速書寫而生的字體。秦代的統一文字“小篆”并未在具體日常書寫中廣泛使用,而隸書則成了當時的主要辦公日常書體。隸書是通俗、簡便、快捷的寫法,隨著不斷的規范化、標準化設計,逐漸形成一種正式書體,甚至曾被稱為“楷書”。然而,人們對書寫便利、快速的需求從未停止。隸書成為通用的正體之后,一方面向著更加標準的楷書進化,另一方面,人們也不斷追求草書變化的創新。草書并不是楷書的快速書寫,它是在篆書、隸書和楷書平行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書體。草書的字形屬于漢字三大形態中的流線體,筆畫流暢連貫,許多筆畫有多種特殊寫法,包括對正體的簡化、替代,以及應用異體字和俗體字[25]。漢代官方也對草書制定了標準化的字形規范,以解決民間漢字因簡化草寫帶來的字形架構混亂的問題,這種規范化的草書體被稱為“章草”,意為有章法可循的標準化草書[25]。這種情況在西文書體中也存在,例如拉丁字母的大小寫最初也是因正體與手寫體的差異而產生的。漢字在傳遞信息的層面上一直追求簡化和便捷性,因此從隸書到隸草再到草書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書體所應具有的規范性標準。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草書漸漸走向純藝術表現的方向,產生并積累了大量新的漢字藝術化表現形式。然而,與楷書不同的是,草書并沒有像楷書一樣向著進一步規范化的方向發展,究其原因是快速書寫的實用功能和將其字形筆畫加以規范、標準化的問題并未得到重視[25]。
近代的章草大家于右任曾力推“標準草書”,但未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來自歷史,漢代章草規范后的近兩千年間,許多著名書法家創作的作品成為書法學習的范本,在這些作品中有許多字體寫法不準確或者存在書寫者的個人主觀發揮。雖然這些與最初的字法存在差異,但已經成為歷史的經典。層出不窮的學習者使之成為約定俗成的形式,這也不能簡單地歸為錯誤的寫法。另一方面,對草書標準化問題的認識在藝術與實用層面存在差異。從實用書寫的角度看,需要標準的字形寫法,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嚴格的標準化會限制藝術個性的發揮和風格的推陳出新。
本文所述漢字四條主線之一的“草”并不僅僅指狹義的書法概念的“草書”,而是涵蓋了漢字發展歷史中各種以快速書寫為目的所形成的字體設計形式,甚至包括漢字速記符號等,見圖3。這是在漢字文化發展脈絡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線索,草寫的漢字有著連貫的歷史傳承。一方面,既有的形式法則、審美表達、書寫規矩應該得以傳承,并活化運用于今天的字體設計與漢字創意設計之中;另一方面,在這條主線中蘊含的設計思維、東方美學也值得進一步挖掘與整理。

圖3 漢字草化設計的發展歷程
2.3 第三條主線——漢字的注音設計
本文第三條主線探討的是漢字的注音設計,見圖4。漢字是一種同音字較多的語言,因此需要關注音的設計應用來解決同音字混淆的問題。尤其是在學習漢字的初級階段、對外漢語交流以及漢語言教學中,漢字的注音設計都對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格外重要。在漢字的六書中,“形聲”部分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在注音設計中不應將漢字的注音與其意義和形象徹底割離。早期的注音方式是一個漢字為另一個漢字注音,且包括音調標注等。同時,在音樂譜也采用漢字作為注音符號,或從漢字的筆畫中提取并加以設計,如工尺譜、古琴譜等。
漢字的注音設計方法也影響了朝鮮諺文、日本假名的設計,以及我國少數民族文字和地方文字中許多注音符號的設計形式[25]。明清之際,東西方文化交流增強,西方傳教士總結了使用西文字母進行漢字注音的方法,如利瑪竇所著的《西文奇跡》、法國人金尼閣所著的《西儒耳目資》,以及近代英國人威妥瑪設計的威妥瑪拼音等。民國時期的注音符號和1958年推廣的漢語拼音至今被廣泛使用,除了漢字作為裝飾元素應用于生活器物的設計和字體設計上之外,漢字注音設計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25]。在計算機互聯網信息時代,智能輸入法也創造性地完成了漢字注音與計算機的融合。
2.4 第四條主線——賦予裝飾設計功能的漢字


圖4 漢字注音設計的發展歷程

圖5 漢字裝飾設計的發展歷程
無論是古代,還是在近現代的政治、軍事、商業生活中,漢字都是標志符號設計中重要的設計元素,在品牌標志、刊頭字體、宣傳標題等設計領域,漢字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25],歷史的積累形成漢字裝飾藝術設計的豐富成果。清末民初書籍裝幀、宣傳媒體中的美術字設計、裝飾字體設計,受到西文裝飾字體與日本美術字等外來形式的影響[26],同時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漢字藝術審美的方法與形式,魯迅設計了數十種書刊的刊頭字體和藏書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學校徽與《奔流》《吶喊》的封面字體等,追求樸素無華、雅致古樸的設計風格。陳之佛在《圖案》的設計中,將文字和圖案融為一體,進行整體設計;在《東方雜志》《中國美術會季刊》的設計中,通過底紋突出雜志或書籍的文字主題,以高度平面化、裝飾化的形式傳達出“東方精神”。張光宇對《三日畫報》《上海漫畫》《時代》等進行了刊頭字體設計。豐子愷設計的《民國課本》,融合了西方元素,簡潔明快,生動活潑。新中國成立后,余秉楠設計的“友誼體”字體設計與“海峽兩岸一家親”海報設計等覆蓋了政治、商業、文化等領域。石漢瑞(Henry Steiner)設計的《香港希爾頓酒店CI》《Jade Creations公司標志設計》等,創新地將毛筆書法體與英文相結合,凸顯了“中西融合”的設計意識[26]。徐學成主持設計的“黑二體”《印刷新字體展評會樣本》為改變印刷字體筆形、字形的混亂狀態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眾多漢字設計作品豐富了漢字藝術設計的內容,延續了這條重要的漢字設計線索。
漢字充分展現了其象形、會意、表音、信息傳播與文化傳播多重功能的特點。“飾”是漢字設計四條并行發展線索中最具藝術表現力,且最貼近人民生活的一條,同時也是字體字庫設計開發、廣告文案、創意設計乃至視覺識別系統設計等方面取之不盡的靈感與素材寶庫。
3 科技發展對漢字設計的巨大影響
在漢字書法的演變歷程中,除了書寫者的性格和修養等因素之外,書寫工具和材料的改變對漢字演進也有著重要的貢獻。在幾千年的時間里,漢字的工具、材料和載體從刻刀、甲骨、青銅、竹木、石材逐漸發展為多種分類系統的筆、顏料、紙張等,最終形成了現在通過屏幕觸控就能獲得的各種漢字書寫方式[25]。科技的發展不斷影響著漢字的表現形式,漢字也見證并記錄了科技的進步,見圖6。
人類的書寫工具在科技的推動下不斷創新,根據這種變化,人們也創造出一個個新的書體和設計范式。漢字的生命力在適應使用和傳播的同時,通過新的字體形態促進了書寫工具和載體等相關技術的改良和創新[27]。例如商人在卜筮時將經過整治的龜甲或獸骨放在火上灼烤,根據裂縫的形態決定吉兇,漢字就因這種鑿刻與涂抹朱砂的方式而成為甲骨文字;冶煉技術的發展和青銅鑄造水平的提高造就了金文字的圓潤、規范、優美;毛筆在簡牘和縑帛上的書寫,使人們手部的控制更個性化,也更流暢,提按力度的變化增強了漢字的表現力。同時,紙張的發明和普及使漢字書寫更加自由揮灑,成為真正的藝術,印刷術的發明也極大地改變了以往手寫漢字的筆畫風格和排列順序,橫平豎直的宋體便是楷書適應雕版印刷的產物。近代金屬活字印刷的發展使漢字的規范性、共性、體量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25]。當漢字面臨20世紀下半葉計算機革命和個人電腦輸入的巨大挑戰時,新技術如代碼輸入法和激光照排也順應時代而出現,輕松解決了這一難題。

圖6 漢字設計中的科學技術
自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和社交媒體的繁榮,漢字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不論是新增的符號表情還是動態字體的設計開發都能夠完全適應并融合于現代社會中[25]。隨著科技進步不同階段的變化,工具從古代的手工處理、近代的機械化處理,到當代的自動化、智能化電腦處理,必然會影響漢字字形的設計和藝術表現風格。這種影響催生了與社會審美相匹配、風格迥異的藝術形態和設計美學。因此,通過科技史的研究視角全面充分地考察、梳理和探討漢字在不同歷史階段科技變革和社會審美影響下產生的適應性和創新性發展,不僅僅是“漢字的科技史”或“漢字的美學史”,而是通過“漢字的歷史”去理解中國“文化史”[25]。這為基于情感與靈感的跨越語言文字學、設計學、傳播學的新字體設計概念——“字文化設計”奠定了良好的學理基礎,并為新一輪科技巨變,尤其是Chat GPT、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軟件介入漢字設計領域,提供了更多參考與啟示。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推動下,漢字一定會繼續適應并生發出新的表現形式。每次技術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形成某種文化傳統和審美范式,漢字適應每一次技術革命的設計進化中也都不斷添加著文化的新語言,而非一成不變的。這種變化所依存的脈絡是連綿不斷的,這或許正是漢字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25]。
4 漢字傳播與推廣設計
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傳播載體,數千年來在我國各地和相鄰地區廣泛傳播,體現了文化之間的密切交流,對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少數民族和國家地區直接使用漢字或根據本民族社會文化及語言的特點,在漢字的基礎上設計了新的文字。這些設計方法包括假借漢字和自造新字,其中自造新字又包括借用漢字筆畫的整體性自造字、借用單個漢字的改造變異字,以及借用漢字偏旁部首重組的仿造字。因此,漢字文化圈的共性與差異主要探討少數民族文字與亞洲部分國家地區的漢字型民族文字,了解其在創造與使用過程中的設計現象、設計規律,以及蘊含其中的設計思維和藝術設計表現語言[25],見圖7。

圖7 漢字與民族文字的關系
4.1 少數民族文化圈的文字與藝術創新設計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了回族和滿族通用漢語外,其中29個少數民族使用了54種文字。這些文字的種類數量大于民族數量的原因是有一些民族使用了多種文字,例如傣族有4種文字,景頗族有2種文字。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民族大遷徙和大融合,建立了由各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許多統治者采取漢化政策,通過學習中原文化實現長久統治。其中,許多少數民族在學習漢族文化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文字體系,例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還有一些創造了與當時民族宗教信仰緊密相連的文字,例如納西族的東巴文、水族的水書等。由于各種歷史原因,許多文字已被廢棄不再使用。而女書等一些地方方言注音字母,則是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是漢語漢字變異發展的一種產物,不是某個少數民族專有的文字[25]。
通過少數民族文字創新設計,可以厘清這些文字與不同歷史時期漢字之間的淵源關系以及進化發展的變化與衍生,從而建立起一個宏觀的漢字設計知識體系;通過理解這些文字創立和使用背后的文化聯系,可以研究不同文化間的影響和傳播軌跡;一些少數民族根據漢字創造的文字體系中蘊含了字形、注音等多種設計方法,這些對當下的漢字藝術設計創作來說具有借鑒和啟發價值;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老文字體系,雖然許多已經失去了實用價值,但是在促進國家多民族團結繁榮、推動地域性文化傳播等方面仍然會成為重要的設計符號載體[25]。
4.2 東亞文化圈的文字與藝術創新設計
數千年來,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亞洲乃至世界,作為文化承載符號的漢字成為許多與中國毗鄰國家和地區的應用文字。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和越南在歷史上都曾使用漢字,其中有一些到今天仍在使用;漢語、漢字在新加坡分別被稱為“華語”“華文”,至今仍是官方語言和文字之一,漢字長期作為官方文字和用于文化交流的國際文字存在。漢字文化圈的各國在使用漢字的過程中也漸漸發展出適用于本地語言特點并更有利于普及推廣的注音、符號或表音文字[25],如日本語的假名和朝鮮語的諺文。日本、越南等國還能根據漢字的造字原理創造出許多新漢字。一些漢字設計的風格、方法甚至反向傳播回中國,形成更加密切的溝通與交融。由于歷史原因,晚清至今一百多年間,中國內地(大陸)及中國香港、澳門、臺灣這三個地區的漢字進化歷程也不是同步發展的。一方面是因為漢字簡化運動導致的繁簡之別;另一方面,由于發展的不同步,許多繁體字形也有不少差異,許多不同時代的字形、異體字被不同的地區選用,所以即使使用的是繁體漢字,也會存在不一樣的現象。歷史上,朝鮮半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有本民族語言而無本民族文字,漢字傳入朝鮮半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朝鮮半島出土的大量中國戰國時期的古錢幣可以證明,最遲在那一時期(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漢字就隨貿易往來從陸路傳入朝鮮半島的北部地區。漢字長期是古代朝鮮的官方文字,公元7世紀,朝鮮人開始用漢字音義來標記朝鮮語,史稱“吏讀”。在借鑒了其他民族文字的經驗并受佛教表音文字的啟發后,1443 年,朝鮮的世宗大王召集眾多學者創制了字母方案,刊印《訓民正音》一書,又稱“諺文”[25]。由于向中國學習,朝鮮半島歷史上很早就有書法藝術,稱為“書藝”。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的漢字書法藝術逐漸減少,出現了用漢字書法筆法書寫韓文的新趨勢。韓文的字體設計最早依據的也是漢字的不同書體以及美術字設計方法,但隨著現代設計的發展,也出現了如著名設計師安尚秀獨創的“安體”那樣具有突破性的優秀作品,這是一套具有現代設計精神,突破了漢字方塊字思維限定的新韓文字體。這種突破對中國漢字設計的傳承與創新來說同樣具有啟發意義[25]。目前,漢字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各種設計精美的漢字牌匾、旗幟隨處可見,在商業開發中使用漢字的品牌標志和廣告也比比皆是。此外,書道藝術非常普及,并存在許多涉及漢字的儀式和活動。由于對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視以及漢字使用的廣泛深入,日本的漢字藝術與設計非常發達。無論是字體創意設計的應用還是應用字庫的設計都值得我們學習。在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漢字設計也有許多成功的探索成果。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使漢字更廣泛地應用于現代設計之中。拉丁字母與漢字結合的設計形式也在商業設計之中出現,并且在改革開放以來對漢字設計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5 漢字設計的思維與方法論
本文所定義的“漢字設計”是一個綜合概念,包括狹義的漢字字體設計、漢字裝飾、圖形創意設計與廣義的漢字設計思維與文化推廣設計等。由于現代設計的許多概念與研究方法都基于西方傳統哲學與科學體系,所以中國古代的許多設計問題并未以設計的視角加以詮釋而被歸入藝術或工藝美術范疇,但漢字作為重要的文化傳播符號,其自身不僅蘊含著豐富的美的形態要素,更隱藏著大量有待發掘的創意設計思維與方法,需要通過社會背景、人文環境去一窺“設計”形式背后的奧秘。因此,有關漢字發展史設計思維、藝術美學和設計方法論的挖掘與分析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能幫助設計師構建更加合理、科學的漢字文化體系,為漢字設計的創新提供有思維深度的支撐和依據,也可以提煉出在更廣闊的設計領域運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設計方法論。
漢字設計思維與方法的研究對象包括:漢字檢字法、輸入法中的模件思維、漢字拆字法中的模件思維、漢字筆順與閱讀順序中的設計問題、漢字設計與網格、“帖學”與“碑學”之爭折射的漢字藝術美學范式、漢字書寫筆跡中的設計問題、甲骨文書法與字文化設計等[25],見圖8。

圖8 漢字設計中的設計思維
6 結語
通過厘清漢字演變與文化發展、科技變革、思維更新的內在邏輯脈絡,立足設計學、傳播學和美學的宏觀視角,建立了獨特的漢字設計史觀。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漢字設計史”學術概念新表述,將漢字在“設計學”的維度下形成相對獨立的史論研究體系,對推動學術界“設計史觀”下的漢字設計研討、研究,指導相關設計實踐具有重要意義[27]。主要歸納了三個方面的貢獻和意義:首先,本文提供了漢字字體形態設計本身發展的理論依據。可以發現,現代印刷術與計算機輸入字體的形式法則、美學風格無不源于傳統文字形態,歷史中漢字隨著科技進步進行了設計、調整應變,還應對了計算機進入設計領域所產生的劇烈沖擊,漢字通過五筆輸入法、拼音輸入法以及各類設計軟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回顧歷史,分析研究在不同時代的科技革命、社會進步到來之時,漢字都相應地產生了哪些新形式、新方法,如何使之適應這種新的變化,進而梳理漢字特殊的文化地位與不間斷的生命力之間的深層關系,剖析科技進步、審美變遷與漢字設計演進的內在邏輯,找尋傳統到現代轉型中漢字設計清晰的發展脈絡。這將為當代設計在面對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時如何實現漢字設計的突破與創新提供了參考。其次,本文為漢字適應新的傳播方式并開展國際化傳播提供了借鑒依據。作為擁有記錄語言、信息傳播與文化象征符號多重身份的漢字,在漢字文化圈的社會生活中也有著廣泛的設計應用,如公共空間導視、海報招貼、報刊書籍、生活用品以及醫療藥物等,在社會生活與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中漢字無處不在。一方面通過分析中國少數民族文字與漢字相關的創造使用過程中的現象、規律、原理及思維方式,指出漢字是各民族漢字型文字的母體,也可以反過來賦予當代漢字設計精神與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對東亞漢字文化圈各國、地區漢字文化的特點以及傳播脈絡的梳理,整理這些學習、改造、發展漢字的設計資料,為漢字設計在新時代中漢字及漢字文化的國際化傳播與創新提供借鑒。再次,漢字設計史中的設計思維與方法論對當代藝術設計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是以漢字設計傳承與創新的發展脈絡為線索,挖掘潛藏于漢字藝術審美和信息傳播功能背后的設計思維與方法,為探索研究型的漢字設計實踐與創新之路提供了指導依據。二是這些植根中華民族文化深處凝練而成的設計思維與方法同樣適用于更廣泛的現代建筑、服裝和產品等設計領域,具有實際的指導價值。最后,盡管學術界主要集中在漢字發展史、構形史、傳播史、美學史、書法史和美術史等方面的研究,設計、工藝美術和圖案設計等概念仍存在爭議,但這些研究結果對構建、豐富和完善中國漢字研究的學術體系、敘事體系和話語體系來說具有支撐意義。
因此,需要從“設計學”的研究視角出發,以鮮明的設計歷史觀來厘清漢字設計史相關概念。通過研究分析古代漢字相關的創作活動,全面研究漢字設計發展的影響因素、互為關系以及潛藏其中的設計思維和方法的“全貌”,建構相對完整、全面、立體的中國漢字設計理論體系和研究體系。這是助力新時代漢字研究學術體系、敘事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路徑,能更好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1] 李硯祖. 藝術設計概論[M]. 武漢: 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9.LI Yan-zu. Introduction to Art Design[M].Wuhan: Hubei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2] WHITEHEAD R.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M].New York: Collins, 2003.
[3] TRENZI R C, FURNIVAL F J.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COLIN M, ANDREW B. Encyclopedia Britannica[M]. Edinburgh: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5] 陳楠. 連接基礎與專業的橋梁:綜合設計基礎課程教學探索[J]. 裝飾, 2022(8): 118-123.CHEN Nan. Connection between Fundamental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Design Foundation Courses[J]. Art & Design, 2022(8): 118-123.
[6] SIMON H A.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
[7] 湯可敬. 說文解字今釋[M]. 長沙: 岳麓書社, 1997.TANG Ke-jing. Shuo Wen Jie Zi Jin Shi[M]. Changsha: Yuelu Press, 1997.
[8] 陸費逵, 歐陽溥存. 中華大字典[M].上海: 中華書局, 1915. LU Fei-kui, OUYANG Pu-cun. Chinese Dictionary[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15.
[9] 陸費逵, 徐元誥, 舒新城. 辭海[M]. 上海: 中華書局, 1936. LU Fei-kui, XU Yuan-gao, SHU Xin-cheng. Ci Hai[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6.
[10] 魏建功. 新華字典[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4.WEI Jian-gong. Xinhua Dictionary[M].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54.
[11] 余秋雨. 余之詩[M]. 北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YU Qiu-yu. My Poems[M].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21.
[12] 李硯祖. 設計的智慧——中國古代設計思想史論綱[J].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 2008(4): 27-32, 80, 161.LI Yan-zu. Wisdom of Design—Outline of Ancient Chinese Design Thought History[J]. Journal of Nanjing Arts Institute (Fine Arts & Design), 2008(4): 27-32, 80, 161.
[13] 王秀梅. 詩經[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WANG Xiu-mei. The Book of Song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14] 張光宇. 裝飾諸問題(二)[J]. 裝飾, 2008(S1): 26-28.ZHANG Guang-yu. Decoration Problems (Ⅱ)[J]. Art & Design, 2008(S1): 26-28.
[15] 謝赫. 古畫品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XIE He. Record of Ancient Painting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16] 周遠斌. 林泉高致[M].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10.ZHOU Yuan-bin. Lin Quanguo Zhi[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17] 陳池瑜. 藝術學理論學科的定位與問題[J]. 藝術教育, 2020(8): 16-21. CHEN Chi-yu. Orient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oretical Discipline of Art[J]. Art Education, 2020(8): 16-21.
[18] 杜明星. 中國“設計”詞語源流考[J]. 裝飾, 2022(8): 72-75.DU Ming-x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Origination of Chinese Design[J]. Art & Design, 2022(8): 72-75.
[19] 李軼南. 新中國設計藝術七十年回眸[J]. 包裝工程, 2020, 41(24): 53-61.LI Yi-nan. Review of 70-Years Design 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4): 53-61.
[20] PEVSNER N. 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M]. London: Faber & Faber, 1936.
[21] 溫克爾曼.論古代藝術[M]. 邵大箴, 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WINKELMANN. On Ancient Art[M]. SHAO Da-zhen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2] CLARK H, BRODY D. The Current State of Design History[J].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2009, 22(4): 303-308.
[23] SPARKE P. A century of design: design pioneers of the 20th century[M]. Hauppauge, N.Y.: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1998.
[24] VICTOR M. World History of Design: Two-Volume set[M].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25] 陳楠. 中國漢字設計史[M]. 武漢: 湖北美術出版社, 2021.CHEN Nan.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M]. Wuhan: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21.
[26] 周博. 中國現代文字設計圖史[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ZHOU Bo. The 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ypogra-ph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27] 周志. 漢字研究的設計思維與歷史思維——評《中國漢字設計史》[J]. 裝飾, 2021(11): 86-89.ZHOU Zhi. Design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Research: Review of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J]. Art & Design, 2021(11): 86-89.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History
CHEN Na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bo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artistic aesthetic func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vision of design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aesthetics, etc., so as to establish a novel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and separate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pure art or typography, thus forming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sign research system, and providing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with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ademic suppor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academic concepts related to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ere clarifi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and presentation carriers were combed, the logical context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and national livelihoods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design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examine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manner.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design style was used as the horizontal axis of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hidden cultural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logical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explor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hinking, supporting technical carrier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s the vertical axis.Firstly, the concept of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as distinctly proposed. Secondly,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as sorted out from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atitudes.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then the accumulated wisdom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were applied to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and concrete design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design wisdom and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nhance the cultural value in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and design practice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pace and practical creation field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design history; design; design education
TB472
A
1001-3563(2023)10-0012-12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0.002
2023–01–22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項目(G1912)
陳楠(1972—),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視覺傳達設計。
責任編輯:馬夢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