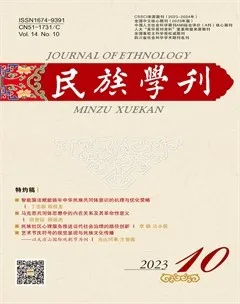對分離主義道德論證的批判
雷勇 楊和英
[摘要] ?分離主義道德論證主要有三條路徑,一是將民族國家的內涵曲解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該觀點混淆了民族國家的本質和國家的民族構成,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具有明顯的政治理想主義色彩。二是濫用民族自決權,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該觀點將作為民族自決權主體的(國家)民族(nation)誤讀為(文化)民族(nationality),邏輯上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對民族自決權的權利內涵理解存在偏差,國際法上的民族自決權并不包含民族分離權;忽視了行使民族自決權的具體條件,只有在一個國家出現殖民統治需要去殖民化時才能適用。三是利用民主政治說事,認為分離是一種民主權利,利用公民投票等民主形式推動分離。民主政治實施的前提是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及公民對其的認同。但是,無論是“分離權”主張,還是利用民主形式推動分離,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解構,在邏輯上難以自洽;在強調一部分人利益的時候,卻忽略了其他人的利益,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初衷和平等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極大的現實危害性,影響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影響民族關系,極易誘發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沖突,影響國際秩序穩定。
[關鍵詞] ?分離主義;民族國家;民族自決權;民主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9391(2023)10-0130-07
作者簡介:雷勇(1981-), ?男,四川閬中人,四川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學; ?楊和英(1981-), ?女, ?苗族,貴州黃平人,中共貴州省委黨校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學。
分離主義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它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而且存在于發達國家;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分離主義既威脅所在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又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分離主義道德論證,是指從應然層面論證分離主義的合理性、正當性,為分離行為提供道德辯護和理論支撐。分離主義道德論證通常有三條途徑,一是把民族國家的內涵釋義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認為一個民族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二是利用民族自決權為自己的行為正名,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三是利用民主政治說事,認為分離是一種民主權利,提出所謂的“分離權”,借助于公民投票等形式推進分離。對于上述三種路徑的分離主義道德論證,張友國、王英津、江玲寶等討論了民族自決權與民族分離權的關系,尤其是對民族自決權的主體進行了澄清。 ?[1][2][3] 王英津、李捷、郭雷慶等對“分離權”進行了批判,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和現實危害。 ?[4][5][6] 已有研究有利于我們深化對分離主義道德論證核心觀點及其危害的認識,但總體來看,仍不夠系統,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中國是深受分離主義困擾的國家,從理論上深入批判分離主義道德論證的謬誤,不僅有利于構建反分離主義的中國話語體系,而且有利于為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實現各民族共同發展,尤其是反對民族分離主義,維護國家統一提供指導。
一、對曲解民族國家內涵進行道德論證的批判
分離主義道德論證的路徑之一是把民族國家解讀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認為每一個(文化)民族都有權建立屬于自己的國家。例如,戴維·米勒(David Miller)指出,“民族主義在本質上要求每個民族組成一個主權國家。” ?[7]397 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也堅持類似的觀點。那么,什么是民族國家?其內涵是什么?民族國家能否等同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它是否符合人類政治發展的現實情況?
首先,該觀點混淆了民族國家的本質和國家的民族構成。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國家的演變經歷了古代的城邦國家—中世紀的普世國家—王朝國家—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關于民族國家的內涵,百度百科是這樣理解的,“民族國家是指歐洲近代以來,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或民族獨立運動建立起來的,以一個或幾個民族為國民主體的國家。”《布萊克維爾政治制度百科全書》認為,民族國家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和原則的融合,一種是政治的和領土的,另一種是歷史的和文化的。‘國家這一要素在此是指現代理性國家,它形成于西方現代初期,是一種自立于其他制度之外的、獨特的集權的社會制度,并且在已經界定和得到承認的領土內擁有強制和獲取的壟斷權力。民族,可以界定為一種名義上的人類共同體;它有著一個共同的祖先、歷史傳統和劃一的大眾文化,據有一塊領土,所有成員都有勞動分工和法定權利,其中包括種族文化[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因素和現代‘公民特征。民族的概念所具有的二重性和模糊性影響著它隨后與國家的融合。民族的公民要素和領土要素越明顯,其融合過程便越為容易。反之,民族概念中種族要素越突出,國家與民族間融合和合一的可能性便越小。……絕大多數所謂的民族國家是一種多民族的混合體,將它們稱為國家民族可能更為貼切。”寧騷在分析民族國家的特征時指出:“構成民族國家的本質內容的,是國家的統一性和國民文化的同質性,是國民對主權國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認同。凡是已經具有或正在具有這一本質內容的現代國家,不管其民族結構如何——相對單一的民族國家機構自不待言,比較復雜的和十分復雜的民族結構也是一樣,都屬于民族國家。” ?[8]269 寧騷認為,民族國家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完全自主和領土統一,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二是中央集權制;三是主權人民化;四是國民文化的同質性。周平認為,“民族國家的核心內涵就是國族。民族國家之所以稱為‘民族國家,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國族,并且與之互為條件和相互依存。國族是由民族國家創造的,沒有民族國家就無所謂國族。但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國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內涵的形成、制度優勢的發揮,都依托于國族。沒有一個強健的國族,民族國家就無法發揮其制度功能,只能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虛設。民族國家構建了國族,國族又承載著民族國家的制度結構,從根本上支撐著民族國家。” ?[9]227 由此可見,周平認為,民族國家的核心內涵和本質特征是國族,即國家民族。從現代國家的民族構成看,可分為單一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單一民族國家是指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實際上是重疊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屬于多民族國家,即多個(文化)民族同處于一個政治屋頂之下。不同民族的民族認同和其國家認同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把民族國家等同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實際上混淆了民族國家的本質和民族國家的民族構成。
其次,該觀點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同歷史時期民族主義的表現形態不一樣,發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由此導致人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不同。例如,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應該是一致的。” ?[10]1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 ?[11]9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和蓋爾納相同,他指出,“我所謂的‘民族主義是采用蓋爾納的定義,亦即‘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是全等的。” ?[12]9 戴維·米勒認為,民族主義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為思考世界的一種方法,它強調民族在解釋歷史發展和分析當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且明確宣稱‘民族特征是人類劃分的主導性因素。習慣上,民族主義主張所有的人都應屬于一個并且只屬于一個民族,它是他們身份和忠誠的主要焦點。這就是說,人們在作為任何比較狹隘或者比較寬泛,或者是相互交叉的組織的成員時,都首先應把自己看成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應該準備好為保衛和發展民族利益做出任何必要的犧牲,不管同其他利益相比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1] 但是,各種理解也有共同的方面,各種民族主義都強調本民族的利益,都是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思想和行為。正如上文指出的,現代國家絕大多數是多民族國家,真正的單一民族國家可謂鳳毛麟角。多個民族共處于一個統一的政治屋頂下是民族國家的普遍狀態。各民族盡管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各個民族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實現共同發展。不同民族在長期的交流、交往、交融過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雜居、混居現象。因此,把民族國家曲解為“一族一國”是一種典型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它過分強調了民族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并將其絕對化,忽略了各民族之間的共性,把建立國家作為維護民族利益的唯一手段,實際上協調民族關系既可以通過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還可以通過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等實現。
再次,該觀點具有明顯的政治理想主義色彩。現代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多民族國家,只有極個別國家是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朝鮮、韓國等。追求“一族一國”的政治目標,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特點,缺乏可操作性。因為,就一個國家的民族分布情況而言,不僅存在民族“聚居”的情況,而且更多的屬于民族“混居”的情況。在此種情況下,追求“一族一國”的政治目標明顯缺乏可操作性,而且極易引發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嚴重時甚至爆發民族清洗。對此,正如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所指出的,“同質的民族國家被揭示為一個幻想,而且,可以預期,關于自由的理念與民族的理念可以在一個政治框架內充分協調的幻覺是注定要失敗的。雖然許多民族運動仍然保持著這個夢想,但是當今的現實卻表明:力圖使這個夢想成真的嘗試必將導致流血沖突。” ?[13]149
二、對濫用民族自決權進行道德論證的批判
分離主義道德論證的又一重要路徑是利用民族自決權為其正名,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例如,西方學者安東尼奧·卡塞斯(Antonio Cassese)就將分離納入自決的范疇,認為自決可以為分離提供正當性。 ?[14]101-140 實際上,民族自決權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其權利的行使有嚴格的條件,有著明確的權利主體和具體內涵,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是對民族自決權的誤讀和濫用。
從民族自決權形成的歷史脈絡看,其形成和發展與近代宗教改革、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美國獨立戰爭等密切相關。法國大革命期間,民族自決權作為一種政治口號被法國資產階級正式提出。法國資產階級積極倡導“平等”“自由”“博愛”“人權”等政治價值,頒布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提出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口號,以此反對封建專制的王權和羅馬教皇的神權。為了反對歐洲其他國家對法國大革命的干涉,1793年法國憲法宣布:法國人民不干涉別國政治,也不容許別國干涉法國政治。這充分體現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和精神。19世紀,民族自決權作為一項政治原則,有力地推動了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20世紀,民族自決權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得到了迅速發展。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全面闡述了民族自決權,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列寧指出,“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合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 ?[15]228 不僅如此,列寧還主張各民族之間的自由合并,反對違背民族意愿的合并。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也積極倡導自決權原則。1917年,威爾遜指出,“任何國家都不應將自己的政策強加給別的國家和人民”。 ?[16]218 二戰之后,隨著自決運動即去殖民化運動的深入開展,自決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自決原則被寫入《聯合國憲章》,并逐漸發展為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之后,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迅猛發展、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以及國際社會民主化的推進,自決權被寫入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隨著20世紀70年代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生效,民族自決權作為國際法的法律原則和集體人權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分離主義利用民族自決權的論證,其錯誤有三:一是對民族自決權的主體理解有誤;二是對民族自決權的權利內涵理解有誤;三是忽視了民族自決權行使的條件。
第一,分離主義將民族自決權主體的(國家)民族(nation)誤讀為(文化)民族(nationality),犯了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首先,從法律文件的規定來看,聯合國大會的相關決議都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如,195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于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的決議》明確指出:“聯合國會員國應擁護各國人民和各民族自決的原則;聯合國會員國應承認并提倡行使各該國管理下非自治領土及托管領土各民族之自決權”。 ?[17]1346 1960年第15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又指出:“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17]1348 又如,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個人權公約也都明確規定“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17]965、972 因此,自決權的主體應該是“任何一國的全體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
其次,從作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集體人權來看,民族自決權的主體也應為主權國家的全體人民,或政治民族。既然民族自決權已經成為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那么,它就應該是貫穿國際法各個領域的規則,也應該是國際法的基礎,否則,就難以成為基本原則。再者,民族自決權已發展成為國際法上的集體人權。從人權的意義上講,也只有將民族自決權的主體理解為“任何一國的全體人民”,它才稱得上是集體人權。因為,人權是普遍性的權利,是每一個人都擁有或應當擁有的權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擁有,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一部分人擁有的權利是特權。
因此,如果我們將自決權的主體理解為“人民”,那么這里的“人民”應該是指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全體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如果我們將其理解為“民族”,那么這里的“民族”應該是政治民族或者國家民族,而非文化民族。英文中,政治民族或國家民族用“nation”表示,如中華民族、法蘭西民族、美利堅民族等使用的民族就是“nation”意義上的民族;文化民族用“nationality”或“ethnic group”表示,如漢族、回族、蒙古族等使用的民族就是“nationality”或“ethnic group”意義上的民族。但是在英語中意義存在較大差異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在翻譯成中文時都用“民族”的概念。這既給理解民族自決權的主體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同時也給分離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民族自決權的主體和民族分離主義的主體雖然同為“民族”, ?其實二者在含義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前者是指政治民族(nation),后者指文化民族(nationality)。
第二,分離主義在民族自決權的內涵的理解上存在偏差,錯誤地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民族自決權雖然作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但是,人們在民族自決權的內涵的理解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異。一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民族自決權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國際法是雙方斗爭、妥協的結果,所以,國際法上并沒有對民族自決權含義的明確界定;二是自決權的含義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演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自決權的含義也呈現出一定的變化。
從《聯合國憲章》《關于人民與民族自決權的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際法原則宣言》等國際法律文件對民族自決權的規定來看,民族自決權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涵:
一是政治自決權。即在殖民體系瓦解之前,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有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的權利。這里“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是指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有權“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或與其他獨立國家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只要選擇是該民族人民自由意志的表達即可。
二是經濟、社會和文化自決權。即殖民地國家或被壓迫民族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后其全體人民在不受外來干擾的情況下追求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權利。政治上的獨立為去殖民化提供了重要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去殖民化運動的結束。第三世界國家只有在經濟上擺脫對殖民國家的依賴,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獨立。
政治自決權是民族自決權的核心內容,政治自決權的行使是去殖民化運動的開始,它為經濟、社會、文化自決權的行使提供重要的政治前提,沒有政治上的獨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獨立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經濟、社會、文化自決權是對政治自決權的進一步延伸,它是去殖民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為實現國家或民族的真正獨立提供經濟、社會、文化條件,鞏固行使政治自決權的成果。
認為民族自決權包含民族分離權實際上是對民族自決權內涵的誤讀。首先,民族自決權是國際法上的集體人權,而國際法是調整主權國家之間關系的法律,不涉及主權國家內部的事情。如果賦予主權國家里的不同民族(nationality)分離的權利,就違背了國際法的“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由此可見,民族自決權并不包含分離權的內容。其次,聯合國1960年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和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對于理解“民族自決權是否包含民族分離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兩個文件都對防止民族分離主義對民族自決權的濫用做出了專門規定,《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第六條明文規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17]1348 《國際法原則宣言》進一步明確指出:“民族自決權”原則,“不得解釋為授權或鼓勵采取任何行動,局部或全部破壞或損害在行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及自決權原則并因之具有代表領土內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之全體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獨立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 ?[18]8 由此可見,國際法上的自決權是專門針對殖民地國家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去殖民化運動的,并非針對主權國家里的民族(nationality)試圖從該國分離的行為。
第三,民族自決權的行使有具體條件的限制,只有在一個國家出現殖民統治進而需要去殖民化時才能適用,它表現為殖民地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擺脫西方殖民國家的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雖然民族自決權的主體是任何一國的全體人民,但擁有權利并不意味著一定要行使權利,也不意味著行使權利不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 ?[19]94-96 從現實的政治實踐來看,只有殖民地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行使過自決權。任何脫離反對實行異族壓迫和統治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體系的前提,試圖瓦解現有國家建立單一族裔國家的分離主義運動,從未獲得國際法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20] 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民族自決權的行使條件,借民族自決權之名,行分離主義之實。對此,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明確提出,民族自決權“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采取任何行動去全面或局部地支解或侵犯獨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 ?[21]371
總之,理解民族自決權理論及其實踐,必須聯系其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語境,尤其是結合現實的政治實踐來理解,明確其權利主體、權利內涵及其適用條件,而不能簡單地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對其進行寬泛的解讀甚至誤讀。
三、對利用民主政治進行道德論證的批判
當今世界,民主成為各國普遍追求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分離主義也常常利用民主說事,為自己的行為正名。一些學者基于“民主”“人權”“平等”“公平”“正義”等政治價值提出所謂的“分離權”,主張分離權也是一種民主權利;例如,哈維·貝蘭(Harry Beran)指出,依據個人自治權利,個人可以聯合組成國家。因此,依據個人自治權利,也應該允許國家的一部分從國家中分離出去。 ?[22] 大衛·高蒂爾(David Gauthier)從政治聯合權的視角出發闡述了分離權。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政治聯合的權利,但政治聯合權需要在雙方都愿意的情況下才能行使,一個人不能強迫不愿與自己聯合的人聯合,所以,通過政治聯合組成的國家,其維系直接取決于要求分離的一方。 ?[23] 此外,分離主義力量還常常利用公民投票等民主形式推動分離。例如,1980年和1995年加拿大的魁北克公投及2014年英國的蘇格蘭公投等。利用民主政治論證分離的正當性具有極大的迷惑性,極易獲得人們情感上的支持,但實際上是民主政治的異化,不僅理論上存在難以自洽的邏輯矛盾,而且實踐上也具有極大的危害性。
第一,“分離權”主張和利用公民投票推動分離在邏輯上難以自洽。民主權利的行使和民主政治的實施通常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范圍內進行的,其邏輯前提是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及公民對其的認同。離開公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民主政治就無從談起。對此,英國學者凱諾文(Margaret Canovan)曾經指出,“在這個意義上,民主預設了某些社會排斥的原則,其運作的先決條件是存在一個封閉的政治共同體,即一個擁有清晰地理邊界的、穩定的人民群體。民主制度越復雜,厘定成員標準就必須越仔細。” ?[24]17 這里的政治共同體通常表現為國家。“民主是現代國家的一種治理形式。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民主。” ?[25]17 國家的存在是民主政治實施的重要條件。因此,一國的公民行使民主權利,參與民主政治,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認同,包括領土范圍、人口數量、主權、政府、政治制度等,因為,公民資格的獲得是行使民主權利,參與民主政治的前提。然而,無論是“分離權”主張,還是利用公民投票等民主形式推動分離,都意味著對國家的領土范圍、人口、主權、政府等進行重構,都成為了國家的解構性力量,在邏輯上難以自洽。
第二,“分離權”主張和利用公民投票推動分離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初衷和平等原則。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民主的本意是要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權利,既要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又要體現少數人的利益。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盡管在地理位置、風土人情、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國家的形成是不同地區、不同民族長期交往、相互學習、共同奮斗的結果,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利益上具有互補性和共同性,而且不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變遷中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居現象。“分離權”主張和利用公民投票推動分離在強調欲分離地區人民利益的同時,卻忽略了欲分離地區之外的人民的利益;而且,即使是在欲分離地區,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分離。如果多數人選擇分離,就會損害少數人的利益,產生“多數人的暴政”;反之,少數人選擇分離,就會損害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分離權”主張和利用公民投票推動分離在強調一部分人利益的時候,卻忽略了其他人的利益,違背了民主政治的本意和平等原則。
第三,“分離權”主張和利用公民投票推動分離具有極大的現實危害性。首先,影響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如果分離成為一種民主權利,動輒利用公民投票等民主形式進行分離,地方政府可以以此為條件跟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向中央政府尋求更多的利益支持和政策保障,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影響央地關系的規范化,國家的發展將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面臨被分裂的危險,影響政治穩定。同時,不確定性的增加將導致政府在道路、機場、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投資變得更加謹慎,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將被投入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安全,進而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影響民族關系,誘發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沖突。現代國家絕大多數是多民族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居”現象是民族分布的常態。如果分離被視為一種民主權利,動輒利用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推動分離,將直接影響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如各民族在資源分配、政治權力配置、政治權利、文化權益等方面存在分歧甚至矛盾,極易激化民族矛盾,嚴重時甚至爆發民族沖突、民族仇殺、種族清洗。對此,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曾經指出,“蓄意謀殺的種族清洗是民主時代的一大危險,因為在多種族狀態下,民治理想開始使得demos與占支配地位的ethnos交織在一起,產生了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這樣的有機觀念,它們鼓勵對少數民族施行清洗的行為。” ?[26]4-5 再次,影響國際秩序穩定。如果分離被確立為一種民主權利,通過公民投票進行分離具有合法性,那么,很多國家的分離主義勢力將借此推動分離,不僅會引起現有國家領土范圍的變更,出現許多“袖珍”國家,而且容易引發領土范圍、財富分配、債權債務分割等方面的矛盾,嚴重時會引發地區沖突。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通過民主方式進行分離具有合法性,將為某些西方國家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分離主義勢力,干涉他國內政,遏制其發展提供了口實,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通過上述的分析不難看出,無論是通過曲解民族國家的內涵,還是通過濫用民族自決權以及利用民主政治對分離主義進行道德論證,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具有極大的現實危害性。對此,我們必須保持理論警醒。當然,分離主義的產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又有經濟、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分離主義的治理,既需要我們從理論的角度對分離主義道德論證展開批判,又需要我們從經濟、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著手,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形成分離主義治理的合力。
參考文獻:
[1]張友國.民族自決:民族分離主義的誤讀[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1):71-76.
[2]王英津.自決權:并非分離主義的擋箭牌[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4):24-29.
[3]江玲寶.“國族”而非“族群”——試論民族自決權的適用主體[J].世界民族,2012(06):1-6.
[4]王英津.有關“分離權”問題的法理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12):19-37.
[5]李捷.對基于自由民主角度的分裂權利理論的簡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12):38-58.
[6]郭雷慶.對西方“分離權”理論的批判[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05):168-176.
[7][英]戴維·米勒,鄧正來.布萊克維爾政治思想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8]寧騷.民族與國家——民族關系與民族政策的國際比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9]周平.多民族國家的族際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10][英]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M].韓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1][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M].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M].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以色列]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M].陶東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Antonio Casses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Reappraisal[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5]列寧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17]董云虎,劉武萍.世界人權約法總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8]王鐵崖,田如萱.國際法資料選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9]王英津.自決權理論與公民投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20]王建娥.民族分離主義的解讀與治理——多民族國家化解民族矛盾、解決分離困窘的一個思路[J].民族研究,2010(02):13-25.
[21]楊侯第.世界民族約法總覽[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
[22]Harry Beran. A Liberal Theory of Secession[J]. Political Studies,1984,Vol.32,No.1:23-26,28.
[23]David Gauthier. Breaking Up: An Essay on Secession[J].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4(03):357-371.
[24]Margaret Canovan.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M]. Cheltenham, UK ;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ress, 1996.
[25][美]胡安·J.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歐洲[M].孫龍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6][英]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M].嚴春松,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收稿日期:2023-04-28 ???責任編輯:丁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