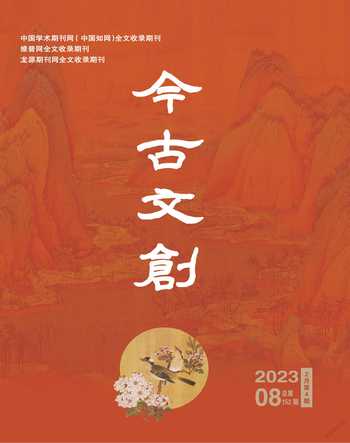《文心雕龍 · 聲律》 “ 雙聲 ”“ 迭韻 ” 研究
楊榆峨
【摘要】 《聲律》一篇在整部《文心雕龍》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劉勰于其所提倡的聲律理論對(duì)當(dāng)時(shí)以及后世詩(shī)歌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而“雙聲”“迭韻”是《聲律》的重點(diǎn)論述內(nèi)容,后人對(duì)其的注釋各有側(cè)重點(diǎn),其中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中有關(guān)“雙聲”“迭韻”相關(guān)部分的注釋值得深入探討研究。文章中出現(xiàn)的“雙聲”“迭韻”的情況時(shí),他們之間或許需要“隔字”和“雜句”來(lái)處理,而不是相反的舉措。對(duì)此的研究有助于進(jìn)一步推導(dǎo)、接近劉勰《聲律》的本意,從而總結(jié)出劉勰的聲律學(xué)觀點(diǎn),同時(shí)觀察他對(duì)以沈約為代表的永明聲律學(xué)的態(tài)度。
【關(guān)鍵詞】 雙聲;迭韻;平仄;聲律
【中圖分類號(hào)】I207?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3)08-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15
《聲律》篇在整部《文心雕龍》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它是齊梁聲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xiàn)存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六朝聲律文獻(xiàn),無(wú)論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還是后世的詩(shī)歌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其中“雙聲”“迭韻”主要源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迭。雙聲隔字而每舛,迭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fā)而斷,飛則聲飏不還,并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忤其際會(huì),則往蹇來(lái)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①一句。今人大家對(duì)其的注釋相差無(wú)幾,他們大體以為“雙聲”“迭韻”中間不能加字,即“隔字”“雜句”,這樣讀起來(lái)會(huì)不順,如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jiān)洝贰埍劐K先生的《文心雕龍全譯》、王運(yùn)熙先生《文心雕龍譯注》、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注》以及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先生注釋此句太過(guò)簡(jiǎn)略,并且參考了范文瀾先生的注本,而范文瀾先生的注本影響深遠(yuǎn),注釋也比較全面,故本文嘗試在后者注釋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
一、“雙聲隔字而每舛”或“雙聲隔字,而每舛”
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對(duì)此句的注釋:“雙聲隔字而每舛,即八病中傍紐病也。《文鏡秘府論·五》引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內(nèi),有隔字雙聲也。’又引劉滔云‘重字之有“關(guān)關(guān)”,疊韻之有“窈窕”,雙聲之有“參差”,并興于《風(fēng)》《詩(shī)》矣。’王玄謨問(wèn)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云:‘“懸瓠”為雙聲,“碻磝”為疊韻。’時(shí)人稱其辯捷。如曹植詩(shī)云:‘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即‘居’‘佳’‘殊’‘城’是雙聲之病也。凡安雙聲,唯不得隔字,若‘踟躕’‘躑躅’‘蕭瑟’‘流連’之輩,兩字一處,于理即通,不在病限。’” ②
首先明確的是“踟躕”“躑躅”“蕭瑟”“流連”以及“參差”此類的雙聲例舉,他們本身是連綿詞,有且只有一個(gè)語(yǔ)素,合起來(lái)表達(dá)的是一個(gè)概念,這是必然不可分割的,并不存在所謂的隔不隔字。而“居”“佳”和“殊”“城”,各組字具備自己的相同聲紐,每組字是兩個(gè)語(yǔ)素的存在,才有“隔字”的可能性。另外《文鏡秘府論》明確,所謂的傍紐就是一韻之內(nèi)出現(xiàn)雙聲字,如一句中有“月”字,就不能出現(xiàn)“魚(yú)”“元”“阮”“愿”等字。而《文心雕龍》則明確“雙聲”字之間不可有字相隔,也就是說(shuō)如果是不間隔而接連的“雙聲”字組合,那是可以允許的。而這現(xiàn)象的存在明顯犯了傍紐,即只要一句之中出現(xiàn)“雙聲”現(xiàn)象,必然犯傍紐,無(wú)所謂隔不隔字。
“舛”,《說(shuō)文解字》注釋:“對(duì)臥也。從夂相背 。” ③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云:“謂人與人相對(duì)而休也……相背,猶相對(duì)也。” ④因此“雙聲隔字而每舛”可以有兩種斷句翻譯法,一“而”作承接,即“雙聲隔字而每舛“,那么暫且翻譯為“雙聲一旦中間隔字,那么就會(huì)使文章抒發(fā)表達(dá)背離音樂(lè)節(jié)奏感,讀起來(lái)不順。”或者“而”作轉(zhuǎn)折,即“雙聲隔字,而每舛”,姑且翻譯作“雙聲應(yīng)當(dāng)隔字,但是往往與此法相背離。”
再返回曹植詩(shī)“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以此為例。暫不考慮其感情藝術(shù)價(jià)值,只觀察其格式。按照唐中后期詩(shī)歌格律方法分析(不考慮八病說(shuō)),那么此句的平仄應(yīng)為“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其正格應(yīng)當(dāng)為“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第一、六、八字不在節(jié)奏點(diǎn)上,可以暫不考慮其平仄。有矛盾的只有第九個(gè)字“百”,它的平仄有問(wèn)題,與第七字“麗”同屬仄聲。或者也可以將后一句“平仄平仄平”視為“平仄仄平平”的變格,那么“殊百城”,即“平仄平”的關(guān)系是可以說(shuō)的通的。從后世規(guī)范化的格律模式來(lái)看,“殊”“城”的音樂(lè)節(jié)奏并沒(méi)有因?yàn)橹虚g隔“百”字而被破壞。若是將其視為后者變格,那它的平仄關(guān)系亦可自圓其說(shuō)。“居”“佳”這組同聲字在詩(shī)句中比較特殊,他們?cè)谝髟仌r(shí),之間會(huì)有語(yǔ)氣的自然而然地停頓,所以“居”“佳”到底算不算隔字,比較曖昧,故不做討論。總之“居”“佳”,“殊”“城”每組同聲字的平仄相同的,比起“平仄平”,“平平”確實(shí)節(jié)奏變化不是那么強(qiáng)烈。
至于“平仄平仄平”這一格式,在唐代詩(shī)文格律規(guī)則明晰,且被作家承認(rèn)、運(yùn)用創(chuàng)作之前,它比較常見(jiàn),且并不被認(rèn)作是有問(wèn)題的。例如《古詩(shī)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fēng),越鳥(niǎo)巢南枝”,它的平仄關(guān)系為: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平,其出句符合。曹植《卻東西門(mén)行》:“狐死歸首丘,故鄉(xiāng)安可忘”,它的平仄關(guān)系為:平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出句符合。可見(jiàn)魏晉南北朝時(shí),“平仄平仄平”這一格式在時(shí)人看來(lái)是正常不過(guò)的表達(dá),不以為病。這與古代漢語(yǔ)不同時(shí)期的發(fā)展表現(xiàn)離不開(kāi)關(guān)系,畢竟上古漢語(yǔ)主要是以單音節(jié)詞為主,直到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交流表達(dá)的日益復(fù)雜,復(fù)音詞才大量增加。因此稍后唐代平仄關(guān)系主要通過(guò)兩個(gè)音節(jié)為一組來(lái)體現(xiàn),而漢魏六朝時(shí)單音節(jié)詞仍是時(shí)人主要的表達(dá)形式,所以以單音節(jié)為音樂(lè)節(jié)奏點(diǎn)變化平仄關(guān)系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世唐人效仿六朝詩(shī)人作古體詩(shī),此類也較為常見(jiàn),比如劉昚虛《尋東溪還湖中作》“云峰勞前意,湖水成遠(yuǎn)心”,平仄關(guān)系為:平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其對(duì)句符合。王維《贈(zèng)劉藍(lán)田》“晚田始家食,馀布成我衣”,平仄關(guān)系: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對(duì)句符合。沈佺期《臨高臺(tái)》“回首思舊鄉(xiāng),云山亂心曲”,平仄關(guān)系: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仄,出句符合。劉長(zhǎng)卿《自鄱陽(yáng)還道中寄褚征君》“元?dú)膺B洞庭,夕陽(yáng)落波上”,平仄關(guān)系為: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出句符合。以及王昌齡《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溪留贈(zèng)》“乘月期角巾,飯僧嵩陽(yáng)寺”,平仄關(guān)系: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出句符合。在唐人眼里,此一形式是頗有古風(fēng)意蘊(yùn)的,所以唐人傳作古體詩(shī),常常故意創(chuàng)作這一類詩(shī)句,以此向魏晉古詩(shī)靠攏,彰顯古樸復(fù)古意蘊(yùn)。值得一提的是它常常用來(lái)做出句,作對(duì)句的情況比較少見(jiàn)。總之“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的平仄關(guān)系在劉勰時(shí)期是正常的,不是所謂的“生于好詭,逐新趣異”也沒(méi)有“忤其際會(huì)”“往蹇來(lái)連”。⑤
正如劉勰所言“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肈自血?dú)狻保哉Z(yǔ)是由不同的發(fā)音器官的相互作用發(fā)出的,“吐納律呂,唇吻而已”。而言語(yǔ)的音樂(lè)變化則來(lái)自不同發(fā)音器官相組合產(chǎn)生的差異,即“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zhǔn),皎然可分。” ⑥因此文章詩(shī)歌要盡可能出現(xiàn)更多的差異變化來(lái)表現(xiàn)音樂(lè)節(jié)奏的波瀾起伏,除了在平仄聲調(diào)高低上做出要求,還要充分利用不同發(fā)音器官的差異性。“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的“居”“佳”同聲紐,“殊”“城”同聲紐,同一聲紐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必然相似,這樣使得差異性減弱。因此需要通過(guò)“隔字“,中間間隔其他聲紐的字,來(lái)增加發(fā)音的變化,從而增加音樂(lè)節(jié)奏感,是可以說(shuō)的通的。
最后,對(duì)于“雙聲隔字而每舛”此句的翻譯注釋,更加傾向于前文提到的“雙聲隔字,而每舛”。即將“而”譯作“轉(zhuǎn)折”,一句或者一韻之間,出現(xiàn)的雙聲字中間應(yīng)當(dāng)隔字,以此來(lái)增強(qiáng)音樂(lè)節(jié)奏變化感,體現(xiàn)詩(shī)歌文章的回環(huán)往復(fù)、錯(cuò)落有致之美,從而表達(dá)作者的匠心獨(dú)運(yùn)。當(dāng)然雙聲連綿詞并不包含于內(nèi),連綿詞有且只有一個(gè)語(yǔ)素,合起來(lái)表達(dá)一個(gè)意思,他們不能也不被允許分開(kāi),一旦分開(kāi)表達(dá)的含義將被破壞。
二、“迭韻雜句而必睽”或“迭韻雜句,而必睽”
范文瀾先生注文:“疊韻雜句而必睽,即八病之小韻病也。《文鏡秘府論·五》引或云:‘凡小韻居五字內(nèi)急,九字內(nèi)小緩。’又引劉氏曰:‘五字內(nèi)犯者,曹植詩(shī)云:“皇佐揚(yáng)天惠,”即“皇”“揚(yáng)”是也。十字內(nèi)犯者,陸士衡《擬古歌》云:“嘉樹(shù)生朝陽(yáng),凝霜封其條。”即“陽(yáng)”“霜”是也。是故為疊韻,兩字一處,于理得通,如“飄飖”“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雜句,《文鏡秘府論·一》引此文作離句,疑作離者是,離亦隔也,謂疊韻字在句中隔越成病也。” ⑦“疊韻”即“迭韻”。同上所述,“飄飖、窈窕、徘徊、周流”亦為連綿詞,只有一個(gè)語(yǔ)素,不可能再分割,因而無(wú)所謂“雜句”“隔越”。而“小韻”說(shuō),即一韻之內(nèi)(除韻腳外)出現(xiàn)同韻的字,屬文最好避免此現(xiàn)象出現(xiàn)。那么一韻之內(nèi)疊韻的出現(xiàn),就意味著已然犯了小韻,故“雜句”本身不必討論。
“睽”,《說(shuō)文解字》注釋:“目不相聽(tīng)也。” ⑧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記載:“聽(tīng),猶順也。二女志不同行,猶二目不同視也。” ⑨那么“迭韻雜句而必睽”也如“雙聲隔字而每舛”譯法相似,“而”作不同用法,就有兩種翻譯解釋。一是支持“雜句”,然而現(xiàn)實(shí)文章創(chuàng)作常常違背此用法;一是反對(duì)“雜句”,以為正是由于“雜句”的存在,使得文章讀起來(lái)奇異,違背常理,不自然。
再返回上文曹植的“皇佐揚(yáng)天惠”,僅考慮平仄關(guān)系,應(yīng)為“平仄平平仄”。第一字不在節(jié)奏點(diǎn)上,可平可仄。其余字的平仄關(guān)系皆合聲律,并無(wú)不當(dāng)之處。“皇”“揚(yáng)”二字是平聲字,中間“雜句”是“佐”。“佐”為仄聲,“平平”增為“平仄平”,反而增加了音樂(lè)節(jié)奏的變化。陸士衡的“嘉樹(shù)生朝陽(yáng),凝霜封其條”,平仄關(guān)系是“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這并不是律句,不符合平仄規(guī)則。“陽(yáng)”“霜”,中間夾了“凝”字,將“平平”改成“平平平“,節(jié)奏平穩(wěn),變化較少。
“皇”“揚(yáng)”都是陽(yáng)部韻,中間夾了“個(gè)”部韻的“佐”字。“陽(yáng)”“霜”亦是陽(yáng)部韻,中間夾了“蒸”部韻的“凝”字。不同韻部的錯(cuò)落配合,促進(jìn)了節(jié)奏的變化。尤其是后者“陽(yáng)”“霜”,它對(duì)“夾句”的要求更加強(qiáng)烈。畢竟它在四聲平仄的變化上太過(guò)于微弱,真可謂“飛則聲飏不還”,若是沒(méi)有“雜句”的緩沖,僅靠聲紐來(lái)變化節(jié)奏,屬實(shí)有些單調(diào)。
最后,對(duì)于“迭韻雜句而必睽”此句的翻譯注釋,更傾向于前文提到的后者,“迭韻雜句,而必睽”。即將“而”譯作轉(zhuǎn)折,一句或者一韻之間,若是出現(xiàn)疊韻字,中間應(yīng)當(dāng)隔字來(lái)增強(qiáng)音樂(lè)節(jié)奏變化感,從而避免趨同性,使得文章的表達(dá)層次感更加分明。亦然迭韻連綿詞也不能被包含于內(nèi)。
三、劉勰的“雙聲”“迭韻”與沈約的“八病說(shuō)”
漢魏六朝是我國(guó)古代聲韻學(xué)自覺(jué)階段。這一階段的諸多著名文人,如曹植、陸機(jī)、鐘嶸、劉勰、沈約等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自發(fā)地運(yùn)用聲韻,并且有意做出相關(guān)理論總結(jié)。其中沈約是當(dāng)時(shí)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南齊書(shū)·陸厥傳》記載:“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shí)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⑩沈約作為南朝的文壇領(lǐng)袖,以他為核心倡導(dǎo)文學(xué)創(chuàng)作應(yīng)當(dāng)符合一定的聲律學(xué)規(guī)則,后世稱為“永明聲律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流傳極廣,聲勢(shì)浩大。而劉勰與沈約同時(shí)代文人,且劉勰借《文心雕龍》一書(shū)得到后者的賞識(shí),劉勰于其中的主張或多或少會(huì)與沈約的文學(xué)思想有著共通之處。
通過(guò)前文,可以看出劉勰在文章聲律理論中,他是允許“雙聲”“迭韻”的存在。無(wú)論“雙聲”“迭韻”是否允許“隔字”“夾句”,這都與“旁紐”“小韻”相互沖突,而后者又是沈約“八病說(shuō)”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wú)疑問(wèn),劉勰本人贊同文章詩(shī)歌的聲律化,以為用音韻聲律來(lái)貼近文章所抒發(fā)的情志,從而使文章的情感意志表達(dá)更加淋漓盡致。但是他對(duì)“八病”說(shuō)頗有微詞,“八病”對(duì)作家創(chuàng)作要求未免太過(guò)苛刻,反而會(huì)極大限制作家自由創(chuàng)作,無(wú)形中提升了文人的門(mén)檻。但是無(wú)論是沈約的“四聲八病說(shuō)”,還是劉勰的聲律說(shuō),歸根結(jié)底是希望一韻之內(nèi)字詞上盡可能表現(xiàn)出較多的差異變化,由這些差異的變化組合產(chǎn)生音樂(lè)上的起伏波動(dòng),能夠通過(guò)文字表現(xiàn)出音樂(lè)的高下、飛沉,進(jìn)一步抒發(fā)情感清揚(yáng)沉郁的變化。要盡可能回避趨同性、重復(fù)性,這有可能致使一韻之內(nèi)文字變化減少,節(jié)奏單調(diào)統(tǒng)一,最終走向“沉則響發(fā)而斷,飛則聲飏不還”的極端。
注釋:
①⑤⑥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shū)局2012年版,第301-302頁(yè),第301-302頁(yè),第301-302頁(yè)。
②⑦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年版,第558頁(yè),第558頁(yè)。
③⑧(漢)許慎:《說(shuō)文解字》,中華書(shū)局2020年版,第108頁(yè),第108頁(yè)。
④⑨(清)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頁(yè),第234頁(yè)。
⑩(唐)姚思廉:《南齊書(shū)》,中華書(shū)局1972年版,第243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啟功.詩(shī)文聲律論稿[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9.
[2]祝誠(chéng),江慰廬.《文心雕龍》聲律論對(duì)格律詩(shī)文制式形成的作用與影響(上)[J].鎮(zhèn)江高專學(xué)報(bào),2002,(2).
[3]祝誠(chéng),江慰廬.《文心雕龍》聲律論對(duì)格律詩(shī)文制式形成的作用與影響(下)[J].鎮(zhèn)江高專學(xué)報(bào),2002,(3).
[4]梁成龍.《文心雕龍》聲律理論探析[J].《傳奇·傳記文學(xué)選刊(理論研究)》,2011,(2).
[5]梁祖萍.《文心雕龍》的聲律論[J].西部學(xué)刊,2014年,(7).
[6]盧余瑋.對(duì)“文家之吃”根于“逐新趣異”的觀點(diǎn)淺析——《文心雕龍·聲律》[J].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14).
[7]戚悅,孫明君.《文心雕龍》的“雙疊”論,暨南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41).
[8]胡海.古代文論的“內(nèi)聽(tīng)”難題與文術(shù)探研——以《文心雕龍·聲律》篇為中心[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34).
[9]于景祥.《文心雕龍》聲律理論三題[J].社會(huì)科學(xué)輯刊,2020,(4).
[10]戚悅.《文心雕龍》“聲律”說(shuō)辨析[J].漢籍與漢學(xué),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