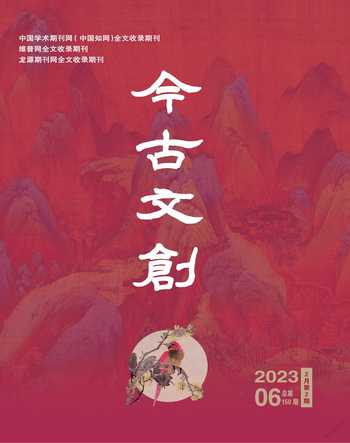顧炎武關注軍事問題的原因探析
付章倩
【摘要】 明清易代之際,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戰亂不休,顧炎武不僅目睹百姓的苦難生活,還親歷國破家亡之痛。彼時,針對明中期以后的社會現實,學者們反對空疏學風,將目光聚焦于“實務”,經世致用思潮興起。顧炎武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具有極強的家國情懷,并在嗣祖教導之下關注諸多“有用之學”,加之戰事不休,復國所需,其關心“實學”中的軍事問題,不僅實際參與到反清復明的斗爭中,還撰寫著作探討軍事問題。
【關鍵詞】顧炎武;軍事問題;原因探析
【中圖分類號】D09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6-006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6.019
自“土木之變”后,明朝由盛轉衰。晚明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內憂外患,政治腐敗、黨爭不斷、自然災害頻發、農民起義迭起、后金伺機而動。在如此動蕩社會環境下,明代學者反對空疏學風,將目光聚焦于“實務”,注重經世致用。顧炎武身處明清易代之際,自小接受“愛國”和“求實”的教育,還親身參與到抗清斗爭之中,并以“明道救世”的治學宗旨著書立說,其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少年文人、青年抗清、中年北游、晚年著述經世”[1]四個時期。
對顧炎武的研究,學界主要依據顧炎武的著作研究其思想和學風,主要關注顧炎武的政治、哲學、教育思想和經世致用的學風,并探討其抗清問題以及從旅游學角度來考察、審視和評價顧炎武的游歷生活。[2]明清易代之后,顧炎武在實際行動及學術活動中始終渴望恢復故國,不僅參加抗清斗爭,還撰寫文章如“乙酉四論”討論兵防等軍事問題,顧炎武的青年到晚年時期一直都很關注軍事問題,但是目前有關顧炎武在軍事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唯周可真的《論顧炎武的軍事思想》[3]分析和論述了顧炎武的軍事思想,并將顧炎武的軍事思想概括為以人為本的軍事觀點、廉恥為本的治軍觀點和重形任勢的戰略戰術觀點。
本文主要探討為什么顧炎武關注軍事問題,通過分析,發現主要有兩大原因: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在家庭教育方面,嗣母王氏教授了顧炎武“愛國”,嗣祖紹蒂則在學術方面指明了“士當求實學”的研究方向;在社會環境方面,明中葉以后,日益嚴峻的衰敗國情使得晚明學者在學術研究方面更加注重經世致用,加之明清之際戰亂頻發,致使顧炎武必然關注軍事問題。因此,本文從以上兩個方面探討顧炎武關注軍事問題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在顧炎武的家庭教育中,嗣母王氏和嗣祖紹蒂給予其最深遠的影響。王氏在生活上照顧顧炎武,在學習上樹立良好的榜樣,教導他愛國。紹蒂指導顧炎武的學業,使其關心時事,紹蒂本人求實的學風更是直接影響顧炎武未來的治學道路。
(一)嗣母教之愛國主義
顧炎武尚在襁褓之中時,就交由嗣母王氏撫養。王氏不僅自己勤奮好學,“初,吾母為婦十有七年,家事并王母操之。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櫛維問安以為常。尤好觀《史記》《通鑒》及本朝政紀諸書……”[4]20-21還教導年幼的顧炎武讀書,六歲時(1618年),“臣母于閨中授之《大學》”[4]27,在教授《小學》時就將忠君愛國的思想種在了幼時的顧炎武心中,“讀至王蝎忠臣烈女之言,未嘗不三復也”[4]107。
此外,王氏還在行動上力行“愛國”。除明末農民大起義外,還有因改朝換代而帶來的戰亂。1645年,清軍破潼關,直下江南,造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大屠殺,江南各地掀起抗清斗爭。在這一過程中,“世家巨族,破者十六、七,或失門戶”[5]251,顧炎武一家的經歷亦十分悲慘,其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顧子叟、顧子武被殺害,嗣母王氏絕食殉國,臨終囑咐:“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6]165國破家亡,至親離世,嗣母遺言,顧炎武恨清愛明。
彼時,身處戰亂環境之下,顧炎武懷有愛國之情,意圖恢復故國,所面臨最直接的問題便是如何退清兵。
(二)嗣祖教之“求實”
顧炎武的嗣祖紹蒂不僅家中擁有大量藏書,還是一位學者,對于學問,認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4]28在閱讀史書時,涉及有關戰略地形和兵法的內容,若其方策可用,則摘錄;而且,紹蒂十分關心時事,手抄邸報的重要時政信息并存之,顧炎武曾回憶祖父“閱邸報,輒手錄成帙……臣祖所手錄,皆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余字。而自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軼,中間失天啟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4]28因此,在紹蒂的教導之下,顧炎武早年開始便關心時事,關注軍事地理等實學。
顧炎武十歲時(1622年),明朝外有后金的猛烈進攻,內有山東白蓮教首領徐鴻儒起義,紹蒂令顧炎武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等,其自述“及臣讀《周易》為天啟之初元,而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并反。其明年,廣寧陷。山東白蓮教起義。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日:‘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7]26十二歲時(1624年),為以待將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應對更加吃緊的國內政治形勢,顧炎武攻讀兵書,“已而三畔平,人心亦稍定。而臣祖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為是闊遠者乎?于是令習科舉文字。”[4]27十五歲時(1627年),又逢陜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百姓不堪忍受,最終殺死張耀采,明末農民大起義由此揭開了序幕,這一年紹蒂令其閱讀邸報,關心時事,“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鑒》后,即示以邸報。”[8]32二十三歲時(1635年),國內形勢更加吃緊,顧炎武讀宋人性理書,其明確當求實學,“當先帝頒《孝經》《小學》厘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4]28
紹蒂早已預見明末動亂,故在其悉心教導之下,顧炎武關心時事民生,明白“士當求實學” [8]189。27歲時(1639年),“崇禎己卯,秋鬧被擯……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4]35,放棄科舉開始有目的地讀書,搜集各類資料,進行《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的寫作,探索明朝救亡之道。這兩本著作的諸多內容都與軍事有關,特別是與軍事地理有關的則“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9]463,張耀孫序也說,“一究生民之利病,治亂之得失;一考建置沿革之規,山川形勢兵事成敗之要,意各有所主也”[10]。
在此之下,嗣祖教導顧炎武,使其關注時事、求實學,隨年歲增長,顧炎武便愈發關注與當時社會現實有著直接關系的軍事問題。
二、社會環境
因嗣祖紹蒂的教育,顧炎武在問學方向上較為關注務實之學,這不僅是因為現實的抗清斗爭的需要外,還受當時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明末學者,尤喜歡談兵,而旁及于天文輿地,政治經濟農田水利之學,他們讀書,不是單停留在書本,而是從實踐中體驗出來,其目的是在致用的。”[11]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國家日益衰微,學者們愈發反對空疏學風,“從純學術的研究轉變為從事與時務密切相關的問題和有用之學的研究上”[12]。
(一)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
明末,家國危機之下,顧炎武意圖恢復故國,青年時期參與抗清斗爭失敗后,中晚年時期又以著書形式關注軍事地理問題。
顧炎武青年時期關注軍事問題,主要是由于現實的抗清斗爭的需要。1644年,經縣令楊永言薦舉,顧炎武被南明福王政權聘為兵部司務。彼時,顧炎武滿懷信心,期待著“春秋大復仇”[6]260。1645年,清軍已將戰線推至西北和黃河,南明殘余勢力則在南京建立起南明政權,顧炎武于1645年春寫下《軍制論》 《形勢論》 《田功論》 《錢法論》四論,就當時南明所面臨的軍隊的改造、軍事戰略的規劃、務農積谷及整頓財政等四個方面的重大實際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張。彼時,清軍定鼎北京,攻破潼關進入長安,南渡黃河逼兩淮,一半天下已歸其所有,故顧炎武在《形勢論》中說道:“竊以為荊、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于中原,則猶可以安。”[6]124實際上也是如此,當時南明守住余下的一半天下,保住南京是最緊迫的現實問題,因而“顧氏的乙酉四論,基本上也是從南明偏安一隅為前提而寫的偏安策”[13]。
自抗清斗爭失敗后,顧炎武北上游學,漂泊終身,直至死去。這一時期,顧炎武從未真正放下對恢復明朝的希望,依舊關心軍事問題,查證、記錄下了許多北方的山川地貌,“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于數十百年之后”[14]1086,這便是為了以后的反清起義提供據軍事資料。
1651至1653年,顧炎武居于南京,參與長江之役中,但秘密抗清武裝斗爭失敗直接釀成了“松江之獄”,最終于1650年選擇偽做商賈,北上游學。顧炎武遍游魯、燕、晉、陜、豫諸省,于1652年完成《天下郡國利病書》初稿,該書中的重點部分便有薊遼[15]。書中對地形特點的調查記錄,都帶有軍事戰略意義的,“顧亭林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實為大規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是其著述動機,全在致用;其方法則廣搜資料,研求各地狀況,實一種政治地理學也。”[16]459-460如1662年完書的《肇域志》就很明顯的彰顯了其歷史軍事地理特點,《肇域志》引錄了諸書對各地地理形勢的認識且軍事色彩濃厚。[17]
顧炎武晚年時期,依舊關注軍事問題。如《日知錄》雖未將軍事問題作為主要部分進行探討,但在卷九《守令》的“郡縣之四權”的概念,即“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就包含兵權,其指出:“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于守令……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于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于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于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于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18]
(二)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的學風
顧炎武身處明末清初,社會環境復雜,明末政治腐敗、農民起義不斷,地處東北的建州女真逐步迫近薊遼重鎮山海關,發動了長期大規模的反明斗爭 ,最終入主中原,這使得人們更多地將目光投注到現實生活中,當時學者們針對“心學”的誤人、誤國以及現實的政治腐敗、戰爭頻繁等情況,反對空疏學風。顧炎武就曾將神州蕩覆歸之于陽明心學的清談:“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言‘一貫,言‘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19]339
顧炎武的學術研究范圍很大,“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槽、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 [20]13167軍事問題,屬于“務當世之務”,顧炎武曾言“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于此,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21]453在祖父的教導和求實學風的影響之下,顧炎武繼承了明代學者倡導的“以天下為己任”[22]的治學精神,考證各地疆域、形勝、關塞、邊防、屯田、水利、物產、賦役等,目的是從這些方面探究明朝所以衰敗的原因,以便針對“時弊”進行改革。
統而言之,明朝末年農民起義的此起彼伏,清兵入關使顧炎武國破家亡,社會民生困苦,顧炎武在家庭教育和現實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選擇了“明道救世”的治學目的和方向,從青年起便開始關注“實學”中的軍事問題,抗清斗爭失敗后,北上游學,對相關軍事地理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最終形成著作“以待后王”。
參考文獻:
[1]牛余寧.顧炎武政治旅行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2009.
[2]周可真.1950-2013年顧炎武著述生平學術研究綜述[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3(06):51-68.
[3]周可真.論顧炎武的軍事思想[J].蘇州大學學報,2003,(04):82-86.
[4](清)顧炎武著,華忱之校注.顧亭林文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清)歸莊.莊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周可真.顧炎武年譜[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
[8]《蘇州通史》編纂委員會編,李峰主編.蘇州通史 人物卷(中)(明清時期)[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9.
[9]馮天瑜,彭池,鄧建華編著.中國學術流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0]朱惠榮.評《肇域志》[J].史學史研究,2001,(01):43-51.
[11]謝國楨.略論明末清初學風的特點[J].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3,(02):1-35.
[12]楊緒敏.明代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及對學術研究的影響[J].江蘇社會科學,2010,(01):235-240.
[13]李洵.論顧炎武在“郡縣”等七篇政治論文中提出的社會問題[J].史學集刊,1983,(1).
[14](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趙儷生.試論顧炎武在人文地理學方面的貢獻—— 《天下郡國利病書》精要之所在[J].社科縱橫,1992,(5):1-4.
[16]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17]朱惠榮.評《肇域志》[J].史學史研究,2001,(01):43-51.
[18]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外七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清)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
[20]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M].北京:中華書局,1977.
[21]趙宗正.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簡論[J].哲學研究,1983,(06):70-76+35.
[22]《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25[M].北京: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