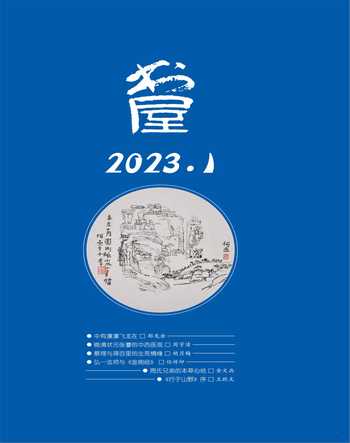晚清狀元張謇的中西醫(yī)觀
周宇清
“醫(yī),技而有學(xué)者也。”張謇高度認(rèn)可中醫(yī)的學(xué)術(shù)內(nèi)涵,而不是僅僅將其視作一種技術(shù)。張謇一生讀書(shū)甚雜,中醫(yī)典籍也在其視野之內(nèi)。從張謇日記中得知,年輕時(shí)的張謇研習(xí)過(guò)《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年后讀過(guò)《醫(yī)宗金鑒》,曾購(gòu)買《產(chǎn)孕集》醫(yī)書(shū),直至七十一歲高齡,還讀完《性命圭旨》這部闡揚(yáng)道教義理和丹道法則的書(shū)籍,張謇對(duì)中醫(yī)的尊崇是一以貫之的。
張謇驚嘆中醫(yī)藥的神奇:蜈蚣、蟾蜍、枸杞、蘆根等“物之以性質(zhì)相引者也,皆入藥”,甚至“燈草之灰、龜之溺猶有用”,激賞良醫(yī)的“得醫(yī)者意也之意”和用藥的“神乎其神”。
“醫(yī)道與人生性命息息相關(guān),亟應(yīng)注意。”為了培養(yǎng)醫(yī)學(xué)人才,普及醫(yī)學(xué)知識(shí),1912年張謇與其兄張?jiān)垊?chuàng)辦南通醫(yī)學(xué)專門(mén)學(xué)校,設(shè)西醫(yī)科,聘請(qǐng)留日歸國(guó)學(xué)生和外籍人員擔(dān)任教師和醫(yī)師,并派教師去日本訪學(xué),派優(yōu)秀學(xué)生去日本和德國(guó)留學(xué),回國(guó)后擔(dān)任學(xué)校重要職務(wù)。優(yōu)質(zhì)的教育、先進(jìn)的理念,促進(jìn)了社會(huì)風(fēng)氣的暢通。1915年4月30日,醫(yī)校師生做了南通首例人體解剖實(shí)驗(yàn),這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也是不多見(jiàn)的。
張謇意識(shí)到中、西醫(yī)各自的價(jià)值,認(rèn)為二者不可偏廢。1914年張謇為學(xué)校題寫(xiě)“祈通中西以宏慈善”校訓(xùn)。1917年學(xué)校增設(shè)中醫(yī)科,聘請(qǐng)有聲望的中醫(yī)師任教,講授《內(nèi)經(jīng)》《金匱要略》等。但中醫(yī)教材缺乏,且中、西醫(yī)學(xué)教材、教法大相徑庭,又鮮有兼精中、西醫(yī)的通才,“一時(shí)溝通亦殊不易”。張謇擬于中醫(yī)科加生理、化學(xué)兩科,西醫(yī)科加本草藥物科,“令學(xué)生自加融洽,希冀溝通”,讓學(xué)生先學(xué)習(xí)數(shù)年中醫(yī),再習(xí)西醫(yī),這樣可使“氣化、形體洞悉無(wú)遺”。張謇很重視學(xué)生實(shí)踐能力的培養(yǎng),鄙棄“徒泥守古方而未嘗臨癥”的教學(xué)。1918年,張謇斥巨資為學(xué)校購(gòu)買了理療設(shè)備、化驗(yàn)儀器等先進(jìn)醫(yī)療器械,充實(shí)完善教學(xué)設(shè)施,提升辦學(xué)質(zhì)量。在張謇心中,中、西醫(yī)皆是瑰寶。
對(duì)待中、西醫(yī),張謇不贊同“軒西而輊中”和“是丹非素”之論,認(rèn)為中醫(yī)有其弊也有其長(zhǎng)。“中醫(yī)主氣化,治虛證亦誠(chéng)有獨(dú)至之處”,但是中醫(yī)“本草”一系,“性味雖別而未精詳。方證治用,或未能知其所以然;即知其所以然之理,未能知所以然之?dāng)?shù)”。中醫(yī)藥“有性有氣有味。性或古今不同,用尤經(jīng)緯各異:有相輔以為用,有相制以為用,有相反相激以為用。故古代主治之說(shuō),不盡可從”。而西醫(yī)“藥取其精,服量少而飲不苦”,“便人服飲”,也有其理,“是在今日尤不能不取西醫(yī)學(xué)說(shuō),以輔吾之不逮”。
欲祛中醫(yī)之弊,“當(dāng)從溝通中、西藥物性質(zhì)功用始”,張謇論道,“醫(yī)但言理則空,藥各有質(zhì)則實(shí),必實(shí)而后空可證,必空而后實(shí)可神”,醫(yī)、藥并舉,相互引證,方可發(fā)揮最大功效。在張謇看來(lái),中、西醫(yī)雖分屬不同的醫(yī)學(xué)體系,但實(shí)有相通之處。有人認(rèn)為西人醫(yī)學(xué)與藥學(xué)分離,“故辨性較精,而施效易見(jiàn)”,張謇指出中醫(yī)之道,出自道家,早在《漢書(shū)·藝文志》里本草家與醫(yī)家就已經(jīng)分途,漢以前醫(yī)、藥并重。中醫(yī)的方劑,“有化學(xué)之意寓焉”,中醫(yī)各類藥物共同煎煮,“劑義取和,有類今所謂化合”。西醫(yī)講究對(duì)癥下藥,“間時(shí)而投,主分治”,而中醫(yī)亦有丸、散等“易時(shí)分治之法。是中、西亦正有合處”。就具體藥品而言,“泰西某藥,猶之吾國(guó)某藥,以其法制吾國(guó)某藥,猶之泰西某藥”,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張謇進(jìn)一步論析,“凡一家之學(xué)垂數(shù)千百年,皆必竭無(wú)數(shù)聰明仁賢之士之才智,極深研幾而底于成,必皆有其獨(dú)到之處。平心論之,斟酌挹注融會(huì)而求其通,必有其通之一日。若各守一先生之言而專己自是,是己見(jiàn)先塞矣”。中、西醫(yī)藥需要會(huì)通,也能夠會(huì)通。
張謇聯(lián)系自己的辦學(xué)實(shí)踐,感嘆“南通設(shè)醫(yī)校有年矣,意在溝通中西”,然而“效未大著”,原因就在于未通藥性。張謇把溝通中、西藥性比作行車必先鋪設(shè)軌道,“思之思之,乃計(jì)先通藥學(xué)。藥通然后可以求醫(yī)之通。猶汽車、電車,藥猶軌與道也”。不知藥性,“中西將永永僢馳”,“中亦必永永固蔽”。基于對(duì)中、西醫(yī)藥的認(rèn)知,張謇擬聘請(qǐng)精通化學(xué)、醫(yī)學(xué)的人,利用近代科技手段,對(duì)《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所載的藥品和后人增加的藥物進(jìn)行定性分析,“藥明而后用藥之法可出而索,而后治病之方可貫而通”。此事若成,無(wú)疑是一件造福民眾、澤被后世的善舉,也必將為中醫(yī)藥開(kāi)辟一進(jìn)路。后來(lái),由于經(jīng)費(fèi)和人力等原因,此議并未實(shí)行,但張謇會(huì)通中、西醫(yī)藥的思想由此可見(jiàn)。
晚清民國(guó)時(shí)期,由于國(guó)力的衰弱和西方列強(qiáng)的入侵,不少人把中國(guó)的貧弱歸咎于傳統(tǒng)文化的惰性,痛加貶斥,中醫(yī)學(xué)也在其列。“今舊醫(yī)之所襲用者,太古以來(lái)人類本能所發(fā)明之事實(shí)也,經(jīng)驗(yàn)也”,這與通過(guò)實(shí)驗(yàn)獲取翔實(shí)數(shù)據(jù)并嚴(yán)格遵循邏輯推理的自然科學(xué)不同,屢遭批判。陳寅恪以為“中醫(yī)有見(jiàn)效之藥,無(wú)可通之理”。陳獨(dú)秀攻擊中醫(yī)“不知科學(xué),既不解人身之構(gòu)造,復(fù)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wú)聞焉;惟知附會(huì)五行生克寒熱陰陽(yáng)之說(shuō),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shù)殆與矢人同科”。魯迅更是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shuō)“中醫(yī)不過(guò)是一種有意的或無(wú)意的騙子”。但是西醫(yī)也沒(méi)有取得對(duì)中醫(yī)的壓倒性優(yōu)勢(shì),“社會(huì)習(xí)慣,信中醫(yī)者多”。1929年,梁?jiǎn)⒊诒本﹨f(xié)和醫(yī)院治病,因診治錯(cuò)誤而生命垂危,梁先生在病榻上著文為醫(yī)院和主治醫(yī)師辯護(hù),以免減弱國(guó)人對(duì)西醫(yī)的信仰、影響西醫(yī)前途。生活在科學(xué)逐漸昌明時(shí)代的狀元張謇,也表現(xiàn)出對(duì)科學(xué)和科學(xué)家的興趣和尊重,他認(rèn)識(shí)到西醫(yī)的價(jià)值,然而也不忽視中醫(yī)的作用,主張二者并重,兼用其長(zhǎng),并試圖用科技手段分析中醫(yī)藥性,顯得特別耐人尋味。1950年第一屆全國(guó)衛(wèi)生會(huì)議上,與會(huì)的中醫(yī)界耆宿主張要把中醫(yī)的經(jīng)驗(yàn)和理論,用科學(xué)方法“加以系統(tǒng)地整理”,“把中醫(yī)科學(xué)化”,并疾呼中、西醫(yī)團(tuán)結(jié)。幾十年來(lái),國(guó)內(nèi)許多醫(yī)科大學(xué)都開(kāi)設(shè)了中西醫(yī)結(jié)合專業(yè),許多醫(yī)院都有中西醫(yī)結(jié)合門(mén)診,張謇的主張終被歷史所證實(shí)。
張謇有著濃厚的救民濟(jì)世情結(jié),他的中西醫(yī)會(huì)通的思想和實(shí)踐與他的辦實(shí)業(yè)、興教育在思想理路上完全一致,都是為了適用,都是為了國(guó)家富強(qiáng)和人民免于疾苦,“竊謇以國(guó)家之強(qiáng),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shí)業(yè)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慈善雖與實(shí)業(yè)、教育有別,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張謇把慈善當(dāng)作磨煉人格、增強(qiáng)修為的方式,發(fā)展醫(yī)學(xué)即是慈善之一種。張謇溝通中、西醫(yī)學(xué)的思想和實(shí)踐反映了近代中國(guó)大變革時(shí)期部分先進(jìn)中國(guó)人對(duì)待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也反映了他們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