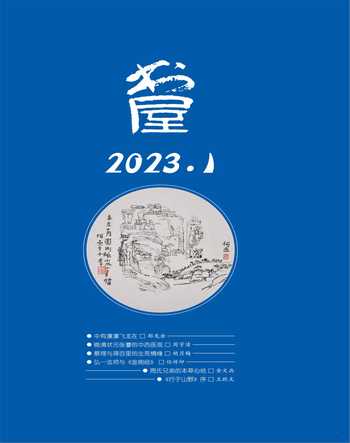一泓源泉各奔流(六)
徐達斯
《春秋》為人學,《易》為天學。《易》發源于歷數和占卜,自然也屬于巫系思想,乃是以象、數、理的形式,對于事物在時空中形成、持續、毀壞、變化的過程和規律加以描述和總結。《春秋》規范人事,賅《詩》《書》;《易》統攝天理,涵《禮》《樂》。《史記·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易》與《春秋》互見,體現了以天節人、以人奉天的天人合一原則。
《易》之為言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謂之《易》者,所以明世道窮變通久之必然;而系以周者,所以明世變剝復循環之有常。周之為言周也,周而復始也。周有原始反終之義,而《周易》以太極為本體,是萬物窮通變化,皆歸根于太一也。太極為天地萬物之始,亦為天地萬物之終;太極在天地萬物之中,亦在天地萬物之外。太極者,太一也,既超越又內在之整體大全也,與《薄伽梵歌》第九章所論述之宇宙神我遙相契應:
4.我以無形之身,充塞于天地之間。眾生皆在我里面,我卻不在他們里面。5.然而一切受造之物又不住我之中。看哪,這就是我的玄通大用!雖然我是一切有情的養育者,雖然我無所不在,我卻在天地之外,因為我是天地之根。6.要知道,就像強風處處吹遍,卻仍在天穹之內,一切受造之物皆住我之中。7.貢蒂之子呀!當劫終之際,天地萬物皆銷融入我的自性;當下一劫波開始,我又以自己的力量再造天地。8.天地大道從我流衍。在我的意志之下,天地不斷自行復生;也是在我的意志之下,天地最后又歸于崩壞。9.檀南遮耶呀!所有這一切作為不能束縛我。我沖虛自處,絕不會對此有所執著。10.貢蒂之子啊!物質自性在我的意志之下運化,創生動不動一切存有。天地順乎自然之道,往復生滅以至無窮。
天地萬物往復生滅以至無窮,而宇宙神我對此并無執著,此即《易傳》:“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徐梵澄先生在《玄理參同》中指出,《神圣人生論》的宇宙觀與中國的《周易》大合,周易學說包含著一種系統化的玄學或精神哲學的氣象。大易哲學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皆統之于陰陽,陰陽則歸之太極,即本體,即一,即道。“澈上澈下只有一事曰‘知覺性’。名相之殊無數,修之為道多途,要歸于‘一’,此‘一’或謂‘至真’,或謂‘精神’,或謂‘上帝’……即此,在華言,此即是‘道’”,這是“不得已落于言詮,則曰至真,即至善而盡美;曰太極,即全智而遍能;在印度教輒曰超上大梵,曰彼一,人格化而為薄伽梵。薄伽梵者,稱謂之至尊,佛乘固嘗以此尊稱如來者也。歐西文字輒譯曰:天主,上帝,皆是也”。
《易·系辭》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
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
乾元為創造意志,即宇宙神我;坤元為生成能力,即物質自性。按照吠陀數論的說法,乾元為補魯莎,坤元為自性。《易》其實就是一套以神圣數字闡述宇宙生成演化的數論哲學。物質自性表現為三德之分合作用,薩埵輕光屬天道,為中和氣性;多磨重覆屬地道,為濁陰氣性;羅阇造作屬人道,為強陽氣性。數論之三德,相當于《易·系辭》所謂三極或三才,其論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兇生焉。”
三才之中,人道屬陽,地道屬陰,天道中和。老子《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或曰太一,轉為天一,天一生地二,地二化出陰、陽、中和三極,三極資生萬物。《易·系辭》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
太極即太一,兩儀為乾坤,四象為元氣變化而生之四種表象(老陰、少陰、老陽、少陽),八卦代表八種不同性質的物質元素。《易·說卦傳》言八卦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為天,為圓,為君……坤為地,為母……震為雷……巽為木,為風……坎為水……離為火……兌為澤,為少女。”
八卦對應于數論之八種物質元素。根據數論,宇宙演化的順序是:補魯莎與物質自性交合,從物質自性生統覺(智),統覺生我慢,我慢受三極之氣,合陰氣而生五唯、五大(地、水、火、風、空),合陽氣而生五作根,合中和之氣而生五知根與心根。由五大組成了人的粗身。心、智、我慢組成了人的細身。粗身、細身、靈魂三者合成整個生命。《易》八卦之中,艮、坎、離、巽、震分別對應于數論之地、水、火、風、空。空與空間、聲音有關,故震取象于雷。心、智、我慢分別對應于兌、坤、乾。乾健主宰,為我慢之屬性;智為分辨判斷能力,隨我慢而動,故順而為坤;心(即心意)流動不息,其性常避苦而求樂,故與取象于澤、少女的兌對應,兌通悅。
綜合而言,《易》相當于吠陀典的智分,其中涵攝了跟天文歷法有關的“象”“數”,以及類似有神數論和有神吠檀多哲學的“理”,由此產生《禮》和《樂》,其核心為一套奉獻于上帝天地神明祖先的祭祀體系,與《易》一起構成了六經之“天學”,以“建中立極”“升中于天”也即溝通天人為其宗旨,即由智分而上升至教分。《春秋》統領《詩》《書》,表現圣王在世間的治平教化實踐,其目的在于建立道德倫理秩序,為六經之“人學”,相當于吠陀典的業分。
吠陀之“智”的根基在于覺性或知覺性,而非理性的思辨演繹。徐梵澄先生認為,《易經》的思維是了解中國精神哲學的關鍵,將“整個精神哲學系統化了”,其中“知覺性是其堅實的基礎。提問者和占卜師之間的心理條件或心理氛圍在占卜時最為重要。雙方必須真誠,占卜師尤其不能用意,需要近乎機械地計數,勿使喜好或厭惡左右其心思。也就說,心思混合體不能干擾占卜,高等知覺性須獨自指出決而未顯的答案。基本上只有高等知覺性在起作用,真誠即是要求心思全力集中于一點。剩下的過程僅是如何有效地解釋《易經》占辭,這更多地有賴于占卜師的世俗經驗和靈感”(參見《孔學古微》)。
吠陀經教強調從業分向智分、教分提升的漸進路徑,讓人通過踐行禮法來培養諸如克己自制、謙卑誠敬、堅定專注、慈悲能舍一類的美德,從而逐漸獲得進入自我覺悟、奉獻神明的資格,這跟《禮記·中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漸修路數相當契合。進一層而言,智分與業分并非截然對立,而是互相融攝,以智慧駕馭業行,讓業行本身轉化為瑜伽,這便是“業瑜伽”之道。這種智慧指向消解二元對立的“無欲”“無我”之境,使人在世間行動中凈化內心、發明本性、實現天道,臻達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性情合一之當下解脫的最高理想。正是從這個究竟了義層面出發,《薄伽梵歌》第二章三十九至五十三偈頌對吠陀業分加以批判和揚棄:
39.至此,我已向你講述了數論哲學。現在,請再聽菩提瑜伽。帕爾特呀!你以這智慧行動,便能脫離業力的桎梏。40.做這種努力,并無損失。沿這道路前進少許,也可免于最危險的恐懼。41.在這條道路上的人意志堅定,目標專一。俱盧族的寵兒啊!猶豫不決的人,其智慧枝蔓叢生。42/43.見識淺薄的人過份執著吠陀諸經的夸飾文字。因為他們渴望感官快樂、榮華富貴,就說除了這些,再無其他。這部分內容教人如何通過種種獻祭和業行,往生天堂星宿;或者如何得到好的出生,獲取功名利祿。44.心意過份執著感官享受和物質富裕,便會為其所眩惑,如此定慧和三昧也無從生起。45.吠陀經主要討論物質自然之三極氣性。阿周那呀!你要超越三極氣性,安住于自我之中,擺脫一切二元性,不為利益和安全而焦慮。46.大淵有小池之用;同樣,一旦領悟了隱藏于吠陀經背后的宗旨,吠陀經的真義便已不言而喻。47.你有義務履行賦定職分,但無權享有業果。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業果的原因,也不可不去履行責任。48.阿周那呀!對職分,你要擔當;對成敗的執著,你要摒棄。這樣的平衡,謂之瑜伽。49.財富的征服者呀!憑借菩提瑜伽,擺脫一切業行。在這種覺知中皈依至尊主吧,想享受業果的人是吝嗇鬼。50.踐履奉愛服務,即使在現世,也能擺脫善惡果報。阿周那呀,瑜伽是行動的藝術,努力修煉瑜伽吧!51.透過踐履對主的奉獻服務,偉大的圣哲和奉獻者掙脫了塵世業果的纏縛,如此,得以遠離生死輪回,超轉無悲無苦之地。52.當你的智慧穿過假象的密林后,對耳聞之言,過去的或未來的,都會無動于衷。53.當心念不為吠陀諸經的浮華文字所擾,穩住于三昧,你已悟入神圣之覺性。
打通超世梵智和吠陀業行之間的鴻溝,再調適而上遂,以對宇宙神我的皈依奉獻統攝之,如此踐履世法即是愛敬神明,日用常行即是自我覺悟,倫理人情即是天命之性,天人、知行、性情在菩提和瑜伽的融合中達到了完美的統一,這便是“建中立極”的中庸之道,也是老子“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的無為之道。常者,中也,執有無而統同者也;極者,易也,太一也。是古人之大體,所以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也。
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有一段孔子答子貢的話,論述德與天命、天道的關系:“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
在這段話里,孔子區分了巫、史、儒。他認為只知祝禱而不了解天道變化的理數,這是巫。明了天道變化的理數而沒有內在之德,這是史。幽贊而明于數,通數而達于德,這才是儒。這里所說的史,具體是指行蓍占的史官。圣人不同于偏執一端的巫、史之處在于,圣人之道涵攝了贊、數、德。贊是愛敬通于神明,數是智慧彌綸天地,而德是心性的真實發露,是愛和智慧的基底。沒有智慧,天命將流于迷信;沒有明德,智慧不過是求利的方技。沒有愛敬通于神明,則一切明德、智慧皆失去了最終的歸宿和依據。《禮記·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易·說卦》云:“古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即是將贊、數、德貫穿于易道。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重點在德之養成,屬于業分范圍;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由智分而上達于教分。贊、數、德分別對應于教分、智分和業分。帛書《德行》曰:“幾而知之,天也。幾也者,持數也。唯有天德者,然后幾而知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上帝臨汝,□幾之也。毋貳爾心,俱幾之也。”
有天德者能持數,乃至知天,此謂“幾”。《易·系辭》云:“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孔穎達疏:“研幾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值得注意的是,帛書把“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作為“幾”的目標,其鮮明的人格神色彩與《薄伽梵歌》所稱揚的巴克提道極為契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