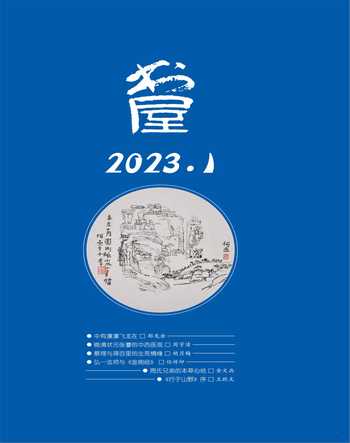從沈從文《邊城》到岳立功“湘西三部曲”
王芳
沈從文《邊城》營造的“田園牧歌”這一典型湘西文學(xué)印象,民初時(shí)曾因極致唯美文風(fēng)與當(dāng)時(shí)革命時(shí)代風(fēng)氣之“隔”而廣受文壇批評,然而在新中國改革開放時(shí)代,卻成為湘西文旅的“金字招牌”;無獨(dú)有偶,隨著《烏龍山剿匪記》《喋血邊城》等電視劇熱播,湘西其境與“匪”相關(guān)的熱血故事深入人心,讓這片土地在牧歌之外,又添一層“勇武喋血”之硝煙魅惑。
生于二十世紀(jì)四十年代的岳立功先生以三十五年之功,讓他在青年開寫《黑營盤》時(shí)便立下的“為家鄉(xiāng)立傳”夢想成真,當(dāng)真是一種令人感佩的“天行健”式生命意志。朋友感動(dòng),因?yàn)椤叭壳卑严嫖麒蜩蛉缟粼诹宋淖掷铮煌袣J佩,因?yàn)椤叭壳比缡中g(shù)刀般解剖了影響湘西歷史走向的田氏家族的興衰歷史。關(guān)于“三部曲”,作者如是說:“‘湘西三部曲’分別為湘西家族悲劇(《黑營盤》),湘西城市悲劇(《紅城垣》),湘西地方全域悲劇(《白祭壇》)。”從《黑營盤》開始,岳立功的湘西便站在薄霧輕紗籠罩的“田園牧歌”的對面。他手提巴爾扎克式的手術(shù)刀,從沈從文的邊城毅然出走:一、重歸生活;二、深植土地,把湘西這片土地上一個(gè)半世紀(jì)時(shí)間長河里一個(gè)又一個(gè)鮮活的人、家庭、家族的愛恨、恩怨悉數(shù)寫出,升騰而成遼遠(yuǎn)宏闊的歷史演遞。不得不說,從沈從文的邊城出走、“走自己的路”的勇敢,成就了岳立功三十五年后實(shí)現(xiàn)的非凡“立功”與立言。“三部曲”中近現(xiàn)代歷史諸多大事件頻見,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抗日戰(zhàn)爭里的嘉善血戰(zhàn)、雪峰山戰(zhàn)役等,“完整講述湘西人民在反清、討袁、北伐、抗日、國共內(nèi)戰(zhàn)的歷史長河中的斗爭史和兒女情長,展現(xiàn)了神秘美麗的自然風(fēng)光和人文風(fēng)情,同時(shí),讓世人了解湘西人民剽悍、剛強(qiáng)不屈的性格、人格及獨(dú)特的精神世界”。而作為長篇小說,大歷史和深遠(yuǎn)意義無不附著于小說中每個(gè)人物的成長、遭遇和命運(yùn)之中。
從《黑營盤》開始,作者先給自己的寫作定了個(gè)調(diào)子:“小說是悲劇,基調(diào)是中灰色的。”作者當(dāng)是深度研究過色彩學(xué),對于視覺變化和人事起伏間的奇妙通感感觸猶深,紅、黑、白等色彩,記憶都會糅合成灰色。此種情狀亦適用于寫作,既忌情緒大紅大綠濃郁不克制、無抽離感而不給讀者留空間,亦不能零度寫作導(dǎo)致作品內(nèi)情感感染力欠缺。
沈從文書寫《邊城》時(shí),是以返鄉(xiāng)者的姿態(tài),初年他因新婚燕爾而正沐浴生命青春飽滿的愛,次年又因親慈離世之慟而“懷著不可言說的溫愛,在一首清澈美麗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園牧歌中,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美、自然而又不違悖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的愛做了恰如其分的說明”。十年后,他亦堅(jiān)定捍衛(wèi)了自己的這個(gè)作品初衷:“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yīng)當(dāng)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是罪惡,可是總不能令人愉快……人應(yīng)當(dāng)還有個(gè)較理想的標(biāo)準(zhǔn)……至少容許在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造那標(biāo)準(zhǔn)。因?yàn)椴还軇e的如何,美當(dāng)是善的一種形式。”《邊城》正面書寫的是他心里一個(gè)美的夢,沈從文期待這個(gè)夢里家鄉(xiāng)淳樸的人性和人類的愛。游客不以“邊城”為是,當(dāng)下湘西人亦不以“邊城”為真,人們對之產(chǎn)生了巨大的隔閡,此種現(xiàn)象,我稱之為《邊城》為湘西“增魅”而生的誤解。
這樣的增魅,顯然為岳立功所洞悉。讀者們肯定還記得,岳立功身上流著湘西的勇武血脈,一個(gè)勇敢者,自然不憚?dòng)趶慕?jīng)典和前輩的“謬誤”處落筆。我以為“三部曲”正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為家鄉(xiāng)祛魅。岳立功寫作湘西歷史、土地、人物之真,“貼到這個(gè)土地上的每一個(gè)鮮活的個(gè)體來寫”。
同樣為家鄉(xiāng)祛魅,沈從文在民初特定時(shí)間的“沈式祛魅”,高揚(yáng)文學(xué)唯美的旗幟。而他的后輩岳立功用三部曲完成了“岳式祛魅”,不止接力《邊城》的唯美,更接過沈從文在大量散文中對故鄉(xiāng)的愛與痛,把所有的光都聚在小說人物身上,寫出了這片土地上的不屈與倔強(qiáng)。唯美《邊城》締造了世界對東方的唯美印象,而唯真的“三部曲”書寫了湘西之魂、國人精魄。兩位作家時(shí)代接力而寫就的,正是由湘西書寫出的中國的精神——真與美。沈從文說“美是善的形式”,而融合真與美,便是至善本身。
從創(chuàng)作論的維度,沈從文《邊城》創(chuàng)作初心是詩性的藝術(shù)品,岳立功“三部曲”初心重在為家鄉(xiāng)立傳。而題材、風(fēng)格、走向的迥異,除了作家個(gè)人氣質(zhì)、寫作際遇之外,我還發(fā)現(xiàn)了寫作和生活之間的“錯(cuò)位式”關(guān)系。
身為行伍世家的沈從文,自己年輕時(shí)當(dāng)過兵,關(guān)于一切和戰(zhàn)爭有關(guān)的丑陋,殺戮、生命喪失,對沈來說便是再真不過的生活本身,是他極其厭惡、以生命原力想掙脫的生活,這些生活的真實(shí),作為作家,他把它們限制在散文和隨筆中。而作為文學(xué)家的沈從文,不僅僅毅然從家鄉(xiāng)出走,“用一支筆打出一個(gè)天下”,題材上也從“真”出走,寫《邊城》等作品時(shí),堅(jiān)決杜絕了正面觸碰戰(zhàn)爭和過于真實(shí)的生活本身,不碰觸、不采集、不黏著,而是選擇了飛蛾撲火般的童話式寫作。而生長在新中國的岳立功,想和讀者分享自己于歷史煙塵中看到的一個(gè)個(gè)清澈面容,生與死,愛與痛,他億萬次追問、追尋故鄉(xiāng)“真”之所在。
作為湘西的一員,從一個(gè)熱愛沈從文《邊城》唯美的文學(xué)青年,到為岳立功先生“三部曲”所吸引、著迷和震撼,其間固然有著奇妙的“偶然和情感”,但隨著年歲漸長,我已然無法僅僅躲在邊城的歌和夢里,止于乘著沅江沱水的波瀾,追逐和映照自己的影子。我曾多次返鄉(xiāng)驅(qū)車穿越十幾公里之長的雪峰山隧道。在讀“三部曲”以前,雪峰山只是雪峰山,讀后再到雪峰山時(shí),《白祭壇》雪峰山戰(zhàn)役中艱毅卓絕的每一個(gè)面孔,會浮現(xiàn)在雪峰山的每一株青松,浮現(xiàn)在每一顆青草的露珠里,這是屬于我的閱讀和生命經(jīng)驗(yàn)。對于文學(xué)不那么流行的當(dāng)前,我更想說,遇見文學(xué),遇見浸透著勇敢和忠誠的作家作品,我們勢將遇見更為深廣而遼遠(yuǎn)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