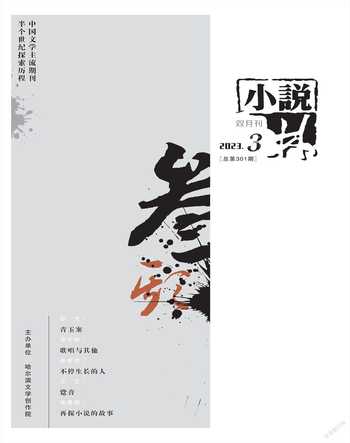朝向未知的無限
思不群
我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我的寫作老師是卡夫卡。寫下這句話,意在表明我對以其為代表的這一偉大文學傳統的尊崇和追隨。然而,細細品味,我不安地發現這句話透露出的卻是無知和狂妄。于是我將它修改為:我的寫作老師是卡夫卡,但我不是他的學生。我只能暗地里把自己當作他的弟子,這樣我的寫作似乎有了源頭和無數次失敗的理由。齊奧朗說:“一個雪萊、一個波德萊爾、一個里爾克,卻是在我們身體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們會像吸納一種惡習一樣,把我們吸納進我們自己。”卡夫卡正屬于這樣一類作家,他不是簡單地改變我們的審美、我們的觀念,他改變的是我們的血液和身體。我也正是如此這般將卡夫卡吸納進我的身體,雖然也許只有萬分之一,但卻像一塊鐳,放出巨大的能量,足以使我大膽地拿起筆寫下自己的文字。
卡夫卡曾說過:“文學力圖使事物顯得令人愉快,討人喜歡,而詩人則被迫要把事物高舉起來進入事實、純潔和永恒的領域。”作為一位把小說當做詩來寫的作家,卡夫卡從不妥協,他總是以直接面對絕對之物的精神姿態來對待寫作,他的作品帶給我們的是內在的破碎,精神的震驚,無畏的探索,這也是我學習寫作所追求的目標。在《歌唱與其他》這篇小說中,我想要表達的是對自我的追尋與自我的迷失是同步展開的,一個為另一個提供了契機,而愛情是其中根本性的力量,更廣大的力量,它甚至超越這兩者。不,也許我概括得并不準確,也許我在提起網的時候而把魚兒全都給漏光了,它們正在讀者的手中活蹦亂跳。即使如此,這無疑也是美好的,也是我的榮光。因為將一篇有著特定生理結構、特殊體溫的小說,抽象為一句話,這根本就是一種虛妄。
隨著歷史總體性的結束和神性的遠去,現代人面臨著日常生活的一地雞毛和精神性空虛的雙重夾擊,文學作為一種創造,它的任務不僅僅在于將一種生活范型或人格樣式帶到大家面前,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寫作行為本身所透露出的那種自由本真的氣息。當我寫作這篇小說時,我像對待一個年幼的生命一樣,力圖減少對它的限定和預設,任其自由生長。當我拿起筆,我幾乎只有一個最終的目的地,而中間要怎么走、經過哪些車站,我幾乎完全沒有預想。寫作過程中,思緒如流水瀉地,自由奔流,新的想法、新的意念不斷閃現,從一條水系上長出了新的支流、新的水澤,從而哺育出一片廣闊幽深的地域。這就像國畫上的一棵樹,從樹身上長出了枝椏,枝椏上又分出新的枝椏,不斷向著紙面上的空白延伸。這些小小的枝椏如同感覺的觸突,將即時新鮮的直覺、突然的頓悟與歷史之感、心靈之嘆結合在一起。在這樣一種向著未知不斷生長、不斷嗅探、觸摸的過程當中,主體的自由精神如動脈之中的氧氣,它既是被運輸之物,又使生命機體順暢呼吸,顯得神采奕奕。俄國作家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說:“詞使受擠迫的心靈自由。”這正是我從寫作中所感受到的最美妙之處,而寫作本身帶給我的這美妙禮物,我很樂意將它轉贈給其他人,使它增殖,在所有有幸相遇的心靈上串聯起一個共同的精神性空間。
在我生活的城市,有著眾多縱橫交錯、曲折蜿蜒的小巷子。它們從一條主干道上長出來,就無限地生發開去,幾乎沒有盡頭。當人們順著它走進去,一條巷子的結束,是另一條巷子的開始。你越往前走,就會打開無限多的未知,無限多樣的風景,你不知道與你迎面相遇的是一段精致的園林花窗,還是一處爬滿墻頭的錦繡薔薇,又或者是一座沉默的老橋,正等著你把腳踩在它身上,用新鮮的震動把它喚醒。我常常漫無目的地游蕩在這些小巷子中,隨行隨止,自由散漫,我所希望的是讀者也會像這樣來穿越這一篇小說。
在我看來,文學與世界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審美、修辭的關系,而不是認識、審視的關系。如此一來,世界和現實可以繼續葆有它的豐富與堅硬,而文學也不失它的超越與自由,它們相互平行,相互映照,如同天空與河流的對視。我愿呼喚讀者與小說中的人物一起生活,不是去認識,而是去體驗。無可置疑的是當下的生活已經越來越內在化了,人們一邊在表露自己,一邊卻又藏得更深。在這種情況下,用一塊平面鏡已經無法反映出它的真實面貌,必須用一根內窺鏡,深入到機體的內部,查看器官的蠕動、血液的流向、隱秘的生長,才能探知些許真相。我執拗地將小說的故事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力圖將人們對表象的注意力轉移到對人物內心的變動和糾纏上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敘述、記錄也許是遠遠不夠的,它們仍然是表象性的,不能突破現實的包裝膜,所以我引入了隱喻與象征,突轉與驚異,混沌與危險,利用這些文學杠桿性的手段,牢牢守住一個精神的支點,如隔山打牛一般,勇敢地、無情地實現更深的進入,將現代工業時代包裝膜封存下的心靈現實呈現出來。
我寫下了一個小小的現代精神圖像的寓言,它無疑是幼稚的,但也許是新鮮的,它還在生長,只有當它走到讀者那里時,它的生長才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