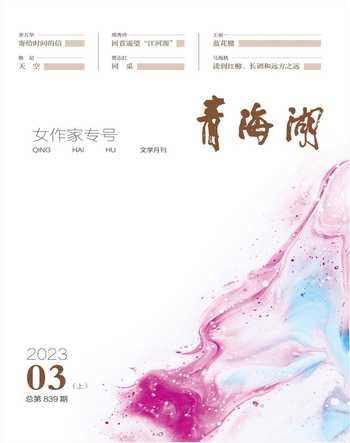回首遙望“江河源”
大約是上個(gè)世紀(jì)七十年代初,《青海日?qǐng)?bào)》副刊編輯王展老師來(lái)到我供職的青海師院(今青海師范大學(xué))院刊編輯室,約我寫(xiě)一篇評(píng)論,隨即將一本《我愛(ài)高原》的詩(shī)集交給我,約定一個(gè)月后交稿。我雖然是《青海日?qǐng)?bào)》的通訊員,但除了寫(xiě)過(guò)一些報(bào)道,只發(fā)表過(guò)幾首詩(shī)歌,從未寫(xiě)過(guò)文學(xué)評(píng)論,能不能完成這個(gè)任務(wù),毫無(wú)把握。翻開(kāi)總后軍旅詩(shī)人時(shí)永福的這本詩(shī)集,立即被他筆下綺麗豪邁的詩(shī)句吸引住了:雪山,草原,峽谷,云朵,太陽(yáng)雨,六月雪;還有那碧波連天的青海湖,遙遠(yuǎn)神秘的海心山……精彩紛呈,令人陶醉。待我讀完詩(shī)集,一篇題為《壯美的高原畫(huà)卷》的評(píng)論順利寫(xiě)出,提前半月交稿。不久,這篇近三千字的文章在《青海日?qǐng)?bào)》副刊發(fā)表。一年后,在王展和劉險(xiǎn)峰
(時(shí)任總編室主任)的大力舉薦下,我從高校調(diào)到《青海日?qǐng)?bào)》文藝部,成為一名心儀已久的副刊編輯,從此,和各路業(yè)余作者們結(jié)下了終生難忘的文字
之緣。
當(dāng)時(shí)正值青藏鐵路破土動(dòng)工之際,鐵道兵七師進(jìn)駐昆侖山下的格爾木,十師進(jìn)駐海西烏蘭和天峻,拉開(kāi)了在世界屋脊修筑鐵路的序幕。那些地方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青海西部,既沒(méi)有紅花綠樹(shù),也沒(méi)有群雁野鶴,峭壁上只有靈敏的黃羊出沒(méi),荒原上只有流浪的野驢漫步……地勢(shì)高寒,空氣稀薄,含氧量不到內(nèi)地的一半。而且氣候變化無(wú)常,一天里可見(jiàn)識(shí)一年四季的景象,讓初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年輕戰(zhàn)士難以適應(yīng)。然而,指戰(zhàn)員們抱著戰(zhàn)勝困難和艱險(xiǎn)的決心,扎下?tīng)I(yíng)盤(pán),揮動(dòng)鎬頭,舉起鋼釬,將一面面戰(zhàn)旗插在工地前,將一根根鐵軌鋪在荒漠上。櫛風(fēng)沐雨的筑路生活催生了火熱的詩(shī)篇,編輯部每天接到的來(lái)稿中,鐵道兵的詩(shī)稿最多,七師的朱海燕、十師的韓懷仁(該作者后來(lái)失聯(lián)),就是那時(shí)嶄露頭角的年輕戰(zhàn)士。
1978年秋天,編輯部派我到格爾木組稿,重點(diǎn)是鐵道兵七師。當(dāng)時(shí),朱海燕是筑路工地上的風(fēng)槍手,他接到通知來(lái)到師部,帶來(lái)了一疊詩(shī)稿,其中有一首《天路剪影》寫(xiě)得很不錯(cuò)。內(nèi)容是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來(lái)到連隊(duì)看望筑路戰(zhàn)士,當(dāng)他吃著戰(zhàn)士們長(zhǎng)期吞咽的壓縮菜,這位曾經(jīng)指揮過(guò)“塔山狙擊戰(zhàn)”的鐵漢竟流下了眼淚,立即作出決定:每個(gè)連隊(duì)每月增加二百斤豬肉,一百斤黃豆,這在物質(zhì)生活還很貧乏的七十年代,真是莫大的福利!
這首熱情洋溢的長(zhǎng)詩(shī)感動(dòng)了我,基本未做刪改,以半個(gè)版的版面在剛剛復(fù)刊的“江河源”隆重推了出來(lái)。朱海燕自此踏入文壇,成為青海作協(xié)“三大軍旅詩(shī)人”之一。
讓我驚嘆不已的是,多年之后,從青藏線起飛的朱海燕展翅翱翔,出版了有關(guān)鐵路建設(shè)題材和其他題材的著作近四十部,摘取了第二屆全國(guó)“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和第六屆“范長(zhǎng)江新聞獎(jiǎng)”以及“全國(guó)報(bào)告文學(xué)獎(jiǎng)”等重要獎(jiǎng)項(xiàng),成為鐵道系統(tǒng)的著名作家。
青海武警部隊(duì)的作家李曉偉來(lái)自陜西關(guān)中,曾在海西香日德農(nóng)場(chǎng)駐守十年之久,對(duì)每一座山巒,每一條沙丘都充滿了感情。他也是從寫(xiě)詩(shī)起步,第一次來(lái)稿題曰“荒原人物”的組詩(shī)就很成熟,由我編發(fā),以頭題位置刊登在“江河源”副刊上,引起讀者好評(píng)。故鄉(xiāng)的陳年舊事和西部的生活積累成為他創(chuàng)作的源泉,他不僅寫(xiě)詩(shī),也寫(xiě)散文、報(bào)告文學(xué)、長(zhǎng)篇小說(shuō)等。轉(zhuǎn)業(yè)到青海電視臺(tái)后,他憑借長(zhǎng)篇紀(jì)實(shí)文學(xué)《昆侖殤》獲得青海省“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后改編為電視劇《魂歸可可西里》,榮獲“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駿馬獎(jiǎng)”。從新世紀(jì)開(kāi)始,他的文學(xué)風(fēng)帆駛進(jìn)了昆侖文化研究領(lǐng)域,將軍人的大氣和詩(shī)人的睿智融為一體,相繼寫(xiě)出了《西王母故地》《觸摸大昆侖》《與大河同行》,這套三卷本的叢書(shū)由軍事誼文出版社出版,獲得青海省人民政府“建國(guó)六十周年優(yōu)秀作品獎(jiǎng)”;根據(jù)《西王母故地》改編的電影紀(jì)錄片《再塑昆侖》榮獲文化部頒發(fā)的“紀(jì)錄片獎(jiǎng)”。此外,他還出版了《柴達(dá)木文史叢書(shū)》三部以及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皇脈》《金魔方》等,可謂成果累累,成績(jī)輝煌。
駐軍汽車(chē)九團(tuán)宣傳干事雷獻(xiàn)和來(lái)自江蘇南通,英姿勃勃,氣質(zhì)儒雅,是一枚帥哥。他被派到報(bào)社文藝部實(shí)習(xí),具體由我?guī)S捎谒言凇敖釉础卑l(fā)表過(guò)詩(shī)作,我就從來(lái)稿中分出部分詩(shī)歌讓他編。小雷文學(xué)基礎(chǔ)比較扎實(shí),看稿認(rèn)真細(xì)心,很快進(jìn)入了角色。九十年代初,他被調(diào)到蘭州軍區(qū)電視劇中心,從寫(xiě)詩(shī)轉(zhuǎn)入電視劇創(chuàng)作,先后編劇或與他人合作寫(xiě)出了十多部電視劇,其中再現(xiàn)長(zhǎng)征的電視劇《大會(huì)師》影響比較大,多次在央視播出,曾獲全軍和全國(guó)“優(yōu)秀電視劇”獎(jiǎng)項(xiàng)。遺憾的是,這些電視劇我未曾觀看,只看過(guò)由他擔(dān)任編劇的電視連續(xù)劇《在那遙遠(yuǎn)的地方》,讓我百感交集,對(duì)他刮目相看。
以上三位青海文壇的“軍旅詩(shī)人”都成功轉(zhuǎn)場(chǎng),各自在新的文學(xué)領(lǐng)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創(chuàng)作成果。
此外,還有一位讓我由衷欽佩的軍旅作家王宗仁,參軍初期,在格爾木駐扎七年,曾駕駛“鐵馬”逾百次穿越青藏高原,積累了大量素材,創(chuàng)作出了有溫度有風(fēng)骨的文學(xué)作品。當(dāng)年我曾編發(fā)過(guò)他的《女兵墓》《走昆侖》等散文。后來(lái)他調(diào)到總后政治部創(chuàng)作室任主任,但仍然牢記著“江河源”的滋潤(rùn),不時(shí)有新作寄來(lái)。九十年代初,我隨夫調(diào)到重慶的一家報(bào)社,重操舊業(yè),卻沒(méi)有再為他編發(fā)過(guò)作品。
2002年,我被推選為重慶市散文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他是中國(guó)散文學(xué)會(huì)的副會(huì)長(zhǎng)兼秘書(shū)長(zhǎng),重新接上了一度中斷的聯(lián)系。
2011年,他以《藏地兵書(shū)》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我第一時(shí)間送去熱烈祝賀。隨后,他在百忙中為我的散文集《西部神韻》寫(xiě)了序言。2012年8月,我們?cè)趶V西北海市舉辦的第五屆“冰心散文獎(jiǎng)”頒獎(jiǎng)會(huì)上見(jiàn)了面,他為我頒發(fā)了獎(jiǎng)狀,讓我倍感榮幸。2013年,他應(yīng)邀來(lái)到重慶長(zhǎng)壽古鎮(zhèn),參加了由我主持的第三屆“西部散文家論壇”,并在大會(huì)上作了精彩演講。
王宗仁老師已經(jīng)年逾八旬,仍然筆耕不輟,出版著作四十多部,可謂軍旅作家中的標(biāo)桿!但他一如既往地謙虛謹(jǐn)慎,樸實(shí)敦厚,令人可親可敬。
當(dāng)年的“江河源”上,不僅閃耀過(guò)“紅五星”,而且云集過(guò)“藍(lán)工裝”。一大批來(lái)自山川鑄造廠、海山軸承廠、西寧鋼廠、西寧鐵路分局等知名企業(yè)的工人作者在勞作之余,創(chuàng)作出了體裁不同,風(fēng)格各異的文學(xué)作品,大多發(fā)表在《青海日?qǐng)?bào)》副刊,為“江河源”平添了幾多翠色,幾縷芬芳!印象比較深的是火車(chē)司機(jī)程楓的短篇小說(shuō),不僅格調(diào)高昂,而且文字流暢,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很快在青海文壇脫穎而出,被省作協(xié)選送到魯迅文學(xué)院深造,寫(xiě)出了數(shù)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后來(lái),鐵路部門(mén)年輕作者馮文超的散文自成一格,多次刊發(fā)于《人民日?qǐng)?bào)》“大地”副刊。
從山川機(jī)床廠走出的“青工詩(shī)人”最多:劉明欣、王度、張義濤等,最有實(shí)力的是金元浦和李鎮(zhèn),他倆經(jīng)常聯(lián)名發(fā)表詩(shī)作,很快聲譽(yù)鵲起。后來(lái),他們一起考進(jìn)大學(xué),又一路奮進(jìn),考上了北京高校的研究生,金元浦成為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導(dǎo),李鎮(zhèn)當(dāng)了中國(guó)國(guó)際廣播出版社總編輯。
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農(nóng)民作者比較少,但是寫(xiě)農(nóng)村題材的作者不乏其人,湟源的井石、互助的蔡西林、大通的張英俊、貴德的軒錫明都有生活味濃郁的作品在“江河源”發(fā)表。特別是湟中的滕曉天和韓玉成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正在青海師大中文系讀書(shū)的滕曉天根據(jù)親身經(jīng)歷,寫(xiě)了一篇接地氣的短篇小說(shuō)《送禮》,將青海農(nóng)村的鄉(xiāng)情民俗描繪得有滋有味,活靈活現(xiàn),突出表現(xiàn)了八十年代農(nóng)村的新變化,新氣象。特別是作者對(duì)青海方言駕輕就熟,小說(shuō)寫(xiě)得妙趣橫生,引起本土讀者的廣泛關(guān)注和好評(píng)。
緊接著,韓玉成也用青海方言寫(xiě)出了短篇小說(shuō)《賬主兒尕七斤》,塑造了一個(gè)好吃懶做,靠救濟(jì)款度日的“貧困戶”,為農(nóng)村人物畫(huà)廊增添了一個(gè)獨(dú)特的形象,一時(shí)引起讀者熱議。由于作者時(shí)任魯沙爾公社青年干事,熟悉農(nóng)村的人和事,從大量生活素材中捕獲了“尕七斤”這個(gè)人物,他憑著出身好,以貧困為借口,一再向組織申請(qǐng)救濟(jì)款,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大家的公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我至今記得尕七斤的“口頭禪”:“吃好點(diǎn),穿爛點(diǎn),見(jiàn)了干部走慢點(diǎn)。”還記得這篇小說(shuō)被評(píng)為本報(bào)“年度優(yōu)秀作品”。之后,韓玉成又寫(xiě)出了《荒地》等頗有深度的中篇小說(shuō),出版了小說(shuō)集《男人的地平線》。如果堅(jiān)持寫(xiě)下去,肯定會(hu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面世,可惜,后來(lái)由于工作的變動(dòng)和職務(wù)的晉升,他忍痛割?lèi)?ài),放棄了創(chuàng)作,至今引以為憾。他在發(fā)給我的微信中說(shuō):“如果再給一次選擇的機(jī)會(huì),我還是選擇文學(xué)。”
正當(dāng)我寫(xiě)這篇稿子之時(shí),遠(yuǎn)在青海貴德的張順祥打來(lái)了拜年電話,得知他在縣委宣傳部供職多年,已經(jīng)退休。兒子考上了中國(guó)武警部隊(duì)工程大學(xué),已成長(zhǎng)為副團(tuán)級(jí)干部;女兒考上了青海醫(yī)學(xué)院,現(xiàn)在貴德縣醫(yī)院當(dāng)大夫,一家人生活十分美滿……
驀地,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一幕往事:那是一次頗具規(guī)模的“青海省各族青年作者創(chuàng)作座談會(huì)”,聚集了來(lái)自省內(nèi)各州縣及西寧地區(qū)的優(yōu)秀青年作家,我也應(yīng)邀赴會(huì),既是代表,又是記者。就在那次會(huì)議上,認(rèn)識(shí)了來(lái)自貴德縣河陰鄉(xiāng)的農(nóng)民作者張順祥。他拄著雙拐,艱難地走在一群生龍活虎的年輕作者中間,格外引人注目,也引起代表們的廣泛同情。為了寫(xiě)好大會(huì)側(cè)記,我特意采訪了他。從交談中得知,他從小熱愛(ài)學(xué)習(xí),喜歡讀書(shū),不幸的是,上到小學(xué)四年級(jí),他突發(fā)脊髓炎,農(nóng)村缺醫(yī)少藥,未能及時(shí)救治,病情越來(lái)越嚴(yán)重,直至失去了行動(dòng)能力。他萬(wàn)分不舍地離開(kāi)課堂,輟學(xué)在家,一邊干點(diǎn)力所能及的農(nóng)活,一邊在土炕上自學(xué),早就學(xué)完了中學(xué)語(yǔ)文課本,又讀了一些課外書(shū)籍,自己也練習(xí)寫(xiě)作,已在本縣的內(nèi)刊和《青海青年報(bào)》發(fā)表了十多篇作品……
我和文友裴林都喜歡“管閑事”,找到時(shí)任省團(tuán)委書(shū)記的李沙鈴,商量為張順祥治病之事。他是這次會(huì)議的主持者之一,又是作家,同樣很關(guān)心張順祥,當(dāng)即答應(yīng)派人聯(lián)系醫(yī)院和床位,讓張順祥會(huì)后住進(jìn)了青海省人民醫(yī)院。經(jīng)過(guò)三個(gè)月的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小張的病情大有好轉(zhuǎn),醫(yī)療費(fèi)用也全部報(bào)銷(xiāo)。出院時(shí),他扔掉一根拐杖,能夠靠單拐行走了。回到貴德后,他更加勤學(xué)苦練,朝耕暮鋤,一篇篇凝聚著心血和汗水的作品發(fā)表在《青海日?qǐng)?bào)》《青海湖》《中國(guó)青年報(bào)》《中國(guó)婦女報(bào)》
《中國(guó)殘疾人》《青春》等報(bào)刊,獲得各種獎(jiǎng)項(xiàng)四十多次。他的命運(yùn)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被共青團(tuán)青海省委授予“新長(zhǎng)征突擊手標(biāo)兵”“青海省十佳自強(qiáng)模范”,貴德縣破格錄用他為公務(wù)員。
張順祥重情重義,不忘當(dāng)年扶持過(guò)他的人,在多篇文章中都表達(dá)了感恩之情。他的散文集《傲立人生》就是請(qǐng)裴林寫(xiě)的序言。他在發(fā)給我的微信中說(shuō):“我最早的一篇散文《迎著朝陽(yáng)》,就是由您修改發(fā)表在“江河源”上,我今天取得的一切成績(jī),都離不開(kāi)當(dāng)年您的扶持和幫助。”我相信這是由衷之言,也是對(duì)我這個(gè)老編輯的最大慰藉和最高獎(jiǎng)賞,我為此而自豪!
邢秀玲 生于青海湟源,現(xiàn)居重慶。中國(guó)作協(xié)會(huì)員,高級(jí)編輯。出版散文集《情系高原》《西部神韻》等五部,作品入選《21世紀(jì)中國(guó)經(jīng)典散文》等幾十種選本。曾獲“青海省建國(guó)35周年優(yōu)秀作品獎(jiǎng)”“首屆重慶散文獎(jiǎng)”“首屆四川散文獎(jiǎng)”,第五屆“冰心散文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