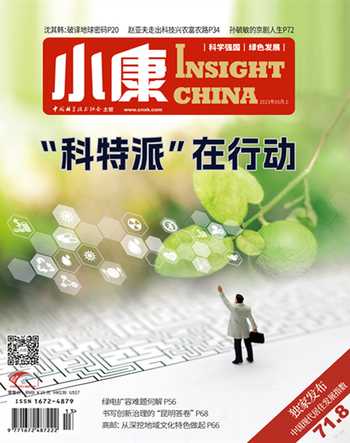程存旺:生態農業的星火燎原
孫媛媛
長期扎根于一線,程存旺表示,基層農民接受到了先進技術、先進理念,創造了財富,這種案例比比皆是。

程存旺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是農業經濟管理碩士、可持續發展管理博士,師從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目前是好農場品牌的創始人兼CEO、分享收獲CSA(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農場聯合創始人。好農場圍繞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憑借溫教授團隊多年鄉村振興的理論研究和項目實踐經驗,為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鄉村振興的前期咨詢、產業規劃設計和產業托管運營的全流程專業化服務,并在此過程中注重產業與生態農業科技的結合,目前已在北京,山東青島,安徽合肥,四川成都,福建福州、莆田、泉州、南平,廣東河源,河北唐山、保定等城市為地方政府鄉村振興的項目提供多種服務。
從2022年到今年9月,是程存旺受聘成為科技特派員的第一個周期,服務區域是福建省和吉林省,服務的領域是生態農業三產融合。
在這兩年作為科特派的服務經歷中,程存旺說:“從高校習得的知識,加之自己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對于其他一線生態農業創業者來說是很好的借鑒,我非常樂于參與其中,也傳授,也獲益。”
將生態領域經驗“播種”四方
程存旺接受《小康》·中國小康網采訪時表示,自己選擇農業作為終生事業的核心動力來源于出生自農村家庭,其父親是工人,母親是農民,親戚也大都生活在農村。“小時候對于農村的印象很美好,并且有身份上的認同,我覺得應該服務于他們。”上大學后,他就開始關注中國農業農村的政策,后來開始返鄉調研,想做一些能夠盡自己力量去改變農村衰敗趨勢的事情。碩士階段,程存旺作為校方代表在“小毛驢農園”實踐,打造北京市第一個社區支持農業的樣板,系統地學習生態農業的技術、生態農場的管理模式,直到學習整個生態農業產供銷全產業鏈。
從2008年開始做生態農業到現在已有15年時間,程存旺表示,他個人擅長與生態農業相關的技術和管理,輸出給有需要的生產者、企業、農戶、合作社、村集體,為他們提供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指導,以及產品流通過程中的資源對接,受聘為科特派后更與其研究方向有了更好的結合。“科特派提供了更多與同行業不同創業者接觸的機會。此外,可以將我們的技術、經驗跟更多的生產者鏈接和結合。”
程存旺目前正在指導的是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的兩家企業,一家從事生態健康零食加工,協助其建立生產標準,并拓寬市場銷售渠道。另一家是做有機種植的農場,協助他們完成生態技術體系的建立,從選品到種植,以及后續的銷售渠道的對接。“生態農業的技術需要更多的人掌握和推廣,才能把更大層面的生態事業做得更好。”
南平是程存旺的老家,他非常有興趣幫當地的生態農戶擴大產能,達到銷售標準,還親身參與農場的創建過程,提供技術指導。目前,經過幫扶企業的產品在北京“分享收獲”、珠海“綠手指”等農場的銷售已經取得非常好的業績。
程存旺認為,生態農場有很多需要跟實際工作結合的點,首先是選品,不僅要符合當地的種植環境、氣候條件,更重要的是有市場。“我們建議種植當地有傳統特色的水稻品種。也建議稻田養殖小龍蝦,還推薦了學習稻田養殖小龍蝦的農場。”關于怎樣才能防治病蟲害,他也給幫扶企業提供農資采購的建議,相關的清單也一并發送給對方。其中也包括產品加工方向的建議,農戶種了甘蔗,程存旺教他們怎樣加工生態紅糖,怎么把甘蔗賣到北京,怎么包裝等,給予全程指導。
程存旺屬于國內比較早在生態農業領域創業的人,他重新建立了一套有別于傳統農產品,更符合生態農產品流通的市場渠道、市場體系。“傳統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加上一級批發商、二級批發商,再到商超、銷售終端,這套傳統的農產品流通體系,比較適合常規的大宗農產品。生態產品不使用化肥農藥,如果通過常規的流通渠道去售賣,無法給出符合生態產品的價格。常規的農產品便宜,而生態農產品成本高,價格體系在傳統流通渠道中是不被接受的。傳統流通渠道也無法辨別真生態還是假生態。我們不得不重新開辟符合生態農產品的全新流通系統,能夠接受生態農產品的高定價,并且能夠有效杜絕造假的生態農產品市場。”程存旺表示,這個過程中歷經十幾年的摸索,不斷試錯,如今才擁有了符合生態農產品的定價體系和追溯體系的全新流通渠道與市場體系。
在受聘成為科技特派員后,程存旺很愿意傳授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可以避開我們踩過的坑,給予對方合理的建議,比如設施建什么樣的,達到什么標準。有的設施做得過大,反倒不利于生產;有的品種不太實用,消費者接受度小……點滴經驗都會跟幫扶的單位進行交流。”
在程存旺所到訪的農場,他發現初創者大都比較缺乏生態農業的技術以及市場渠道資源。“這方面有疑問找到我,基本上都能解決,雖然我也不是萬能的,比如生態養殖是我的薄弱項,但我會為他們對接專門做生態養殖的專家,為他們提供服務。”對于幫扶的生態農產品農戶,程存旺都會幫他們對接銷售渠道,有的產品80%的銷量是由他對接的渠道帶來的。“科特派初代以傳授技術為主,某種程度上我把技術、產品的開發以及后續銷售,一套系統全部輸出。如果農戶能夠按照技術標準產出好的產品,那也意味著為我們提供了貨源,我們也可以通過他們的產能來擴大銷售額。”
在北京積累的技術、商業模式能夠復制到外地,既有挑戰也有學習的過程。程存旺表示今年疫情管控放開后,到福建出差的次數明顯增多。
“把脈開方”為莆田荔枝賦新活力
除了服務南平,程存旺還參與了莆田城市中心公園——綬溪公園的農業公園板塊的運營。綬溪是木蘭溪最大支流,該公園有得天獨厚的天然、人文、地理等環境優勢,是一個以5A標準打造的城市中心公園。其中農業公園板塊現狀是除了有基本農田外,還有大量的荔枝樹,程存旺認為公園可以打造成全國為數不多的市民可以參與的農業公園。在得到莆田政府支持下,該公園打造成CSA社區農業和荔枝產業化為主的項目。
莆田荔枝是福建省莆田市特產,中國國家地理標志產品。莆田荔枝始于唐代,其味香甜、醮核率高,具有止渴、滋補功效。宋代蔡襄曾寫下世界上第一本《荔枝譜》,稱興化荔最為奇特。后來,荔枝樹又被莆田定為市樹。郭沫若20世紀60年代初在莆田考察時,曾題下“荔城無處不荔枝”的詩句,盛贊莆田荔枝。
程存旺觀察到現今的莆田荔枝與歷史傳聞中的荔枝差別很大,眼前實地的荔枝樹情況是部分荔枝種植的密度過大,且樹形奇特,朝天上長,有的甚至高達十幾米,無論是采摘還是管理都變得非常棘手,甚至有危險性。因過度密植,頂部少量有樹葉,產能也非常低。
莆田的荔枝歷史上很有名,品質極好,莆田的別名叫荔城,現在還有荔城區,但是荔枝產業基本已經快消亡了。“我們說到荔枝首先想到的是廣東荔枝,像妃子笑、三月紅、桂味、掛綠、糯米糍、香荔……現在莆田這樣的荔枝在同類市場上沒有競爭力,所以我們也想就這個產業再做一些探索。”
程存旺和團隊進行實地考察后,發現有可以提升改進的空間,但是否需要改造則存有爭議。有關部門認為荔枝樹沒有問題,盡管樹形有些奇特,可仍具有一定的觀賞性,哪怕不結荔枝僅用于觀賞也可行。而程存旺認為,經過改造后的荔枝樹,既能保持觀賞性,又能讓產能得到恢復。
經過努力,莆田市政府也支持程存旺的想法,“首先,希望把荔枝重新進行矮化培育,讓它恢復產能。其次,延伸荔枝的產業鏈。”莆田有四大名果,除荔枝外還有龍眼、枇杷、柚,都面臨著產業發展的瓶頸。“政府也希望我們能有一些創新和突破,提升整個產業層次。”程存旺打算未來對莆田荔枝進行開發,比如向荔枝啤酒、汽水、冰淇淋等衍生產品進行延展。
生長了幾十年的荔枝樹,要將它的生產能力重新培育出來,過程非常具有挑戰性。程存旺講述了參與荔枝矮化復壯的過程:“原來一直朝天上長的枝條已經老化,給它‘截肢‘砍頭,讓它降低高度,保留3~4米,它會重新生長出新的枝條,新的枝條引導著垂下來,往兩側向下生長,整個塑型就會變成球狀,這樣掛果的枝條就多了,產能也隨之提高,過程中要注意養分、水分以及病蟲害的防治。矮化是為了接受更多的陽光,有更多可以掛果的枝條。”
強化產學研融合落地生“金”
當問及科技特派員工作,是否是一種以服務生產促教學、科研,以教學和科研提升服務能力的良性循環?程存旺肯定地說:“這是顯而易見的。所謂教學相長,作為農業科技人員,我們在創業中積累的技術,在跟新的創業者接洽的過程中,對于我們自身也是非常好的學習過程。我所接觸到的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大學、福建農林大學的科技特派員們,他們更是有這種感受,實驗室里研發的技術能不能在田間地頭得到應用,甚至形成一個產業,得在生產實踐中去接受檢驗。一個科研工作者,要提升自己的學識,檢驗自己的認知,必須在實踐中進行。”
科技特派員制度為解決“三農”問題而生,這項創新實踐被時間證明了人才與科技對農業所能貢獻的力量之大。當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急需更多的優秀人才,推動新時代科技特派員制度更好落實,充分發揮科技創新人才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長期扎根于一線,程存旺表示:“基層農民接受了先進技術、先進理念,創造了財富,這種案例比比皆是。科特派的模式也歷經多次迭代,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力且雙向帶動的事情。”
接受采訪時,程存旺不久前剛和科技特派員制度的創始者、原福建省副省長李川同志進行過交流。李川表示,目前科特派已經涌現出4種不同的服務模式,不單純是20年前簡單的技術輸出,多種力量相互支持,高位嫁接國家農業部、國家農科院、省級農科院等科技資源,成體系輸出,涵蓋技術、品牌、市場渠道等,這樣可以令被幫助的對象能夠行穩致遠,更快速提升獲得成效。
作為一名科特派新人,程存旺坦言,他更看重的是可以與自己扶持起來的生產者未來在產業鏈上進行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就會有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