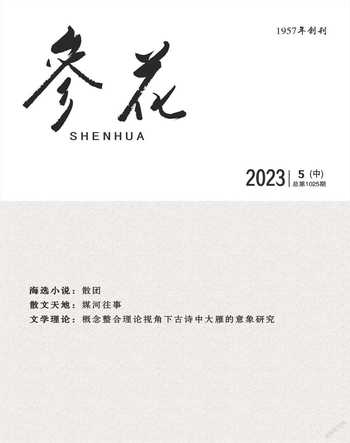走筆黃河
黃河是什么?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很難用簡單的幾個詞來概括它的全貌。有著太多歷史記憶和文化烙印的九曲黃河,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而我,愿意在有限的視角里,用中國畫中勾皴擦染點的傳統筆法,慢慢描繪出山石泉澗、云霧森林,讓胸中的大塊噫氣隨著狀如龍蛇的筆墨自由游走,將一幅站在黃河之巔的寫意山水幻化成眼前的萬里山河。
勾筆:天下黃河貴德清
我們的心底都有一個夢幻般的故鄉。和所有的江河一樣,黃河的源頭也是清澈的。位于巴顏喀拉山麓的黃河源,一定有著純凈剔透的水花,就像冰山上的來客。可惜我沒有去過黃河源,那片高峻神秘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是我心中企望,卻難以到達的遠方。我只能在想象中勾勒黃河水的晶瑩與曼妙,由涓涓細流,一點點變寬變大,匯入兩顆綠寶石般的湖泊——鄂陵湖、扎陵湖,再流出一條清澈的上古之河,繼而延宕成我們民族古老而璀璨的文明傳說。
不過,我始終沒有見到黃河上游真正的模樣。直到我來到了青海——黃河第一個流經的省份。
那是我去參加一家雜志社組織的夏令營活動。游玩完青海湖,向東,汽車蜿蜒盤旋,一路穿行在崇山深谷之中。
起初的風景比較荒涼,經過一輪的連續下坡,視野逐漸蒼翠起來,青山如黛、牛羊成群、樹林繁茂、人煙稠密,令人忘了這是在西北青海,仿若中原氣象。
導游說,前方是貴德,號稱青海的江南,氣候溫潤,海拔低平,所以不一樣,不過這里還有江南沒有的風景,看路邊。
但見峰巒如削、山石似鐵、溝壑叢集、寸草不長。有鉛灰色,有赭紅色,與周圍的綠樹人家構成了奇異的組合。原來那是丹霞地貌。
印象中,北方的丹霞地貌以甘肅張掖聞名于世,沒想到,在這青海高原也有,真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嘆為觀止。但更令我意外的,是前方見到的一條河流。
我在一座鐵橋邊下車,久久駐足凝望。遠方,是連綿的群山,黃中透紅的丹霞地貌,像燃燒的火焰,映照在藍天蒼穹之上。近處,是大片的水中綠洲,分散在廣闊的河道之中,倘若不加提示,不知道已身在黃河,不禁會聯想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或“所謂伊人,在水之湄”的詩情畫意,那些來自《詩經》,帶著潮濕和溫度的先民歌唱。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黃河。我沒有想到,眼前的黃河竟是如此的清澈平靜,與想象中的混濁蒼黃迥然不同。它全然沒有怒濤滾滾的脾性,水面寬廣、舒緩,映著兩岸蓊郁的植被和西天的夕陽,靜靜地流向遠方。
這是真正的母親河。在生態未被破壞,水土未曾流失之前,她原本就是這番模樣,襟懷坦蕩、儀態雍容,甚至,兼具幾分南方河流的秀媚。她超越了時空和歷史,將千萬年的乳汁養分無私地奉獻給蒼生黎民。
再次見到黃河,是第二天的上午。我們驅車離開住宿的貴德縣城,來到一處開放的黃河景區。這里有更長的岸灘,更古老的鐵橋,更密集的船艇,一派典型的黃河風情。我見到岸邊立著刻有“天下黃河貴德清”七個大字的石碑。
我們登上一艘快艇。黃河之水在身旁快速掠過,我與母親河從未如此親近過。白浪飛卷、快意橫生、夾岸綠樹、藍天白云,此情此景,讓我頓有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之感。我完全想不到黃河能給我帶來這般豪氣干云的感受,仿若身處湘江,帶著永不褪色的青春激情,一路劈波斬浪,激揚人生。
這是一部如風行水上的少年中國說。它還原了我們民族理想的摹本——黃河之水天上來。也唯有黃河之水天上來,才能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美哉我少年中國,壯哉我中國少年,“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
在貴德,我見到了一條來自上古的清澈之水。
皴筆:塞上江南
我無數次想象著這片土地的模樣。為什么是這里,得到了黃河最多的垂青和眷愛,為什么是寧夏,讓遙遠、偏僻,帶著蒼涼底色的北國,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譽。
我驚詫于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地理版圖。沙漠、高山、大河、綠洲,紅與黃,灰與綠,大漠孤煙,長河落日……對比鮮明而和諧共生,歷史與現實相互交融滲透,閃爍著一種奇妙的光芒。
源自一次義無反顧的北伐。呈巨大幾字形的黃河,可能自己也沒料到,正是由于她的勇氣和果敢,才贏得了如此豐厚的回報。這里,阡陌縱橫、平林如織、人煙輻輳、車馬駢闐,仿若鋪開的巨大而平坦的宣紙,隨著一滴黃河水落在紙的中央,便迅速洇開絢麗的豐收之花。
那朵花盛開著故鄉的氣息。我會聯想起小時候從地理課本學寧夏平原時的場景。那些樸素的文字和插圖,令我對塞上江南充滿了神往,盡管我身在魚米之鄉,卻不自覺地對那遙遠的西北邊地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甚至希望我就生長在那里。所謂塞上江南,也就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了相同的意味,都成為一種兒時祈盼,卻難以實現的夢想,它與課本里氤氳的油墨香味交織一起,在記憶里散發著歷久彌新的芬芳。
因為畫面太美,不忍打破這早已定格的初心印象,所以我決定以鳥瞰的視角,游歷令我魂牽夢縈的塞上江南。應該要感謝如今發達的資訊手段,能讓我自由翱翔于天上人間。正如《中國國家地理》展示的那些精美畫頁,我看見大地躍動著生動宏富的調色板,它們條分縷析、精耕細作、一針一線繡出豐足祥和的人間康樂圖。
我看見一條巨龍馱著希望在緩緩前行。進入寧夏平原的黃河水略顯橙紅,深沉的外表下蘊含著豐富的營養,又像擎舉著明艷的火炬,照亮這一片熱切的天空。我看見,一旦離開山脊,離開沙嶺,哪怕只有一小塊土地,只要浸潤了黃河水,都披上了一層蓊郁的綠色,那些被黃河之唇親吻的綠色,與周圍近在咫尺的沙漠的蒼黃和禿山的鉛灰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這寥落的西北大地猶顯彌足珍貴,讓人不得不感慨黃河母親的偉大和神奇。
我看見黃河水繼續著化學反應。越往前,風景越秀麗,感覺越細膩。樹木成林,水網密布,一塊塊方正整齊的農田,像綠色的錦緞,平鋪在廣袤的原野之上,就連黃河水也卸去了黃色的外衣,變得青碧透亮。這樣的黃河灌區,倘若不仔細分辨,真的就和江南水鄉沒有太大區別了。在遠處,鄉村發展成城鎮,城鎮又聚變為城市,順著發達的交通駛上時代的快車道,最后,眼里出現一顆又大又亮的塞上明珠——銀川。
天下黃河富寧夏的故事由此達到高潮。因為黃河,蕭瑟的賀蘭山有了依托,因為黃河,岳飛壯懷激烈的《滿江紅》有了支點。踏破賀蘭山缺,這里是起點,也是歸宿,引發人們內心強烈的共鳴。
黃河也就擁有了立體的飽滿豐盈。在更高處,黃河徹底打開了我們的視野,奔流不息的河水縈繞成長長的綢帶,扎系在山嶺之巔、沙漠之心,以及每一處凸起醒目的地方,它讓一幅平淡無奇的山川地形變得濃墨重彩,它讓一幅了無生趣的風俗人情從此獲得了靈魂。
擦筆:奔騰的壺口
遠遠的,我聽見了轟隆隆的聲音。于是,加快了向前的腳步。
但沒有見到想象中的壯觀場面。只見到一面不太陡的石坡,有黃色的河水傾瀉而下,落進一道不寬的河溝里。
石坡是對岸山體的延伸。奔騰的河水自東向西,而非自北向南下落,而且越向前走,水流越細,有一段甚至變成了一道道分割的小水簾,像下雨天從檐瓦間自然落下的水柱。腳下的河溝更是窄得僅有數米寬,讓我不禁懷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難道鼎鼎大名的壺口瀑布,只是一條匯集了若干個并不大的水柱的小水溝而已?
我當然錯了。在路的盡頭,我見到了真正的壺口瀑布。
萬馬奔騰、暴風疾雨、雷霆萬鈞。來自黃土高原深處的喉嚨,盡情抒發著大自然的天籟之音。原來,我起初見到的一條細流,只是若干條水流中的一支,現在,它們終于匯聚一起,沖破了那道狹窄的隘口,發出最嘹亮的爆破音。
壺口瀑布不算寬,落差也不大,卻在華夏民族的人文史和心靈史上,寫下了最為恢宏壯麗的篇章。濁黃咆哮的河水,猶如沸騰的地火,貼著大地瘦骨嶙峋的脊梁,合奏鐵與火洗禮的黃河大合唱。經歷了漫長的旅途,經歷了太多的含辛茹苦,黃河將一路的曲折磨難盡皆隱藏,只有在到達路的盡頭時,才潑墨山水般掀開故事的高潮。
如果與南方的黃果樹瀑布相比,壺口瀑布也許體量不算大,但是,這絲毫影響不了它的厚重分量。河流是文明的血脈,黃河則是孕育中華文明的血脈,流經中國北方的黃河,從高原、荒漠、戈壁、風沙中一路走來的黃河,猶如大地上不屈的精血,在苦寒和貧瘠的抗爭中閃爍著耀眼的生命底色。
有時候,我把黃河想象成大地的傷疤,或者勒痕。是的,穿行于刀鑿斧劈的晉陜大峽谷,黃河已把自己忍耐到了極限,對外界的需求到了極低,甚至化身為不起眼的涓涓細流,正如我看到的那樣。但這正反映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隱忍、質樸、謙遜,縱然身體已瘦如竹片,意志卻堅如磐石,在越來越深的勒痕中,始終指向一個光明的出口。
壺口就是那道光。是卸下了千斤重擔,豁然開朗的那道光。這道光如此質樸而粗獷,它用黃沙淘盡了我們的汗珠,用泥塵洗刷了我們的淚水,它帶著我們向曾經的喜與樂、悲與傷告別,在將往事一飲而盡的決絕姿態中,迎來一個從未有過的寬廣未來。
我看見了遠方。盡管天色陰沉,瀑布激起的巨大水浪迷矇了視線,我仍然看見了更遠的遠方。在壺口下游,有著同樣天下聞名,也同樣狹窄險峻的龍門。而黃河一旦沖出龍門,便從僅僅幾十米的寬度猛然擴展到十多公里,就像在巷道中摸索的人們,推開了通向世界的一扇大門。
那是整條黃河最寬的地方。浩瀚、磅礴、博大、雍容,所有贊嘆的形容詞,在這一刻噴薄而出,為一條大河的執著與堅守,為一個民族的輝煌感動得熱淚盈眶。在這一刻,我們終于能感受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視野和胸懷,何須登高,只要張開想象的翅膀,心中就有一座鸛雀樓。
而欲窮千里目的原點,是壺口。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壺口,野馬者、塵埃者洶涌而過的壺口,永遠以奔騰不息的姿態,眺望靈魂中的詩和遠方。
染筆:桃花峪的寓言
提及河南,便無法不與黃河發生聯系。在天下之中,在九州腹地,數千年來,黃河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難以用一兩句話加以概述。況今之黃河,與古之黃河相比,是桀驁依舊,還是已然溫馴平和?
謎語像一柄長劍,謎底懸掛于劍尖之上。鄭州黃河風景區,距離市區有三十公里的路程。我沿著西去列車的窗口一路尋覓,只為迫切知道黃河在莽莽中原留下了何種印跡。我腳下的鄭州,包括下游的濟南,地處黃河岸邊,卻不屬于黃河流域,這是一種奇怪的悖論,驅使我盡快找到答案。
黃河風景區終于走進了眼簾。我坐上氣墊船,這是專門適用于黃河水文狀況的水陸兩用船。氣墊船發出巨大的轟鳴,像一只鉚足了勁兒的怪獸,以距離水面六七十厘米的高度,向著黃河深處咆哮而去。
坐在小學課本里就學過,但沒體驗過的氣墊船里,蒼涼、寥廓、落寞這些詞,很快代替了短暫的興奮。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有些英雄氣短的黃河風景圖。水很淺,不時可見裸露的沙洲,水面也不算寬,對岸并不遙不可及。水自然是黃色的,兩岸的風景也幾乎都是黃色的,只有些許的草綠點綴在不算高的山丘之上。
黃土地,黃水謠,黃河在鄭州,在河南,在整個下游,可能都是這般場景。沒有想象中的波瀾壯闊,也沒有想象中的芳草萋萋,我眼里的黃河,沒有田園牧歌式的寧和柔美,外表的風平浪靜之下,掩藏的是一顆不知疲倦的悸動之心。
逆流而上。氣墊船掠過水流和沙洲,向前方繼續駛去。河面稍狹窄了些,岸邊山崖稍高了些,不多時,船擱淺在一片挺大的沙灘上,上岸。
這里是桃花峪。現在,這里是黃河中游與下游的分野。中學學過的地理知識告訴我,孟津,由此再上溯幾十公里的地方,是黃河中下游的分界點。桃花峪取代孟津,除了地形地貌的原因外,也許,還在于一層寓意。
桃花峪以下,黃河正式成為懸河。黃河的蒼涼,黃河的悲慨,黃河的災害不斷滋養生民,組成了一種無比復雜的黃河情結。人們愛黃河,從四面八方奔來,為的是一睹母親的真容,不管它賦予子孫后代怎樣的饋贈。而人們愛黃河,又得小心地筑上大壩,如給蒼龍縛上了手腳,使其馴順地獨自東流,成為唯一沒有下游來水的世界大河。
我佇立在黃河岸邊。面前是蕭瑟的風景和落寞的河水。期待中的浪遏飛舟如過眼云煙,幻想中的水禽芳草不見蹤影。這不是理想的游樂園,不是純粹的風景區,也不是我在青海見過的那條清波蕩漾的上游黃河,這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黃河,這是寫進歷史和文化內核的黃河,它不會溫情脈脈或風和景明,除了視覺上的單調灰暗外,還在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刺痛和思索。
這是黃河母親留給每一個華夏兒女的寓言。我的身后有一座山,刻有“鴻溝”兩個鮮紅的大字,提醒人們這是當年楚漢相爭的那條分界線。出現在這里的鴻溝,更為黃河中下游的分野增添了意味深長的注解。無論在歷史故事里,還是在民族心理上,鴻溝在時刻警醒著人們,黃河的災難史,黃河的辛酸史,不要在我們的將來重演,抹平黃河中下游之間的鴻溝,是當代人,也是我們的子孫永不放棄的偉大使命。
點筆:黃河口的大音希聲
我在最美的季節來到黃河口。此刻,綠草依依、蘆花勝雪,不時有丹頂鶴、蓑羽鶴從茂密的草叢中振羽而出,在低空盤旋,又撲棱棱飛向遠方。
這里是鳥的天堂,是絕佳的濕地公園,有碧波淺水、樓臺長廊,有澄澈天空、和風輕拂,對于休閑度假來說,自是適宜不過,可唯獨不像我心中的黃河口。
也許是沒走對地方。繼續向前,我看到了裸露的泥灘,棕黃色的泥灘,這是黃河特有的顏色,與我的想象接近了些。再向前,我看到了一條濁黃的大河,河邊有一座瞭望樓,于是登了上去。
視野一覽無余。奔騰了五千四百六十四千米的黃河,即將迎來它的終點。這里的河面很寬,也很平靜,遠遠地,可看見對岸的綠樹,一副平林如煙、漠漠廣野的模樣,這是一條雍容渾樸的黃河,也是一條謙謙君子般的黃河,不再有原始野性的桀驁不馴,而是像所有河流一樣,最終平靜地奔向大海。
最鮮明的標志,是它依然保持了蒼黃的本色,與我們的土地一樣的顏色,也是與我們的皮膚一樣的顏色。聽說可以坐游船,從這里抵達入海口,運氣好時,可以清晰看到河水與海水黃藍相融的奇觀,不過我無意前往,我想眼前就已經夠了。
迥異于大多數河口地區,這里看不到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繁忙場面,偌大的河面上甚至看不到一條船,這是一條安靜而平直的大河,關于九曲黃河的所有跌宕起伏和喜怒哀樂,統統尋不到一絲蹤跡。而令人欣慰的是,穿越整個中國北方干渴的土地,眼前的黃河雖然累了,卻始終沒有斷流,就像始終擔著一副鋼鐵的肩膀,托著一個民族向著大海的方向一路前行。
是的,這里是黃河三角洲。這片六千多平方千米的扇形三角洲,猶如巨大的海中蓮花,仍在依靠黃河母親最后的乳汁,不斷地拔節生長。或許,這源于玄鳥生商的悠遠傳說。數千年前,從一只大鳥中降生的祖先就居住在黃河之濱,開啟了東方文明,而今天,繼續向海中掘進的黃河三角洲,又像玄鳥張開的垂天之翼,沿著后代們凝聚的磅礴意志展翅翱翔。
遠遠地,我仿佛看到了一排鋼鐵的身軀,那是勝利油田林立的井架。一群可愛的人,將來自大地的焰火排列成行,點燃這一片古老而現代的時空。那些飽滿的黑色精血,喚醒了遙遠的故土記憶,也反哺了日夜劬勞的黃河母親。它們是遼闊而沉默的曠野上高聳的音符,在這片最年輕的土地上,以聽不見的大音希聲,反復演奏時代的最強音。
垂野草青、岸闊浪平,獵獵揚起的秋風,悄然傳來海的訊息。我知道,被稱為黃河口的所在,遠比我看到的更為遼闊,更為精彩。我沒有見到絢麗的紅地毯,也沒有倚靠大橋碼頭,觀賞壯麗的長河落日,包括一些鳥類博物館等科普場館,也都是走馬觀花,作匆匆一瞥而已。因為,這片土地實在是太廣袤了,它超越了一般三角洲的城鎮密布和地域劃分,卻相互交融為一個整體,那就是大自然的懷抱。
這是一條最渾濁,也是最清澈的大河。在即將抵達大海的時候,它放下了所有的包袱,金戈鐵馬、風云際會、悲歡離合。它將往事一飲而盡,純粹簡單得如不著一字的白紙。它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時光,聽著風日復一日地呼喊著水,用盤古遺落下的這對機杼,一張一翕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唇。
九九歸一,再長的旅程也有歸途。黃河用匯入大海的輕輕一躍,點睛綿延不絕、永不凋謝的萬里江山。
作者簡介:張凌云,系中國作協會員。作品散見于《青年文學》《延河》《山東文學》《四川文學》《湖南文學》等刊物,出版過散文集《高樹鳴蟬》《曉月馬蹄》等。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