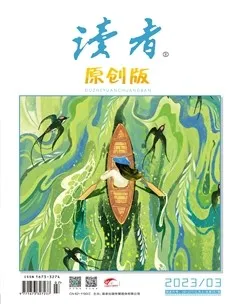春天的臉孩兒面
肖遙
一
對(duì)小學(xué)生們來(lái)講,世界上最兇險(xiǎn)的事就是換同桌,誰(shuí)都想要一個(gè)人畜無(wú)害的好同桌。三年級(jí)第一學(xué)期,我的同桌調(diào)成了彭靜。
彭靜是個(gè)比我還矮的小女孩,面相苦兮兮,眼圈紅通通,仿佛隨時(shí)都要哭出來(lái)。我不想跟她坐同桌,不僅因?yàn)樗龑W(xué)習(xí)差,還因?yàn)樗夤殴帧⒈砬榭鋸垺Kf(shuō)話一驚一乍,常嚇我一跳;偶爾嗲聲嗲氣,聽(tīng)得人渾身起雞皮疙瘩。剛剛坐同桌時(shí),我倆還能做到客客氣氣,她只要小心翼翼地求助,我就會(huì)給她講解習(xí)題。但是,她一說(shuō)聽(tīng)不懂,我就會(huì)煩,一旦感覺(jué)我講題的語(yǔ)氣里有一絲不耐煩。她就把本子一摔,臉一甩,說(shuō):“有啥了不起的!”然后就不理我了。

剛開(kāi)始我還覺(jué)得:好呀,你別理我最好了,我也不伺候你了!但隨即我就發(fā)現(xiàn),壞了!她有一百種辦法攪擾得我心神不寧。比如,趁我上課認(rèn)真聽(tīng)講時(shí)她故意用本子扇風(fēng),扇得嘩嘩響,動(dòng)作很大地發(fā)泄她的不滿;當(dāng)我準(zhǔn)備回應(yīng)她的情緒的時(shí)候,不管是安撫還是譴責(zé),她都會(huì)立刻扭過(guò)頭去,給我一個(gè)后腦勺!
我曾經(jīng)覺(jué)得世界上最難看的是一個(gè)人的冷臉,但沒(méi)想到還有更難看的,那就是一個(gè)人的后腦勺。
我也曾想把煩惱告訴老師,可是我要怎么說(shuō)呢?我總不能說(shuō)“她總是給我個(gè)后腦勺”,這樣,難保老師不會(huì)說(shuō)“她不理你,你也不理她不就完了”。我媽就是這么說(shuō)的。明明我是受害者,可她說(shuō)的好像我應(yīng)該為自己的在乎感到愧疚一樣。于是每當(dāng)彭靜對(duì)我擺冷臉,給我個(gè)后腦勺或白眼的時(shí)候,最折磨我的不是她傷害了我,而是我自己的無(wú)能,或者是我的太在意。這種女生之間的小別扭特別誅心,這種微型的雙邊關(guān)系冷戰(zhàn)其實(shí)就是一種冷暴力,看上去只是在抗議,實(shí)際上卻是一種進(jìn)攻,你能做的,只能是視而不見(jiàn)。可是,倘若任憑空氣變得冷颼颼,自己也很難受啊。
二
見(jiàn)我每天回家都不開(kāi)心,我媽領(lǐng)我去彭靜家,準(zhǔn)備跟彭靜她媽談?wù)劇R贿M(jìn)門(mén),別說(shuō)我媽?zhuān)B我也覺(jué)得沒(méi)必要開(kāi)口了。彭靜她媽躺在床上,彭靜連晚飯都沒(méi)吃,也沒(méi)的吃。彭靜她媽拉著我媽說(shuō)呀說(shuō),從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的老彭說(shuō)到正值青春期、極其不省心的彭大、彭二 ……
顯然,彭靜的媽媽已經(jīng)被生活壓垮了。我們聽(tīng)到的,就像是老鼠被壓在重物下面發(fā)出的那種吱吱叫的聲音。從彭靜家出來(lái),陽(yáng)光刺眼,我和我媽都長(zhǎng)舒一口氣。彭靜的喜怒無(wú)常好像有了緣由,畢竟她可能從未被好好對(duì)待過(guò)。我媽準(zhǔn)備第二天就去學(xué)校跟老師說(shuō),給我調(diào)座位!
倘若是男生,我不介意家長(zhǎng)出面解決,但女生之間的關(guān)系太微妙了。如果處理不好,我擔(dān)心同學(xué)們會(huì)覺(jué)得我“小心眼兒”或者“缺心眼兒”,這兩種標(biāo)簽中的任何一張貼在身上我都不好過(guò)。
何況,我和彭靜也不總是冷戰(zhàn)狀態(tài)。通常每次吵完架,到老師讓同桌互相背誦課文的環(huán)節(jié),我倆就會(huì)相視一笑泯冤仇。不知為什么,男女同桌之間到了這個(gè)環(huán)節(jié)互相不笑也不會(huì)記仇,但女生之間,這相視一笑是必須的,如果誰(shuí)沒(méi)笑,就表示這個(gè)梁子還結(jié)著,而且疙瘩結(jié)得更死了。有些女生,可能就因?yàn)闆](méi)有及時(shí)笑,關(guān)系徹底僵了也說(shuō)不定。
三
事情悄悄地發(fā)生變化,始于四年級(jí)的那個(gè)春天。那期間彭靜開(kāi)始躥個(gè)子,她就像被放進(jìn)空氣炸鍋里的蝦片,肉眼可見(jiàn)地膨脹起來(lái),那張苦兮兮的青皮核桃般的小臉變得飽滿紅潤(rùn),表情也變得柔和了,連聲音都不那么刺耳了。她的性格也慢慢有了變化,這大概要?dú)w功于她的小狗—彭靜收養(yǎng)了一只眼睛亮亮的小黑狗。彭靜見(jiàn)了她的狗,語(yǔ)氣立刻變得溫柔甜膩。要是放到一年前,我肯定無(wú)法把“春風(fēng)化雨”這個(gè)詞和她聯(lián)系起來(lái)。
因?yàn)橹牢乙蚋改腹ぷ髡{(diào)動(dòng)要離開(kāi)那個(gè)三線廠了,老師免了我的作業(yè)。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在乎班上的排名,也不會(huì)緊張兮兮地懼怕老師提問(wèn),更不必“處心積慮”地只和學(xué)習(xí)好的同學(xué)交朋友,給彭靜答疑解惑的時(shí)候也不暴躁了,遇到不會(huì)的題也不再自感無(wú)能而狂怒了。我甚至有了一個(gè)計(jì)劃:在離開(kāi)之前,我要把廠子周邊的山山水水玩?zhèn)€遍。
彭靜熱烈響應(yīng)并支持我的計(jì)劃。她反正一天到晚都尋思著咋玩、到哪兒玩、跟誰(shuí)玩、玩啥……她的訴求剛好和我的打算不謀而合。于是那一年,我倆每個(gè)周末都會(huì)找個(gè)理由約著一起玩耍:去山上摘桃花、杏花、梨花,去竹林里割筍子,去河里捉小魚(yú),一起去附近的縣城徒步遠(yuǎn)游,我們爬了很多座山,游玩了好幾個(gè)水庫(kù)……
夏天,我父母接到了調(diào)令。一想到馬上就要離開(kāi)廠區(qū),我發(fā)現(xiàn)自己最遺憾的,竟然是新的地方縱然有更大的山河,但是沒(méi)有彭靜了。在大自然里,那個(gè)在學(xué)校里不是劍拔弩張就是縮成一團(tuán)的刺猬一樣的彭靜,就像被泡發(fā)的木耳,變得舒展開(kāi)來(lái)。在山水之間,她的神經(jīng)兮兮變成了敏感熱情,她的跋扈和脆弱體現(xiàn)為膽大心細(xì)。在挖空心思游山玩水這方面,我再也找不到這么默契的伙伴了。
這些話沒(méi)辦法跟家人說(shuō),畢竟就在一年前,我還絞盡腦汁想著怎么擺脫彭靜這個(gè)小惡魔。多年以后,看劉子超的游記《沿著季風(fēng)的方向》,說(shuō)到他在菲律賓一座城市的見(jiàn)聞,“一場(chǎng)大雨不期而至,我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見(jiàn)證了街景的迅速轉(zhuǎn)換:前幾秒還是淅淅瀝瀝的雨,轉(zhuǎn)眼就變成瓢潑之勢(shì)……然而,雨突然停了,毫無(wú)征兆,干脆異常,前一秒還是暴雨如注,后一秒就像突然擰緊的水龍頭,幾乎沒(méi)有拖泥帶水的中間過(guò)程”。雖然說(shuō)的只是天氣,我卻想到我和彭靜忽而凜冽如冷風(fēng)、忽而暴烈似驕陽(yáng)的奇怪友情。
也許春天的臉孩兒面,小女孩的心思就是這樣反復(fù)無(wú)常。當(dāng)夏天到來(lái)的時(shí)候,我很是惆悵,我知道,我的童年結(jié)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