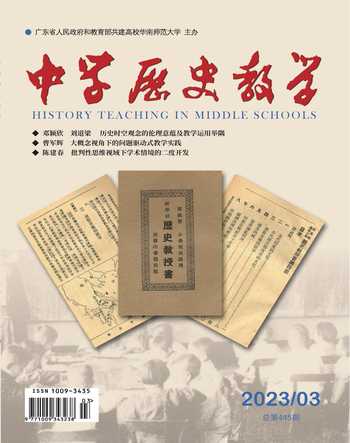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和實踐探索
李強國
當下的歷史課堂或因教材的綱要化思政化而趣味不足,或因教法學法的單一而生機不足,或因考試考核的壓力而從容不足……種種原因之下學生的興趣不足。如此,落實立德樹人和核心素養的目標只能大打折扣。要引導學生從歷史知識的學習中獲得現實素養,歷史教學就離不開生活,且須牢牢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因此,歷史教學生活化的價值取向,實為新時代歷史教育的本質要求。大部分枯燥寡淡的歷史課堂,皆是缺乏生活的味道。
一、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
進入21世紀,課程改革深化發展。就課程內容而言,要“改變課程內容‘難、繁、偏、舊和過于注重書本知識的現狀,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生活以及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的聯系,關注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經驗,精選終身學習必備的基礎知識和技能”[1]。生活化教學正是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積極應對新時代發展要求的具體體現。
第一,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是基于行知思想的生活化指向。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學說,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命題。其中“生活即教育”占中心位置,包括以下三層意蘊:首先,生活含有教育的意義,過什么樣的生活便受什么樣的教育;其次,教育來源于生活,由生活產生,在生活中求得的教育才是活的、有用的教育。以文字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書,好比是有纖維而無維他命之蔬菜,吃了不能滋養體力;最后,生活決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兩者相互促進。[2]鑒于當下歷史課堂的種種不足,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體系完整,內涵豐富,生動鮮活,重視生活和教育的關系,對歷史課程改革不無裨益。
第二,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是基于課程性質的生活化定位。2003年《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對歷史課程的定位是“在初中歷史課程的基礎上,根據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質、任務以及課程目標和基本要求,遵循時代性、基礎性、多樣性和選擇性的原則,規定適合高中學生學習的課程目標和學習內容,為其進入社會和高一級學校奠定基礎”[3],“在內容選擇上,應堅持基礎性、時代性,應密切與現實生活和社會發展的聯系,關注學生生活,關注學生全面發展。”[4]《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也明確要求學生通過高中歷史課程的學習,“為未來的學習、工作與生活打下基礎”[5],在課程目標上,“能夠將唯物史觀用于歷史的學習與探究中,并將唯物史觀作為認識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指導思想”,“能夠客觀評判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問題”,“能夠以實證精神對待歷史與現實問題”。[6]
第三,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是基于課程內容的生活化題材。2003年版高中歷史課程專設“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內容專題,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2020年版新課標規定普通高中歷史課程由必修、選擇性必修、選修三類課程構成。其中,歷史必修課程“通過中外歷史上的重要的事件、人物和現象,展現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從分散到整體、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歷程”[7]。選擇性必修課程社會生活意識尤其突出,共設《國家制度與社會治理》《經濟與社會生活》和《文化交流與傳播》三個模塊。三個模塊“引領學生從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文化等不同視角深入認識歷史”[8]。
第四,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是基于課程評價的生活化設計。生活化教學的價值取向,既要靠課程內容來實現,也要靠課程評價來落地。21世紀以來的普高歷史課程標準,其生活化的評價要求是一貫的、具體的,而且側重于實踐性評價,如“學生可自愿組成調查小組,圍繞家庭收入、衣食住行、醫療衛生、文化教育、通信手段等多方面的調查主題,確定具體目標,制訂調查計劃,選定調查對象,編寫調查問卷或訪談提綱……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在全班展示各組的調查研究成果,學生之間進行交流,師生共同對各組的調查研究活動進行評價”[9]。如此,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學生社會調查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學生接觸社會,提高與他人溝通、合作的能力,這是對學生核心素養的實踐化培養,也是優化傳統單一考試評價的一條途徑。
二、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實踐探索
(一)定靶:滲透生活理念確立教學目標
長期以來,受傳統考試的影響,不少教師把純知識的傳授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這種做法異化了歷史學科應有的價值教育功能,使得原本豐富多元的歷史教學變得僵化單一,學生淪為知識的奴隸。陶行知說:“學校應該給學生一種生活力,使他們可以單獨或共同征服自然,改造社會。”[10]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知識儲備及現實生活條件,預設指向生活力、創造力的教學目標是實現高中歷史生活化教學的第一步。
以選必三《文化傳承的載體及發展》一課的教學目標設定為例,教師通常會著眼于知識點,陷入就知識論知識、只為落實知識的誤區,文化傳承變得空洞而遙遠,學生的核心素養也得不到有效落實,因為死記硬背這些知識點并不能助力解決現實問題。為了真正達成核心素養,應該基于課標確定指向生活力的教學目標。故本課的教學目標可設定為:(1)能夠依據教材內容,提取有效信息,表格梳理文化傳承載體的發展歷程,分析其作用(時空觀念水平3,歷史解釋水平2);(2)對圖片史料、文字史料進行解讀,分析文化傳承載體發展的趨勢及原因(史料實證水平2,歷史解釋水平2);(3)作為當代中學生,在為祖國家鄉的文化感到自豪的同時,了解身邊文化載體的基本情況,思考如何從自身出發傳承文化。(家國情懷水平3—4)。
(二)激趣:依托鄉土資源創設學習情境
生活化教學必須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創設豐富多元的學習情境,這樣才能抓住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興趣。鄉土歷史資源近在咫尺,看得見摸得著,生動直觀,與學生生活沒有距離。歷史課堂教學適切地開發、運用鄉土歷史資源創設學習情境,學生會倍感熟悉和親切,從而拉近距離,激發興趣。
《文化傳承的載體及發展》一課涉及到的載體主要包括學校、書籍、圖書館和博物館。這四大載體就在學生身邊,因此完全可以從身邊取材。筆者在授課時,就以本校校址的前身作為導入,學生眼前一亮:原來小小的學校竟然可以追溯到明宣德年間的儒學堂,是本地文脈之根,不禁生發自豪之情。如此導入,一方面拉近課堂與學生的距離,另一方面也自然引出了“文化傳承”這一主題。再比如講到圖書館與博物館,筆者給出本地兩館的資料,本地兩館現代大氣,功能豐富,能有效滿足市民需求,但因建成不久,學生對兩館并不熟悉,因此多未去過,影響兩館效能的發揮。通過文字、圖片等資料的呈現,學生又一次眼前一亮,對兩館產生極大興趣。如此這般,既調動了學生的興致,又有利于獲取課堂與課外的雙重效益,使文化傳承變得不再空洞。
(三)升華:深化歷史知識對接現實思考
陶行知曾有小詩一首,名曰:“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的巧,愚者問的笨。人力勝天工,只在每事問。”[11]生活化教學倡導營造民主寬松的課堂氛圍,鼓勵學生敢問、想問、勤問,致力于培養學生問題意識,提升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體到歷史學科,教師不僅要引導落實教材上的知識,更要引導學生思考與現實相關聯的問題。
《文化傳承的載體及發展》這一課中,學校教育從私學打破“學在官府”開始,教育服務的對象就不再只是少數貴族,隨著數千年學校教育的發展,教育越來越面向大眾;印刷書的誕生也使得掌握書籍的不再是少數人;圖書館與博物館在古代多為官藏和私藏,到了近代它們都出現了服務公眾的職能。由此可見,文化資源的使用逐漸從小眾走向大眾。一個學生腦洞大開,他問如果有一天一場大火把這些載體全都燒掉,那么人類的文化是不是就終結了。此問題引來大家熱議,最后筆者總結道:所有的文化載體都是人造的,因此文化傳承真正靠的是人,其他的起輔助作用。文化資源的使用從小眾走向大眾,有大眾在,文化就能傳承下去。學生若有所思,筆者因勢利導: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匯集于此,多少帶有家鄉文化印記,如何保證家鄉的文化不被遺忘,做好傳承與傳播,也值得思考。如此,在深化課本知識的基礎上對接現實思考,引發了在座學生的強烈共鳴與深思。
(四)落地:布置生活作業涵育多種素養
生活化的價值取向不僅是新時代歷史課程改革的理念,也是優化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改善歷史教育實踐的方向標。新課程開展以來,設計、布置生活化作業成為越來越多歷史教師的新選擇。陶行知提倡“教學做合一”,目的就是培養在勞力上勞心,手腦雙揮的人,以克服傳統教育重知而不重行的不足。[12]布置生活化作業,引導學生在生活中動起來,也是在呼應“教學做合一”。
《文化傳承的載體及發展》涉及到的四大載體均在學生身邊,因此完全有條件設計、布置一份生活化作業。經過深思熟慮,筆者設計了一份富有探究性、綜合性、可操作性的作業:(1)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不斷發展,請搜集資料,說說家鄉的學校教育發展到了何種地步;(2)請你打卡家鄉圖書館,記錄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和功能區域,辦理借書證并完成借書;(3)請你打卡家鄉博物館,記錄博物館的開放時間和功能區域,記錄你最喜歡的展廳并說明理由;(4)條件允許的話,可以在兩館做一天志愿者,記錄你的工作和感受。這份生活味道很足的作業,從內容上看,既關聯教材又貼近生活;從價值上看,既能拓展知識面又能提升實踐能力。面對如此不一般的作業,學生眼前一亮,態度積極而主動。
三、總結反思
基于行知思想的生活化指向、課程性質的生活化定位、課程內容的生活化題材、課程評價的生活化設計,生活化的價值取向是當代歷史教育實踐改革的必由之路。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朱永新教授說:“生活的味道越濃,教育的意義就越大,堅持下去就會產生奇跡。”目前,高中歷史教育教學的實踐效果與課程改革的目標和要求還有較大距離,究其原因,大有可能就是歷史教學缺乏生活的味道,遠離真實生活。很多老師認為落實知識點考出好成績才是最關鍵的,關注學生生活經驗和現實問題往往費力不討好,但為了立德樹人和核心素養的真正落地,我們應該有使命感,應該有所擔當。
【注釋】
[1]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人民教育》2001年第9期,第6頁。
[2][12]周洪宇:《人民之子——陶行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142、195頁。
[3][4]教育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2頁。
[5][6][7][8][9]教育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6、9、9、20頁。
[10]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4頁。
[11]董寶良:《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