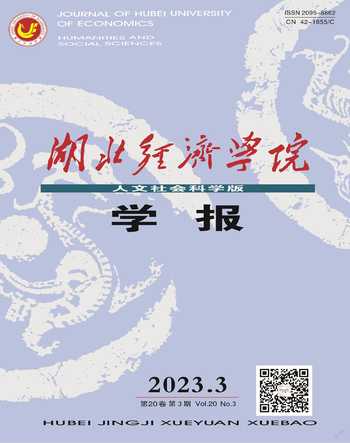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下仲裁程序之重構
摘 要:在我國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中,勞動仲裁是解決勞動爭議的前置性強制程序,在勞動爭議處理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目前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存在與訴訟程序銜接不暢、仲裁組織設置不健全、行政化色彩濃厚以及仲裁程序訴訟化等問題。因此應進一步明確裁審關系,以去行政化手段強化勞動爭議仲裁組織的獨立性,并規范仲裁程序以避免其訴訟化傾向,綜合性地對我國勞動爭議仲裁制度予以調整,進一步完善勞動爭議多元化解新機制。
關鍵詞:勞動爭議仲裁;裁審關系;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作出重要指示,明確提出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2021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強調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自1987年恢復以來,逐步形成了“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勞動糾紛多元解決體系。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關系日益復雜化、多樣化。但現有的勞動爭議處理模式顯然難以應對與日俱增的勞動糾紛處理需求,勞動爭議多元化解機制面臨考驗。
一、我國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的現狀與問題
在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中,由于協商與調解屬于可選擇的程序,而仲裁則屬于強制程序,由此,勞動爭議仲裁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在目前的“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下,勞動仲裁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角色,表現在它既可以讓較多的勞動爭議在仲裁階段即告結束,又對后面的勞動訴訟有直接的影響。但同樣地,仲裁程序在施行中并未充分發揮在勞動爭議處理中的主導作用。
(一)仲裁與訴訟程序銜接不暢
依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仲裁程序是處理勞動爭議的必經程序,也是勞動案件審判程序的前置程序。仲裁前置的程序性設計一方面能夠有效分流、過濾案件,從而減少后續爭議處理渠道的壓力,實現簡易案件簡易辦理,疑難復雜案件著重辦理的目標;另一方面,這樣的處理機制步驟較多,處理機構也較為龐大,能夠盡可能地減少錯案,維護勞動安全[1]。勞動仲裁在爭議處理機制中處于居中地位,從立法設計的角度出發,期望通過中立、有效的仲裁裁決,可把較多數的勞動爭議直接解決掉,從而減輕后續司法訴訟的案件受理壓力。但從目前勞動仲裁案件的數據來看,顯然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以山東省為例,“十三五”以來,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共受理爭議案件45萬件,涉案標的額達97億元,勞動爭議數量呈高發態勢。在目前調解程序尚屬雙方當事人自愿選擇的前提下,仲裁程序成了勞動爭議處理的第一道防線,這也給仲裁前置的法律執行以及與訴訟程序的銜接帶來壓力。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以仲裁方式處理勞動爭議無法實現“一裁終局”的法效果,當事人訴諸法院仍是普遍選擇。當前,全國勞動爭議仲裁服裁率常年維持在50%左右,勞動爭議仲裁存在信服度不高,競爭力不足的問題仍很突出[2],“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并未如期運行。
目前的“先裁后審”模式弊端日益明顯,突出體現在“進口”狹窄、程序冗長、成本高昂和限制訴權,在目前的勞動爭議數量迅猛增長形勢下,訴愿渠道已不夠暢通,將勞動爭議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必然意味著只有經過“一裁兩審”的漫長程序,方可獲得法律上的終局解決[3]。另外,冗長的環節也使得仲裁成本以及勞動爭議解決成本的顯著增加,反致失去了勞動爭議仲裁具有的靈活特點。法經濟學角度認為效益是其核心,勞動爭議仲裁本應作為高效率、低成本的勞動爭議處理模式,但仲裁制度運行的孱弱,使得盡管在勞動爭議仲裁中,當事人已投入人力與金錢等沉沒成本,但不會影響理性人對訴訟程序所獲收益的判斷。易言之,當事人仍最終選擇訴訟作為解決勞動糾紛的終極途徑[4]。此外,該模式也限制了當事人自由選擇仲裁與審判的權利,不利于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障。裁審關系彼此不協調,損害勞動仲裁結果的權威性,這種損害表現在勞動仲裁裁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能使爭議得到最終的解決,只要有一方當事人不服并提起訴訟,仲裁的結果便無任何效力,即使最后法院的判決與裁決相同,也以判決為準而不以仲裁裁決為準,這樣的結果完全背離了仲裁制度迅速徹底解決爭議的目的[5]。
現行的“一裁兩審”程序環節影響了勞動者對其合法權益的維護,不利于提高爭議處理的效率,尤其是在勞動者身患工傷等情況下,冗長的程序也一定程度延誤了治療時機。從服裁率數據來看,相當一部分當事人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的目的是為了盡快獲得仲裁裁決,從而進入訴訟環節,又由于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非終局性結果,導致訴訟比例居高不下,仲裁與訴訟的銜接出現了問題,勞動爭議仲裁的居中地位亦虛置化。
(二)仲裁組織設置不健全,行政化色彩濃厚
從法律文義分析看,我國對于勞動仲裁機構的組織定位是第三方社會性機構。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工會代表和企業方面代表組成。”可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法院等司法機構,而是由行政部門、勞動者、企業三方代表共同組成的社會性機構,其目的是為了從勞資關系角度體現雙方的利益和權利要求的平衡,通過三方代表組成仲裁機構的方式體現出公平、公正和制衡的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特點[6]。有觀點指出,仲裁制度作為ADR(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機制的一種,核心在于其非司法化、非訴訟結構等特點,其優勢在于通過市場自發形成對勞資關系進行調控,但地方上出于社會維穩考慮,以主動介入的方式化解勞動糾紛,避免釀成社會事件,并未將仲裁制度作為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的優先選項[7]。
通過審視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隸屬關系和人員組成,來自勞動行政部門的影響更為顯著,勞動仲裁委員會的運行呈現實際上的行政化狀態,使得相關機構建設滯后于日益增長的勞動爭議案件處理需求。由此帶來機構設置不健全,人員經費短缺等問題,進而導致仲裁權威性不足。從勞動仲裁機構的數量和人員配置數據來看,全國已調整組建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3097家,擁有專兼職仲裁員2.3萬人[8]。根據前述統計數據推算,我國平均每個勞動仲裁機構有專兼職仲裁員7人至8人左右,人員配比仍然不能滿足目前的勞動爭議裁審需求。
在勞動爭議多元處理程序中,勞動仲裁組織的行政化傾向,與法律原本設計的社會性,即“三方性原則”的特點大相徑庭,也不利于案件審理的公正、公平,影響仲裁的權威性。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經費由財政予以保障。由此可見,法律在規定著仲裁委三方組成的同時,亦規定該組織的運作經費由財政予以補貼,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能否擺脫經費掣肘,以獨立、公正的裁審地位處理勞動糾紛,頗值探討。
(三)仲裁程序訴訟化
我國勞動仲裁程序在運作過程中,基本上套用了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致使勞動仲裁不僅越來越向訴訟程序看齊,而且在具體的審理程序上也較為煩瑣[9],仲裁程序逐漸顯現訴訟化特點。在現行機制中,訴訟程序不以仲裁裁決作為援引之基礎,故而法院忽視了對仲裁程序合法性、事實認定準確性的判斷,裁決結果有無失當并不直接影響法院對相關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法院仍按照完整的審理程序重新對相關勞動爭議作出裁審,仲裁裁決結果僅作為參考依據[10]。
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仲裁程序包含案件受理、答辯、舉證、組庭通知、開庭審理、調解、制作文書、送達等各個環節,與民事訴訟程序趨同。將訴訟規則引入至仲裁程序中,本意是避免仲裁結果公信力的下降,但與仲裁本應具備的即時、有效、迅速、靈活等特點背道而馳,勞動者的維權周期也顯著增加。根據基層法院調研的仲裁裁決數據分析顯示,在仲裁委作出實體裁決的144件案件中,仲裁委平均處理周期為51天。法院一審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勞動爭議平均審理周期為51天,適用普通程序平均審理周期為94天。勞動者維權周期(即勞動爭議提交至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起至爭議訴至法院審理結束時間止)平均時間為108天,其中,最長325天,最短4天[11]。勞動仲裁本應作為勞動糾紛的便捷處理程序,與訴訟程序高度近似,無法緩和因訴訟化傾向帶來的審限延長等問題,反致爭議解決的時間被不當拖延,勞動者不得不經歷時間、金錢與精力的多重考驗。
概言之,仲裁程序的訴訟化是勞動仲裁在實務中遇到的難題,它與裁審關系不明確共同導致仲裁地位虛置化,使得勞動仲裁難以發揮其特色,使得一些本應快速解決的勞動爭議因為程序的復雜而延宕。仲裁程序的訴訟化也使得許多勞動爭議案件變相成了“三審終審”,仲裁的權威性不當減損,仲裁的效率也大打折扣,仲裁雙方當事人選擇繼續訴訟程序,造成了目前“雙輸”的現狀。
二、我國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的建構與完善
在我國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中,仲裁制度承接著數量龐大的勞動爭議與糾紛,旨在發揮更快捷、更有效地解決勞動爭議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作用。但鑒于目前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存在與訴訟關系不夠明晰且行政化色彩較重,以及訴訟化傾向等諸多問題,反致勞動者維權成本與難度顯著增加。勞動爭議仲裁未能發揮其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因此有必要針對現有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因事制宜地加以完善與優化。
(一)明晰裁審關系,強化仲裁地位
在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中,仲裁程序與審判程序的關系是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中的核心。建立銜接緊密、運行順暢的裁審關系亦是勞動爭議處理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目前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并沒有沖破原有的制度框架,仍舊延續了“先裁后審,仲裁前置”的模式,該模式未能充分適應勞動糾紛特殊性所產生的制度需要,已經暴露出諸多弊害,與法律程序追求的公正與效率不相契合[12]。對于裁審關系如何定位,理論層面也有一定的嘗試性論證。例如,有觀點認為,我國的裁審關系宜采用“裁審自擇,裁審分離,各自終局”的方案,即選擇仲裁的不再訴訟,選擇訴訟的不再仲裁。一方面,選擇仲裁的實行一裁終局;另一方面,選擇訴訟的實行兩審終局,其優越性在于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并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實現勞動爭議案件的合理分流,減少制度改革帶來的震動[13]。裁審分離的制度設計,實際上明確了仲裁與訴訟的平行互補、多元協調的關系。有鑒于目前仲裁前置導致裁審關系不明確的問題,應當從法律層面明確勞動爭議仲裁的終局效力,勞動爭議仲裁的裁決書應當具有強制執行力。也有觀點將仲裁程序進一步規范與仲裁機構對勞動爭議糾紛處理能力的進一步提高,視作與訴訟程序的同質化,仲裁機構是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和勞動司法的合并,此類同質化與合并構成了我國未來獨立裁審體制發展的前提[14]。
勞動爭議仲裁制度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之一,相比于訴訟制度,它應當更迅速、靈活、經濟地解決勞動爭議,鑒于目前勞動仲裁地位的虛置化問題,在裁審關系中應將仲裁的地位予以補強。由于目前的仲裁結果權威性不足,除了仲裁結果本身弱勢外,勞動爭議訴訟結果的效力大于仲裁結果效力也是裁審關系銜接不暢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以進一步明確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中部分裁決事項不服提起訴訟的,對于未提起訴訟的部分即發生法律效力。此外,仲裁機構的改革與仲裁程序的優化也都是加強勞動仲裁制度地位的應有之措施。
(二)去行政化,增強仲裁組織獨立性
由于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缺乏獨立地位,行政化色彩凸顯,使得勞動仲裁效力難以彰顯。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對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性質和獨立地位仍然含糊不明,由此在實踐中帶來了很多問題,因此加強仲裁組織的獨立性尤為關鍵。比如,要以立法確立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獨立地位,并逐步改變仲裁機構的性質,設立勞動爭議仲裁院,以及改革仲裁委的人員構成,只有仲裁員獨立才能保證仲裁委的獨立,才能改變仲裁委的性質[15]。201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勞動人事爭議仲裁組織規則》,規定“仲裁委員會下設實體化的辦事機構,具體承擔爭議調解仲裁等日常工作。辦事機構稱為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從部門規章的層級統一了各地勞動爭議仲裁委會實體化辦事機構的名稱,將其明確為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簡稱為仲裁院。
由于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設置在勞動行政部門,仲裁組織行政化的傾向明顯,使得原本在法律中設計的“三方性原則”未能很好運行,仲裁實效難以發揮。“三方性原則”是公正的基礎和象征,在勞動爭議仲裁處理中堅持“三方性原則”以避免串通,有利于增強當事人的公平感,且各方仲裁員專業背景不同,有利于爭議問題得到全方位的研判和解決[16]。此外,還應當從“人、財、物”等多個方面,切實解決其資源問題,優化資源配置,以進一步改革仲裁機構的設置,朝著脫離勞動行政管理機構建制范圍的方向發展。比如,在人員社會化問題上,對新人實行聘用制,逐步加強仲裁員的專業化建設,建立仲裁員的準入制度,提高勞動仲裁員的素質;對于經費問題,仲委會的經費要進行單獨預算進而到單獨列支,擺脫在經費上對行政部門的依附。
現行的勞動仲裁委員會在其性質上沒有較大獨立性,使得在處理勞動爭議時容易受到行政干擾,損害仲裁的權威性和公正性。通過機構、人員、經費、辦公場所等方面的獨立,進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仲裁組織獨立。各地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實體化措施,發揮仲裁院中立與三方性機制作用,去除多余的行政職能,真正體現準司法機構的特點。截至目前,山東省在省、市、縣三級共建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171個,其中,省級1個,市級17個,縣(市、區)級153個,全省仲裁組織機構網絡基本建立健全[17]。
(三)規范仲裁程序,避免訴訟化傾向
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有一定的優越性,主要原因是其具備處理效率高、用費小等特點,相比于訴訟程序更顯柔性化。因此對于仲裁程序的改革,應立足于還原仲裁之本性,使得勞動仲裁在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中發揮其應有的獨特作用。在宏觀層面,在突出仲裁靈活特征的同時,也應當堅持若干根本性原則:回歸仲裁協商解決的主要表征,維護仲裁自愿申請和自主調解的特性,不宜過分強調對抗,其核心是應維護當事人對于規則的自決權,并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
在微觀層面,勞動仲裁程序仍有待后續完善,如財產保全制度的規定,亦是仲裁程序予以規范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國有關處理勞動爭議的法律法規等均沒有對勞動仲裁程序中的財產保全作出明確規定,成為法律上的空白點。在實踐中,通過引入財產保全制度,使當事人或仲裁機構根據實際情況行使實體權利的保障權,也就是為了免除后期執行難的問題,當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財產保全措施[18]。對此,部分地區在缺乏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結合實際制定了相關規定,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1條規定:“勞動爭議仲裁過程中,用人單位可能出現逃匿、轉移財產等情形的,勞動者可以申請財產保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發布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浙法民一〔2009〕3 號)第23條規定:“勞動爭議仲裁過程中,用人單位出現企業主逃匿或轉移財產等情形的,勞動者可以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通知書》,向人民法院提出財產保全申請。”此類規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在勞動爭議處理中有關財產保全的運作依據,但是其立法層次較低,因此仍需要提高立法位階對勞動爭議仲裁中的財產保全問題作出統一安排。
因此,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應當發揮其不同于訴訟程序的彈性化特點,不應照搬訴訟程序。對于因仲裁程序訴訟化引致的維權周期較長的問題,鑒于仲裁制度的價值即是便捷、高效,在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的設計上,應充分體現靈活和尊重當事人合意的特點,可以將標的金額較小的勞動爭議以簡化程序審理,縮短審限,從而還原勞動仲裁靈活、簡便、快捷的優勢和目的。
三、結語
勞動仲裁制度是我國勞動爭議多元處理機制中的重要一環,它上承勞動爭議調解的優勢,下啟勞動訴訟的公信力,在勞動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中承擔著重要任務。但裁審關系不明,使得大量案件進入訴訟環節,仲裁程序未能發揮其柔性化作用。仲裁組織建制于政府部門,行政化背景揮之不去,而仲裁程序的訴訟化,也降低了本應具有的高效與簡捷優勢。究根結底,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未能形成一個完整且獨立的系統,使它不得不依賴于行政部門的財政、人員,仲裁權威性的不足又使得仲裁程序被迫向訴訟程序靠攏,如此往復,仲裁地位即陷入死循環。職是之故,重構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時,應以其行政化傾向為主要癥結之所在,強化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獨立地位,在運作過程中真正有所本、有所用。合理劃分勞動仲裁和其他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范圍,令其有所分工、不可混淆,讓勞動爭議調解制度、仲裁制度、訴訟審理制度真正成為處理勞動關系爭議的“三駕馬車”,促進新時代下中國特色的勞動爭議多元化處理機制的加快形成。
參考文獻:
[1] 董保華.勞動爭議處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89.
[2] 王蓓.我國勞動爭議仲裁制度的缺陷與完善[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8(3):75-82.
[3] 陳彬.論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的重構[J].現代法學,2005(6):95-101.
[4] 黃麗娜.新時期下勞動爭議非訴訟解決機制問題與對策——以效益最大化原則為視角[J].社會科學論壇,2021(5):150-160.
[5] 孫德強.中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68.
[6] 寧靜波.勞動爭議裁審關系模式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22.
[7] 王蓓.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1.
[8] 司法部.司法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4364號建議的答復[EB/OL].[2022-06-14].http://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jyta/202111/t20211119_441952.html.
[9] 蘭仁迅.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90.
[10] 孫國平.英國行政法中的合理性原則與比例原則在勞動法上之適用——兼談我國的相關實踐[J].環球法律評論,2011,33(6):43-56.
[11] 成都市新津區人民法院.淺談勞動仲裁與法院訴訟的銜接與完善——基于339件勞動爭議案件的實證分析.[EB/OL].[2022-06-14].http://cdxj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2/id/1552910.shtml.
[12] 朱京安.我國勞動爭議裁審關系之審視[J].理論探索,2016(4):113-117.
[13] 侯海軍.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和審判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8.
[14] 沈建峰,姜穎.勞動爭議仲裁的存在基礎、定性與裁審關系[J].法學,2019(4):146-158.
[15] 王琦.勞動爭議非訴法律制度研究[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77.
[16] 董保華.論我國勞動爭議處理立法的基本定位[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8(2):148-155.
[17] 山東省人社廳調解仲裁管理處.全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實體化建設實現全覆蓋[J].山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2014(9):15.
[18] 鄭尚元.勞動仲裁建立保全和先予執行制度的必要性[J].中國勞動,2002(6):34-35.
基金項目: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2022年度學術型研究生專項科研基金課題“破產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實現研究”(2022LAW008)
作者簡介:李田坤(1992- ),男,山東淄博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