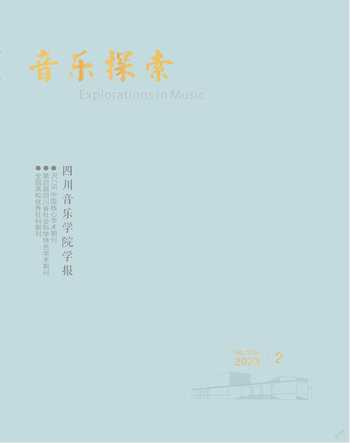談二胡經典作品中的中國音樂審美觀The Chinese Aesthetics of Music in Erhu Classic Works
摘 要 :文學與藝術本該是表達生命內涵的重要方式,是生命中愛與美的呈現。但在一些音樂學習者和從業者中卻出現了日益功能化、技術化和功利化的傾向,舞臺上夸張而超越內心的外化形體動作、對速度和競技技術超過音樂人文情感本體的過度追求,千人一面的標準化藝術評判標準等,讓具有生命溫度的音樂藝術逐漸減少。嘗試從生命中愛與美的本源出發,還原藝術的本質,以二胡經典作品為例,探究中國音樂的審美思維,以及中國音樂文化所具有的本真屬性。
關鍵詞:中國音樂審美;中國音樂文化;二胡經典作品
中圖分類號:J63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23)02-0102-07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12
內在和外在,內涵與形式是音樂審美的兩個方面。外在包括如音樂表演的音色、韻律、情感表達、技術完成,作品的和聲、旋律、結構等。內在則包含生命與愛的內在信息傳遞,音樂所傳遞出來關于生命和哲學思考的共鳴等。生與死、愛與恨、美與丑、浪漫愜意與質樸自然都是音樂表達的內在主題。這種內外相互作用的音樂審美,便形成了中國音樂的演化邏輯。
一、審美的維度和內涵
審美是對美的一種主觀感受和價值判斷。審美是多層次多角度的,以不同角度的局限入手,會陷入單一化,形成審美盲點。例如,作曲家習慣從作品創作角度看音樂;演奏家習慣從演奏好壞的不同標準角度看音樂;而愛好者則習慣從氛圍和自身喜好角度看音樂。因此,同一個人演奏的音樂,這三種人聽后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評價結果。如果從宏觀(整體)把握,跨越專業的局限性,著眼于多種局部和多元微觀,則容易形成較為完整全面,跨越通道的審美思維。
宏觀審美能夠產生一種氣象(氣勢、氣韻所構成的意象),它以整體感覺的形式來呈現。如曹操《觀滄海》中,“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①詩句中所描繪出的種種感覺都可以稱之為氣象。宏觀審美中所產生的氣象之美是較為容易感知到的,不需要經歷過多細細的品味、豐富的經歷或系統的訓練,只要有片刻的專注即可感知。那種撲面而來的宏觀氣象給人以強烈的審美沖擊。①
局部審美則指一般情況下人們所普遍能夠觀察到的相對細節。局部審美是對人或事物的內在規律到達某種深度的了解,越過了第一印象的感知,但又沒有進入精深的階段。在這一層面,已經需要去細細地品味和解讀才能發現其中的意味了。
微觀審美是審美的高級階段。進入審美微觀境界需要深厚的相關專業素養和通達的思維境界,實現透過事物表面體察本質的審美層次。②在物質生活極其豐富的當代,人們在不斷獲得物質的反復中極易產生一種審美的疲勞和麻木。覺知上的專注和耐心也會因為得到過多而減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③人的感知系統變得更加麻木和難以滿足。培養對平淡事物的覺知力,回歸自然和簡單的斷舍離等潮流理念,正是人們試圖找回覺知和專注的探索。
二、二胡經典作品中的中國審美
二胡作為中國傳統樂器,承載的是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美學思想表達。但當代二胡演奏及作品的解讀多注重于外在,如演奏技術完成的標準、外在審美的音色,而從力度和情緒、作品強弱規律、氣息及樂段樂句的連接等相關問題的分析較少,缺少了對內在中國歷史文化審美的解讀。本文所舉二胡經典作品中的音樂意象,意圖從中國文化歷史觀的角度還原中國音樂的內在審美,通過音樂意象來帶動作品的形神和演奏的技藝,而非用技藝來表現音樂內涵。
審美是生活追求的升華,在物質豐富的今天,美已經成為人類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但審美遠遠不是好看與否這么單一的含義,而應是多元化的理解,是不同民族、地域、時代文化精神的標志。中國音樂的審美觀是由中國各民族地區的文化土壤培育起來的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在當代國人思想中傳遞而成的音樂文化審美思維,具有深刻的時代性和歷史傳承性。用二胡經典作品解讀的視角,是對中國文化內涵的一種再認知。
本文選取八首二胡經典作品是以中國音樂為載體,用寫意和具象等手法對中國文化思想進行凝練。中國古代音樂多為文人和貴族所用,貴族用樂彰顯地位。禮樂制度讓音樂有了等級產生的審美觀;而文人用音樂,或寄情山水,表達愛意,或抒發理想抱負。修、齊、治、平,儒、道、墨、法,百家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歷代的中國文人音樂,文人音樂多是以“音樂意向”來表達思想和美感。而意向,是類似于中國繪畫中用寫意的手法對情景含蓄卻又讓人心領神會充滿期待與想象的勾勒。這種中國音樂獨特的文化現象,給人提供了具有中國浪漫主義情懷的期待和想象空間。④
三、中國音樂審美八意象
音樂的審美是多元的,每個人都可以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去解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⑤意思是說音樂的本初,是由人內心的感動而產生的,人內心的感動,是源于外物的觸發。每個人所感不同,對音樂的理解也就本該是多角度的。那么該如何理解、欣賞及把握中國音樂文化審美觀中的這種思維呢?筆者用清、堅、逸、健、莽、凄、渾、采八個字分別引出八首二胡經典音樂作品中的音樂意象①,借此引導讀者去感受中國民族音樂中的審美趣味和人文情懷。
(一)中國音樂八意象之“清”——《月夜》
“清”是雅的根本,是音樂的精神。環境的清幽,一把好琴所帶來的清透,琴弦的爽利,都是音樂能否通透的所在。心如果不靜則不清,氣息如果不順暢則不清,手指按音和運弓如果猶疑不定、遲重渾濁,音樂就更不能清。
清雅是音樂中心靈的沉靜。不追求情緒的大起大落,不被焦急所催促,清新淡雅、安穩自然。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它的一切美好都需要在過程中細細地品味。凝神靜氣,化神為意,形神氣韻合于一弓,一顰一笑、一揚一落、一招一式,順著樂句的氣韻,將每一處虛、實、濃、淡都泰然處之,不將就、不刻意。輕松恬淡,則能真正到達外明音而內精神,通透卻靜謐的清雅意向。如果草率出弓發聲,神未聚,氣尚散,那聲音中就只剩下外在渾濁的力量軀殼,而失去了音樂文明的厚度與神韻。只有進入疏密有度,張弛相應的無我、沉靜、通達、清明狀態,才能夠體悟到音樂中的清雅意趣。
《月夜》這是民國時期國樂大師劉天華先生十首二胡獨奏曲之一,也是十大二胡名曲中夢幻和富于詩意的一首。樂曲創作于1918年的夏天,那時,年輕的劉天華先生正在家鄉江蘇江陰居住。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他觸景生情,有感而發,寫下了這首《月夜》。在欣賞或演奏這首樂曲之前,可以想象一下這位23歲內心細膩的年輕人在面對皓月當空的景象時,內心所泛起的波瀾。
樂曲第一段,觸發了一種從容淡雅的意境之美。月兔東升,皎潔如雪,在這種氛圍之下,人的思緒沉醉在美景之中,仿佛是置身于天地間,同自然融為一體。從古至今,無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都被這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同一輪明月牽動過心弦,人生中那美好的瞬間也定格在了這一輪明月映照下的夜晚。王國潼先生曾談到二胡音樂中的三種意韻——清、淡、雅,而此曲第一樂段所蘊含和表現出來的樂思,也正是這樣清雅之感。樂曲第二段,似乎有一種內心的流露,有彷徨、有留戀,也有向往。這一樂段仿佛是心靈在訴說,感懷生活與自然中美麗的花草樹木,亦感懷某一個夜晚,那輪明月下的時光。作品第三段中,音樂開始流動起來,一種向上的動力流淌而出,好似對人生的憧憬和追尋,讓人內心沉浸。
(二)中國音樂八意象之“堅”——《二泉映月》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二泉映月》是描寫瞎子阿炳(華彥鈞)悲慘人生的悲情作品,演奏時應著力刻畫阿炳波折坎坷的情感內涵。其實,作為二胡傳世經典,《二泉映月》有著巨大的內涵容量,可以承載悲、歡、堅、樸、得、失、憤、舍等無數個解讀視角。以悲為意不是唯一,只是對《二泉映月》的一種解讀方式。每個人對音樂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此曲的內涵也同樣應該是包容而非局限于悲情基調上的。
堅,有堅守、堅定、堅毅、堅韌等含意。堅可以是一種品格,也可以是一種信念。藝術中更有一種堅的境界,就是用眼淚來表現喜悅,而用微笑和豁達來表現悲傷。堅的演奏在音量與力量上的控制尤為重要。體現堅韌時,運指以壓代按,先按而后壓,壓揉結合,力度強而音量先弱后強,之后再加力而減音量,形成聲音意向的不屈不撓感。在表現堅定時,可通過先以幅度小而快,壓力重而緊的壓揉起勢,運弓形成鋒利音頭與強結構感,形成外果決而內扎實的穩定性。隨之左手持續不斷而立刻松右臂,轉而為右掌指運弓,再造層層遞進,形成堅定的聲音意向。老子曾說,“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這白與黑之間的反襯和交錯,更凸顯出演奏內在表達的深層力量。
華彥鈞自幼隨父在道觀中學習音樂,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宗教人士的社會地位較高,阿炳算得上是思想文化和藝術水準兼而有之,同時衣食無憂,一帆風順的幸運青年了。但世事不可預料,在走入人生的后半段時,阿炳由于雙眼失明和父親的離世而跌入了人生的谷底。被趕出道觀后,開始了異常艱辛的生活。哀莫大于心死,置之死地而后生,這前后人生境遇的強烈反差,恰恰成了讓內心成長和堅韌的契機。
用堅的品格來品讀《二泉映月》可能會有人疑惑琴聲中缺少阿炳的悲涼和痛苦。然而這正是堅的性格,用堅強、堅韌來面對苦難;用波瀾不驚,甚至平淡的筆觸去書寫人生的跌宕。
(三)中國音樂八意象之“逸” ——《椰島風情》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則不能也。”①逸致是人天賦中蘊含的能力,這種天賦讓靈魂能更自由地去表達,進入沒有掛礙的舒適狀態中從而迸發出獨具魅力的美感。逸是浩然之氣充盈后綻放的光彩,是天地賦予人天性精華的顯現,這樣的天性之美還蘊含著恬淡虛無間的一股灑脫,透出了本性具足的雍容和自信。
《椰島風情》是二胡演奏家陳軍先生根據海南西沙音調創作的樂曲,描繪了一幅風情獨具的夢幻“逸”境。樂曲引子部分以自由的散板開始,仿佛從現實進入了夢鄉,又在夢境中蘇醒,一股朦朧和慵懶的氣息彌漫開來。樂曲的上板段落,旋律的開始是以前調的結束音為起點,呈現出一派新鮮的海南風情之中。
樂曲運用“連滑揉”的演奏技法,結合長線條氣息自然起伏的運弓,給人慵懶而略帶異域風情之感。左手動中有靜,而右手靜中帶動,兩手配合絲滑嚴密,形成奇異、飄逸的意向之境。此時應十分小心仔細對地每一寸運弓進行工筆描繪,隨境而轉入一個個不同景象,景象豐富層次遞進,但風景不同心境不同。接下來過渡性的樂句,以前段的結束音為開始進入B調的散板。這段盡情陶醉的華彩雖然短小,卻大膽表達出了內心自由而充滿愉悅的深情獨白。隨著歡樂小快板的鋪墊,音樂逐漸進入激情的高潮段落,從聲音中透露出內心如火一般熱烈的張揚。盡情揮灑中,一根引線的長音將音樂慢慢地拉回到樂曲的再現場景,讓音樂在朦朧夢幻中逐漸遠去。
這蘊含著逸之美的音樂感覺,令人心馳神往。明代徐上瀛先生曾說:“臨緩則將舒緩而多韻,處急則猶運急而不乖。”意思是在演奏緩慢的樂句時,需要做到恰到好處又充滿神韻;演奏快速的樂句時,又要操作迅捷而又不毛躁、不慌亂。這種得心應手,也造就了演奏這首作品時動中有靜的演奏樂趣。
(四)中國音樂八意象之“健” ——《賽馬》
健是天的品德。天在運行時,是剛毅堅卓,發憤圖強且永不停息的。君子也應當效法天地的德行,披荊斬棘,砥礪前行。以健為題來引出《賽馬》這首黃海懷先生的經典之作,正是因為此曲中蘊含著健之意象的諸多內涵。
《賽馬》是一首極富奧妙的傳奇之作。說它極富奧妙,是因為《賽馬》的演奏技巧并不復雜艱深,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但其音樂效果卻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沖擊力。樂曲帶給人熱血沸騰,眼花繚亂之感,用寥寥幾筆凡塵之音,便可激蕩風云,足見此曲的奧妙精深。作品不僅好似一匹黑馬在全國大賽中脫穎而出,被評為優秀新作品演奏獎后,更是很快風靡全國。
如果說《賽馬》的奧妙和傳奇是它雄健姿態的兩個體現,那它樂曲內容所展現出的底蘊就更顯示出此曲“天行健”的品德。聲音遠近(強弱)造成的距離對比感形成了賽馬場上大輪廓下的你追我趕,樂曲演奏中用粗獷的音頭帶動整個弓段,展現出駿馬不畏懼、不退縮的雄健風姿。兩個相同樂句用一強一弱來呼應競賽的場面,四個相同的句型則以由弱到強、起承轉合來表現競賽的激烈豪邁以及路途的揚塵與激蕩。時而穿插著一大段悠揚的旋律襯托出晴空萬里之下在無盡大草原上奔馳的痛快,描寫了蒙古游牧民族馳騁、奔騰的賽馬場面,在聽覺起伏的追趕中呈現出近大遠小的視覺聯想效果。其中不僅有爭奪追趕的激烈,更揉入了瀟灑張揚的歡樂,在民歌的旋律之中,騎手們仿佛忘卻了比賽,沉浸在一片信馬由韁,盡情放歌的歡樂之中。馬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奮斗不止,自強不息的代表,中國成語中就有龍馬精神,龍馬是炎黃子孫的化身,代表了中華民族進取向上的精神。
這首作品使用中國民族五聲調式與蒙古族民間音調,運用了二胡與蒙古族音樂風格的音樂語言,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展現了中國音樂中雄健意向的民族精神。
(五)中國音樂八意象中的“莽” ——《寧夏川好地方》
二胡音樂八意象之中的“莽”字是廣博、遼闊的意思。音樂中有了莽的意境,便平添了一種胸懷。人心中有了莽的信念,便融入了一份擔當。
《寧夏川好地方》是二胡演奏家周維先生2014年以寧夏民歌音調花兒為基調創作的一首二胡曲。樂曲描繪了祖國大好河山的壯闊秀麗,傳唱出了當代華夏兒女的積極向上,朝氣蓬勃之心。
樂曲開場的引子,就像是一位樸實無華的西北漢子高唱山歌號子,來贊頌自由自在的山里生活。同時,這好聽的大山之聲也仿佛展開了一幅西北風土人情的畫卷。樂曲第一段旋律平穩而舒緩,大段憨厚樸實的旋律中其實包裹著一顆熾熱而細膩的心,用偶爾點綴對比的手法來襯托樂曲憨厚純粹的性格。主線條以飽滿的運弓來完成,在銜接處不經意間透出弱起音和幾起幾落帶出長音的委婉和羞澀。樂曲第二段是歡樂的生活場景,描繪了人們干勁十足的狀態,充滿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此時的音樂在粗線條中加入抹壓滑音與短吟揉弦的結合,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場景中,恰到好處地點綴出西北人的性格,用生動活潑的音樂形象描繪出中國西北的山川大地、風土人情和家長里短。樂曲的末段在經過了幾個樂段后,回到再現部分,升華出莽莽若山之巍峨的大寫意情景之中,此時的每一弓,每個音符都更加開闊。用時間放大手法,將運弓氣息拉寬,呈現出歷經滄海桑田,再回首已能容納萬千的莽莽意向。
(六)中國音樂八意象中的“凄” ——《江河水》
凄美,是從悲情之中綻放出來的美。歡樂的作品能讓人獲得輕松愉快,但要讓作品內涵更加深刻,則多數都需要具有悲情的元素。跟開心相比,悲情色彩更能激發人去深刻地思考生命中的問題。《江河水》就是這樣滿是凄情的樂曲,這首曲子是二胡演奏家、作曲家黃海懷先生移植創作的一首二胡傳世經典。
樂曲講述了一對相依為命的恩愛夫妻,新婚不久,丈夫就被官府抓去外地做勞役。妻子不舍,江邊相送,一對新人灑淚分別。不曾想這一別竟成了訣別,很快便傳來了丈夫在勞役中客死他鄉的消息,一對伉儷從此陰陽兩隔,再無相見。妻子聞訊悲痛欲絕,跌坐在那條曾經數里相送,同丈夫分別的江水邊失聲痛哭。
樂曲《江河水》開頭便是低聲的抽泣和嘆息,在凌厲的音頭后,樂句呈現出一種無力和有力相映的起伏,就像女主人公的內心一樣,難以平靜。在一陣哭泣之中,她疲倦了,音樂的旋律里仿佛是女主人公在睡夢中回憶起了兩人當初的日子。心中滿是甜蜜的小兩口,夫唱婦隨充滿幸福。朦朧中妻子從睡夢中醒來,她驚醒后想起丈夫已經不在人世了,那一切美好只是一場夢中的記憶罷了。如此殘酷的現實讓妻子陷入了驚恐之中。她呼喊著、奔跑著、尖叫著、痛哭著,這一樂段在一片驚恐中回蕩,最后她終于用盡了力氣,音樂在微弱的旋律中結束。但這個柔弱女子今后的命運該怎樣呢?留下對主人公命運的擔憂。
情到凄處,已經沒有語言能夠再去表達什么了,只剩那種滋味回蕩空中。藝術中的凄其實是一種美,藝術中的丑也是一種美。就好比法國文學家雨果筆下《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鐘人卡西莫多,作者將生活中外表丑陋、地位低下的敲鐘人,轉化為藝術上的一種美。這種藝術化對美丑的表達是人類共通的審美語言。①
(七)中國音樂八意象中的“渾”—— 《秦風》
渾之美是一種敦厚質樸之美。渾是天地的起源。《幼學瓊林》中寫道:“渾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②這里的“混”“渾”互為通假字。
《秦風》是二胡演奏家、作曲家金偉先生創作的二胡曲,也是眾多秦派二胡曲之中的上乘佳作之一。樂曲中音樂具有濃郁的陜西民間音樂風格,反映了秦地人們的音樂審美和性格,同時展現了當代陜西地方的音樂韻致,也是先秦時代中國民風樂律的文化藝術傳承。樂曲在二胡標準音的定弦基礎上降低了大二度定音,使音色發生了微妙的改變,變得更加渾厚沉穩。在演奏技法上,根據陜西民族音調的風格,也進行了壓滑揉以及反向滑音等技術處理,在陜西方言同民間音調、戲曲等充分融合的基礎上,表現出秦地音樂的鮮明性格。
(八)中國音樂八意象中的“采”—— 《空山鳥語》
二胡音樂意象中的“采”,是富有活力、神采飛揚的意思,是天地精華外化出來生命的神韻和光華。
《空山鳥語》是國樂大師劉天華先生所創作十大二胡名曲之一。樂曲的創作初稿源于1918年。但直到1928年,才真正定稿完成,并公開出版發表。《空山鳥語》的曲名來源于唐代詩人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③詩中大自然秀麗風采的意境讓劉天華先生心生靈感,想到何不反其意將詩中“人語”二字換為“鳥語”,將“響”字換為“聲”字,并以《空山鳥語》作為樂曲的標題。
《空山鳥語》一曲中點出了兩個主要的音樂形象,其一是空山,其二是鳥語。從空山幽谷,鳥語交映的靈秀山光中表現出一幅空山不見人,但聞“鳥”語聲的詩情畫意之景。空山的聲響是回聲空蕩的效果,在演奏中運用虛實相間的手法來表現山谷的遠近濃淡,讓聲響在山谷中呼應,實音飽滿洪亮,回音則微弱悠遠。鳥語則二胡的用點、按、壓、滑等手法,來表現鳥之間跳、躍、飛、落、蕩、鳴、啄、扇的各種自然形態。
這首曲子中還有一些十分別致有趣的技法,如同音指的運用,就是以無名指、中指和食指三個手指在交替中快速依次滑按出同一個音位,從而產生類似琵琶輪指技巧的點狀效果。再加上輕重緩急的力度變化,在音樂形象上給人以珠落玉盤,鳥鳴不絕回響的感覺。
筆者記得年少時初見《空山鳥語》曲譜,覺得滿紙都是技術和音符,又難學又不中聽。到大學再演奏此曲時,感覺簡單,但卻膚淺而無趣。隨著人生的積累,慢慢地開始對藝術有了一些理解,如今再見《空山鳥語》,可感受到神游在川谷飛鳥之間,進入那種忘我的空山無人之境,雅趣靈韻、神采無限。
結? 語
音樂作為直達靈魂的聽覺藝術,是一種高級的智慧。能夠感知聽覺審美的人,要具有更加敏銳和清明的感知力,它超越了知識的層面,進入思想和智慧的意境。中國音樂審美觀是在審美的角度上與中國哲學思想的一種深刻融合,而文人音樂思維也推動形成了中國音樂審美觀的主要形態。通過二胡經典音樂作品提煉出清、堅、逸、健、莽、凄、渾、采八種具有中國音樂寫意文化思維的意向,以含蓄而古典的音樂方式來抒發對這八種意向美的認知,希望通過這一視角傳遞出人生苦辣酸甜承載的愛與美。音樂藝術是感知宇宙萬物和人生大愛、大美的絕佳路徑,音樂可以直達大腦皮層,更能觸碰心靈。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和諧的基礎是完美的數的比例,音樂與宇宙天體存在類似。音樂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宇宙運行的規律。” ①站在中國文化來看,音樂、美術抑或是文學、歷史和哲學都是人靈魂、思想和情感外化連接天地時空的文化表達,體現出作為每個個體以及不同文化生命群體對哲學精神的詮釋。用覺知力去觀察和感受生命,去愛和聆聽,是完成從肉體到靈魂;從外在向內在的文化升華。中國音樂以中國古典文化思想的視角詮釋出了具有東方魅力的獨特音樂審美觀,將中國民族音樂藝術同中國文化相結合,在深入傳承的基礎上進行挖掘、思考和梳理。
以二胡經典作品中的審美意為基礎進行研究,對中國音樂審美觀的闡述,不僅僅是針對二胡音樂文化的美學邏輯,更是對整個中國音樂文化的一次思考。
本篇責任編輯 李姝
收稿日期:2023-01-04
基金項目:2021—2023年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和教學改革重點項目“基于OBE理念與PDCA方法的音樂表演專業特色實踐教學體系的探索”(JG2021-1181)。
作者簡介:張國亮(1979— ),男,碩士,四川音樂學院民樂系講師(四川成都 610021)。
- 音樂探索的其它文章
- 周以詩樂化性The Moral Cultivation with Music for Poetry in the Zhou Dynasty
- 銅磬考述A STUDY ON BRONZE CHIME
- 川南合江漢畫像石樂舞圖像考A STYDY ON THE STONE CARVINGS OF MUSICAL DANCE OF THE HAN DYNASTY IN SOUTHERN SICHUAN HEJIANG COUNTY
- 游于城:宋代成都城市音樂略考THE CITY MUSIC OF CHENGDU IN THE SONG DYNASTY
- 北朝時期貴族階層的樂舞生產與消費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論清代湖北禮俗音樂文化的社會屬性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