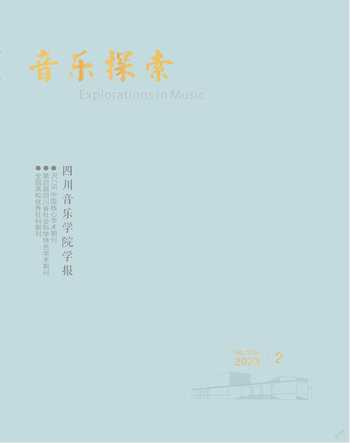論清代湖北禮俗音樂文化的社會屬性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
摘 要 :清代禮俗音樂是在社會不同階層組織的各種禮俗儀式活動中呈現的,官有朝廷地方政府,民有宗族組織,商有商會,從業者有行會,信民有香會等。不同層面的社會階層和組織均對禮俗音樂活動有著不同的需求和期望。梳理清代湖北社會中的禮俗音樂文化,官方以禮樂維護統治、教化風俗;宗族以禮樂迎神祭祖,敬宗收族;而商業的興盛則進一步刺激了迎神賽會和演劇的興盛,商行會以俗樂敬神賽會、融睦四民、彰顯實力。
關鍵詞:清代;禮俗音樂;社會屬性;宗族;
中圖分類號:J609.2;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23)02-0039-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05
禮俗音樂,包括官方禮儀中的儀式音樂和民間禮俗活動中的音樂,自上而下如血脈融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曰:觀為人“廣博易良,樂教也”①。音樂對人的教化功能是如沐春風潛移默化的。社會的不同階層組織在各種禮俗儀式活動中多以合樂作為社會活動的一種呈現方式,同時也期望通過這樣的儀式和活動行為達到其理想的目的。而清代地方組織自上而下,官有朝廷地方政府,民有宗族組織,商有商會,從業者有行會,信民有香會等,不同層面的社會階層和組織均對禮俗音樂活動有著不同的需求和期望。梳理清代湖北社會禮俗生活中的用樂習俗借鑒,其體現了禮俗音樂文化復雜但殊歸同源的社會功能與屬性。
一、官方禮樂與風俗教化
歷代王朝實施禮樂的根本目的,是繼承和完善中國封建王朝禮的制度,將其普化深入地方,從而彰顯天授王權的神圣性,以禮樂教化風俗,鞏固王朝統治。皇帝是王朝官方祭禮和典禮的主持人,體現了神權天授的神圣性;地方官員則是地方祭禮和典禮儀式的主持者,體現了對于一方土地的守土職責和權利象征。清代列入地方祀典的儀式種類繁多,如孔子的祭禮、關帝祭禮和文昌祭禮等廟祠祭禮。孔子的祭禮采用雅樂的最高形式——樂舞,并配合著延續古老禮制傳統的鐘磬金石之樂,還有對于地方神靈的各種祭禮,樂用鼓吹。各種祭禮和典儀皆是維護國家統治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禮樂治國是中國封建王朝堅守的政治體制。晚清政府在強敵環伺、農民戰爭等內憂外患的困頓之時,又把提升關帝、文昌帝君和孔子的祭禮規格作為挽救王朝頹敗的稻草繩,3種祭禮被推崇至歷史最高峰。但是禮法的完備與實際執行的完備之間差距巨大,湖北清代地方禮樂的興衰,一方面與王朝興衰密切相關,一方面由于地方經濟而與官員、士紳的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
清代湖北的地方官員不僅主持列入祀典的各種官方祭禮,有時也會帶領民眾進行祭祀,并按地方宗教風俗配合民意進行祈禱祭祀和參與民俗節日。地方官員以教化地方風俗為責任,需以儒教為重,反對巫儺之風,甚至迎神賽會之風氣;但是,實際上地方官員往往也得遵循地方習俗民風。如城隍的祭祀和民間的城隍神會就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官員一方面進行祀典的祭禮,一方面也會參與民俗的城隍會。地方出現重大災情時,地方官的責任之一就是親自督導祈禳的儀式,有時應民意,還必須主持協助民間的儀式活動,甚至是參與巫覡之祭禮。這也并非完全是對民意的妥協,而是彰顯了地方官員在地方所擁有的至高話語權利,包括通神鎮鬼的祭祀權,而民眾顯然對此是報以惶恐之心并認同的。又如“迎春”之禮,也是以官方為主導的舉城皆歡的節日活動。整個活動禮則按儒家禮法,有禮生掌禮執行祭儀祭祀和鞭春牛等儀式;樂有官方的鼓吹儀仗,樂歌等,如施南府來鳳地區還有禮生唱《鞭春歌》。①此外,樂又有民間的歌舞、百戲、戲曲的表演,如黃州府黃安地區的表演扮故事、打插秧鼓、唱插秧歌;②鄖陽府房縣有農夫表演擊社鼓、鳴大鑼、唱秧歌;梨園子弟則進呈曲本,演出三劇。③各地民間亦有樂戶鼓吹歌舞送小春牛給鄉紳和民眾的這一傳統。在官民共參與的儀式活動中,儀仗鼓吹用樂、祭禮用樂、歌詩吟唱和民間節俗用樂在這樣的儀式過程中展示和融合。官方和民間的禮樂俗樂融合也體現在祭祀城隍和城隍神會儀式中。由此,也使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民俗趨勢:民間禮俗越來越形同官禮,而又不能真與實際官禮等同,從而走出了一條“戲化”的儀式表演模式,呈現出一種如“王制”的民間神會禮樂實景。
教化風俗,還以教育為本。自宋以來禮下庶民,規范的家禮儀式的禮樂教化也是需要進行教育傳承傳播的。清代官方對于儒家家禮主要通過行令的頒布和具體實施教育教化民眾。如改土歸流后,鄂西原土司地區鶴峰等官員就立即以政令,約束風俗,推行儒家家禮。從當代土家族傳統婚禮以及土家族喪儀堂祭之禮盛行地區來看,顯然是起到了實際的教化作用。此外,明清地方城鎮到鄉村的各級社學也承擔了這樣的教化風俗的作用。社學是明清政府為負擔不起學費的民眾提供的受教育機會,而修建社學教化風俗、推廣家禮也是地方執政官員成績的重要體現,是可以被列位政教、名臣志的政績。雖然沒有實際經費支持,但地方官員和士紳也多愿意募集捐款來進行社學和義學建設。社學教習內容通常以教庶民及子弟行“冠婚喪祭之禮”為基本,這一制度是源自明代。明清對于家禮的推行,以家禮教化民眾,也使得清代儒家家禮禮樂與民俗婚禮禮樂構成了豐富的民間家禮儀式音樂文化。
在上古與中古時期,禮樂僅針對士大夫以上的君子階層;而自宋以后,禮樂成為教化民眾的重要國策,也用于一般士人和庶民階層。儒家家禮禮樂是封建王朝國家禮樂制度之禮下庶民的組成部分,如康熙《漢陽府志·典禮志》記:
“然,行之于下則有冠、婚、喪、祭;行之于上則有吉、兇、軍、賓、嘉。”①王朝禮樂、家禮禮樂,自上而下建構了封建王朝的整體禮樂制度。然而,官方的意志和法令雖然可以約束廣大的人民,但是人民原本的習俗和信仰是不可能輕易動搖的。那么,由上至下的禮,雖然經過宋代大儒的斟酌設立和明清儒生的通俗解讀,在民間仍然形成基本類同,但仍是“和而不同”的各種儀式模式。至于原本融入民生的道家、佛教,以及巫儺宗教信仰,更不可能退出民眾的家禮儀式之外。如湖北婚禮中的攔車馬儀式,以及喪、祭儀式中參用道家和佛家法事活動等。
關于家禮之樂,至今沒有看到任何文獻有言及制定家禮之樂的,推測應是由那些常被歷史記錄者遺忘的樂人們逐漸完善的。古代為官員服務的樂人為樂戶。禮下庶民,樂戶從服務于官員,漸次服務于一般士人,漸下移至庶民。因此,家禮之樂的創造的最初由來必然與樂戶相關,而樂戶為官家服務,那么一條可行的創作道路就擺在了眼前——官員家禮之樂向士庶家禮之樂發展。樂的發展,在清代應該有了進一步的俗化過程。清雍正年,樂戶制度廢除,音樂人不再是賤民,一些家族也在家族內培養樂師,從而參與家族家禮禮樂活動,以及其他迎神賽會的活動。因此,各地的家禮禮樂,儀式相近,用樂模式相近,然樂風迥然。此外,家禮儀式多為三教合一的儀式和用樂模式,即使士大夫也不能免俗。
明清官方繼續大力推行儒家家禮禮樂,而民間宗族也樂于建祠堂、設祭田以用于家禮儀式。究根結底,這還是源于中國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禮制”社會,社會各階層具有接受儒教禮制的傳統。自上而下的儒家家禮禮樂,在政府的強力推進中,在地方士階層的響應中,逐漸深入民間禮俗體系。更多的興盛宗族,如清代中葉鄂東地區,從興建家廟,轉向興建祠堂,并以公產祭田等維護家族祭禮。②在官方制度法令中,在少數民族地區,如鄂西土家族,儒家家禮禮樂也漸次成為主流禮俗制度。綜上,家禮禮樂的下移,對于地方禮俗制度有著完善的意義,從而自上而下進一步統一禮制思想,以儒教為核心進行國家政權的維護。
二、宗族禮樂與敬宗收族
聚族而居是中國封建王朝時期以宗法制度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模式。至宋以后,以儒家儀禮教化天下庶民,即使庶民也重視宗法制度,開始注重修纂家譜,樹立家規,修建家廟或祠堂,施行家禮禮樂,以鞏固家族的凝聚力。明清以降,宗族已然成為基層民間社會的重要組織,也為地方新興勢力,不僅在商業,也在地方治安、教育、行政以及慈善事業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宗族是儒家家禮推廣的重要組織,家族成員的人生禮儀皆是家族大事,而伴隨著人生的誕生、冠禮、婚禮、壽誕,死亡之喪儀、葬儀,以及對于祖先考妣的祭祀,皆可為宗族繁衍興旺的大事,是家族成員必然要參與的活動。對于家族中無力承擔者,宗族也會有義務進行扶持,并涉及資助婚喪嫁娶、教育科考等人生大事。乾隆《廣濟縣志》記:“廣濟風俗大半聚族而居,雖在齊民,必立先祠,春秋祭祀,少長咸集焉,頒胙均惠,猶存敬宗合食遺風。”③由于聚族而居,合家族之力,故而即使一般平民也可建立祠堂,進行春秋祭祀。雖有“敬宗合食遺風”,但實際則是新的宗族模式的家族祭禮,乾隆《黃梅縣志》記:“富家大族皆立祠,然皆合族公立歲暮合食祀祖者,非五服宗子祀先之古法也。”①明清的宗族已經擴展到了包括五服之外有親緣關系聚居的每個同姓家族,這樣勢必擴大了區域宗族的合聚力和影響力,從而宗族對于地方風俗同化等諸種問題起到決定性作用。又如同治《通山縣志》記:“大族各建祖祠,置祭產、立祭會。清明寒食間,合族老幼衣冠輿馬詣墓所,掛楮錢、殺牲備物以祭,鼓吹聲不絕于道。祭畢,而歸計口分胙,紳耆倍之。秋冬聚族于祠,以序昭穆,遵行三獻禮,招優演劇以燕,或百數十席不等,亦敬宗收族之一端也。”②遂,家禮禮樂的推行是與明清地方家族宗族的勢力擴大有著直接關系的。這一文化現象也遺存于當代中國各地,如在湖北仙桃鄉土農村的熊家灘(熊姓)、沈灣(唐姓)等這樣的行政鄉村區域,其中仍體現了以同姓同宗聚族而居的現象,祠堂、家廟漸次被修復,儒家家族家禮文化正在復興,喪儀也有延請伙居道做法的現象。
除了歲時中的祭祀,節日和宗教活動也是宗族闔族參與的重大事件。如明代《石埭縣志》(今屬安徽省)記:“燈節有四十八大姓,輪放花燈照天燭地,笙歌達旦,為魚龍曼衍之戲。此雖耗費,然亦見升平日久,風景繁華。”③這是記錄了明代嘉靖前舊志所描繪的明代盛期安徽石埭縣大宗族在元宵節放燈鼓吹的繁華景象。聚族慶賀節日也是宗族的重要活動,如民間舞龍常常為“聚族”的表演形式。“聚族為龍燈,或披錦為獅猊,咸鼓吹導之。”④龍燈在玩燈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這與悠久的龍圖騰有著密切的關系。傳統制作龍燈是家族在新年前的準備,民間要請陰陽師“看日子”,典籍稱之為“筮日”。擁有家廟和祠堂的大族往往在廟堂內制作龍燈,包括賽龍舟或送瘟的龍船,制作前后還往往請俗道黃冠進行請龍的儀式。玩龍燈的日子首先要進行祭家廟或祠堂的拜神祭祖儀式,祭拜罷還需先娛神,將龍燈在廟堂前玩耍。廟堂是玩燈觀燈的核心地區,匯合其他諸燈歌舞,娛神娛人。龍燈還需遍巡本族,為本族各家逐疫,常以在堂屋巡回一圈表示驅邪避災。表演者都為男性,小兒則舞草把龍。
以流傳在崇陽縣、蒲圻隨陽、通山南林橋一帶的龍燈“龍虎斗”(又稱“單龍戲虎”)為例。舊時燈節開始后,宗族要先請陰陽先生選吉日良辰,在家廟或祠堂中進行祭祀神靈、祖先的儀式。這一儀式應當是按照家禮的三獻禮模式展開。祭祀畢,還需在廟堂前為神靈和祖先先行表演,然后才按照河流自下而上巡游。隊伍由大打樂隊(大鼓、大鑼、大鈸、銅鼓、馬鑼)開道,龍燈居中,小打樂隊隨后(堂鼓、堂鑼、小鑼、鈸、馬鑼)。龍分五色,按五行五色,其中紅、黃兩色只有區域的幾個大戶才能使用。九人舞龍,一人耍虎,舞龍隊伍首先要巡遍本村本族。然后沿河上行,每進入其他村落,必須先入此村的家廟或祠堂進行祭拜,然后依次各家巡游,需進入人家堂屋轉一圈。按當代的遺存來看,這一儀式有著消災祈福的意義。玩燈的地方是村子的寬闊場地,如曬谷場(大禾場),主要由小打樂隊伴奏。此外,還有當地的村民加入腳盆鼓擊節。腳盆鼓是當地居民添丁所制,有一兒男制鼓一面,家族男丁越興旺,腳盆鼓就越多。聚族而居幾百面的腳盆鼓伴奏玩燈,體現了家族興旺的勢力展現。此外,端午節的賽龍舟、送瘟船等儀式活動也是具有宗族組織的特色。
宗族也是神會興起的重要推動力量,這是因為宗族和廟宇原本就有著直接的聯系。祠堂源于前代的家廟制度,自宋儒學名士倡導修祠“收族”之風俗。在祠堂尚未興起時,地方士大夫多有家廟,既供奉神像,也供奉家族祖先。如鄂東地區在明代中葉至清康乾前后,大家族多以家廟為主,祠堂罕見;康乾之后,祠堂的建設進一步興起,建廟熱衷則衰減,但是家廟仍未消亡,而是漸漸成為僅供神像的香火廟,廟產依然在宗族手中傳承。①遂,康乾之后興起的神會必然得到了地方宗族的直接支持。此外,宗族的祭祀活動也與迎神賽會融合。同治《大冶縣志》記:“大家則建祠堂興瑞,人于冬春之際,舁其祖神,行鑼過邑,遍歷彼族,”②光緒末年,因國家變法維新,創建新學、新軍需要大量經費而征收廟祠資產,神會逐漸衰落。民國六年(1917年),安徽黟縣鶴山《李氏宗譜》卷末記:“明季流寇擾亂,蹂躪幾遍天下,而新安尤甚。我族當年人丁尚微,因邀集松領、榆村、湖洋川凡四十余姓,名曰六關,同供奉文孝皇帝諸神像。每逢九月塑,迭相迎送,自外視之,為踴躍,而實則聯眾姓以資捍衛,即古者守望相助之意也。后人不察,夸奇斗富,踵事增華,寢至入不敷出,姓姓受累,不其戚歟!今幸圣天子下明詔,凡迎神賽會一是嚴禁。于是同關諸君子上體天子微意,下恤窮黎苦衷,筑廟于立川僧寺之旁,將神像送入,俾神靜人,無復迎迓之勞,蓋善舉也。……光緒三十年仲春月……”③由《李氏宗譜》可見,家族參與神會是由其修建神廟開始:一方面期望獲得神靈的庇佑從而保佑祖先神靈,期望香火不息;一方面通過迎神賽會來展示自身的實力,聯合宗族力量,從而得以捍衛自保。但是,隨著經濟的富足,夸富之風又再次在清代中葉以后漸興,而晚清時期的資本商業的興起,神會并未因為帝國的沒落而衰落,甚至至光緒中期達到了極致。晚清湖北各方宗教信仰和用樂皆體現了或夸富競奇或展現自身實力的競賽之風。
鑒于家禮禮樂、節日慶典、宗教迎神賽會等對宗族的重大意義,民間音樂品種的產生和發展也會與宗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家禮用樂中,家族對于自家家禮用樂的設置有一定話語權。如其中的歌樂文章,有時恰是族中有聲望、有學問的族人自己編寫的。宗族為了區別于其他宗族也會產生具有本區域特色的迎神賽會歌舞,如湖北嘉魚煙墩鄉大屋孔家的“五龍拱圣”龍燈就是孔氏家族所特有的龍燈。此外,家族也會為了自身的用樂需求培養家族的樂班,如黃安縣“打得勝鼓”。清代志書中的“打得勝鼓”今日可考的有蕩腔鑼鼓,是一種家族傳承的鼓吹樂,主要傳承人為“王氏家族”④。目前有記錄的有七代傳承人,第一至第三代傳承人皆為晚清時期王氏家族的族長級別或士紳階層的重要宗族人物。族長是組織家族活動的領導者,清代節慶活動中,王氏家族當以王氏族長領導族中壯男子,組織春節和上元燈節的各種活動。再者,宗族凡有重大事件皆有演劇之習俗,地方戲曲的興起歷史中不乏宗族的助力,這一點在當代的學術研究中多有體現。①明清宗族演劇習俗涉及宗族的紅白之事,歲時節日和迎神賽會等諸事,各地皆是如此。明清時期的戲臺、戲樓皆主要是廟宇和祠堂修筑,專門演戲的戲院直至晚清才出現,如湖北第一座商業戲院為1899年徽商創辦的丹桂茶樓。因此,促進湖北清代的演劇繁榮活動中,自是包括受雇于宗族家族的各類活動。此外,各地宗族修續家譜、修祠之際也有著演劇的傳統習俗,一般連演三日,稱之為“唱譜戲”。宗族熱衷地方戲曲,但是對于戲曲也是有著區別對待的,比如清政府所禁的楊柳花鼓之戲,也多被地方宗族所鄙,甚至也有宗族立家規禁止子弟觀看花鼓戲。
在變革時代中,一些宗族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弊端。如民國三年(1914年),監利《平氏族譜·卷首別錄三》記:“其三曰:禁游戲。古者儺以逐疫,而民間歌舞太平傳為歡樂,冬春行之。今四季皆然,監邑毛市小鎮,必用漢班,動糜千金演戲,經月鄉里。獅子、花燈,竟用羊皮新口,龍燈紅緞刺繡。端午競渡,楚之故習,民家樂事,吊古人之忠魂,為□悅今人之耳目,則實亦止于五日而已。今邑之龍舟動輒經月,沿岸采物,皆用珍珠、琉璃、羽毛、綢緞所為。鞭炮雷轟,煙火迷天,夸賒斗靡,日化千金。其用物采之奢麗與獅子、龍燈同一暴殄。近來,有沔陽戲名曰:‘花鼓班,此皆匪類斗就之班。晝則演唱淫詞,夜則賭博行竊,久逢嚴禁不止,今延及各縣。邪曲道淫,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又有無恥紳豪,勾留圈養,比為頑童。凡此數事,鄉邑皆然,男女雜沓,游觀成群,荒時廢業,又復勾引外方賊盜,擾害鄉民。此種惡習,至今未除,懇示嚴革,有為班主者,罪之,為首演此戲者,亦罪之,以正鄉里風俗。”②此文論及晚清時期監利春節元宵燈節,端午競渡,歲時迎神賽會的奢華之風,以及花鼓戲敗壞風俗等時俗。這是平氏家族族人感懷之言,警戒子弟;但將“盜賊”與花鼓戲曲藝人如此關聯,也是有失公正的,而這種言論在明清政府文人禁毀戲曲、小說的言論中多有所見。③
綜上,禮樂在宗族是家族家禮之本,闔族迎神祭祖,歡度佳節,在長幼尊卑的儀式中完成禮樂的教化,以促“敬宗收族”大義。在我國封建王朝的宗族禮樂和宗教活動中,由于同樣存在時代的局限性,不乏夸富斗奇的陋習,也為宗族提供了轄制愚民的某些禮儀習俗。
三、商業行會的俗樂彰顯
藝術的繁榮是離不開物質經濟基礎的,歷來商業發展都對音樂藝術有著直接的促進作用。湖北位居中國的中部、長江中游地區,依賴天然的地理優勢,商業發展迅速。清代中葉,漢口成為清代四大全國性城鎮之一,以商業通達而著稱。各地商人形成商幫在漢口和湖北各地經商,代表有徽商,以晉商和秦商為代表的山陜商幫,江西、廣東、浙江、河南、四川等地區商幫,本地又有咸寧幫、黃州幫、武昌幫、荊襄幫、東湖幫等商幫。行業間為了各自利益也組成了各種行業行會。湖北原本就有濃郁的宗教信仰傳統,而商業的興盛則進一步刺激了迎神賽會以及各娛樂行業的興盛。
湖北的鄉村迎神祭賽活動常是以宗族為組織,以族長為首,或以社為單位,但也多為聚族而居,也是以同姓宗族為主力,小姓為附屬參與。而在城鎮,尤其是商業發達的城市,如漢口、沙市、宜昌等在清代中葉已經成為商業中心的核心城市,就不可能以宗族為核心,而是以街坊為區分進行節慶活動和迎神賽會。但是市民醵金所出還是有限,因此,形成了商家攤派的責任義務。如在官方執行的迎春活動中就有著商戶攤派的久遠的習俗,可追溯至宋代。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禮部曾議準直省府州縣迎春不可以采用鼓吹、彩亭,對于向商戶征收的用于裝潢故事的臺閣、張鼓樂樹旗幟等科派以及里長科派,其實也多由民醵金,用于迎春的馬匹車輛以及征用優伶藝人等項一律嚴行禁止。①而實際這樣的禁令在許多地方都是名存實亡。從湖北來看,民俗活動中的迎春多有臺閣故事、鼓吹歌舞,并醵金演劇。商人尤重祭祀,看重神靈的庇護,是迎神賽會活動的主力。除了坐商商戶的攤派,商會是出資的核心主力。尤其是形成巨大經濟體的商會,如上述涉及的本土與外來的商團。清代神會的再次興起也恰是進入康雍乾盛世時期,各地商團每到一地,但有實力首先就是開創會館,而早期會館多形成了“廟館合一”的特色,增修寺觀,設立神會,購置廟產田產,以租金作為會館演劇酬神之費用。至道咸同光之時,隨著商會多年積累,祀神的廟產自然越來越多,神會也在競爭中越顯奢華,直至光緒末神會才漸漸衰落。
在清代,無論官員還是士庶,看戲是生活娛樂的重要內容。對于市民而言,沒有能力豢養家班,觀看演劇的主要場所就是廟會戲臺、戲樓。而這在清代主要是商會神會帶來的福利,神廟前設戲臺,甚至搭建戲樓。會館有內外戲樓,在內招待會館內部親眷、官員、友人和商友;外戲樓敞開向街道,在各種迎神賽會的活動中以娛神為名,實為招攬人氣,也和睦四民。所以,清代市民觀劇多不用費用,演劇是以酬神為由,出資請戲班則多是組織神會的出資者。商會是神會創辦的主要經濟體組織,遂各地的戲劇傳播和發展與商業的興盛關系密切,由此,也就有了“商路即戲路”之說。湖北地區以徽班和山陜商人最具有影響力,迎神賽會的活動中徽調和秦腔變得不可或缺。徽商是最初在湖北最具有影響力的商幫,明代中葉已經活躍在漢口,以鹽業起家,涉及茶葉、木材、糧食等等多種產業。徽商實力強盛,自然安徽地區的戲曲也是迎神賽會的主要戲種。如明代中晚期隨徽商水陸兩地傳入江西、湖北等地區的青陽腔,在晚明時期逐漸在各地形成了地方高腔唱腔戲曲,明末清初湖北清戲產生。此外,清代徽商帶來的徽調也是深受湖北觀眾的喜愛。清代康乾時期,隨著山陜商人的強勢進入,秦腔也大舉而來,湖北遂產生了以秦腔和本地楚調結合的西皮唱腔。徽班以二黃唱腔為主,西皮二黃在湖北于嘉、道年間形成漢調,而聲腔融合的時期恰是山陜商人進入湖北的時期。至道光年間,本地產生的漢調就后來居上,山陜商人也出資創辦漢調科班,對漢調早期發展多有促力。如德安府的桂林班,即是由山陜商人商團興辦的著名漢調科班,連續有八屆科班,影響深遠。①
商會興辦神會除了期望獲得神靈的庇佑,以信仰團結同幫商眾,還能夠更好地融合到市民的信仰生活中,更容易與鄰舍和顧客形成更融洽的關系。除了祭祀酬神,山陜商會演劇一般還有以下的一些名目。除了熱衷四時迎神賽會,商人也得進行宗族祭祖活動、商人經商也重于宗族觀念,商團也常具有宗族的特征,同宗同姓也需祭祀先祖。演戲也為娛樂和聯誼,在聚會的時候,可用演劇排解鄉愁,聯誼同鄉。除了自身娛樂,也多用于娛賓——上可招待達官顯貴,下可以戲鬧會,招攬人氣。人氣足,就形成了商業宣傳的作用。山陜商人等有實力的商會常以重金聘請戲曲名家,彰顯自身的經濟實力,也招待各方來客,從而獲得當地民眾的好感,促進自身商業發展。②
商業興盛,行業也就豐富。各行當均有自己的行業祖師,并在祖師誕等重要日子大興慶賀,其模式也是迎神賽會和醵金演劇。除了每個行業祭祖師的迎神賽會演戲活動,清代湖北還形成了多個行業同場競技的賽會活動,最著名的是武昌磨子會。磨子會是武昌地區四十八行當利用端午期間的迎神賽會活動形成的展示各自實力的神會。每一個行當都形成自己的迎神賽會隊伍,既各自為政,又相互競爭彰顯各行實力。從用樂的角度看,每一支迎神的隊伍有傘蓋、旗幡、回避牌……儀仗具備,鑼鼓齊鳴,歌舞雜扮必然也穿插其間。四十八行磨子隊;蜿蜒曲行,極為熱鬧。武漢竹木業要在端午節祀楊泗水神,漢口是竹木業的匯流核心地區,此時更是要高價聘請漢劇名角演劇幾日酬神。因此,敬神賽會和演劇為凝聚行會聚力,彰顯行會實力的手段。
結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禮俗音樂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歷代帝王將禮樂視為政治之端。禮俗音樂文化對于區域空間的政府和四民而言也不僅僅是作為“娛樂”之樂,還被賦予了禮樂教化的社會功能。政府以禮樂風俗教化作為治理地方的首政,也被認為是居于刑罰之上的上策。宗族以禮樂實踐儒家家禮,以禮樂敬神祭祖,以迎神賽會驅趕瘟疫,通過禮樂活動,融睦宗族。而商業的興盛則進一步刺激了迎神賽會以及娛樂各行業的興盛,商家行會的最大助力直接促成了“月月酬神,行行做會,六臘不停,天天唱戲”③的民俗景象。通過這些民俗音樂活動,商會行會遵循宗教完成四時迎神祭祖的儀式活動,也彰顯了自身的經濟實力,甚至是“原始力量”的實力。
本篇責任編輯 錢芳
收稿日期:2023-02-20
基金項目:2016年武漢音樂學院優秀人才培養項目、中央部委屬高校與地方支持合作計劃項目·武漢音樂學院藝術博士點建設項目“湖北清代禮俗音樂文化研究”(XW2016B01)。
作者簡介:李莉(1976— ),女,博士,武漢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湖北武漢 430060)。
- 音樂探索的其它文章
- 周以詩樂化性The Moral Cultivation with Music for Poetry in the Zhou Dynasty
- 銅磬考述A STUDY ON BRONZE CHIME
- 川南合江漢畫像石樂舞圖像考A STYDY ON THE STONE CARVINGS OF MUSICAL DANCE OF THE HAN DYNASTY IN SOUTHERN SICHUAN HEJIANG COUNTY
- 游于城:宋代成都城市音樂略考THE CITY MUSIC OF CHENGDU IN THE SONG DYNASTY
- 北朝時期貴族階層的樂舞生產與消費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文獻記載與現實關照Documentation and Reality: The Stories of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ese Music Doc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