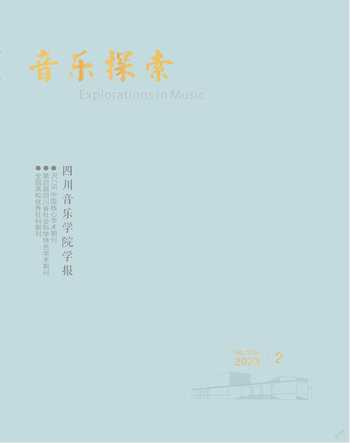團伊玖磨歌劇《素箋鳴》和聲技法思維探賾THE HARMONIC TECHNIQUE IN DAN IKUMA’S OPERA SUSANO-O
張雪鋒 魏揚



摘 要:日本歌劇《素箋鳴》是團伊玖磨創作生涯最前衛的一部神話題材作品。作曲家在該劇中的和聲技法運用純熟,和聲的基本構成材料、和弦的結構形態、和聲的序進方式及和聲的終止樣式等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個人風格與現代質感,以無調性、泛調性技法營構神秘的音響特征,音樂表現與戲劇功能緊密扣合。作品突破傳統的戲劇審美功能邊界,以新的戲劇音響表現布局全劇的音樂結構力,對現代歌劇音樂創作而言有其借鑒價值。
關鍵詞:素箋鳴;團伊玖磨;日本歌劇;和聲技法;戲劇音響
中圖分類號:J6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23)02-0122-1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14
引 言
日本作曲家團伊玖磨(Ikuma Dan,1924—2001)一生創作了大量的體裁多樣的音樂作品,以其多元風格的交響樂、歌劇、藝術歌曲及影視音樂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較大影響。他一生共創作了7部不同主題的歌劇,而他的第一部歌劇《夕鶴》(1952)就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奠定了他在日本歌劇創作上的重要影響力,他中后期的歌劇創作主要體現在音樂語言的探索與不同技法的嘗試上。7部歌劇作品既代表著團伊玖磨在寫作技法、表現內容及思想觀念上的不斷演進與成熟,又顯示出他在不同時期創作理念上的風格變遷與音樂語言的階段性嬗變。這些作品所展現出的東方音樂的哲思韻味和美學品格,形成了作曲家強烈的個人音樂風格與藝術特征。
由團伊玖磨編劇、作曲的《素箋鳴》(Susano-o)(1994),是其后期創作的歌劇,選自《日本書紀》《古事記》中的神話題材,三幕聯綴體正歌劇,1994年11月首演于神奈川縣民大廳。該劇講述了本該治理大海①的素箋鳴尊②,突然現身于天照神③所轄的天界④領地,并開始了一場粗暴的破壞……由此震怒的天照神,移居歸隱于洞穴“天巖戶”之中,天地隨即陷入無光的幽暗境地。而生活在葦原中國①、處在痛苦中的人們,尋求智者思兼②進行磋商并獻出一計,將群眾與女人們聚集在“天巖戶”的洞口前,引出天照神出面討誅素箋鳴的暴行,將其問罪、懸吊,最后被驅逐、流放人間。第二幕切換至朝鮮半島的海岸小國:曾尸茂梨國,曾尸茂梨王的妹妹金姬與銀姬向海而生,終日在和平的國度里唱著幸福的贊歌。一天,不省人事的素箋鳴被抬了回來,在金姬與銀姬的悉心照料及巫師的神秘儀式下,不久便恢復了神智。曾尸茂梨王也急忙趕來噓寒問暖,素箋鳴第一次體會到人間的真情。第三幕發生在出云國③的鳥發山中。葦原中國已陷入一片混亂,最為棘手的是出云國。因此,素箋鳴來到了出云國并遇到了怨靈妖怪,于是拔劍將它斬殺。“天之鳥船”④繼續在黑暗的河流上行駛,素箋鳴歷經磨煉,最終贏得尊重與赦免。
本文從和聲技法層面剖析該劇的戲劇性音響效力與宏觀和聲邏輯。《素箋鳴》中的和聲語言十分豐富,既能管窺到日本傳統技法的承襲與運用,又清晰地營造著現代和聲的音響審美,以無調性為主,在一些特殊的唱段表現出調性、泛調性特征。透過整部歌劇,不難發現其創作技法是西方的,而音樂思維的內在邏輯卻是東方的,現代和聲技法中所蘊含的傳統調式主題元素與現代半音體系的交織及其變異、復合式和弦結構形態的分布、和聲序進中的衍展邏輯、和聲終止樣態等方面的理性安排與布局,是形成作品獨特風格且異于其余幾部歌劇的重要體現。筆者通過對該劇和聲技法的分析,梳理團伊玖磨現代性和聲思維與創作軌跡,探索作曲家晚期音樂創作中的個性化和聲語言、使用手法及觀念,以便于對其歌劇音樂特征進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參照。
一、和聲材料的基本構成元素
歌劇《素箋鳴》中的和聲材料較為多樣,大致可歸納為四種類型,各種類型的構成因素并非單一形式,更多是相互混合、穿插的搭配關系,以此來強化和聲音響的豐富性和結構的交緣性。
(一)以五聲調式為基礎的構成成分
該劇多表現為泛調性與無調性特征,但在一些特殊的唱段中,仍然能清晰看到日本的五聲調式印跡。
(二)以復合調式為基礎的構成成分
復合調式意味著在縱向上形成調性與和聲的雙重復合思維。
(三)以全音階為基礎的構成成分
全音階是整部歌劇中重要的樂思組成元素,占據相當多的內容篇幅,其音響材料的結構形態、表現方式和功能屬性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宏觀音樂設計和布局,具有主題性意義。
譜例4為第一幕《天照》詠嘆調中的和聲片段,此處人聲旋律以全音階上行級進,剛好與樂隊的全音階結構下行級進形成反向進行,內聲部大二度結構的和音E—F和F—G、低聲部的低音同樣呈上行級進關系,這種全音形態成為該詠嘆調的重要音響材料,同時在不同場、幕之間多次運用,具有基礎性結構作用。
(四)以半音體系為基礎的構成成分
半音化是這部歌劇主導性音響的特征體現,以半音材料構成的和聲要素、結構形態及發展動機所形成的主題式進行近乎貫穿全劇。
譜例5是第一幕中的合唱和聲節選片段,半音化發展思路清晰,前4小節上行半音級進,后2小節開始反向雙音下行級進,音響強勁有力。整個結構屬于泛五聲音階的橫向演進,織體密度均勻、和聲性格凸顯表情化陳述,音樂語調急促且富于戲謔特征,進而強化著不協和性與戲劇性沖突。
以上四類音樂材料基本上構成了歌劇《素箋鳴》的骨干性和聲元素,這些素材的選擇與組合勢必產生某種特定的音高關系并以體系化方式呈現,為音樂風格的個性發展和獨特面貌提供“顏料”保障。作曲家既立足于日本音樂的色彩基調,又融合了西方現代技法的創作思維,使作品始終具有東方美學理念的同時,亦兼顧多元化藝術思潮和音樂視野,進而極大豐富了歌劇的音響內容。
二、和弦的復合結構形態
前面梳理了和聲材料的基本構成成分,它們自然成為該劇主體性和聲語言。若將主要的和聲材料進行系統化整合,可以劃分出四類復合式和聲結構類型,分布在全劇的各個場、幕之中,作用于整個戲劇情節和唱段表現需要,形成豐富多彩的和聲音響結構力。
(一)和音式復合結構
“和音”是指“特定結構的音的縱向集合體。”①“和音式”復合脫胎于“中心和音”的衍生與擴展,同時又具有某種“中心”原理性結構意義。中心和音是指:“作曲家選擇自己美學上合乎理想的、特定結構的和音(一個或一組),為音高關系體系的基礎——中心成分,通過重復、移位、變化、變形、派生對比等發展手法,產生出整首作品的音高關系體系”②。進而言之,它具有技術上的三個基本特征:“(a)有中心;(b)通常以不協和的音高綜合體為中心;(c)通過以不同的方式發展這個音高綜合體,而構成作品完整的音高體系關系。”③
譜例6為和音式復合的典型結構。首先,它具有主題性(中心)特征,高聲部緊密圍繞半音化和音以“階梯式”形態下行不嚴格模仿發展;其次,中心和音不斷變化、移位、衍展派生,以不協和性為特定音響基礎;其三,通過相同的發展方式(尤其是節奏型的重復)形成半音化序進軌跡,低聲部形成和聲補充。這里主要以和音為基本構成成分展開衍生,通過特定結構的音高組織思維來發展特定結構的和音樂思,上、下聲部構成反向復合式和聲結構,營造緊張且富有日本音樂特征的情緒基調,和聲張力得到有效發揮。
(二)音組式復合結構
“音組”通常是指“三個音以上的音程集合體,雖然它也可能由兩個音構成單一音程,但在20世紀的音樂作品中仍以三個以上音程的聚集為多見。”④
譜例7是第一幕第一首合唱中的和聲片段,單從高聲部來看,它主要體現和音式半音下行級進,結合低聲部的發展動機,作曲家明顯選擇了三個音由遠至近縱向疊合的方式構成反向音組結構,其音高組織方式在某種意義上與傳統調性音樂的“主題動機”保持類同的音高組織技術,即使脫離了調性和聲的制約,但模進的音高關系仍具有統一性作用。
譜例8是第一幕第四首合唱中的節選片段,是典型的線性音組式復合結構。這里同樣借鑒調性音樂中的“線性和聲”(Linear-Harmony)思維,但基礎結構成分卻是不穩定的音組集合體。作曲家創造性的賦予其特定的音樂形態,通過模進、移位、變形及派生的組合手法,充分寓以主題形態來展示音組中的音程內涵與表現意義,形成發散式貫穿衍進,既呈現了樂思意圖和音響追求,又使整個音高結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音列式復合結構
音列式復合主要以作曲家在某種創作思想、音響觀念或文化視域、藝術審美的驅動下,選擇某種有結構意義的“音列”為作品的基本成分,它不同于完整意義上的音階結構,似乎界定在介于音組結構與音階結構之間的音高組織形式。
(四)無調性復合結構
整部歌劇的宏觀音響布局重點展現泛調性與無調性音響內容,因而無調性復合材料與音高組織手法成為該劇的主導創作特征。
1.半音化復合
半音化在歌劇中近乎貫穿使用,而且是各有特點。
譜例11是第二幕第一首合唱唱段的節選,它的特點在于隨時置換不同的音型與結構動機。前2小節是柱式和弦結構,第3~4小節是雙音級進式線條結構,第6小節是綜合型結構,形成不同的音型模塊相互嵌合,雖不受調性思維和終止式的束縛,但都分別截取不同模塊間的共性材料(純五度和音)來衍生發展,以實現在變化中求規律性陳述的功能意義。
2.三全音復合
三全音復合音型結構是固定且有明確導向意義的設計。
3.音塊結構
在這部歌劇中,無調性和聲結構以密集的“音塊”(Tone Cluster)①音響形態呈現的不算多見,譬如《天照》詠嘆調開場就以這種音響表現方式,目的是為了展示天照神的威嚴形象與宏大氣場。
譜例13為第一幕倒數第二唱段的片段節選,它的主要特征是以音塊的形式集中表現某種神秘的儀式和陰冷氛圍,低聲部泛五聲性旋律快速起伏也進一步配合并強化音響的緊張性,“這種不協和的音群在觀念上能驅除邪惡,連續鳴奏越集中、聲音越鏗鏘響亮”。②
4.包置型結構
包置型結構在近現代和聲中是常見的形態之一,可看成是分層和聲的一種。在這部歌劇中,作曲家以類同疊置的方式分別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中安排了三次。
譜例14是第二幕第五唱段的和聲節選,一開始上方聲部為八度形式重復疊置,將結構分裂成二度關系的旋律形態,表現為包置和音旋律,隨后將旋律躍然至高聲部,形成旋律包置和聲的形態。整體材料以二度與四、五度和音為主,運用半音夾置的方式復合而成。這種做法既類似于中國“五聲性調式和聲”①的配置方法,又兼具“純五度復合思維”②的擴展性特征。
可以發現,這部歌劇中的和聲結構形態均建立在復合邏輯基礎上。這種復合邏輯既保留了日本民族調式的和聲材料,又將音高組織方式和現代和聲思維與無調性技法相結合,尤其是半音和聲與全音音階、調式音列與純五度復合和聲的有序搭配,既可以保持調式風格,又能突破原有調式色彩,形成具有鮮明現代質感的戲劇性音響,但又沒有完全脫離傳統和聲元素,在有效突出歌劇和聲語言個性化的同時,也使和聲結構力滿足戲劇矛盾沖突的布局特征。作曲家的和聲手法運用,不同于東西方任何音樂流派的和聲體系,但又借鑒了各個時期的和聲思維,一方面保證了民族性基調,一方面又具有非常時尚的現代感,同時蘊含著深厚的東方美學觀念與文化外延。
三、和聲的序進方式
“和聲材料的相互關系是通過和聲連接進行體現,而和聲材料進行時促使產生統一作用的邏輯稱為和聲序進,它是由聲部的橫向運動連接產生的規律。”①
(一)主題式和聲序進
主題作為樂思進行的特有結構形式,對音樂發展具有引導性功能意義。歌劇中的和聲序進以主題式展開,有利于強化音響的呈示性內涵。
譜例15為第一幕第二首合唱的和聲節選,旋律帶有明顯的重復人聲主題旋律特征,基于復合和聲結構與旋律上、下聲部交替進行,樂思與和聲動機以交疊方式貫穿發展,形成主題式強調。
持續音在傳統和聲中頗為多見,常見的有主音持續、屬音持續等方式。
譜例16在劇中出現多次,這種持續進行借鑒傳統和聲中的持續音方式,意在突出某一和聲結構的主體性地位。這里以純五度復合和聲為基礎,一方面增強高聲部和聲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又以動力化節奏來凸顯平行和聲的律動性,從而獲得矛盾、對抗的和聲音響效果。
(二)音列移位序進
音列移位是指在音列結構基礎上,巧妙運用重復或變化重復的手法進行展開,以求得重復狀態中的和聲變異。
1.概括性模進移位
“在一個音樂片段中,音高組織部分是原樣移位性重復,部分是變化移位性重復,具體地說是部分音高移位處理,并在橫向移動后可能產生縱向的音程的縮減或擴張,促使和聲在縱向結構上產生本質性變化,稱其為‘概括性移位。”①
譜例17選自第一幕第六首的和聲片段,這種用法是以第1小節的和弦為模型,按照級進、八度移位的方式衍展,移動中的和弦按半音化平移進行,但基本上完全保持其結構外殼。第4小節發生結構變形,和弦內部的音高排列疏密既有重復又有細微差異,上下聲部既相互獨立,又有整體性差異律動,形成兩個旋律層。
2.全音階輪廓移位
該移位是在某一和弦基礎上,以全音階為構型材料,進行和聲輪廓截段(contour segment)②的概括甚至變異發展。
3.三音列平滑推移
(三)裝飾性序進
裝飾性序進即和聲按照裝飾音的形式發展或在進行中附加裝飾性手法。
1.經過音式
譜例20第1~2小節以震音演奏法展開,使平行和聲結構獲得裝飾性音響效果;第3小節低聲部的和聲進行,內聲部衍生出八分音符和音并以傳統和聲的經過和弦方式序進,體現明確的填充作用。
2.輔助音式
譜例21高聲部按震音奏法八度進行,低聲部整體是平行和聲進行,但在每小節第4拍的后半拍上,會出現一個低半音和音,立刻在后一小節強拍回歸正常。這種做法在功能和聲中是典型的輔助和聲進行,有效增補了和聲律動性。
(四)對稱式序進
對稱在音樂中也稱鏡像結構,“通常是對某一音樂片段作具有特殊意義的、有形式美感的結構化設計,體現音樂發展的平衡感及形態輪廓的協調性”。①
譜例22為第二幕第十二唱段的和聲片段,該和聲結構以第1小節最后一個和音(c1—e1)為基本對稱中心,從第2小節起分別高十五度和低十五度反向進行形成對稱,使整個和聲主題具有勻稱性與協調性,這類進行在歌劇中的某些唱段也多次出現。
該劇的和聲序進方式看似紛繁復雜,實則都是經過作曲家精心考量和設計的。各種序進方式在不同場景中交織呈現,一方面凸顯日本音調思維框架下的和聲布局效果和戲劇情節脈絡,另一方面又謹慎處理戲劇與音樂的矛盾耦合關系,尤其是戲劇情節、沖突設置同和聲結構形態、技法、序進方式及自身創作觀念的協調問題。可以說,不同情節與矛盾沖突,直接影響了不同和聲進行,反之不同性格的和聲音響也極力配合戲劇情節所需要的和聲張力。
四、和聲的終止樣態
和弦的終止形式是和聲序進的最終收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音樂的句逗停頓與音響的合理圓滿,從而獲得結構意義上的功能統一。在共性音樂寫作時期,“定型的和聲終止式”①成為該時期普遍遵循的結束方式,其終止位置也是程式化的,終止感的性質基本上由最后兩個和弦的根音決定。而在非調性音樂中,傳統的調式調性被隱匿、瓦解,其終止式被多樣化的自由形式所替代,其中包括單音結構、和音結構、二度疊置結構、三度疊置結構、四度疊置結構、附加音結構、復合結構、倒影結構、音列式結構及混合結構排列等。通過對歌劇《素箋鳴》中的終止和弦進行考究,發現一些唱段似乎已經不存在終止式的“式樣”了,僅僅是對終止處起著結束功能的作用,或是對下一唱段起著引導與過渡作用。當然,即使在多元豐富的終止樣態中,依然存在一些傳統的終止元素,總體將該劇的終止樣式總結和歸納出以下類型:
(一)終止和弦的排列
整部歌劇的和聲終止式共有26種,見譜例23。
整體而言,和聲的織體排列形態包括單音形式(終止19)、二度關系的和弦(終止1)、三度關系的和弦(終止10、12、15、26)、三全音關系的和弦(終止4),其余基本上是以四、五度關系為主的復合結構或多種和音的混合排列。
(二)終止式的分屬類別
1.有調中心意義的終止
有調中心意義的終止式通常會強調某一核心音級或和弦,在歌劇的一些唱段中有明確的調性傾向。根據譜例23可知:終止3以C—G純五度為中心音程,終止6以長音A為中心,終止7以G為中心音,終止10強調C—E—G和弦,終止12強調D—F—A和弦,終止16強調A—C—E和弦,終止19強調單音E,終止23強調長音G,終止26強調A—C—E和弦。這些將各個唱段的和聲終止刻意停留在某一音級或和弦,有效暗示或直接完滿收攏于調中心音或和弦上的做法,體現了對傳統調性和聲思維的延續與繼承。
2.聯綴性終止
聯綴性終止式是指在有情節的音樂作品中,某些具有雙重和聲屬性的音樂片段,類同于純器樂作品中的半終止結構特性,既是對前面音樂段落的簡單停頓或過渡,又是對后面樂段的開啟與引導。結合歌劇具體情節與唱段,對應譜例23的終止式有:終止1、終止2、終止3、終止11、終止21、終止22。它們分別處于歌劇第一幕第二首混聲合唱、第三首《天照》詠嘆調、第七首混聲合唱、第二幕第七首混聲合唱、第三幕第三首《素箋鳴》詠嘆調、第三幕第四首《素箋鳴》詠敘調唱段的過渡性收攏,也是第一幕第三首《天照》詠嘆調、第四首混聲合唱、第八首《天照》詠敘調、第二幕第八首四重唱、第三幕第四首《素箋鳴》詠敘調、第三幕第五首中三重唱唱段的引述開始,加上表情符號、力度術語的生動運用,既有一定的終止屬性,但更多又是動態思維下的音響遷移,且基本形制相似,使符號化音樂片段演變成具有聯綴性特征的終止用法。
3.總結式終止
總結式終止是以傳統和聲終止樣式與終止感為參照,但終止樣態與結構邏輯卻是現代性的,多以復合式結構為主,包括調式復合、音程復合、音組復合等。結合歌劇具體唱段,主要有終止4、終止5、終止6、終止8、終止10、終止14、終止15、終止16、終止17、終止18、終止20、終止23、終止24、終止26。這些終止式通常出現在歌劇較為圓滿結束或大的情節轉換抑或是劇幕切換以及全劇終止處,基本形態與結構功能在劇中具有重要地位,強調音響的相對穩定感,被賦予完滿性、總結性音響意義。
4.色彩終止
“傳統和聲的終止式通常包含旋律及和聲兩個要素。固定的和弦組合模式可形成和聲的終止式,有調式意義的聲部傾向亦可形成終止式。”①在無調性或泛調性音樂的終止中,基本脫離了傳統和聲的思維軌跡,音響色調建立在不協和性與調性功能的喪失層面,故而色彩性終止更多是指區別于傳統功能意義、有獨特音響風格的終止樣式。根據統計可知,該劇中主要有終止9、終止13和終止25三種,它們分別處于劇中第二幕第四首《金姬與銀姬》二重唱收束、第二幕第九首《素箋鳴》詠敘調收束和第三幕第九首四部混聲合唱收束終止。這類色彩終止賦予其唱段以獨特的、律動性音響變化,織體形態與結構排列都作了分層處理,加固不協和、不穩定性的矛盾效果。
通過對歌劇中和聲終止式的運用、整理與歸類,發現作曲家的終止和聲思維與音響建構邏輯是采用東方素材與西方技法相結合的方式來展現。終止和弦的結構類型、排列方式、織體樣態與戲劇情節安排、音響布局及其衍生關系相互觀照、彼此照應,既有對調中心意涵的暗示與強調,又有雙重功能的聯綴性特征彰顯,也給予了色彩性音響的特別關注,獲得豐富多樣的終止音響意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具有傳統意義的非功能性總結式終止的低音關系,已沒那么突出和重要,但縱觀以上門類的終止低音或相應的和弦結構,依然能夠觀察到對某些調性的隱意關聯及主體性傾向,其中所蘊含的調性意涵亦不容忽視。
結 語
綜合對歌劇《素箋鳴》中的有關和聲技法分析與概括,認識到團伊玖磨在晚期歌劇創作中的和聲手法依然建立在日本傳統和聲音調框架上。包括對五聲性(田舍節、都節及去四七音階的變形結構)調式和聲素材的運用、對日本傳統調性語匯(如全音階中采用小二度和小三度開啟與收攏)的運用、音組式復合和弦的排列、純五度主題式序進等,無不與本土調性邏輯相關聯。以終止式視角來看,從有調中心意義的終止與總結性終止式的使用,可以了解作曲家晚期歌劇中的和聲思維仍然強調或突出調性歸屬,其特點包含對傳統和弦終止結構的繼承、對調中心音的暗示、對主和弦的彰明以及泛五聲音階的縱向復合。從音響的戲劇性效果來看,劇中很多特定場景、唱段的技法邏輯呈現泛調性與無調性思維,包括對三全音和聲的使用、全音階和聲的運用、半音化結構的多層次組合與變形、音塊結構的運用等。總體而言,是將日本調性元素與現代技法相結合,這種調性特征一方面體現五度相生的民族和聲邏輯,保持穩定的東方和聲性格與音樂語境;另一方面又突破五聲和音的結構張力,以不同技法、不同素材的組合方式構建音響內容、表現藝術旨趣,營造各類適應情節矛盾與戲劇語境的音響表征。
團伊玖磨作為20世紀日本有影響力的作曲家,以極具洞察力的音樂稟賦和飽滿的創作熱情引領著日本音樂走向世界,尤其是他對日本本土音樂、傳統文化、戲劇文學及民俗風尚等元素在歌劇作品中的運用與體現,將感性思維與理性觀念融入與眾不同的音響邏輯之中,以成熟而獨立的聲音理念一以貫之,鑄就其音樂作品深刻的東方美學品質與哲思內涵。團伊玖磨的和聲技法顯然體現著民族調式調性和聲的深層元素,他將某些調性音樂原料(如五度音程)植入非調性音樂的總體構架中,使有序的調性思維在無序的非調性音樂中承擔起隱在的結構力功能,在協和與不協和、穩定與不穩定、平衡與不平衡的音響矛盾中不斷碰撞、融合、衍生,獲取音樂發展的結構動力以達成音樂性格層面、音樂審美層面的完整呈現。這部歌劇中,作曲家繼承了20世紀諸多前衛技法,特別是借鑒德彪西、梅西安等法國作曲家的創作技法和藝術風格,同東方民族音樂觀念、審美理念相結合,加以融會貫通形成具有鮮明個人音樂性格的表征。
團伊玖磨的創作在現在看來已成為過去和歷史,但其音樂創作中所蘊含的傳統元素與現代半音體系的交織、重組及其變異手法,復合式結構形態的分布與處理、模型化和聲邏輯及整體音響布局等方面的理性安排與設計,會對當下歌劇音樂創作形成可資借鑒的視角。作品突破傳統審美功能邊界,運用現代性戲劇音響表現布局全劇的音樂結構力,對現代歌劇音響美學、戲劇美學和接受美學亦有參照價值。梳理團伊玖磨的和聲思維與創作脈絡,管窺其晚期歌劇音樂創作中的個性化和聲語言與技法觀念,將有助于揭示日本歌劇音樂的內部肌理和整體面貌,以促進歌劇創作、歌劇文化交流及歌劇理念認知,豐富東亞歌劇文化的學術縱深。
本篇責任編輯 李姝
收稿日期:2022-09-20
基金項目: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歌劇思維中視覺喚起研究”(18BD053)。
作者簡介:張雪鋒(1992— ),男,碩士,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藝術系講師(廣東東莞 523419);
魏揚(1975— ),男,博士,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34)。
- 音樂探索的其它文章
- 周以詩樂化性The Moral Cultivation with Music for Poetry in the Zhou Dynasty
- 銅磬考述A STUDY ON BRONZE CHIME
- 川南合江漢畫像石樂舞圖像考A STYDY ON THE STONE CARVINGS OF MUSICAL DANCE OF THE HAN DYNASTY IN SOUTHERN SICHUAN HEJIANG COUNTY
- 游于城:宋代成都城市音樂略考THE CITY MUSIC OF CHENGDU IN THE SONG DYNASTY
- 北朝時期貴族階層的樂舞生產與消費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USICAL DANCE AMONG ARISTOCRA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 論清代湖北禮俗音樂文化的社會屬性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Hubei in th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