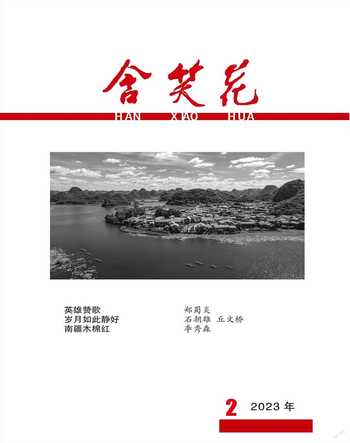牽牛花呼喊著你
西西弗斯
塔吊堅毅如犀牛,用靜止之力
拉抻時間的波弦
猶如準備好隨時拋射出去的捕鯨叉。
大西洋一陣震顫。
我把自己斬斷——為著一種不完善——
我不斷地將自己驅逐
流放到腳踝疼痛的邊緣,就像驅趕一只
貪食的野狗。我把自己斬斷
為著一種不可原諒的殘缺,驅逐
伴隨著——被斬斷的我返回時
帶來的劇痛:
我不斷排除我自己,就像很多人
會將智齒拔出:以這種方式
我嘗試將自己從時間的淤泥中拔出來
——與過往的殘缺告別——
以此成為一個“新的”——一個新的人。
可那些被斬斷的部分緊咬著我
總是在我不留神之時,開始撕咬
他們試圖穿過時間的裂縫——重新占有我:
我必須返回我,作為我的生命的押運員
——我必須親自把我送往生命的終點。
就像一棵樹——只有在荒野上
才能與晚霞候鳥大海與南北極——重合;
我背起我自己——走向歲月的荒蕪!
在白色的不安中
一朵櫻花開在時間的邊緣
花蕊里——一臺小型鏟車
朝著下午一點整跑去
舉著小城,作為“花之城”
給春天的尾聲獻上。
借此,櫻花想要回到時間的中央。
我遠遠地看著它
——我們之間隔著一個星期天。
在黃色指示燈熄滅時
——恍如回憶——
我與它一起,在新的時間里醒來
將“白色”這個詞填滿。
我站立我行走我奔跑跳躍
時間在我們之間靜止不動
時間靜止片刻,然后紛紛下陷
像一場雪。
是否時間是一個整體?
也就是說:它漂浮著,將我們包圍
直到有一天,它會忽然塌陷
然后就再也沒有時間。
還是說,時間是永恒之河:
它流動著,從“未來”向“過去”
無論我們能否感知:
它創造著自己并消耗自己?
我們是搖晃在時間之外的風鈴。
在黃昏的夕陽下,初春
在貿易市場門口的電纜上
陷入混亂。從這里——
春天開始燃燒!
街上的最后一輛車,從身后朝我駛來
用我的雙肺——朝我轟鳴
在一場白色的不安之中。
海棠花從有到無
很多次地,我想去看一看海棠花
直到一場暴雨在某個夜晚收縮起來:
就像反向爆炸的炸彈——一場暴雨——
在某個夜晚收縮起來:
大雨慢慢變小,變成稀疏的幾滴
變回到雨滴落下之前。
然后是一聲雷鳴由強變弱
變回到雷聲響起之前。一道閃電
慢慢從亮變暗縮回到云層內
到還沒有閃電時的寂靜。月光。
海棠花也在雨中收縮起來:
從盛開的花簇,到半綻開的花朵
到緊實的花蕾。到沒有花。
夏天空蕩蕩的——一道閃電
從遠方的山巒間收縮回云層里。
陽光普照。
海棠花收縮起來,春天收縮起來
夏天也在慢慢地收縮起來
在我趕到以前:世界變成了虛無;
我看著我的回憶收縮,在我人生的現場
收縮回到童年到幼兒。到——
我變成了我未出生的孩子。
我的孩子也將趕到新的人生現場
看著新的回憶收縮
縮回到童年到幼兒,到重新變成
——另一個未出生的孩子——
海棠花從有到無,生命從無到有。
未封戳的夏天
用血的沉默——一棵石榴花
對我說了滿天空的話
可是天空不會忽然落下
所以你需要——聽!夏天
并不會忽然——落下!
你需要聽:用耳朵紫色的敏銳
抄寫滿天空話語藍色的輕細。
直到一棵石榴花向我說了
滿天空的話——夏天忽然到來
我已聽見的,變成云朵飄散開
而我沒來得及聽的——變成了暴雨!
暴雨落下,就無法復原
所以我學會了讀,在六月到來以前
我掌握了讀夏天的能力:
我把白云讀作太陽背面的靜坐冥想
把燕子讀作傍晚翻耕空氣的犁鏵
我把母親的額頭——讀作半個多世紀的
風雨的準確標記。
我把晚霞讀作穿透腸胃的火
把湖泊讀作三月休眠的夢開始躁動
把風讀作馬群從額頭跑過
把雨讀作兩邊太陽穴上的,太陽和月亮
彼此通信。——我把夏天讀作:
你從遠方歸來,左手托著一個熟透的桃子。
還可以是火焰
我幾乎沒有走出過小城
是遠方的語言,不斷地朝我趕來
它們自很久以前就開始流浪:
復活的鐵牛
用水銀的柔軟,和晨風的輕
從每一根手指的指尖走向我。
就像童年時,母親穿過集市
雖然疲憊、喘息、負重、擁擠
但依舊能準確返回家,找到我。
如今。
我并不比母親種在樓頂的繡球花
知道得更多
而我也不多不少:恰好是這個夏天的一半:
當遠方的語言抵達我之后——每次——
它們都有足夠的空間安放自己。
語言朝我趕來,有時候是孤零零一朵云
有時候是一只受驚的鴿子
有時候是玫瑰花在慢慢凋零
或者母親不小心摔碎一個碗
——靜立片刻。
從遠方趕來的語言,是在生活的鋒利中
被割傷的時間流出鮮血
血液凝固,留下印記。
不清晰的印記——隨時準備著——
當號令發出時——重生!
就像三月的水:
如果你把三月的水儲存起來
倒入五月的天空,云就會漂浮起來
浮起來的云距離太陽很近
很容易就會被點燃。三月的水
——還可以是——火焰!
【作者簡介】少莫,原名徐建江,云南省作協會員。 有詩歌作品發表于《星星》《詩林》《含笑花》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