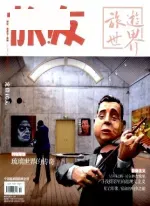瓜子,中國年貨里的“釘子戶”
朱國偉

有人說過,區分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最好的辦法是看他嗑不嗑瓜子。這雖是一句戲言,但足以說明我們有多么熱愛瓜子。其實,中國人吃瓜子有著上千年的歷史。考古人員從長沙馬王堆女尸辛追夫人的胃部和海昏侯劉賀的體內,都發現了未消化的瓜子。只是當時的瓜子并不是作為零食食用,而是藥用。
古人食用的是什么瓜子呢?向日葵瓜子?南瓜子?西瓜子?它們又有怎樣的前世今生呢?
“由來已久”的西瓜子
對瓜子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葵瓜子和南瓜子都是舶來品,唯有西瓜子“由來已久”。當然關于西瓜的起源,頗有爭議,有人說它原產于非洲,也有人認為它是土生土長的地道風物。關于起源暫且不說,就說西瓜子“老大哥”的地位是有據可查的。
北宋初年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在其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 幽州》土產部分,對“瓜子”作了歷史上第一次記載。這里的瓜子,就來自于當時水果界的大哥——西瓜。
雖說,瓜子首次亮相在宋代,可真正盛行成風卻在元末明初,最早記載西瓜子可食的是元代的《王禎農書》:(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薦茶易得。《飲食須知》又載:食瓜(西瓜)后,食其子,不噫瓜氣。
宮廷中食用西瓜子的情況可以參見晚明宦官劉若愚的《酌中志》,書中記載了先帝(明神宗朱翊鈞)“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宮廷御膳的制作方法影響了上層社會對瓜子的喜好。上有所好,下必興焉。瓜子在民間也格外受歡迎,萬歷年間興起于民間的時調小曲《掛枝兒》有《贈瓜子》一曲:瓜仁兒本不是個稀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 吳越廣為流傳的《歲時歌》也記載了“嗑瓜子”的習俗: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鷂子,三月種地下秧子,四月上墳燒錠子……

總之,無論是帝王將相、文人墨客,還是平民百姓,都喜食瓜子。到了明代時嗑瓜子已經成了日常生活習俗。
三“子”鼎力,葵瓜子異軍突起
清末民初,南瓜子、葵瓜子就已經開始流行,瓜子界,也就變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老大哥”西瓜子的光環慢慢黯淡,兩個“小弟”逐漸壯大,尤其是葵瓜子異軍突起,這個被稱作是“香瓜子”的小零食,很快就受到國人的偏愛。
時至今日,最常見的瓜子依然是葵瓜子。葵瓜子又是什么時候來到中國,并征服中國人的胃的呢?
目前最早記載向日葵傳入中國的文獻為明代萬歷年間學者姚旅所著的《露書》,該書稱:“萬歷丙午年(1606 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無枝,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旁有一兩小朵。其大如盤,朝暮向日,結子在花面,一如蜂窩。”明代金石學家趙崡撰寫的《植品》一書對向日葵也有記載:“又有向日菊者,萬歷間西蕃僧攜種入中國。干高七八尺至丈余,上作大花如盤,隨日所向。花大開則盤重,不能復轉。”
由此可見,向日葵是在明代萬歷年間傳入中國的,這其中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據傳,萬歷年間的一個春天,有外國使團到京覲見,并進奉多種貢品,其中有葵花子。禮部官員認為洋品種不宜在御花園內種植,遂令人將其種在南海子(南苑)大紅門內一片空地上,到了七月,葵花盛開,格外耀眼。此時萬歷皇帝到南苑狩獵,剛進宮門,便看見一片金黃,于是走到跟前,駐足觀賞,但見其花碩大,甚是艷麗,雖然御花園里植有百花,但從沒有如此巨大之花,越看越喜歡,便令海戶(明清時南苑內從事蕃育鳥獸、栽培林木和蔬菜種植的戶民)按時令種植,花開之時,便到此觀賞,后被引種到西苑(今中南海)。
清代,有關向日葵的記述逐漸增多。康熙年間臧麟炳、杜璋吉所撰《桃源鄉志》稱:“葵花,又名向日葵,色有紫黃白,其子老可食。”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謝方在《花木小志》中言“向日葵處處有之,既可觀賞,又可食用。”光緒五年(1879年)《京畿雜錄》載:“直隸及京畿植有向日葵,一名西番葵。高丈余,六月開花,每桿頂上只一花,其形如盤,隨太陽回轉,如日東升則花朝東,日中天則花直朝上,日西沉則花朝西。”

據《花卉園藝》記載,清代中期向日葵已在華東及西北地區廣泛種植,但不再只是觀賞性的花卉,而成為油料作物。此后傳入華北地區,并以直隸(即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地區)作為傳播中心。不過,至少在光緒年間,北京的向日葵還沒有大面積種植,只在農村的屋前屋后、地邊地堰有零星種植。因葵花多籽,在崇尚多子多福的年代,人們在庭院及房前屋后栽植幾株向日葵,寓意多子多福、家丁興旺。
由此可見,大概到了清末時期,向日葵已在民間流行,而成為瓜子界的“主流”產品大概要在民國時期。民國時期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是瓜子的鐵粉。比如,我們最敬愛的魯迅先生。女作家蕭紅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寫道:“還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來客人必不可少。魯迅先生一邊抽著煙,一邊剝著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魯迅先生必請許先生再拿一碟來。”
不止魯迅對瓜子癡狂,林語堂也將嗑瓜子列為人生的一大樂趣,用他自己的話說:“吃瓜子,用牙齒咬開瓜子殼之樂和吃瓜子肉之樂實各居其半。”更夸張的是國學大師黃侃,在暨南大學上課時,他向自己的學生瘋狂“安利”瓜子,表示耳邊沒點嗑瓜子的聲音,這堂課就算你們聽得有意思,我上著也沒意思。嗑瓜子的魔力,由此可見一斑。
再看南瓜,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的早些。晚清以來,南瓜子可食的記載非常之多,遠超葵花子,較早的記載如咸豐(貴州)《興義府志》:“郡產南瓜最多,尤多絕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同治《上海縣志》:“子亦可食”,同治(浙江)《湖州府志》:“子亦可炒作果”等,此外,記載如“(南瓜)子白色佐茗酒,產金川者貴”。“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賓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賓筵則必以陜西之瓜子為貴,忽近圖遠良可慨矣。”“(南瓜)子,市人腹買炒干作食物,終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競買食之。”南瓜子流行程度均可見一斑。
雖然南瓜子與葵瓜子的起步差不多,但南瓜子如今的勢頭,可無法與葵瓜子匹敵了。如今,向日葵作為重要的油料作物在我國大面積種植,成為國人茶余飯后的頭號零食。
千百年來,小小的瓜子總是讓人念念不忘,或許,我們所貪念的不僅僅是瓜子仁的香,而是那些默默地被瓜子驚艷過的時光,是那些最簡單隨意、最輕松的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