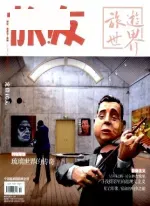“立體國畫”長治堆錦,堆出人間錦繡生活
白英


閆向軍講解博物館展出內容。
春色滿園 堆錦流芳
“聚千古氣象,與天為黨開門戶,攜太行造化,許地同根鎮版圖。” 古稱“上黨”的長治, 位于山西省東南部太行山深處的高地上,東漢劉熙所著的《釋名》中是這樣記載的:“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從中可見這座城市的悠久歷史與鐘靈毓秀。穿過市中心雄偉壯觀的上黨門,就來到了當年的老城區,爐坊巷、錫坊巷、鐵匙巷、銅鍋巷這些隱藏在城市深處彎彎繞繞的古舊小巷,無言地訴說著老街的溫情與市井,不用說就能知道當年曾是手工業者的聚集地,而“長治堆錦博物館”就藏在鄰近爐坊巷的東獅子街一處院子中。古色古香的門樓前,“長治堆錦博物館”“長治市城區非遺博物館”“長治市工藝美術家協會”幾塊牌子掛在兩側,院內二層小樓工藝車間保留著上世紀八十年代“長治堆錦研究所”時期的舊日風貌,而一層用作展覽的博物館重新裝修后,顯出堆錦這項古老工藝重新復蘇與蒸蒸日上的氣象。
長治堆錦博物館館長閆向軍老師,是長治堆錦技藝的省級非遺傳承人,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自在謙和、平易近人,雖年過半百卻是精神奕奕,說到他堅守與喜愛的堆錦技藝,滿臉笑意兩眼放光。跟隨他步入博物館,仿佛進入了美輪美奐、巧奪天工的堆錦天堂,四壁陳列中既有明清時期的遺作,也有現代工藝的新品。明清堆錦,顏色古雅,造型厚重,從中可見堆錦技藝的成熟與發展歷程;現代作品,色澤飽滿,題材豐富,人物、動物、植物等造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展現出堆錦技藝的創新發展與勃勃生機。堆錦,剎那芳華里堆大衍世界的蕓蕓眾生,大美無言間表達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天之驕子》《素衣觀音》《夜讀春秋》《意氣風發》《花開富貴》《金母元君朝元圖》……均出自閆向軍與同是省級傳承人的父親閆德明與弟弟閆向輝父子3人之手,一幅幅堆錦作品,巧奪天工、精美絕倫,花鳥逼真誘人,人物形神合一,文化底蘊渾厚,創作手法精湛,讓人應接不暇,嘖嘖稱贊。“春色滿園關不住”“簇錦攢花斗勝游”這形容春天繁花盛放的古詩佳句,若放在長治堆錦這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中,也是名副其實。

技藝傳承
這是一座袖珍專題博物館,面積雖小卻是內容豐富,展品140余件/ 套,以實物、圖片、文字等形式,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展示了長治堆錦從明代中晚期形成至目前發展與傳承的基本狀況。每一件展品在閆向軍的口中都是一段故事,讓長治堆錦在社會發展中傳承和創新,一直是他的目標,為此閆向軍與父親于2014年共同創建了長治堆錦博物館,并免費面向大眾開放,至今已接待近十萬人次參觀。看到通過自己的努力,對長治堆錦文化進行有效保護與宣傳推廣,更多的人通過堆錦了解上黨地區悠久的歷史文化,欣賞長治堆錦的藝術魅力,閆向軍也是倍感欣慰。
薪火相傳 堆錦磨藝
在閆向軍老師聲情并茂的講述中,堆錦博物館里的展品仿佛都成了活的歷史,一幅幅長治堆錦定格了生活的美好,從造型到材質,再到其樣貌,包含了各個年代特殊的社會風貌、人文氣息、手工技藝、材料應用,以及背后人物體現的各種悲歡離合的故事,折射出歷代匠人薪火相傳的高超技藝,也印證著這門藝術的絕妙之處,更匯聚了長治堆錦的前世今生。博物館的展品中,有制作于清咸豐五年(1855年)的山形內折圍屏堆花擺件《東來設齋圖》表現對佛的虔敬,制作者為鳳山居士,是存世時間最長的堆錦實物;制作于1869年的堆花通景六條屏《群仙集慶》,為早期體量最大的堆錦作品,從說明中可知實物每扇高1.7米、寬0.45 米,總面積達4.59平方米,畫面主要描寫八仙、壽星及獻桃童子等仙人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其貢獻在于突破了以小單體組成大畫面的難題。還有一件兩側裝飾堆錦的鏡子實物,既具實用功能,又有欣賞價值,閆老師打趣地稱之為古老的文創產品。
就著館內的陳設展品,閆老師說起堆錦藝術的歷史淵源,言語間滿是感慨。長治堆錦起源于民間香包、針扎,形成于明、清時期,與當地發達的潞綢產業、繁榮的地域經濟和豐富的民俗文化息息相關。當年長治與江浙、四川、閩粵一起合稱“全國四大絲綢中心”,絲綢產業十分發達。

堆錦產品成形
堆錦依托“潞綢”而生,伴隨“潞綢”繁榮而長。同時,自秦漢以來,長治地區一直是晉東南地區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所謂“平陽、澤、潞豪富甲天下,非數十萬不足富”,這為長治堆錦的制作和銷售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手藝人們將宮花、貼絹、堆綾、布貼畫、絹人、扎花、繪畫等技藝加以提取、整合,制成了一種既非刺繡又非布藝,但卻保留了絲綢華美和美好寓意的獨立畫面。這一具有驚人藝術效果的新型工藝品裝入木框,做成中堂、座屏、條屏等各類裝潢形式,因其奢華的材質、繁復的工藝和獨特的形制,成為清末至民國達官貴人家庭必備裝飾,滿足了晉商富賈達官貴人追求奢華的需求,遂代代相傳,工藝不斷改進,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長治市內爐坊巷著名堆錦藝人李模(1867—1933)、李時忠(1890—1967)父子歷時3個月精心制作的一套四季條屏“春夏秋冬”,以獨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藝,于1915年榮獲巴拿馬博覽會銀質獎,這項技藝隨之蜚聲海內外。“這兩件作品都是李時忠先生親手堆制的。”閆向軍館長的手指向墻上陳列的兩幅堆錦實物,雖然由于時間的磨洗,畫面色澤已不復從前,然藝術品味并未衰減。《東風朔》是件人物作品,完成時間是1956 年,人物體態優美,性格鮮明,衣飾飄逸,線條流暢,須眉鬢發,根根見肉。《世界和平》是件花鳥作品,完成于1959年,花鳥形體肥厚莊重,材質柔順,色彩飽滿,層次分明,立體感強。當年李時忠創作的以和平鴿主題的作品,還曾作為國禮贈予朝鮮金日成將軍與蘇聯友人。
閆向軍時常揣摩學習前輩名家作品,對堆錦前輩倍加崇敬,也深知這門技藝傳承的不易,堆錦技藝隨著民國初年名聲提振,開始在李氏家族內傳承,建國后,李氏后人李時忠、李時杰加入了國營的油漆裱糊社、工藝美術廠,傳承模式轉向“社會傳藝”,培養更多的人掌握這門技藝。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堆錦畫曾大量出口法國和東南亞地區,為國家賺取外匯。閆向軍的父親閆德明就是在1964 年奉調到長治市工藝美術廠主持堆錦的產品設計,與長治堆錦藝人李松、李時忠、李時云、李時杰等合作研發產品,見證了長治堆錦半個世紀來的發展歷程,他最早開始對長治堆錦史料進行研究,出版了《長治堆錦——堆錦文化的輝煌記憶》一書。在一代代堆錦藝人的努力下,這門技藝不斷發展,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試制

雕型塑芯

調型
創新工藝 堆錦換“胎”
二樓的工作室內,閆向軍正在和藝人們制作一幅大型的堆錦作品《花開富貴》,畫中孔雀羽毛開屏半張,姿態優雅,牡丹花雍容華貴,怒然開放,整幅畫喻意著吉祥富貴,神圣平安。最引人注目的是畫面上大面積的花朵,造型各異卻朵朵唯美,色彩厚重豐富,結構層次分明,立體感極強,“花瓣的組合一定要注意層次,這樣作品會更有張力”。閆向軍耐心地指導著學生們完成牡丹花瓣的制作。拿過一朵花,閆老師仔細的觀察著每個花瓣的造型,原來,這一朵花光構件就是百十來個,需要運用多種技法,看似簡單制作工藝卻很復雜。
一幅堆錦作品往往需要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首先要設計底稿,這是整個作品完成的藍圖,非常考驗設計者的繪畫功底”。閆老師拿著新設計的稿件,仔細推敲著,底稿完成后,要根據堆錦的工藝特征,把底稿分解成若干塊,用絲綢包芯,形成浮雕狀,再按圖拼接在一起,這種“拼”就是堆錦的“堆”。長治堆錦之所以被稱為“立體國畫”,秘密就在于畫中各個部件要用絲綢包裹胎體形成“軟體浮雕”,胎體可以說是支撐整個堆錦畫的骨骼。
回憶起自己多年的創作經歷,閆老師對堆錦畫胎體塑形工藝感觸最深。傳統的堆錦制作,要經過:畫稿、描稿、分拆、塑型(軟胎還要經過:壓紙捻、絮棉花、貼飛邊、壓平)、包絲綢、染色、描繪、拼堆、調型、拼接、上板、定型等工序。胎體采用的是軟胎,也就是中間絮棉花,需要制作人用棉花粘貼在硬紙板上,再將絲綢黏貼包裹于棉花之外,并捏拔出軟硬褶,最后在絲綢上畫上圖案,完成作品。硬紙板和棉花胎芯等材料不宜長期保存,同時工藝過程繁瑣,制作難度相當大,耗費時間很長,在題材的表現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別是在一些細節的表現上,都是畫上去的,缺少立體感。對于這些技術難題,閆向軍也曾困惑,他下決心迎難而上。

長治堆錦作品《金母元君朝元圖》(閆德明 閆向軍 閆向輝作品,長治堆錦博物館 提供)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讓堆錦易學易做易保存,閆向軍一家人對工藝進行了大膽革新,以“硬胎”換“軟胎”,先在硬質薄殼材料上雕刻出作品的骨骼,再黏貼各色絲綢和錦緞,更好的體現出“立體國畫”和“軟體浮雕”的特點,同時在題材、構圖、色彩、裝潢形式等方面不斷改進。他拿起正在制作的一片花瓣一邊比畫著,一邊娓娓道來,舊工藝花瓣包綢子以后,上面的脈絡和光影效果,正反轉折是必須經過繪畫才能呈現,這一過程不僅增加了制作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絲綢表面特有的質感。新技術則是讓絲綢表面呈現出設定起伏的制作工藝,以使花瓣層次分明,花瓣與花瓣之間分界明顯,呈現出更強的立體感。這樣既節省時間,造型又更加準確合理,還有效解決了堆錦制作繁雜的問題,同時在防絲綢的風化脫落、防蟲蛀、防霉變、防褪色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把老工藝“無法做、做不好、做不快”的工藝過程,變得“做得了、做得好、做得快”。
精彩絕倫 堆錦力作
長治堆錦博物館鎮館之寶,是2018年第十四屆深圳文博會金獎作品《金母元君朝元圖》,整幅作品寬4.2米,高2.08米,畫面上的35位神仙人物,造型各異栩栩如生,冠飾精美表情生動,衣紋流暢姿態逼真,不僅體現出傳統藝術中的莊嚴肅穆和神秘,而且成功地融入了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將溫柔婉約之美和崇高莊嚴之美融合在一起,頗具東方神韻。精湛的工藝、獨特的層次、變幻莫測的紋理、優美而不失質樸的情趣,洋溢著堆錦特有的色彩鮮艷與光澤瑩潤,充分體現了堆錦藝術強烈浮雕感的工藝特色,展現出堆錦藝術獨特的視覺效果。這件以芮城永樂宮壁畫為題材,兼取長治觀音堂懸塑藝術表現手法,用長治堆錦的技藝展現出來的力作,堪稱“技藝絕倫”,曾先后榮獲中國工藝美術文化創意獎金獎和中國工藝美術屆最高獎項“百鶴金鼎獎”。

《金母元君朝元圖》由閆向軍與父親閆德明、弟弟閆向輝耗時兩年三個月制作而成,金獎背后是父子三人對長治堆錦傳承與創新發展的思考與努力。說起這幅堆錦力作的創作過程,閆向軍印象很深,這幅作品不僅在目前長治堆錦作品中畫幅最大,而且工藝最復雜、融匯多種技法于一體,技藝也最完整,共使用各色綢、緞、紗、綾、線、珠等材料近50 種。其中光金母元君前面臺安上的一朵“玉花”,就由近三百個包綢緞的小件組合而成,其中最小的部件寬度不足兩毫米,整朵花看不到一絲毛邊和線頭,其制作和拼貼難度都屬堆錦工藝的極限。父親閆德明從事堆錦創作多年,一直在琢磨著創作一幅彰顯山西省地方文化特色的作品,永樂宮壁畫是中國古代壁畫的翹楚,長治市觀音堂懸塑被譽為“懸塑之冠”,長治堆錦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將三個“國寶”級藝術融合在一起,是他琢磨已久的事。然而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制作過程卻極為不易。由于永樂宮壁畫一些細節部分殘缺或模糊,為了完整清晰表達,閆家父子三人查閱了大量資料,比如王母娘娘的鳳冠是什么造型,上面有幾只鳳,胸前的飛天是什么樣子……每一處細節都精益求精。堆錦的完成過程中往往還會遇到各式各樣特殊而繁瑣的制作難題,尤其是堆粘人物毛發時,由于造型極其微小,工藝制作難度相當大。為了顯得精細逼真,他們絞盡腦汁選用了各種生活材料,讓作品顯得更加精細、生動。創作技法上“師古而不泥古”,繼承前人精湛技藝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創新,《金母元君朝元圖》創作中獨創了二十余種技法,同時運用疊加、懸貼等新的裝配方法,提高了堆錦的藝術效果,大大推動了堆錦工藝的發展。
時代芬芳 堆錦輝煌
多年從事堆錦創作的閆向軍,對這個行業可謂感情深厚,出生于1968年的他,自小成長在民間藝術之家,父親閆德明長期從事堆錦工藝的設計與管理,前輩祖爺爺(閆德明的爺爺)當年也曾是長治爐坊巷里有名的堆錦店掌柜。在家傳工藝的特殊氛圍中,閆向軍十幾歲便考入長治師范學院學美術,后來又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潛心進修,進一步提升了對于堆錦技藝的深度理解和創作技能。在這樣的機緣中,閆向軍接過了傳承堆錦技藝的重擔,與父親和弟弟同心重振堆錦昔日輝煌。

制作中的《富貴平安》作品
作為傳統老工藝,閆向軍深深地感受到,長治堆錦如果不創新就不能生存。傳統的堆錦制作,需要制作人有良好的美術基礎,并有多年的堆制經驗,一系列特殊而繁瑣的制作工藝,讓堆錦的制作難度大大提高,這就使得它在很長一個時期,成為達官顯貴、豪商大賈們的庭堂陳設,只能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無法“飛入尋常百姓家”。如何讓這一藝術奇葩綻放在世人面前,讓更多人了解它、欣賞它、傳承和發展它? 2000年7月,閆向軍創辦了長治市類通堆錦工藝有限公司、長治市德藝坊堆錦工作室,走上邊開發邊保護的路,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開發的設計的堆錦產品已經有三大系列,30多個品種,他設計《竹報平安》榮獲“2009中國旅游商品大賽”銀獎;《前程似錦》在2013第九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上獲得“中國工藝美術文化創意金獎”;《戲荷》《四季平安》《花好月圓》《春色》等多款產品也多次獲國家級各種獎項。
經過多年的技術創新,堆錦制作的準入門檻降低了,效率提高了。閆向軍又把重心放到了非遺的傳承和推廣上,開始面向社會免費招收學徒,為的是將長治堆錦逐步推向規范化批量生產,讓普通人通過簡單培訓,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加工堆錦零部件,這樣就能帶動周邊的困難家庭和自己一直制作堆錦。很多人說,堆錦是歷經艱辛搞出來的東西,為什么要傳給別人呢?閆向軍卻不這么認為,他的心里傳承堆錦技藝,發展堆錦產業是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讓長治堆錦得以廣泛傳承,突破對從業者專業要求高的瓶頸,才能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從而帶動長治堆錦產業化發展。
令人欣慰的是,隨著近年傳統文化的復興,許多中小學校開始主動走進堆錦博物館,品味、感知、接受堆錦文化,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北京服裝學院、西安美院等十多所院校藝術專業也前來洽談合作,使得長治堆錦在逆境中峰回路轉。堆錦工作室進校園、接納畢業生完成與堆錦有關畢業設計輔導工作、開設體驗課堂、孵化文創產品等方式,讓堆錦這幾年呈現了“井噴”式的繁榮發展勢頭。2016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服裝系研究生楊凱越的畢業設計作品,將長治堆錦技藝與現代服裝完美結合,設計出《竹影》系列服裝,在學界引起不小轟動。原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培訓部主任盧瑩老師盛贊:“堆錦不光是掛在墻上,還是能穿在身上的藝術品。”
“手藝人就是要精益求精、踏踏實實、不慕虛華、不為利趨,新時代給我們提供了更大的舞臺,堆錦產業發展空間很大,堆錦技藝也一定能更輝煌。”閆向軍心中有夢有未來,初心不改矢志前行。長治堆錦作為頗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非遺文化產品,從陳設到收藏,從裝飾到實用,從美化生活到服務旅游,以及禮品饋贈到文化交流,攜歷史的輝煌走到今天的蓬勃,也必將帶著時代芬芳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