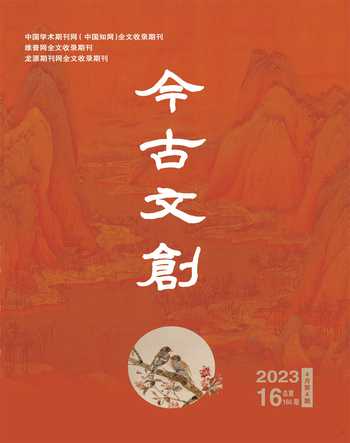赫塔·米勒作品中的創傷敘事研究
王穎
【摘要】 赫塔·米勒早年的創傷經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主題和風格,并滲透到她小說觀念中,奠定了特有的悲涼基調。創傷在赫塔·米勒的作品中無處不在,本文以短篇小說《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為例,探討了她早年的創傷經歷,創傷的具體文本實現方式以及創傷敘事的意義。
【關鍵詞】赫塔·米勒;《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創傷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6-003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09
赫塔·米勒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她的小說以個體傷痕來描寫二戰后期羅馬尼亞在齊奧塞斯庫政府統治下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況,敘寫他們的流浪、孤獨和恐懼。赫塔·米勒筆下的風景描寫十分具有特色,往往伴隨一些我們不熟悉的意象,余楊認為正是這些不熟悉的意象幫助她完成了感覺的自我虛構,也使她的創作成為自我虛構的隱晦文學[1]。赫塔·米勒的寫作具有重復性,她一直在重復創傷,讓人感到她似乎是為了抗拒遺忘而寫作。去年,后浪出版社再版了她的羅馬尼亞三部曲,這說明赫塔·米勒的作品在當下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集中體現了她小說的“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真,描寫了那些被剝奪者的境遇”的創作特色,也是她敘述個體創傷的一次實踐。
一、赫塔·米勒的創傷經歷
“創傷”一詞源于希臘語,原來僅指身體層面的傷害,于19世紀末期才有了意義上的延伸:指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創傷。阿斯曼:“威脅生命與嚴重傷害心靈的經驗因其極端無法為心理所消化[2]”。赫塔·米勒的創傷性經歷按時間順序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童年家庭創傷、極權統治創傷和流亡創傷。
童年經歷作為個體生活的開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作家的素材來源,思維方式以及作品風格的形成。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童慶炳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童年經驗可分為豐富性經驗和缺失性經驗。”[3]豐富性經驗指的是物質和精神上的豐有富余,即童年幸福而美好。而缺失性經驗則完全相反,或是物質匱乏,或是精神壓抑,童年生活艱難而不幸。赫塔·米勒的童年經歷顯然屬于后者。她的父親整日酗酒,只關心極權政治,對妻子兒女不聞不問。母親的勞改營經歷使她郁郁寡歡,祖母沉湎于死去兒子的痛苦中,整日與經書作伴,而祖父則無法放下他那被沒收的田產,潦倒失意。家庭生活沒有給赫塔·米勒以溫暖。
除了家庭環境,赫塔·米勒所處的社會集體環境也很殘酷。赫塔·米勒出生于巴納特施瓦本村落中,那里種族中心主義盛行,人們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德意志民族性”,認為自己是優秀的德國中的一員。其中,赫塔·米勒用“德意志蛙”來指代村莊中的種族主義者,他們是赫塔·米勒接觸到的第一種獨裁者,即巴納特施瓦本地區的人們,在內在精神上保持著自己作為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性,但與此同時又不得不收起自己驕傲,為二戰中納粹犯下的罪行而贖罪[4]。1973—1976 年,赫塔·米勒從鄉村進入城市求學,畢業之后,留在城市工作,直至1987年移居德國。這段在羅馬尼亞城市的經歷,成為其孜孜不倦地批判極權“集中營”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后來稱為‘極權主義和‘國家的東西,只是一個偏遠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5]后來赫塔·米勒遭受到秘密警察不斷地騷擾審問和恐嚇,接著失去了工作。羅馬尼亞國安當時有16.2萬名簽約的秘密線人[6],完全脫離于其他機構[7],秘密警察這一角色后來多次出現在她的作品中。她是這樣描寫這么一群人的:總是充滿了恨意,一副怒氣沖沖的樣子,然而這些人很可能也是在鄉下長大,為了過好日子,跑到城里,幻想著不用再赤著腳在冬天的雪地上趕羊。他們一心一意想要做的就是要加入這個體制里,然后為它服務,當然不是出于熱愛或者忠誠,只是為了生活。然而,他們心里面總是有莫名其妙的恨意,看路上有什么人不順眼,決定行動與否的不是應不應該、合不合理,而是那一刻的恨意是否足以點燃他們的沖動,讓他們忽然變得暴戾起來。秘密警察的不斷騷擾毀滅了赫塔·米勒最后的生活希望,在這種高壓的社會環境下,處處充滿恐懼,不得不逃離。
此后,赫塔·米勒又經歷了流亡創傷。趁著德裔回歸政策,赫塔·米勒和丈夫一起于1987年移居到德國。而移民的過程中又是另一番艱辛。即使是在移民后,她的人生又遇到了新的挑戰,在成功移居德國的一段時間后,赫塔·米勒感受到了身份焦慮。他們不為羅馬尼亞所容,在德國依舊如此。他們無家可歸,永遠處于流亡離散之中。后來赫塔·米勒根據這段經歷寫了《人是世上大野雞》:“一條腿上是旅行的人,另一條腿上是迷途的人。”[8] 赫塔·米勒經歷了故土創傷,無處是故土,羅馬尼亞不是樂土,德國亦非家園。這種缺失的歸屬感又增添了一道傷疤。
赫塔·米勒的創傷經歷,以及一系列對創傷的體驗和認知是她小說中創傷性敘事的根源,下一個部分將討論赫塔·米勒的創傷敘事是在具體文本中是如何表現的。
二、《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中的創傷敘事
該短篇中使用文學性的創傷敘事,具體以文字宣泄情感的方式來療愈創傷。蘇珊·漢克提出“寫作療法”,她認為“寫作療法”是以“重新經歷創傷的治療方法書寫創傷經歷”[9]。這一方法被赫塔·米勒頻繁使用,不僅僅回憶敘述創傷,而且重新審視和評估創傷。在書寫過程中,作家以講故事的形式將他的創傷經歷娓娓道來,“將其人生中的痛苦一一剝開,隨著故事的深入,傷疤逐漸裸露,結痂,彌合”[10],弗洛伊德把這稱為“宣泄治療”[11]。
《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中的創傷敘事與赫塔·米勒母親的早年經歷有關,自1945年始,包括赫塔·米勒母親在內的8萬德裔羅馬尼亞人被流放到勞動營。因為母親的緣故,赫塔·米勒從小就一直聽到有關蘇聯的消息。這些消息被隱含地、壓抑地提起,甚至成為禁忌話題。在經歷了長達5年的勞動營生活后,赫塔·米勒的母親才得以返鄉,但是此前高強度的勞動生活已經摧毀了她的健康和精神,使她郁郁寡歡。赫塔·米勒在她的作品中多次敘述這一段屬于個體或群族的創傷性經歷,本文所討論的這一短篇即為一次實踐。
創傷幾乎構成了整篇小說的內容,在敘述層面上展露無遺,在這篇小說里,創傷體現為兩個結點,一是恐懼;二是饑餓。
恐懼源于對“那幕慘劇”的多次回憶。小說中的主角“我”是一名女工,上夜班,黎明時回家,回家路上總是會想起“那幕慘劇”。即使周圍并沒有任何顯性的事物觸發這一聯想,但我卻總是莫名其妙地,不經意間想起“那幕慘劇”的主人公“他”。即使是在夢里,“他”也會出現,伴隨著土豆田。根據生活經驗,創傷性經歷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才使我日夜想起,籠罩其中不得安心。“那幕慘劇”重復出現多次,卻一直沒有說明那幕慘劇的具體內容和“他”是誰。直到出現了手帕這個意象,“我”在火車上看見了那塊手帕,又一次聯想到了“那幕慘劇”。 赫塔·米勒在她的演講《今天你帶手帕了嗎》中提到,手帕是一種體面,溫暖的象征,生活中不論做什么都少不了它,它使你想到家和母親。 但在這部短篇中,手帕使“我”聯想到的卻是悲劇性的“那幕慘劇”。轉而插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多是與食物相關。假設自己不是單身則要燒四杯水,撣兩個枕頭。多出來的一個枕頭和兩杯水暗示著“他”即將要浮出水面。終于,一個關鍵性的意象出現了,土豆,當“我”在削土豆時,想到了“他”藏在土豆里的字條,想到了作為勞改犯的“他”,也想到了那幕慘劇,即他所遭受的苦難[12]。
恐懼是赫塔·米勒眾多作品中的母題,有時候她自己也不知道這一直伴隨她的恐懼來自哪里,究竟是什么,“這種恐懼只在普遍意義上存在,只作為概念,作為總數存在。” “即使是能夠說清楚的地方,也只能是一部分。往往是對于痛苦的恐懼。人們可以確定這種痛苦時在身體上的,是關于與人類的交往的,也是關于與事物的交往的。然而,當我們將這種想法進行到最后時,這種恐懼就成了對于一些對我們來說很成問題的東西的恐懼,關于生命的恐懼,對于死亡的恐懼[4]。”而在這篇小說中,恐懼有了實體,即那幕慘劇。正因為我對于那幕慘劇的心有余悸,才會產生一次又一次的鏈式聯想。
恐懼是本篇小說中創傷性經歷的情感后癥,創傷性經歷的特質有兩點體現在作者的碎片化敘事中,第一,它能夠引起強烈的負面情感反應,對主體的心理及生理造成震蕩,對“那幕慘劇”的多次回憶使得主體無時無刻不陷入對死亡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且重復性多次回憶往往會“超出當年事實的強烈程度”繼而導致個體的崩潰。第二,它是一種被動記憶,往往由外物不經意觸發感官引起,人的思維是漫無目的,不可控制的,導致了創傷性經歷回想的不可控性與不可預見性。“那幕慘劇”多次被“我”的聯想所喚起,即使是一些毫不相關的人、物。第三,“那幕慘劇”頻繁地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像網一樣包裹“我”,讓“我”時常陷入絕望的恐懼之中。
饑餓就像恐懼一樣無處不在,它變成了一種創傷,留在了人們心底。關于饑餓的創傷敘述自始至終沉降于細節。短篇中沒有明面上的“創傷”“苦難”或是“傷害”這樣的詞眼,因為太輕易的,大都俗不可耐。創傷源于細節,關于日常生活的細節:患有萎縮性胃炎的女乘客說她一塊大土豆就能吃飽,土豆是溫暖,而寒冷就是鐵絲,把她的手指緊緊纏繞。當她吃飽了之后,她瘦骨中的靈魂備感孤獨,她就像死神一樣煢煢孑立。[12]
赫塔·米勒將饑餓事件串聯起來,除了寫女乘客的饑餓,還有兩個男人的饑餓:那兩個男人在刑滿釋放后愛上了吃土豆,但進監獄之前并非如此。可以說監獄生活殘忍的方式改變了他們原先的飲食習慣,對于土豆的喜愛也是一種病態的喜愛。因為苦難是如此深重,而幸福短暫不可及。“我”的饑餓:總是吃得很快,習慣性的向上吞咽,食物蓋住頭腦。我的眸子變暖和,溫暖淹留眼中[12]。只是滿足了精神,并沒有滿足胃。如果土豆這一貧瘠的食物代表溫暖和幸福,那么“我”的溫暖和幸福也是如此的短暫,根本來不及咀嚼,且只停留在頭部,到達不了其他任何地方,剩余的都是苦難和不幸,使我的身體仍舊僵硬著。對于每天被饑餓侵襲的勞動改營的人來說,“吃”已經變成了一種有尊嚴且幸福的事情,它變成了一種病態,不但在人的身體中,而且在人的思維中生根發芽。即便當人們的肚子已經裝滿食物,饑餓依然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帶給人如此巨大的創傷。這些事件皆由饑餓引起,它們由餓牽線共同豐富了故事的內涵,也作為故事的動力源泉,一步步地傳遞能量下去,直到故事的高潮與結束。
三、赫塔·米勒小說創傷敘事的意義
赫塔·米勒小說的創傷敘事具有三重意義,一是對集體記憶的書寫;二是情感創傷的修復;三是審美價值。
赫塔·米勒小說的創傷性敘事書寫了兩代德裔羅馬尼亞人的痛苦遭遇,包括肉體上超負荷的勞動改造和精神上的流離失所。從母親那一代人的離鄉別井,長達數年的勞改營生活,到她這一代人移民德國,飽受流離失所的身份焦慮。赫塔·米勒的創傷敘事還原現實,揭露勞動營的那段無聲歷史,通過記錄和反思集體創傷,以更深刻地闡明歷史和人性。赫塔·米勒曾說:作品主題是強加于我的,不是我自己可以選擇,就像生活也是強加于我的一樣,這不是自由的決定,它們相互制約[13]。如赫塔·米勒所言,書寫創傷于她首先是道德訴求,她必須為國家極權機制的受害者發聲[14]。
其次,如前所述,創傷是一種心理宣泄,通過文字敘述排解心中恐懼與怨恨。這種宣泄是心理治療,讓它從潛意識層面顯現出來,躍入尋常生活的意識層面,以獲得更好地處理與應對。赫塔·米勒的創傷敘事的獨特之處在于她通過敘述個體層面的創傷,來達到修復集體創傷的目的。關于個體創傷體驗的敘述,赫塔·米勒以碎片化的敘事手法,詩化的語言反復描述。以反復訴說表達譴責,她認為:“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相反的,布羅茨基認為,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賦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他拒絕“展覽創傷”[15]。這兩者的對比可能不是某些人所認為的,即男性精神體格和女性精神體格在面對同樣傷害時做出的不同反應,這僅僅是兩個個體面對創傷的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不必歸結于男性和女性精神體格的差異。但無疑的是,前者以無言表示藐視,后者以反復訴說表達譴責,都是一種自療式的愈痊方式。
四、結語
“人不應該忘卻,寫作終其終了,不過是反抗遺忘。以寫作感受地獄的消逝,同時又不忘地獄的存在,這是人的權利”[16]。赫塔·米勒的小說帶有濃烈的自傳色彩,而自傳強調的是個人甚至是個性的歷史。[17]看起來是一個個虛構故事,實際上是個體創傷記憶的真實記錄,目的是重復個體傷痕以重構和治愈集體創傷。
在她創造的虛構的世界里,赫塔·米勒可以毫不顧忌地將自己的創傷經歷和感受以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這種記錄就是一種文字性的創傷敘事,只不過中間添加了很多虛構的成分。即便帶有了很多的虛構成分,赫塔·米勒依然在無法再面對自己和自己的周遭,無法再忍受自己的感官和自己的思考的時候,用寫作中將自己的創傷經歷一一挖掘出來,認真地觀察它們,勇敢地面對它們,認清其本質,直到不再害怕。然而,以文字表述創傷,無法避免二律背反,即便竭盡所能也未必能道盡。赫塔·米勒曾討論過這種兩難之境:當我們沉默時,會讓人覺得難受;當我們說話時,會讓人覺得可笑[18]。但她仍然不得不繼續書寫,因為是主題選擇了她,她別無選擇。在創傷的書寫中表達自我,超越自我,是赫塔·米勒作品中生命的意義所在,也是她延續自我生命的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1]余楊.論赫塔·米勒《呼吸秋千》中的創傷書寫[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8(02):20-28.
[2]Aleida Assmann. 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nagenheit. Erinnerung skulter und Geschichtspolitik, Munchen: C.H.Beck,2006.
[3]童慶炳.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J].文學評論,1993,(4).
[4]余楊. “我望向廣闊的風景,體會到無邊的絕望。”——解讀赫塔·米勒作品中的自然[J].德國研究,2018,33(04):90-104+142-143.
[5]赫塔·米勒.鏡中惡魔[M].丁娜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94.
[6]康慨.赫塔·米勒非常震驚:“像被人抽了一記耳光”[N].中華讀書報,2010-09-22.
[7](德)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M].林驤華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539.
[8]赫塔·米勒.人是世上大野雞[M].陳民,安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96.
[9]Suzette A. Henke: Shattered Subjects-Trauma and Testimony in Women's Life-Writing,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8.
[10]王智敏.“殘缺的愛” —— 《喜福會》“創傷性記憶”的心理學解讀[J].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79.
[1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孫紹武主編.論無意識與藝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119.
[12]阿讓.蒼蠅與森林——讀赫塔·米勒之一[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25(06).
[13]赫塔·米勒.呼吸秋千[M].余楊,吳文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4]讓文學記載歷史——對赫塔·米勒作品的解讀[N].中華讀書報,2010-1-20,(17).
[15]列夫·洛謝夫.布羅茨基傳[M].劉文飛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16]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219.
[17]菲力浦·熱勒訥.自傳契約[M].楊國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01.
[18]赫塔·米勒.心獸[M].鐘慧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