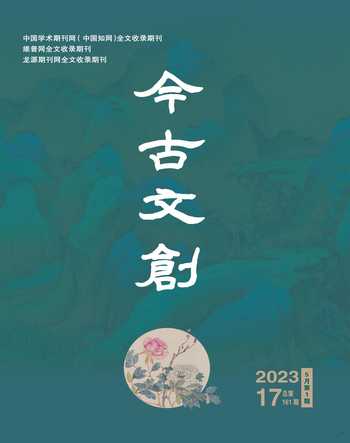董仲舒人性論探析
【摘要】 人性論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重要議題,歷來備受關注,董仲舒作為漢代及中國古代儒學史上的關鍵人物,其人性論思想具有重要影響。他積極順應漢代大一統的政治、社會需要,整合、發展了先秦儒家孟子性善說、荀子性惡說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比前人更全面、更符合實際的人性善惡并存觀點;性三品說詳細分析了人性品級并以中民之性為性;倡導教化指明了向善的途徑,形成了獨特的人性論學說體系,深刻影響了漢以后唐、宋明的人性論思想,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同時加強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完成了儒學體系構建,為儒學在中國古代政治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 董仲舒;人性論;影響
【中圖分類號】B234?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7-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7
縱觀我國人性論思想,在先秦時期已取得重要成果,以儒家孟子性善論、荀子性惡論為代表,至漢代人性論的發展成為又一重要節點,董仲舒是最早對孟、荀思想進行整合的儒學家,完成了儒家思想的質變與飛躍,因此董仲舒人性論研究對于把握人性論發展演變、漢代思想和對后世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學界對董仲舒人性論研究成果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剖析了其人性論內核,盡管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多數學者如金春鋒、劉國民等認為他批判、繼承了孟子、荀子的學說,為深入理解其思想提供了重要參考,具有重要思想價值。
一、董仲舒人性論背景
(一)先秦人性論思想基礎
天命觀作為中國古代社會闡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理論長盛不衰,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同樣以此為基礎提出各自學說,《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之句,表明性出自命,而命由天降,即將人的性命與上天緊密相連,在此思想背景下的人性論思想固然帶有天命色彩。儒家人性論具有代表性的首先為孟子性善說,孟子認為天人相關,人天生帶有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①四端即仁、義、禮、智,是人天生帶來的性,人性并無差別。孟子主張善的根本原因即基于人有實現四端之心,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②這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孟子承認人的欲望,但不把欲望當作人性,而將其稱為小體,相對的仁義禮智則為大體;更具體的小體指“耳目之官”,大體指“心”,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質與作用。從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將心中的仁義確立起來,耳目之欲才不會擾亂、奪取它,如此便能成為有德行的大人君子。
孟子通過人禽之別和倫理道德分析提出性善論,其實是即心言性,認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體現為實際具體的善的行為,并進一步由心善確信人皆有善性;并且提出人應當以此善性為性;人的意義、價值在于充分擴充、實現自己的善性,其核心觀點即性本善、性向善。
與孟子相反,先秦時期另一重要人性論思想即荀子性惡說。荀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主張人的性與情統一,人性中天生帶有好利、好聲色等惡的一面;人性中存在欲望是合理的,但欲望是無休止的,過度欲求必然會帶來爭端、破壞社會道德秩序,甚至導致爭戰禍亂,正如《荀子集解》所說“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③,人性天生帶有負面因素,由此提出人性惡。
另外荀子肯定人性中存在善的部分,但擁有善質不等同于人性善,“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之性無法改變的稱為“性”,善是后天學習教化的結果,是可獲得的,稱為“偽”,經過教化的民眾獲得良好品質,而教化途徑有賴于統治者。教化則必有禮儀準則,因此達到善的核心要素歸結于禮義,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離不開禮義教化作用,并且個人經教化達到善才能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和諧穩定,秩序統一。
荀子雖主張性惡論,但其終極目的同樣是引人向善,主張通過后天人自身的努力與修養來達到善的境界。因此孟子、荀子人性論雖對于人性善惡判斷不同,但最終都指向“善”,區別在于二者側重點不同,孟子旨在揚善,而荀子旨在抑惡,并且都肯定人具有向善的資質,通過教化與修為皆可成善,且二者都主張性與情統一、性情相關,這些觀點為董仲舒研究人性論提供了基礎和動力。董仲舒批判、繼承了孟子、荀子的學說,順應時代要求,形成了自身頗具特色的人性論體系。
(二)漢代社會現實需要
漢代實現了大一統,但經過長期戰爭與改朝換代,漢初社會凋敝、經濟衰弱,統治者推行休養生息政策,經數年調整,經濟逐漸恢復,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國家社會中問題重重,政治方面諸侯王勢力日益擴張,官員隨著實力壯大而腐敗加深;經濟上因商業發展商人實力雄厚導致僭越禮儀行為;日常生活中偷盜等不良風氣蔓延,一系列問題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等級秩序、道德禮儀遭到破壞,階級矛盾等問題亟須解決。董仲舒深刻認識到在此復雜情況之下確立統一的思想、實行倫理教化勢在必行,他主張用儒家學說來統一百姓思想,用儒家禮儀制度規范社會秩序,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加之漢初以來眾多儒生倡導儒學的努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順勢而出。這一主張不僅為統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措施,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而且使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董仲舒正是在此背景下開創了適合漢武帝時代的思想體系,包括陰陽思想、天人感應、人性論思想等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人性論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在漢代社會乃至后世都有重要作用。
二、人性論觀點
(一)人性善惡并存
董仲舒在結合先秦人性論的基礎上辯證地提出了人性善惡并存的觀點,他繼承孟子性善說,肯定仁義禮智的先天性,“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同樣認為人性來源于天,把性看作天生的自然之資,又從陰陽論角度引入情的概念,“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 ④性情之關系猶如天有陰陽:性中有情,情是性的一部分,情是人的欲望,是不善的,需要加以節制。“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 ⑤人身上同時存在仁和貪兩種氣質,性仁情貪,含天生善的本性與含惡的情都屬于人的性,所以人性善惡兩種潛質并存。董仲舒綜合了孟子性本善與荀子人性中欲望的存在的觀點,正如強中華所言:“董仲舒在綜合孟荀二人人性論基礎上,把趨善、趨惡兩種潛質均納入人性的范疇,從生命科學層面講,更符合人的實際。因此比孟荀僅就人天生屬性中的某一部分論‘性更為合理。” ⑥
董仲舒肯定孟子所說人性中善的部分,但并不完全認同孟子所說的人性善,“善”應為人與人的對比,而非人禽之別。“質于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于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者許之,圣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于圣人之所為,故謂性未善。” ⑦若與禽獸之性相比,人性可稱之為善,若以人道的標準或者圣人的準則來衡量,普通人之性是無法達到善的。這也點名了董仲舒與孟子觀點不同的來源,即二人對比的范圍與標準不同,孟子向下與禽獸作比,而董仲舒向上與圣人相比,兩種對比各有可取之處,董仲舒更嚴格的規定了人性之善,對于當時漢武帝時期統一民眾思想,實行教化、規范社會秩序而言更加具有約束力,并且為后世人性善理論奠定了一定的高度。
(二)以“中民之性”為性
董仲舒人性論中極其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即性三品說 ,他將人性劃分為三個等級,“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⑧圣人之性與斗筲之性為善惡兩個極端,圣人具備高尚道德與人格,不僅善且超越了善,是難以達到的境界;斗筲本指容量極小的容器,斗筲之人“弗系人數而已”,違背倫理道德與禽獸無異,外界教化對其并不起作用,因此不在人性范圍之內;只有中民之性似繭似卵,需經過孵化與繅絲,中民天生有善質而有待后天教化成善,代表一般群體,包括官員、百姓在內的大多數人的本性。結合董仲舒人性善惡并存學說可知中民之性,性中有情,有善有惡,即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惡的部分可通過受教育而被改造為向善。反觀圣人之性指有性無情,其“善”與孟子性善論契合,而斗筲之性則有情無性,與荀子性惡說相同,都在強調性情中的一方,中民之性將二者結合起來,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性三品說闡明了人性教化范圍,完善了自身人性論,以中民之性為性的主張適應教化民眾、改造百姓價值觀的需要,同時與其為君主服務的政治目的相符。中民之性作為人性代表顧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層次與境界,中民之性善而未善則使對民眾實行教化順理成章,為民眾接受教育創立了理論基礎。
此外,董仲舒的學說體系中,君主即天子受命于天,國受命于君,而圣人之善來自天,天子即圣人,是中民的教化者,擔任著使民向善的職責,以此使君主統治具備完全的合理性,董仲舒的人性論極大地適應了統治者和社會現實的需要,也是其學說能被采納和產生重大影響的重要原因。
(三)倡導教化向善
無論是人性善惡并存還是以中民之性為性,董仲舒都主張人性有善質而未善,他運用禾與米、繭與絲、卵與雛、璞與玉等七組典型之物闡明性與善的關系。“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異辭,其實然也。” ⑨而趨善潛質唯有依托外部教化才能進而轉化為實際之善,在他看來善與教緊密關聯,教是抑制惡的有效途徑。
董仲舒以儒家倫理作為教化參考與準則,繼承孟子仁義之說,主張以仁義修身而獲取善性,具體來說即對他人仁,對自己內省,尤其是統治階級更應以仁對待百姓。他重視教育的教化作用,堅持教為政之本,邢為教之末,選取儒家六經作為教材,以此培養人民心志、獲取知識來修身養性。董仲舒人性論體系中不可忽略的即三綱五常,他以天陰陽運行闡釋人之間的關系: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君臣、父子、夫婦構成三綱,三者關系即古代社會中基本的尊卑等級與倫理秩序,而更加能夠維護這種秩序的即在孟子仁義禮智四端基礎上提出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以仁為核心規定了個人日常行為準則要求,三綱五常互相支撐構成了教化的重要內容,董仲舒將其視為人道之善與孟子人皆有四端相之說一致,是其人性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教化比之于嚴厲的刑罰既以潛移默化的形式使民眾歸順又體現統治階級之仁政與愛民,這樣的思想在封建社會當中所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由此亦可窺見董仲舒作為漢代儒者的貢獻與影響力。
三、董仲舒人性論的影響
董仲舒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運用天人感應宇宙觀及陰陽運行觀創新性地提出人性論體系,為漢代君主治理和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重要理論。他以上天權威來闡釋君主權力和教化民眾向善,實現了理念的統一,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有效依據和途徑。而教化論以使人性向善為目的,以儒學為基本依據,不僅提高了民眾思想道德素質,營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為鞏固統治做出了重要貢獻,關鍵的是有力地推進了儒學發展。在董仲舒建議下,儒學成為官方推行的正統思想,改變了先秦以來儒學并未受重視的現實狀況,成為儒學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三綱五常的倫理規范弘揚了儒家的仁、義、孝等精神,使儒學蔚然成風,人民教化取得了良好效果,為儒學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董仲舒最先提出情性問題,對情性做了區分,影響了漢及以后的人性觀念。東漢王充直接承繼了董仲舒人性來自天的理論及性三品說,認為性與命密不可分,并同樣肯定外在教化與環境對于人性的作用,對人性善惡繼續加以探究。唐代韓愈在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基礎上提出性五品說,細化了性情具體內涵;宋明時期理學家受董仲舒啟發,綜合前人思想,以氣言性,對人性善惡進行了新的闡述,形成了更完善的人性學說,董仲舒作為人性論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人物,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結語
董仲舒的人性論承接孟子、荀子的人性思想,融入天人感應與陰陽二氣思想,提出更全面、更系統的人性善惡并存觀,形成了初步的性三品說,為后世唐、宋明時期人性論研究提供了啟發,具有繼往開來的作用。他以中民之性為性、教化成善的學說更適應了漢武帝時期統一思想的需要,服務于政治,使儒家學說得到弘揚,并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為儒學奠定了官方正統思想地位,為此后兩千年的思想奠定了基本框架,董仲舒人性論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注釋:
①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2頁。
②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9頁。
③王先謙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
④董仲舒著,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80頁。
⑤董仲舒著,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76頁。
⑥強中華:《正名·時間·人性論——董仲舒人性論的邏輯層次及理論困境》,《孔子研究》2012年第02期,第4-11頁。
⑦董仲舒著,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83頁。
⑧董仲舒著,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春秋繁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88頁。
⑨蘇輿著,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13頁。
參考文獻:
[1]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0.
[2]王先謙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3]董仲舒著,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2012.
[4]強中華.正名·時間·人性論——董仲舒人性論的邏輯層次及理論困境[J].孔子研究,2012,(02):4-11.
[5]蘇輿著,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2.
作者簡介:
劉彩云,女,漢族,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