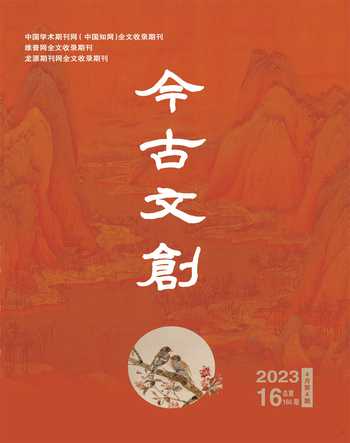人文題材紀錄片的社會記憶建構探析
鐘家豪
【摘要】 社會記憶是一個大我群體過去全部經驗和認識的總和。喚醒社會記憶,人們才能系統地看見過去,謀劃未來。社會人文紀錄片《人生第二次》將關注焦點放在歷經風雨后,普通人與現實生活恒久的對抗與和解。通過鏡頭將個人記憶上升為社會記憶,獲得觀眾的情感共鳴與認同,進而喚醒部分群體的社會記憶。
【關鍵詞】社會記憶;人文紀錄片;《人生第二次》;記憶建構
【中圖分類號】J95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6-009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28
紀錄片是記錄社會思潮和發展脈絡的重要影像資料。人文題材紀錄片作為紀錄片類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鏡頭對準時代洪流下的具體人物,著重挖掘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用細膩的筆觸和關懷的姿態抒寫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用貼近現實、貼近觀眾的影像拼貼起大眾的社會記憶。如張愛玲所說,“人生看起來很長,其實要緊的就那幾個黃昏”,《人生第一次》著重展現人生最重要的那幾場黃昏,串聯起出生、上學、進城、養老等十二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從細節出發記錄下普通人在面對未知時的顧慮和勇氣。而《人生第二次》講述的則是黃昏前后的漫漫白晝與黑夜。影片用“圓缺”“納拒”“是非”“破立”四組互相映照的關鍵詞記錄下高光時刻之外,鏡頭暗處恒久的抗衡與和解。
與《人生第一次》的樂觀蓬勃的氛圍不同,《人生第二次》在此基礎上多了一絲浴火重生的厚重感。第二次并非只是第一次的單調重復,而是經歷大風大浪后,依舊直面生活苦難的韌性與思考。走失多年的孩子在親生父母和養父母之間的掙扎躊躇;不同群體對容貌焦慮的思索和回應;服刑人員再次回歸家庭和社會的陣痛與調整。《人生第二次》在一個個真實的故事里,犀利地剖析著社會現象背后的復雜成因。藝術社會學的奠基人阿諾德·豪澤爾(Hauser Arnold)提出:“最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直接觸及現實生活的問題和任務,幫助人們理解產生那些問題的環境。《人生第二次》從暗流涌動的平淡生活出發,持續動態地建構人們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
一、《人生第二次》中社會記憶的塑造符號
(一)身體:社會記憶的鮮活抒寫
記憶是人體的機能,身體是人類最原始、最古老和最直接的傳播媒介,天然地具備生產、傳達、儲存和反饋信息的能力。人們以身體作為媒介來感知世界的存在,進而認識世界。在紀錄片中,創作者通過對拍攝對象的身體、年齡、職業等特征的著重表達,以期再現人物本身的生命力,以及人物作為一定的社會角色所彰顯的群體記憶的力量,這種力量來源于長時間的記錄和特定景別帶來的認同感。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的舉動也在曲折的事件里生成新的意義。然而作為獨立的個體,盡管個體記憶都是從社會實踐中獲得,但是受到身份、年齡、階級、家庭等多種環境的影響,每個身體的生命經驗與記憶仍然體現出很強的差異性,不同個體對同一事物的看法與記憶往往不盡相同。這種社會記憶的分層正如保羅.康納頓所說“不同輩分的人雖然以身共處于某一個特定的場合,但他們可能會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絕緣。”[1]因此,《人生第二次》充分展現了不同生活境遇面前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不僅拓展了觀眾們的社會記憶,也帶了一種新的啟示:關心社會的運轉,尊重擦肩而過卻可能身陷漩渦的身邊人。
《人生第二次》將鏡頭對準蕓蕓眾生,通過大量的身體抒寫展現他們在逆境中的對抗與和解,用充滿個人感悟的微觀敘事打開社會的多面窗口,觀眾得以真正看見身邊的人。例如第三集《納》,一小時的片長專注于講述因車禍導致下半身癱瘓的何華杰重新建設自我的故事。盡管下半輩子要在輪椅上度過,但在媽媽的精心照料下,何華杰對待現狀仍然樂觀。夏天,他和四個輪友踏上318川藏線這趟找回自我的旅途,在陰雨夾雜冰雹的旅途中,何華杰首次完全憑借自己的力量,從地面挪到輪椅上。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困境同時出現在何華杰的身體上,讓這一舉動顯得格外悲壯和感人。在輪友前輩的鼓勵下,何華杰開始擺脫母親的協助,建立起獨立生活的信念。在片尾,何華杰之母不再只是作為母親的形象存在,而是作為邱娟妹她自己。
再如第七集《破》將視角瞄向離婚夫婦關于子女撫養權的問題。法律阻斷不了血肉親情的羈絆,影片通過拍攝三組離婚夫婦對于撫養權的爭奪以及由此產生的敵對關系,來探討婚姻的復雜和關系的脆弱。片中反復出現的爭吵、人來人往的律所、針鋒相對的模擬法庭將關于離婚的社會記憶平鋪到觀眾面前,即便是未曾經歷過離婚的觀眾,也能通過身體的在場體認到離婚記憶的痛苦與唏噓。《人生第二次》通過多樣的身體敘事,將被攝者的個體記憶上升為社會記憶,折射出各種社會現象之下豐富內涵及脈絡,補充觀者的社會記憶。
(二)空間:社會記憶的依存場所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認為空間是社會的產物,因而具有生產性,且空間集物質性、精神性、社會性為一體。空間是紀錄片敘事的重要符號,也是社會記憶的依托載體。無論是承載集體儀式行為的公共空間,或是個體居住生活的私密空間,人們對往事的回憶與對社會記憶的喚醒都需要通過實體對象來傳達與體現。
《人生第二次》在法院、整形醫院、監獄等極具故事張力的場景展開敘事,通過多處兼具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空間補齊大我群體的社會記憶。如第四集《拒》,在錐子臉、A4腰、精靈耳接連登上熱搜,引發輿論熱議的后現代語境。種草平臺與商家和意見領袖合謀,一邊有意無意地引發社會的容貌焦慮,一邊又通過正能量的內容輸出消解著用戶的容貌焦慮,在焦慮與反焦慮的對峙中,整形醫院這一空間獲得除整容外的額外功能,成為收納醫美用戶社會記憶的場所。從“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到“我的身體我做主”,身體成了觀念的戰場,醫院也成為整形群體記憶里的一部分,承載著人們渴望美、追求美的記憶,見證著無數人在變美路上的前仆后繼,引起醫美用戶的情感共鳴。片中真實記錄了術前交流、手術過程及術后恢復的情景,沒有參與醫美消費的群體也能在鮮活的案例和真實的影像敘事中建立起個人與社會之間補充性和想象性的密切聯系。再如第六集《非》講述了服刑人員出獄后與妻子的相認和社會再適應的過程,影片內充斥著大量監獄里的實拍畫面,片中的監獄是灰暗的、毫無生機的、破舊的。被攝者出獄后來到人才大廈找工作,卻被告知招聘早已轉移到了網上,去政務大廳辦事也因與社會脫節太久不會操作小程序,多重日常生活空間的抒寫營造出一個出獄人員重新走向社會后與現實的脫節和困局。
與記憶相同,遺忘也是人體的機能。由于個體記憶的不穩定性,過去的回憶可能會無法確認,或夸張失實。實體空間可以將個人與過去、與集體聯系起來,復現社會記憶。
二、《人生第二次》中社會記憶的建構路徑
(一)敘事視角:多元視角共筑差異化呈現
紀錄片中的敘事視角是指講述人與故事之間的不同關系。法國學者熱奈特根據講述人定位的區別把敘事視角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外聚焦”三種。[2]“零聚焦”又稱“全知視角”,突出特征是使用旁白解說,為影像提供更宏觀的視野以及鏈接影片的不同時空。“內聚焦”又稱“限制敘事視角”,采用相對局限的角度,只能看到事件的局部。“外聚焦”又稱純客觀敘事視角,只是如實記錄人物的外貌、行為及客觀的外部環境,不會過度解說,與“直接電影”有類似之處。隨著觀眾觀影經驗的豐富,單一的敘事視角無法滿足觀眾所需。創作者普遍在影片中綜合用多種敘事視角,從不同維度串聯社會記憶。
如《人生第二次》的第一集《圓》。開篇首先是被拐少年衛卓的母親占緒蓮的視角,占緒蓮簡單概括了這十八年來尋親的心酸。毫無情緒波動的獨白配合雨天團圓餐館落寞的空鏡頭瞬間將觀眾拉進占緒蓮的個人記憶,引起觀眾的共情。隨后“零聚焦”以文字解說的形式出場,簡要交代了衛卓尋親案的背景——公安部“團圓行動”。幫助觀眾掌握事件脈絡,并勾勒起觀眾對于打拐這一社會記憶的認知與想象。難能可貴的是本片采用了衛卓、占緒蓮、打拐民警王自強三重“內聚焦”的敘事,將尋親這一過程放置在三個視角之下,觀者得以了解打拐尋親背后盤根錯雜的面貌,因創業欠債的衛卓備受良知與親情的拷問,占緒蓮心底由衷的喜悅和揮之不去的擔憂,民警王自強對拐賣案件的解讀,以及打拐路上的艱辛與感慨。上述種種個體記憶經由創作者篩選后走進大眾視野之中,實現社會記憶的構建。
(二)敘事結構:合理編排拼貼碎片化記憶
在人文紀錄片關于社會記憶的表達中,結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必然會在保證真實的基礎上對各種要素進行合理的編排,運用恰當的藝術加工方式展現影片的主題,達成紀實與藝術的統一。為了更好地留存和傳承社會記憶,人文紀錄片多會采用易被觀眾接受的漸進式結構和并列式結構。漸進式結構以邏輯或時空為依據,通過層層遞進的深入,保持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推翻的姿態,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事件的流暢性,符合觀眾了解陌生事件的次序。而并列式結構是指片中各要素之間保持平行、并列的關系。各要素之間既可獨立成篇,又可打碎,在要素之間穿插敘事。兩種敘事結構的合理使用可以降低觀眾的理解難度,擴寬觀眾的社會記憶面向。
在《人生第二次》第五集《是》中,影片使用漸進式的敘事結構講述了兩組心里含冤的被攝者到最高檢申訴的故事。兩組被攝者的故事在影片中按照事件展開的邏輯交織進行,兩起錯綜復雜的案件讓觀眾充分感受到申訴過程中含冤者心里的痛苦、憤懣和無助,最終只能和過去和解,放下沉重的包袱繼續前行。橫觀《人生第二次》全貌,“圓缺”“納拒”“是非”“破立”四組相互映照的片名,八集主題鮮明的故事,將社會記憶的不同面貌整合在一起,它們相對獨立又密切聯系。集中展現了面對不同的困境,中國人從來不缺從頭再來的勇氣,依然滿懷笑對人生的豁達。對社會現象的關照引發觀眾的身份認同,構建社會記憶。
在信息爆炸的當代,為避免觀眾在信息風暴中集體失憶。漸進式的敘事結構有助于受眾理清記憶的認知,產生清晰的邏輯思維。而板塊式的敘事結構能將不同社會群體的記憶拼湊成整體,促進人與人的相互理解,以及群體的認同。兩種敘事結構合力喚醒一代人共同的社會記憶。
(三)視聽語言:聲畫同謀強化影像審美性
德國文化記憶學者阿萊達·阿斯曼指出:文本、圖像、身體與地點是構成記憶的四個關鍵媒介。[3]紀錄片通過文本和圖像來闡述意義,詮釋價值。其中視聽語言是紀錄片構建社會記憶的重要元素。通過對畫面、聲音進行藝術化的組接,紀錄片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接壤,在打通、更新社會記憶的同時,精湛的視聽語言也能給觀眾帶了美的享受。
《人生第二次》中的運動鏡頭多是以手持鏡頭的面貌出現。不規律的晃動給畫面帶來一種自然的“呼吸感”,能夠增強紀錄片的真實性,而真實性是社會記憶得以成立的基礎。《圓》中使用了較多的手持鏡頭從背后跟拍人物,營造出真實的在場感,觀眾如同親臨現場,直面事件中的喜怒哀樂。固定鏡頭方面,中近景和特寫鏡頭的占比較大,短小精悍的鏡頭散落在全片的各個環節,視覺上的強制牽引著觀眾的視線,為沉浸式的觀影體驗奠基。在第三集《納》中,鏡頭多次對準何華杰的輪椅以及何華杰母親的舉動。無需解說詞贅述,母親鏡頭與何華杰鏡頭的交叉剪輯,用最易被觀眾接收到的信息再現母子之間血濃于水的親情,足以還原一個愛子心切的母親形象。
聲音語言在意義的傳達中與鏡頭語言相輔相成,解說詞和同期聲的合理編排能夠提高紀錄片的文獻價值和審美價值。解說詞體現創作者某種態度和傾向以及串聯不同時空,拔高故事主題。而豐富的同期聲可以直接表達被攝者內心的所思所想,無意間的人生感悟不僅沒有高高在上的說教感,觀眾與片中人物共情之后,反倒會更認同這些人生感悟,進而完成社會記憶的融合。例如第六集《非》,全片的聲音語言主要由第一人稱的畫外音敘事和被攝者的同期聲組成。[4]“第一人稱畫外音敘事”指被攝者的自我講述以類似畫外音的方式出現,簡而言之就是被攝者為自己解說,聲音與畫面內容不構成同步敘事的關系。在本集開頭,服刑人員的自我講述“現在回想起來,接受這個紀錄片的拍攝,有點莫名其妙。我已經在這十一年了,還有一個月就要出獄了。”與深思熟慮的第三人稱解說相比,第一人稱的講述更加隨意,非常口語化。能夠最大程度地還原人物的真實情感,建構社會記憶。
當代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曾提到“美感是一種冷靜后的回味”。豐富的視聽語言能讓受眾感受到更具記憶點的視覺景觀和情感體驗。兼具觀賞性和知識性的紀錄片是維系社會記憶的絕佳載體,能夠更好地鏈接社會記憶、傳遞價值。
三、結語
社會記憶是各種社會集體所保存的記憶,是一個集體過去全部認識的總和,對一個群體的凝聚和延續至關重要。記憶的另一面是遺忘,采用一定的措施保存、加深社會記憶十分必要,媒體作為保存社會記憶的絕佳工具,對于形成民族身份,連接民族成員、民族經歷以及共同記憶也具有重要作用。人文紀錄片作為媒體的一種表現形式,不僅能夠真實還原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可以通過敘事結構、視聽語言等手段讓受眾站在某些視角再次體驗事件的經過與細節。紀錄片留存給后世的不僅僅是社會記憶的樣本,更涵蓋了不同的時代難題之下,親歷者、創作者等個體對于社會的理解和探索。一個時代的記憶除了官方的宏觀抒寫,還需要個人鮮活的生命體驗加以補充,個體的生命體驗也只有納入牢固的集體框架,才能長久留存。唯有如此我們的歷史和記憶才有可能是真實可靠的。《人生第二次》將鏡頭瞄準尋親、留守、整容、婚姻此類當今社會棘手的問題,展現了二十余位被拍攝者的思考與作答,由此打通類似群體的社會記憶,觀眾在觀影中獲得凝聚力和認同感,社會記憶的力量得以顯現。
參考文獻:
[1](美)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2]方圓.熱奈特“敘事”概念研究[D].浙江大學,2019.
[3]張琰.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中的媒介思想研究[D].河北大學,2021.
[4]邵雯艷,倪祥保.紀錄片新方法:第一人稱畫外音敘事[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40(03):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