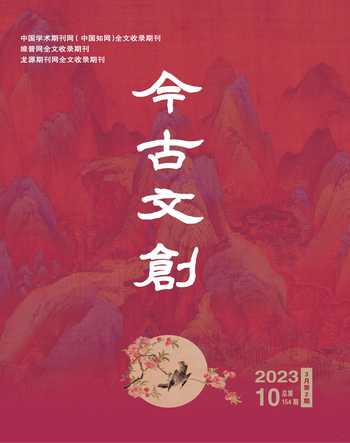論柔石小說中的人道主義精神
【摘要】 20世紀西方人道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左翼作家柔石青年時代即受到人道主義思想影響。本文以“對愛情與個人幸福的追求”“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博愛同情”“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肯定”三個層面分析柔石小說中所蘊含的人道主義精神,順著柔石小說創作藝術逐漸成熟的道路,認識柔石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對被侮辱與被欺凌的中國勞動人民的愛與同情,體會他作為動蕩不安時代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對人性的思考。
【關鍵詞】柔石;“五四”文學;人道主義;左翼作家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0-005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18
“人道主義”一詞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所提的人文主義(Humanism),內涵在于“要求擺脫宗教神學的禁錮,要求人格獨立、個性解放、意志自由,要求恢復人作為人的地位和尊嚴,追求個人才智的發展和世俗的幸福生后”①。人道主義思想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柔石從第一部短篇集《瘋人》開始就表現出對自由、個性和個人幸福的追求,正符合五四風潮所推崇的民主、科學、個性主義等人道主義思想。小說《二月》《為奴隸的母親》等的發表,集中展現了柔石對底層貧苦人民的關懷,對麻木的國民的痛心,和對知識分子應走道路的探索,是其思想逐漸成熟的表現,體現出當時左翼作家深廣的人道主義精神。
一、人道主義傳入中國
歐洲經歷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直至18、19世紀,人道主義逐漸成為文學主流之一。作為近代歐美文學高峰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就是以人道主義理想為核心,披露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同情苦難民眾的遭遇,探討人的自由與解放,具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藝術感染力,對于推動社會制度的進步,其積極意義無可替代。20世紀初,“五四”運動爆發,大量西方思想文化被引入,知識分子高呼民主與科學,使中國大地上的人們耳目一新。陳獨秀《敬告青年》指出:“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②,即是要提倡自由與民主。《新青年》所傳播的大量新思想皆為提倡以個性主義為核心的人道主義新道德,要求考慮每個個人所應該獲得的獨立、權利和愛,諸如尼采的超人哲學、易卜生的個性主義、叔本華的自我意志說、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以及馬列主義等。胡適等人倡導的“文學革命”向國內傳播西方文學史,將19世紀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大思潮譯介進來。新的人文思潮、藝術內容與創作方式為作家們所吸納,在其后助力他們開拓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嶄新局面,也對當時正奮力掙脫封建枷鎖的青年們影響深遠。
在文學實踐中,“五四”初期的白話詩,如劉半農《相隔一層紙》、沈尹默《人力車夫》、胡適《嘗試集》,表達對底層民眾的人道主義同情,抗議貧富兩極分化的世道;魯迅《狂人日記》吶喊“救救孩子”,其中蘊涵中國文人的憂憤深廣力透紙背,與當時所推崇的人道主義相呼應。蔡元培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上發表《勞工神圣》,將“勞工神圣”社會思潮引入文壇,隨即出現一批以勞動人民為主人公的作品,促使知識分子從對勞動人民悲慘境遇“隔岸觀火” ③似的悲憫同情轉向探索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況、思想情感和國民性,如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魯迅《吶喊》等。其后沿魯迅所開辟的路走出的鄉土作家,以及問題小說、自我小說等,都顯示出在民族危亡的時代以筆為矛的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民族的憂患與熱愛,對于土地和人民的關切與企盼。這一時代的作家,包括柔石在內,用他們的作品推動了人道主義思潮在中國文學以至文化領域的發展。
二、柔石小說中的人道主義的形成
(一)柔石的成長經歷
柔石幼時家境貧寒,原名“平福”被地主強令改為“平復”。作為社會底層,連擁有自己名字的權利也沒有,這件事在柔石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使他開始對被剝奪人權之事有了認識。柔石從小便目睹勞動人民生命中的不幸,“農民五哥,背著鋤頭從田里回家,疲乏地往床上一躺,連雙腳上的草鞋也沒來得及脫下就咽了氣……木匠陳定福貧病交迫,借了財主的高利貸無力償還,棄世前為不使妻兒受驚嚇,竟然躲到山野里去身懸高枝” ④。這些悲苦的現實在柔石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使他成長為一位正直、善良、堅定的人道主義作家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
(二)魯迅的人道主義觀對柔石的影響
柔石與魯迅關系密切,他的人生道路與文學創作之路都得到了魯迅的幫助。魯迅早期的人道主義觀與其改造“國民性”的想法相通,即為了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徹底砸碎封建專制制度及其精神枷鎖,把人從黑暗、愚昧和麻木無知的狀態中解救出來。魯迅早期的作品,《狂人日記》《吶喊》《彷徨》等都是反“神道”“王道”“妖氣”,鏟除“野蠻”“獸性”,以爭取“真正的人道”。有魯迅開風氣之先,緊隨其后的鄉土作家、東北作家群等,在文風、內涵、創作手法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了魯迅的影響。柔石作為魯迅所記“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唯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⑤,是魯迅較親密的友人,對魯迅秉先生之禮,他的作品中自然有魯迅的痕跡。《瘋人》集中“瘋人”有著魯迅“狂人”的影子,瘋人因失去不被允許的愛情,失去愛人而瘋狂、死亡,“狂人”則因“吃人”的世道下,滿目都是吃人的人而狂。《二月》描寫逃離與尋找出路不得的具有博愛精神的知識分子蕭澗秋,在封閉的芙蓉鎮力圖挽救婦女與孩子;他在芙蓉鎮是為逃避“五四”后的失落世道,最終尋找出路失敗,又是魯迅《彷徨》集“孤獨者”的延伸。《為奴隸的母親》中被剝奪了自由人格與母愛權利的“春寶娘”,她在絕望的泥沼中的掙扎又可見被欺凌與被損害的“祥林嫂”“閏土”們的身影。
(三)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觀對柔石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中,西方文學與社會思潮被譯入中國,柔石得以廣泛接觸到托爾斯泰的思想和作品。“在柔石的小說中,可以看到他對自我懺悔、勿以暴力抗惡和博愛主張的認同”⑥,也可以看到他對受壓迫的底層勞動人民的表現及其中透露的反抗意識。托爾斯泰可以說是影響柔石創作最深的西方作家。柔石早期的中篇《三姊妹》講述了一個自我救贖的故事:章先生在八年的時間內先后與三姊妹中的蓮姑、蕙姑戀愛,卻又拋棄她們,使她們的人生陷入黑暗絕望;在章先生又試圖追求小妹藐姑時,被藐姑憤怒地驅逐,章先生最后在流著鮮血的回憶中想明白了自己過往所做事情的罪孽深重,開始挽救三姊妹的人生。對比托爾斯泰的《復活》,章先生年輕時對蓮姑、蕙姑的愛戀與占有,與聶赫留朵夫青年時代對瑪斯洛娃的誘奸是相似的;被章先生拋棄的兩姊妹的悲慘境遇,與瑪斯洛娃的墮落、重逢時境遇的差別相似;長大了的藐姑就是走向成熟的蓮姑與蕙姑,她作為姐姐的代言人對章先生禽獸本質的揭露,與瑪斯洛娃獄中對聶赫留朵夫之流的唾罵,其思想認識是相同的;聶赫留朵夫奔走為瑪斯洛娃伸冤,使她最終得以免除死刑,章先生也做出相似的挽救行動。
從《三姊妹》中可以看到柔石深受托爾斯泰自我懺悔、友愛寬容、勿以暴力抗惡等觀念的影響。柔石在《三姊妹》中表達不該受“別人隨意指給”的苦,不該不做反抗地受到階級的壓迫,這是他作為知識分子要告訴底層貧苦人民的;作為作家,他也宣揚了自己的平等觀念,認為為自己的快樂而斷送別人的快樂是多么罪惡的行為,他借著藐姑之口,罵這是“禽獸”的行為,亦是罵那些將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踩在腳下奴役的剝削階級。
三、柔石小說中人道主義的體現
柔石來自貧苦的底層民眾中,早期期望可以通過教育這條路來拯救國民與國家。后經歷北上求學,及南下上海與魯迅結交,在魯迅幫助下創辦《晨光》刊物,在文學創作上逐漸成熟。柔石不同時期的作品中表現出一個人道主義作家思想不斷豐滿、成熟與深刻的過程,其中有他對苦難的中國人民的深切憂慮,表明他必然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成為優秀的左翼作家,勇猛的革命戰士。
(一)對愛情與個人幸福的追求
作品集《瘋人》,創作于1924年前后,此時柔石教育救國的理想受挫,開始長期孤身漂泊在外的生活。這一時期也是他人道主義思想形成的初期,他結合自身經歷寫了《瘋人》等表達對自由愛情與婚姻追求的短篇。瘋人本被吾鄉望族某家收做養子,因他“賦性之高傲與不羈,逆主人耳,遂貶為書記”。瘋人成長出自己的個性,他有學書學劍都很成功的才能,他自然要有獨立的人格,要求不受人控制與役使的自由,高傲與不羈也是他追求平等身份地位的體現。瘋人因此受到打壓,被貶為“下層”人,這是瘋人遭遇的第一重悲劇。被貶為書記的瘋人不配與主人的少女相戀,但光明正大的戀愛是人的正當追求,追求愛情、美和幸福生活是人生來就應有的權利。少女以生命的代價來爭取自己的愛情,瘋人則以發瘋來表現他的悲痛、壓抑和抗爭。被剝奪追求愛情與幸福的權利,被剝奪深愛的人,最終一無所有,這是瘋人的又一重悲劇。
在小說中有一個“破衣者”形象,他企圖以一種道家的虛無主義勸瘋人放棄對現實幸福的追求。讓人聯想到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以宗教的無欲無求、自甘受苦、追求后世幸福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來統治人民,使他們麻木地忍受壓迫,不期反抗。但瘋人的覺醒是徹底的,他無懼無畏,發出“莫令我裹足!我必須尋求我的愛人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的宣言后殉情。《瘋人》寫的是對愛情和自由的追求,表達著肯定個人幸福的人道主義思想。
(二)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博愛與同情
中篇小說《二月》是柔石創作成熟的標志。1929年柔石已與魯迅結交,魯迅“強調要正視黑暗,暴露黑暗,要執著地反映現實,在其引導下,柔石小說的現實性大大增強,表現出啟蒙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⑦,描述現實以直抒人道主義關懷。
《二月》對于知識分子群像和個體形象的描寫十分到位:以蕭澗秋為代表的,包括陶慕侃、陶嵐在內的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對弱者充滿同情與關愛的一類知識分子;以方謀為代表的,熱愛談論各種“主義”而不做任何實際行動的一類知識分子;以錢正興為代表的,卑鄙的封建禮教保護的虛偽的一類知識分子。三類人匯聚芙蓉鎮,蕭澗秋在其中探索著自己的道路。蕭澗秋是一個懷著熱情和崇高人道主義理想的富有正義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五四”落潮之后,一代人苦悶、孤獨、悵惘、彷徨的體悟集中在他身上。他經歷漂泊后厭倦了都市的平庸生活,來到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芙蓉鎮,偶遇為革命犧牲的李先生的遺孀與兒女,文嫂眼中極烈的悲哀刻在他心上,他為這個在寒冷中岌岌可危的窮苦家庭送來了溫暖和希望。蕭澗秋的人道主義思想是明確的,他不忍看著別人受苦,不忍貧苦的人挨餓受凍,他將對底層人民的博愛與同情付諸實踐。蕭澗秋沒能挽救文嫂家的家破人亡,芙蓉鎮的這一場人道主義援助以失敗告終。他離開芙蓉鎮的時候,又看見與文嫂、彩蓮同樣神情的悲愁的婦女兒童,明白過來:這樣的婦人與孩子在這個國土內是有很多的,救救婦人與孩子——這是他內心的呼喊。
柔石在《二月》中寫了孤獨的人道主義者蕭澗秋的嘗試、探求與逃離,討論了在當時混亂的中國備受欺凌、無依無靠的婦女兒童的處境,提出對她們進行人道主義幫助的必要,也提出徹底地挽救婦女與孩子,要將數百萬的人都變成蕭澗秋這樣的人,要讓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大眾中樹立起來才行。
(三)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肯定
柔石也是鄉土作家中的一員。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柔石著力描寫家鄉浙東農村的風土人情,以勞動婦女為主要描寫對象,寫在傳統的重負與苦難的重壓下她們身心受到的摧殘。《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寫婦女一生只寄望于嫁與生子,嫁給似鬼一樣的人受折磨唯有忍氣吞聲,兒子死去就失去生的意義,一生悲苦卻不能受任何幫助;《摧殘》寫母親生下兒子無力撫養,得知兒子意外死去時自認是殺死他的兇手,揭露“窮人原是不配有兒子”的荒謬現實。通過對多重壓迫下艱難生存的底層人民悲慘命運的敘述,柔石表達出對在極悲苦命運中掙扎的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肯定。
“文化迄今加諸于女性身上的要求主要是自我犧牲”⑧。無論是作為母親還是作為妻子,婦女作為個體的尊嚴與價值都被剝奪、被犧牲。在《為奴隸的母親》中,春寶娘不斷地被犧牲、被剝奪,直到失去所有尊嚴和價值。春寶娘第一次失去尊嚴,是她不能守住她作為皮販的妻子的身份,在婚姻關系中要求的忠貞被丈夫賣出;春寶娘被典到秀才家,成為秀才的泄欲工具、秀才家族的生育工具,她作為人的尊嚴被無視;當為秀才家生下兒子,她便被無情地丟棄,作為母親的尊嚴與價值也被徹底損毀。在這個典妻的故事中,婦女完全被剝奪了她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只能吞咽無盡的痛苦,忘記自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像死尸一樣在世上拖延。
在創作這篇小說時,柔石在日記中寫“決心用文學反映人生,同情被損害與侮辱者” ⑨,他用深沉的筆調刻畫悲慘命運中的人性,通過人物的心理矛盾寫人的尊嚴與價值被剝奪的處境。此時的柔石作為一個成熟的人道主義作家,開始關注在極端貧弱的生活中,人受到壓抑以致異化的狀況。皮販將嬰兒“如屠戶捧將殺的小羊一般”投進沸水中溺死,這極殘忍的殺子一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讓人無法忽視的一幕。麻木的民眾的行為讓人在觸目驚心之余,深切感受到當時的社會多么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覺醒與改變,自由與平等必須深入到民族的骨髓之中才能喚醒人們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肯定。
四、結語
柔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創作風采與人道主義關懷。他對動蕩變遷時代的底層人民苦難生活的描寫,對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追求、迷惘與痛苦的掙扎的剖析,以及對國家與民族的憂患,都是他作為一個永存于后世的作家的藝術魅力所在。柔石的小說與同時期的一些空洞而狂熱的作品相比,具有更值得后世傳承與研究的沉郁風格、悲劇意蘊和人道主義情懷。柔石的作品反復被重印,小說《二月》《為奴隸的母親》在當代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進入大眾文化視野,不同時代的學者們也更新著對柔石作品精神內涵的理解,使其不斷綻放新的光芒。
注釋:
①邵伯周:《人道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遠東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頁。
②李光云:《淺議人道主義思潮對“五四”文學作品的影響》,《楚雄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
③王強:《“勞工神圣”與五四新文學》,《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
④王艾村:《柔石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⑤魯迅:《魯迅全集:為了忘卻的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頁。
⑥李雯:《淺論柔石與托爾斯泰主義》,《文學教育》2013年第3期。
⑦張國紅:《柔石小說創作與五四文化影響》,曲阜師范學院2008年學位論文。
⑧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37頁。
⑨趙帝江:《柔石日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頁。
作者簡介:
張榮,女,漢族,四川廣安人,天津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漢語國際教育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