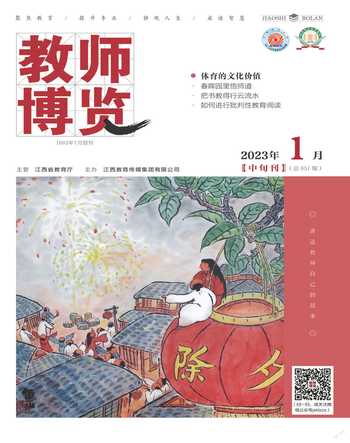吃苦是磨煉自己的利器
吳懷林


回顧自己的教育教學經歷,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很多,山村、鄉鎮、縣城、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省城南昌,每一個地方都留下了我摸爬滾打的印跡。其間,我除了擔任小學語文教師外,還兼任過班主任、年級組長、語文學科組長、大隊輔導員、教導處主任、政教處主任、副校長,酸甜苦辣咸,個中滋味,皆已品嘗。歲月無情,這一路走來,不知不覺已39載。39年來,有汗水,也有收獲,可謂幾多付出幾多喜,一路艱辛一路歌。然而,最難忘的,當數在農村教學的七年。
1983年8月,我18歲,從萬年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余江縣(2019年改為余江區)馬荃鄉霞山大隊小學(“大隊小學”現在都稱為“村完小”)。記得這所小學坐落在一個山岡上,大概有兩個籃球場那么大,東邊是敞開的(即校門),南北各有一排低矮的瓦房,分別為教室和教師宿舍,西邊有廚房和柴火間。踏進這所依偎在山溝里的山村小學,我便開始了我的教學生涯。剛滿18歲的我,和本地的5名“赤腳老師”(當地人對民辦教師的稱呼)承擔著全校的教育教學工作。學校每個年級各有一個班,共有5個班(當時小學為五年制),近300名學生。由于老師少,每個老師分擔的課量特別多。我承擔了三年級的語文、思想品德、音樂、美術、體育、自然等科目的教學工作,每周22節課,還兼任班主任和大隊輔導員。初為人師的我,簡直不堪重負,每天傍晚放學后便累癱了!
然而內心的孤寂更讓人難熬。每天放學后,我的5個同伴便比賽似的,騎著自行車猶如騎著“洪都125”(當時很時興騎的一款摩托車,只有少數有錢的村民才買得起),風馳電掣般地回家,空曠的校園只剩下我一個人。一到天黑,整個校園漆黑一片,唯有我獨守在約6平方米的斗室,面對一盞昏暗的煤油燈,聽著偶爾傳來的鳥鳴聲,倍感孤獨!夜深人靜,我陷入深思:該怎樣度過這難耐的時光?得過且過嗎?心有不甘啊!于是我決定沉下心來,努力工作,充實自己,開啟幸福的教育人生。
刻苦練字
做中學教師的父親一直叮囑我要好好練字。他說,老師有兩張臉,第一張是天生的臉,這張臉是爹媽給的,好看與否無法改變;第二張臉便是粉筆字,這張臉通過努力完全可以改變。父親說得確實有道理,寫一手漂亮的字是老師的基本功。于是,我決定在無聊時練毛筆字。
工作第一年是見習期,每月基本工資33.5元,副食品補貼5元,每月總收入38.5元。我買了一本柳體字帖,還有筆、墨、紙,一下子就花了近20元。每天晚上,我便在狹小的房間里練習毛筆字,讀帖、描摹、臨帖。堅持了一個學期,寫出的字還算剛勁、挺秀,有點兒“柳味”。雖然每月買紙和墨要花費10多元,可看到自己的字日漸長進,便毫不可惜!后來,我練字越發癡迷,下課練、飯后練,早上練、晚上練,連入睡前也在背帖,琢磨筆畫寫法和結構布局,食指還忍不住比畫著,若有頓悟,立馬翻身起床練習。房間的四面墻壁貼滿了我寫的毛筆字,小楷、中楷、大楷。“字怕掛”,空閑時,我便瞧瞧這些字,哪個字好,哪個字差,筆畫差在哪,結構錯在哪,一清二楚。這樣癡迷練習了近一年,我的字遒勁多了,“柳味”更濃。同事每每到我的房間,看到我的字,都夸贊不已。我聽了,心里喜滋滋的。
練字給我帶來了成功的愉悅。學年末,全鄉每個學校都要參加統考,共有14個大隊小學和一個鄉中心小學,統考成績要排名。為體現公平公正,采用滾動監考、統一評卷的方式。學校安排我到管坊大隊小學監考,我監考五年級。學生們看到是個瘦小且稚氣未脫的年輕老師監考,就肆無忌憚地交頭接耳,教室里鬧哄哄的。看到這情形,我便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寫下了個大大的“靜”字。學生們被這個漂亮的“靜”字給鎮住了,教室里頓時鴉雀無聲。一個字居然有如此奇效,我喜不自禁。
同事見我的字還好看,家里有結婚、蓋新房等喜事時,便買來紅紙和墨汁,要我寫喜慶的對聯。我的字派上用場了。為了寫好對聯,我絲毫不敢馬虎,先在廢舊報紙上反復練習,特別是自己覺得寫得不好的字,有時要寫幾十遍,直到自己滿意后,再在紅紙上一絲不茍地寫。慢慢地,我的字在這個方圓十來里的大隊有了點名氣。于是,村民們辦喜事時,紛紛請我寫對聯。這下可好了,我不僅不用自己買紙墨,免費練字,還滿足了村民的需求。更有意思的是,每一次寫對聯,純樸好客的村民都會邀請我們學校的老師喝喜酒。我們狠狠地改善了一下伙食,連校長都說,“我們學校的老師沾了懷林老師的光”。
練字也給我的教學帶來了便利。三年級學生開始學習寫作文,農村的孩子基礎差,覺得沒東西可寫,我決定采用范文引路的方法來指導。為此,我自費訂購了《小學生優秀作文》《小學生作文選刊》等雜志。每次作文指導前,我從這些雜志中找到合適的作文作為范文,用大白紙抄下來,在課堂上指導學生寫作文。“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學生根據范文聯想到自己的生活,有話可寫、有文可作,大大降低了寫作的難度。學年末,全鄉三年級統考時作文題目是《大公雞》,我班學生大多能根據自己平時的觀察,仿照范文,抓住大公雞的外形和生活習性來寫,寫得有條有理,表達了對大公雞的喜愛之情。由于作文成績特別突出,我班語文平均分名列全鄉第一,超過鄉中心小學兩分多。正因如此,第二學年,校長安排我教五年級語文。我同樣重視作文教學,尤其重視作文評改。每次評改前,我認真批改學生作文,從中選擇有代表性的作文,用大白紙抄下來,課堂上指導學生評改:優點在哪,缺點又在哪,怎樣修改。學生認真讀著毛筆抄寫的作文,凝神思索、各抒己見,慢慢地,評改作文的能力大大提高,作文水平也就不知不覺地提高了。全鄉畢業統考,我帶的班語文成績以微弱的優勢超過了鄉中心小學,名列第一,考取初中的學生占全班人數的70%以上(當時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初中要擇優選拔)。當時,擔任鄉中心小學畢業班語文教學的是頗有名氣的黃老師,他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點不服氣,因為我接的班四年級統考成績列全鄉倒數第一。第二年,我再次帶畢業班語文,接的班四年級語文成績還是列全鄉倒數第一。但我充滿信心,除了用同樣的方法指導學生評改作文外,幫助他們考前復習時也用上了自己的特長,把題目進行歸類,抄寫在大白紙上。這樣復習既集中了學生的注意力,又節省了教學時間,大大提高了復習效率。結果畢業統考時,我班成績又名列全鄉第一,初中升學率達80%以上,黃老師不得不服。
堅持家訪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有些家長沒有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小孩因放牛、做家務、帶弟弟妹妹等原因經常遲到甚至輟學。我想和家長溝通,便想了一個辦法,讓班上的其他學生轉交我寫的紙條給經常遲到或輟學的學生的家長,請家長來學校溝通,可家長根本不搭理。為此,晚飯后我便抽空到村里家訪,苦口婆心做家長的工作,請求家長減輕小孩的家務負擔,使小孩盡量不遲到,或讓輟學的小孩重返學校讀書。第一年教三年級時,我跑遍了整個大隊的12個村莊,有的家庭去一次沒有效果,還要家訪三四次。記得一個冬天的傍晚,我騎自行車去西鈄毛家家訪,迎面來了一輛拉柴火的手扶拖拉機,車斗的兩邊堆滿了柴火。我躲閃不及,被一側的柴火帶翻,栽倒在路邊的小溪里,頓時棉襖濕了,人凍得瑟瑟發抖。更險的是我旁邊有一口枯井,我的腦袋差點磕到井沿的麻石上。家訪20多次,家長被我的誠心打動了,我班輟學的6個孩子全部復學,遲到的孩子也少了許多。現在想來,我原來的家訪比現在的電話通知家長到學校來,效果要好十倍乃至百倍,可謂“一次老師家訪勝過十次家長校訪”。第二、第三年,我仍然堅持家訪。村民們看到我這么用心對待他們的子女,紛紛夸我是個好老師,親熱地叫我“懷林老師”。家長叫得多了,連學生也叫我“懷林老師”。直到現在,我回余江碰到家長、學生,他們還是親切地叫我“懷林老師”,叫得我心里熱乎乎的。
在大隊教書三年,我和村民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月十六開學,天天有家長請我吃晚飯,一直要吃到正月結束。雖然只是粗茶淡飯和自釀的谷酒,蘊含的卻是淳樸、濃郁的民風鄉情!
勤奮教書
因為我帶的班成績連續三年列全鄉第一,更因為從下學年開始,全縣要進行畢業統考,我如愿以償被調進了鄉中心小學,擔任五年級語文老師,兼任教導主任。至此,我便結束了大隊小學的教學生涯。
說實話,雖然已教了三年書,但我還是不懂備課。不會備課,我就“背”課。上課前,我捧著語文書,一遍一遍地讀,少則三五遍,多則十幾遍。讀的時候,我把自己想象成學生,想他們在讀的時候,有什么感覺、有什么問題,這些問題怎么解決。像《桂林山水》《鳥的天堂》《匆匆》等要求學生背誦的課文,我都能流利地背下來。所以我先背給學生聽,跟學生承諾:如果老師背錯了,學生不用背。結果每次我都贏了,學生心悅誠服,也下決心背下來。由于對課文爛熟于心,我上課基本不用看書,課文中的句子、詞語,張口就來,學生更是對我另眼相看。
為了教好書,我自費訂閱了《小學教學》《教學月刊》《小學語文教師》等刊物。深夜,我如饑似渴地拜讀,從中認識了很多名師,學到了很多很好的教學方法,如斯霞老師的隨文識字教學、于永正老師的“情趣教學”、賈志敏老師的特色作文教學等。這些教學方法我都嘗試著在課堂中運用,比我自己瞎琢磨好多了。記得有一期《小學教學》中介紹于永正老師采用“看著老師讀”,即表演朗讀的方式指導學生有感情地朗讀,大大激發了學生的朗讀興趣,學生讀得入情入境。于是在教學《少年閏土》中的“看瓜刺猹”這部分內容時,我也采用表演朗讀的方式,把當時的場景活靈活現地呈現在學生面前;然后師生、生生分角色表演朗讀,學生如臨其境,深刻地感受到了“看瓜刺猹”是多么有趣!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為方便日后查找教學資料,我專門設計了“摘抄記錄卡”,把雜志中實用的教育教學方法摘抄下來,年末分類裝訂成冊。三年來,我的摘抄卡有十多本。
在鄉中心小學,為了讓自己的班級在全縣畢業統考中取得好成績,我更加勤奮教書。臨近期末,我安排了一個月的考前復習,還經常給學生補課。那時根本沒有補課費這個概念,補課當然是無償的。學校有油印機,我便把小學的知識點進行歸類,自編復習資料,編好后,便在鋼板上用蠟紙一筆一畫地刻寫好,再一張一張人工油印。刻印資料并非易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緊握鐵制刻筆,每刻一筆,尖尖的鐵筆便在鋼板上發出“滋滋”的聲音;每刻寫十來分鐘,便手臂酸痛,要放下刻筆活動活動手指關節,刻寫好一張蠟紙最快也要兩個小時。更糟糕的是,有些蠟紙是發霉的,快要完工時,一不小心,蠟紙被鐵筆劃破了,那就得重新刻寫。人工油印就更麻煩,先要把刻好的蠟紙固定在油印機上,再用滾筒滾勻油墨(要是油墨干了,就要用煤油將油墨化開),最后緊握滾筒在油印機上從前往后均勻用力地推動,這樣便印好了一張油墨飄香的復習資料。然后翻過印好的這張紙,再涂上油墨,推動滾筒,如此循環往復,一張一張、小心翼翼地印。大約一個小時,我便印好了50來張復習資料,而緊握滾筒的虎口不知不覺起了個大血泡。就這樣,馬不停蹄、日夜奮戰,刻了印、印了刻,血泡長了又破、破了又長,一套套20來張的復習資料終于大功告成。我把這套復習資料整理、裝訂好分發給學生,比原先用白紙抄復習題效果好很多,學生可以提前做題。上課時,學生對照做了的復習題,小組討論并自行訂正,特別難的題目再由老師講解。課后,我再布置學生做資料上相應的題目消化鞏固。這樣下來,學生復習效率大大提高。
老天眷顧勤奮人。在鄉中心小學四年,我連續帶了四屆小學畢業班,畢業統考語文成績在全縣200多個班(含縣城一小、二小)排名均進入了前五名。1990年畢業統考,我班語文成績在全縣排名第二,平均分比縣城一小最好的班僅少0.1分。因此,我在全縣出名了。1990年教師節前,我被評為“市優秀班主任”(當時全縣農村學校2個名額)“市優秀青年骨干教師”,在鷹潭市的兩縣一區做了三天共6場先進事跡巡回報告,聽講老師累計超兩萬人次。就這樣,我調入了余江最好的小學——余江縣第一小學。
我在農村教書7年,回過頭來,并不覺得苦,因為吃苦是磨煉自己的利器,讓我成長得更好。的確,成長會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疼痛,不計后果的那段,叫作青春。成長中,我們總是要經歷深刻而沉痛的磨煉,才能一步一步,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作者單位:江西省南昌市紅谷灘區教師發展中心)
(插圖:羅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