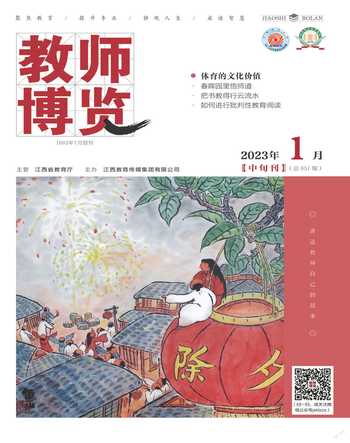體育的文化價值
李慶明
體育意義上的身體生命從根本上講是生物性的。正如貝塔朗菲所言,人的生命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所以,理解體育,也應當高度重視和全面揭示它的文化意蘊。盡管我們必須承認人的生命文化和體育文化的生物學基礎,但是,如果認為生命的文化基因、體育的文化價值是伴隨體育活動自發地得到實現的,那就錯了。人的生物機體中蘊藏的文化元素只是一種遺傳基因,而一種潛在的、沉睡著的力量,需要我們通過全面持久的教育實踐加以挖掘、激活和喚醒,否則它永遠只是生命機體的一種可能性,隱而不顯,甚至會因此而泯滅。那樣的體育就淪為無意義、無價值的純知識與技巧,甚至是與“馴獸”無異的粗暴訓練了。
從這個意義上看,西方的生命哲學倒是可以為我們倡導的新體育提供某種借鑒。例如,狄爾泰就認為生命具有某種非理性的永恒活力、創造沖動或客觀精神。柏格森認為生命是川流不息的“綿延”或“意識流”,它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覺加以把握。所謂“非理性”,作為理性(科學、技術)的對應物,無非就是與情感、道德、藝術、信仰等相關的東西。體育在任何時候都需要這些非理性的精神補充、支持甚至引領。梅洛-龐蒂的現象學哲學也認為:身體作為生命存在的本質,它的可交流性和開放性是人與人共存的基礎,并且是人類走向和平的希望。奧林匹克精神宣揚的不正是這種身體生命的哲學嗎?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身心一元論的生命哲學更為深刻地揭示了身體與情感、欲念、性靈、意志之間的內在關聯。古人所謂“反身而誠”“止至善者,安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所有這些,雖然并非完全在談論體育,但對于我們思考體育的文化價值,通過體育培養健全的文化人格,無疑可以提供深刻的啟迪。
體育的文化價值表現在許多方面,撮其要者,大概有以下幾點。
一、體育文化的民族品格
文化最初的醞釀與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例如,海洋環境和陸地環境、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孕育的文化無疑存在很大的差異,體育文化也不例外。以體育運動為例,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之所以成為世界體育運動的源頭,與它很早就興起的海上文明尤其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地中海出現的邁錫尼文明有關。它是希臘文明的早期形態,這時就已經出現斗牛、海上搏擊、賽跑、拳擊等體育項目萌芽。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臘的邁錫尼文明衰敗、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多利亞人的文明,他們就是后來斯巴達城邦居民的祖先,驍勇善戰,威武不屈,構成希臘文明中軍事與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健壯而又野蠻的希臘人用復仇式的討伐徹底征服了克里特人,充分顯示了他們身體的雄偉力量。后來的英雄崇拜、力量崇拜和體育競技都是為了紀念戰爭的偉大勝利,希臘體育從此發端。由此可見,希臘體育之所以發達,與海上民族、游牧民族的天性有一定關系。但這還不能解釋它的全部。希臘多山、臨海的地理環境驅使居民發展航海業,與東方的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地區之間開展頻繁的商貿活動。人口的流動瓦解了人與人之間凝固的血緣紐帶關系,摧毀了內陸民族容易滋長的等級制度,孵化出與商貿相伴相生的平等、公平、民主觀念與制度。正是這一制度環境,催生了希臘的奧林匹克競技運動,并孕育了它公平競爭的文化內涵。
我國古代與邁錫尼文明相對應的文明是商代文明,商代文明的崛起也與游牧民族有關。它的早期是典型的游牧社會,畜牧業發達,商業繁榮,武力強盛,絲毫不遜希臘,按理說也能為希臘式的競技體育創造條件。當古希臘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的時候(公元前776年),我國差不多進入“春秋”時期。這一時期尚武任俠之風空前高漲,軍事體育如“射”“御”等在“六藝”課程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們卻無法發展成為公平競爭的希臘式競技體育。原因就在于,從商朝開始的血緣紐帶關系從來就沒有被解構過。它是數千年來中國宗法等級制社會與文化的根基。當一個游牧社會走向日漸成熟的農耕社會,由沿海一帶走向內陸平原,血緣紐帶關系更加牢不可破,等級制度愈加森嚴,影響至深至遠,這樣就很難發展起奧林匹克式的體育運動了!
當然,這不是說,我國古代就沒有體育運動。農耕社會也會造就其獨特的體育運動文化。雖然在日漸文弱的儒家和本來就崇尚“守柔”的道家思想長久影響下,我們的傳統體育總體崇尚和氣、貴于頤養、鐘情修身,甚至還存在“蔑視體格上的勇猛,蔑視體育運動”的嚴重缺陷,但畢竟也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導引(如五禽戲、八段錦等)、氣功(如吐納功、靜功、動功、導引功、站樁功等)、太極(如楊式太極、吳式太極、武式太極、和式太極、孫式太極等)、武術(包括刀劍、摔跤、弓弩、石鎖、馬術等)等傳統體育運動,以及琳瑯滿目的民間體育游戲如斗百草、放風箏、騎竹馬、蕩秋千、捉迷藏、斗蟋蟀,還有跳房、跳百索、拔河、賽龍舟、摔跤、下土棋等等,它們是我們不能忽略和拋棄的體育文化寶藏。
再說,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本來就具有開放、包容的一面,古代胡漢之間、中西之間曾發生過包括體育在內的廣泛的文化交流。隨著交流的深入,體育文化的民族性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內涵與形態,民族性的邊界也逐漸模糊。例如,在漢唐時代的絲綢之路上,就留下包括弓箭、馬術、蹴鞠、博弈、武術、導引、角抵、百戲甚至與現代競走、滑雪體育運動有直接聯系的大量體育文化交流的文物。考古學家們在絲綢之路的石窟、塑像、簡牘中發現了大量有關醫療保健的資料,包括佛教心理療法、瑜伽修持、辟谷、導引、吐納、優生、環境衛生、個人衛生等。進入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的時代,不同民族的體育文化更是加入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交流,越來越多地走進世界體育的大家庭。例如,日本的空手道、韓國的跆拳道、泰國的泰拳,就引入了現代標準機制,現代化較為成功。2020年1月8日,武術被列入第四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隨著它的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其被列入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增加。但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即使體育的現代化、國際化程度再高,也不會、不應、不可能消弭體育文化異彩紛呈的民族品格,哪怕是一個蕞爾小國歷史悠久卻不入流的體育項目!
二、體育文化的人文之維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與自然(“天文”)相對,突出的是人之為人的人性教化。肇始于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強調的也是人性教育。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盡管內涵各異,但體育一開始就高度注重它全面化育人性的人文價值。尤其在西方,古希臘時期就開啟了世界性的奧林匹克運動,更建立并完善了一整套廣泛涉及體育智慧、體育倫理、體育審美、體育政治、體育經濟、體育社會化、體育現代化的人文文化。在我看來,它涵蓋了衛生、強身、性愛、死亡等所有身體生命的領域。如何在這些領域實施人文教化,都是值得我們深思和謀劃的。這里重點強調一下奧林匹克的人文精神追求。
提及奧林匹克精神,人們說得比較多的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這一口號體現了奧林匹克運動在展現人的身體生命能量方面的訴求,它表現了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的奧林匹克競技運動對于體格力量與健康的崇尚。但是,它并非奧林匹克精神人文內涵的完整表達。既然是競技運動,理所當然地要追求“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它體現著古希臘人競爭與奮進意識,也許還是希臘人將城邦之間經常兵戎相見的血腥戰爭轉化為形式化、游戲化、藝術化的“體育戰爭”的一種境界升華。但戰事還在繼續,體育又令人神往,怎么辦呢?于是,公元前776年召開第一屆奧運會前,古希臘三個文明的城邦國家達成協議,舉辦奧運會期間,停止一切戰爭。這就是著名的“奧林匹克神圣休戰”。正是“神圣休戰”賦予了奧林匹克運動遠遠超越身體競技的希臘精神內涵:捍衛生命、捍衛自由、捍衛獨立、捍衛團結、捍衛公平。它使奧運會成為和平與友誼的盛會,并對現代奧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不會忘記,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之父顧拜旦,即奧林匹克精神的倡導者,他年輕時代就關注研究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揣摩它的內在精神。在《體育頌》和《奧林匹克精神》中,顧拜旦把體育看成是美麗、藝術、正義、勇敢、榮譽、樂趣、活力、進步與和平的化身,并表達了通過復興奧林匹克運動改革教育進而促進青少年全面均衡協調發展的初衷。他認為奧林匹克的本質就是為了教育人:“古希臘人組織競賽活動,不僅為了鍛煉體格和顯示一種廉價的壯觀場面,更是為了教育人。”第一部《奧林匹克憲章》是由顧拜旦親自擬定的,它在1894年巴黎舉行的國際體育代表大會獲得批準;同年6月23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應運而生。《奧林匹克憲章》對奧林匹克精神做出這樣的表述:相互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百余年來,《奧林匹克憲章》雖經多次修改和補充,但顧拜旦所提出的奧林匹克精神始終未變。2021年7月20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138次全會投票表決,同意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提議的在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之后加入“更團結”,使之合成奧林匹克的新格言: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旨在表明,基于奧林匹克運動以及全人類應對共同危機,我們更加需要團結精神,團結是實現更快、更高、更強的前提,也是它們的歸宿。這一新格言可以視為對奧林匹克精神的一個很好的注腳。
隨著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化,它已經成為跨越地域、國家、文化、等級的大眾狂歡,但奧林匹克運動的過度商業化、極端政治化、職業化腐敗、興奮劑丑聞、濫用納稅人金錢謀求獎牌與利益等問題嚴重侵蝕奧林匹克精神,全球化的諸多重大危機也在影響奧林匹克精神的延續。也許,我們還需要一場復興奧林匹克的革命,恢復并繼續弘揚奧林匹克精神,使奧林匹克運動不僅追求更高、更快、更強,而且也追求更團結、更真誠、更公正,這樣才更加貼近奧林匹克精神,使之真正擔當起促進人性健全和人類和睦共處的神圣使命!
三、體育文化的游戲精神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英語為Olympic Games,Games不僅是運動,也是游戲。正是這個Olympic Games,一語道明體育運動和游戲之間的內在聯系。
盡管游戲的表現形態不一,但無論是人類、民族還是個體,它們轉變成文明的游戲,都經歷了循環往復的艱難過程。這里仍以競技體育為例。
競技運動脫胎于古老的戰爭,起初都非常殘暴。古希臘神話中的與希臘體育運動有關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傳說,也許就隱含了競技運動最初的暴力基因。赫拉克勒斯天生力大無窮,在搖籃里就曾殺死過兩條巨蛇,他一生都在用暴力和傷害滿足自己的欲望,曾完成過12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死后升入奧林匹斯山,被宙斯封為大力神,參與了奧林匹斯諸神與癸干忒斯的戰爭,并取得勝利。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本身就是為了紀念荷馬時代希臘人贏得特洛伊戰爭,不過,從此開啟的自由民主的希臘文明時代并沒有讓野蠻的戰爭在奧運會上演,而是將實體戰爭轉化為一種充滿公平競爭的“形式戰爭”,也即自由游戲。但到了古羅馬時代,好戰而嗜血的古羅馬人恢復了殘酷的暴力競技。角斗士游戲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據說,角斗起源于古希臘祭奠英勇戰士的喪葬人祭習俗,到了古羅馬時代成為達官貴人隆重葬禮游戲(這屬于死亡游戲)的組成部分,目的是為死者開路。因為角斗,死者的靈魂將在人血中凈化,與此同時,角斗還可以展示為羅馬帶來光榮的元素——力量、勇氣和決心。“彰顯戰爭中的這些美德,有助于激勵年輕人追隨先輩,博取人生榮譽。”角斗表演由死者家屬的私人贊助變為官方支持舉辦,受到熱烈追捧,風靡古羅馬。凡是看過電影《斯巴達克斯》《角斗士》的人都會看到這樣的場景:角斗士們手持短劍、盾牌或其他武器,為了取悅各個階層的觀眾,在圓形劇場進行搏殺,直到一方當場斃命,或雙方同歸于盡,觀眾擊掌相慶。不過這種慘烈表演一開始也受到批評與譴責。古羅馬著名學者西塞羅和塞涅卡就加入其中,盡管他們的批評是溫和的,甚至還承認角斗表演的教育價值,但不少有影響的希臘作家認為角斗表演違背了古希臘體育的高貴精神。隨著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根除角斗表演的一紙敕令頒布,這一血腥的表演開始走下坡路,角斗表演更多由斗獸表演代替。公元393年,角斗表演成為重點打擊對象。至此,兇狠的角斗表演終于壽終正寢。
但是,人們對于暴力表演的迷戀卻沒有到此結束,而是改換門庭,變著花樣滿足自己的欲望,有時還會出現血淋淋的實體表演。例如流行于歐洲中世紀的生死決斗,早期歐洲的重犯公判儀式,17世紀在荷蘭依然廣受歡迎的斗獸(斗熊、斗牛、斗狗)表演……盡管后來對競技制訂了越來越嚴格的游戲規則乃至出臺禁令,但人類還是無法徹底分割體育暴力行兇與體育暴力美學之間的界限。這些在摔跤、拳擊、足球、橄欖球、斗牛等競賽中出現的眾多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中都能找到證明。法國學者喬治·維加雷洛在他的《從古老的游戲到體育表演——一個神話的誕生》一書中提到過“兩種體育暴力”,一種是顧拜旦體育理想中受到規則限制帶來美感快樂的現代體育“暴力”,它“既抑制了暴力又給人以使用暴力的幻覺,它幾乎始終對危險動作實施著控制,成為一種想象與現實相結合的運動”;但是,與現代體育相伴隨的另一種暴力如比賽暴力、對抗暴力、動作暴力、流氓球迷滋事、球場踩踏事件等層出不窮,遠比過去強烈和粗暴。為此,維加雷洛不無沮喪地提到這種“繼血腥社會之后的自由社會所導致的”體育暴力怪圈:“體育表現出了兩面性:它既是一塊規則明確的領域,暴力帶有表演的性質并受到控制,又是一塊極易引起隱蔽的憤怒的領域。”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育暴力如今越來越不可分離。菲克·梅杰也告訴我們,雖然現代大眾對過度張揚暴力普遍心存反感,也贊成對暴力表演實施嚴格的限制,但對暴力的審美迷戀卻絲毫不減。他把這歸結為揮之不去的古羅馬情結的延續。在西方社會,我們仍然能看到種種殘酷行為跟古羅馬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盡管形式載體置換,但難以言喻的殘酷仍然形影不離。血腥戰爭、黑幫爭斗、街頭暴力、謀殺搶劫、施虐受虐——這就是我們的影視題材。過去半個世紀,我們究竟拍攝了多少暴力電影?每時每刻,總有電視頻道在播放以暴力殺人為主題的電視劇。文學藝術以及虛擬化的電子游戲對于暴力的追捧不論出于娛樂還是教育的動機,都在不斷打破想象與現實的藩籬,誘發越來越多的現實暴力事件。這是我們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面臨的既渴望游戲又容易被游戲異化的二律背反。對此,我在《“風乎舞雩,詠而歸”——游戲哲學暢想》中做過比較詳細的分析,并用格斯·范·桑特執導的獲第5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的電影《大象》中關于暴力游戲與校園喋血慘案之間聯系的隱喻,表達了我的擔憂。這也許是我們最為迫切需要面對又最為棘手的教育問題。
再說說中國體育的游戲精神。在長達550年的春秋戰國時期,武風昌盛,雖然興起了“擊技”“競技”“比武”“賽會”等競技性的運動,卻沒有發展為大體同時期的古希臘Olympic Games(游戲)。李力研曾借助李澤厚提出的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屬性給出了解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種過于‘實用的理性精神。這種過于強大的理性精神,極大地抑制了中國人的‘游戲意識的表現。”的確,那時的武藝競技賽會由于受當時危機四伏、戰事頻仍的社會現實的影響,講究的是實用的理性權衡,而非浪漫的游戲情調,崇尚真刀真槍、你死我活,很像羅馬時期的角斗,顯得異常殘酷,完全不同于古希臘的奧林匹克游戲。這種實用理性文化在此后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綿延不絕,自然很難成就希臘式的體育游戲精神了!這也是當今中國體育文化建設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當然,如前所說,受儒道兩家守柔思想影響的另一類民間體育游戲卻發展繁榮起來,其中有不少好玩的體育游戲可以在今天發揚光大。
關于游戲的哲學本質,我曾在《“風乎舞雩,詠而歸”——游戲哲學暢想》一文中指出,游戲不僅是兒童的天性,而且如胡伊青加所說,也是人的本性——人即游戲者。游戲不僅是人的本性的表現,而且如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所說,也是人的全面完整本性的表現:“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游戲的本質是自由的、審美的,“游戲與自由的關系,是一種深刻的表演關系,就是說,游戲是人的自由的表演,而且是自由的喜劇性表演”。這就意味著當我們進入游戲狀態,就能全面自由而超然物外(也即審美)地把握一切,包括體育。一旦人的充滿人性快樂的自由“活動”,如馬克思說的那樣淪為不自由的異化“勞動”,自由的游戲與快樂就蕩然無存,人只會“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悵然若失”。體育也是如此,一旦丟失了游戲精神,我們就沒有了希臘奧林匹克運動那樣的自由、超然和浪漫,很容易陷入實用主義,將體育與現實生活聯系得過于緊密。我曾以米盧接手中國足球的大起大落為例,批評了體育游戲精神的失落。足球本是身體游戲,我們卻過分夸大了它的社會功能。我們既要最大限度地為體育注入游戲精神,又要避免陷入西方體育游戲的二律背反,任務自然就更加艱巨了!
四、體育文化的終極追求
體育文化的終極追求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人的自然化。”
好友李力研生前很早就敏銳地察覺到體育與人的自然化的關系。他認為,體育說到底是一種防止由于伴隨文明的快速演進而帶來的人種退化和機能衰竭的活動,是人類感性如何從自身理性的重壓下獲得解放的努力實踐。“在‘自然的人化過程中,只有‘人的自然化才能阻止人類的物種退化。體育的本質就是‘人的自然化。”這一主張實際上來自李澤厚先生對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獨特發掘。我非常認同李澤厚和李力研對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然化思想的基本理解,但也覺得有必要從我倡導的田園教育哲學的角度再做一點補充。
我越來越確信,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全新形態的自然主義。馬克思曾把共產主義表述為“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這就是田園教育的哲學根基。它可以理解為一種解決工業文明造成人與自然以及其他嚴重對立的新“天人合一”主張,內涵非常豐富。在這個總體主張的語境里,馬克思提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命題。在他看來,“人的自然化”與“自然的人化”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個命題的兩個方面,是歷史而辯證地統一的。
“自然的人化”是“人的自然化”的絕對前提。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在的自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馬克思所說的“人自身的自然”,也即我們一直強調的人的身體的生物生命。“自然的人化”意味著全部自然界與世界歷史“對人說來的生成”,也意味著讓人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這里顯然是汲取了康德關于“自然向人生成”“人是自然的最后的目的”的思想。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的人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改造外在自然,打下人的生命力量的印記,實現“外在自然的人化”,使之成為人的“無機的身體”,進而為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貢獻力量;另一方面是改造人自身的自然,激活和喚醒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力量”,不斷豐富和壯大自身的生命力量,并超越生物族類的限制,彰顯無限發展的可能性,進而實現“人自身自然的人化”。毫無疑問,人類的教育尤其是體育,不管是衛生、強身、軍體、性愛還是死亡的教育,在促進人自身的自然的改良與變革中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說,體育的一個崇高使命,就是促進“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
但是,單純促進“人自身的自然的人化”是不夠的。體育的終極目標或最高境界,是在“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的基礎上再一次超越自身,實現“人的自然化”。
這意味著,體育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相伴隨,促使業已高度優化的人的生命機體重返自然。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返外在自然,將體育與人的生命機體視為值得永遠依靠的“無機的身體”和“精神的食糧”,二者不再是敵對的、掠奪性的、相互報復的“擴張主義”關系,而是“人同自然的和解”的“田園主義”關系;二是重返更高層次的人自身的自然,人自身的小宇宙與身外的大宇宙冥合如一,進而完成馬克思所說的自身的“人的自然主義”,實現另一種意義上的“自然界復活”。這時,人就成為棲居于自然化世界的人,也即我所謂“田園世界”中的“自然化的人”。從體育的角度而言,“自然化的人”彰顯出來的應該是“力”與“美”、“武”與“文”、“剛”與“柔”、“勇”與“智”的交融統一。培育這種“自然化的人”必將成為未來教育尤其是未來體育的最高使命。
最后,還想特別提一提馬克思當年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說,人類的“異化勞動”一旦得到歷史性的揚棄,重新回歸合乎人類本性的狀態,成為“自由勞動”或“自由活動”,就具有了體育鍛煉的性質。“由于勞動要求實際動手和自由活動,就像在農業中那樣,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身體鍛煉。”這個說法常被視為一種過于浪漫的觀念。我倒不這樣看,反而覺得它隱含了馬克思對于未來人類活動回到“身體”本體又抵達更高境界的洞見。如果一切活動都升華為自由的“身體鍛煉”,那么是否意味著一切教育也都從根本上歸于一種意義特殊的體育呢?
我自小愛藝術,尤其愛跳舞,每當踏歌起舞,四肢翩翩,就覺得生命在凌空飛揚。所以,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閱讀藹理斯研究藝術的著作《生命之舞》時,就覺得書名特別貼切。不過,我現在不完全這樣看了,我認為用“生命之舞”來揭示體育的本性才是最貼切的。因為身體是生命的載體,也是生命運動的舞臺,體育的世界上演的就是宣泄活力、激揚意氣、綻放靈性的“生命之舞”。
新的生命之舞——新體育將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吸引人們,并全面提升人的生命質量,因為導演這場生命之舞的,是一種全新的機體生命觀——生物學世界觀。有人曾聲稱,貝塔朗菲提出的這一觀念是“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如果這是確切的話,那么,我們倡導的新體育很樂意為這場“文明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做一點添磚加瓦的微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