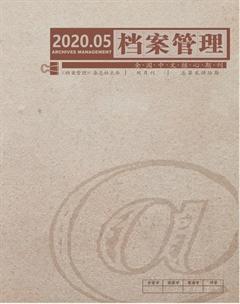文化傳承視角下革命歷史檔案的開發利用
王冰麗
摘? 要:本文以革命歷史檔案為研究對象,從文化傳承角度分析其價值與當前開發利用的現狀,并提出拓展延伸利用的建議。
關鍵詞:文化傳承;革命歷史檔案;教育意義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rchiv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its value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expanding and extending utilization.
Keywords: Cultural inheritanc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rchive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1 革命歷史檔案文化傳承的具體表現
1.1 弘揚了優良的革命文化。革命歷史檔案中蘊含有艱苦樸素、百折不撓、堅定的革命信念等一些崇高的革命精神,還培育出了延續至今的優良革命傳統。[1]這些記錄作為我們優秀的精神食糧,深入挖掘其內涵,并結合時代特征賦予其新的內涵,則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前進道路上的燈塔。
1.2 推動了地方的歷史文化建設。目前,許多地區十分重視對革命歷史檔案的開發。深入挖掘某一地方的革命事跡和英雄人物,并對事件背后的革命精神進一步拓展,能夠成為當地文化創新的素材。比如電影《西柏坡》,電視劇《井岡山》《延安頌》等,都是根據革命歷史檔案記載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實際情況,再結合新時期的時代精神創作的紅色影視劇。通過影視劇的傳播,增加了革命圣地的歷史厚重感和文化魅力。[2]
1.3 提升了紅色旅游的文化性。革命歷史檔案是開展紅色旅游的基礎條件。紅色旅游和革命歷史檔案在時間、主體上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內容上則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革命歷史檔案和紅色旅游在信息和空間上是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3]革命歷史檔案和紅色旅游高度融合后,許多地方不僅能夠充分利用本地區的自然環境和革命遺跡開發旅游業,還能夠讓旅游者深度體驗革命精神,借助革命遺跡開展形式多樣的檔案開發活動。
2 文化傳承視角下革命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現狀
2.1 檔案展覽,加強宣傳。革命歷史檔案中除了紙質檔案外,還有很多實物檔案。許多黨史機構和檔案館經常聯合舉辦革命歷史檔案的展覽,讓廣大用戶可以近距離查看這些珍貴的檔案,以此來加強對革命歷史檔案的宣傳。
2.2 檔案編研,出版發行。早期的革命歷史檔案都是在戰火中保存下來的,缺少存儲檔案的條件,而且還面臨經常轉運的問題,不少已出現內容不清晰等現象,這對革命歷史檔案的利用造成了影響。要使革命歷史檔案發揮其價值,則需要對原始檔案進行加工。有的檔案機構組織專業人員對原始革命歷史檔案進行編研,從而將那些分散、字跡不清的檔案進行加工,以現代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將革命歷史檔案信息加以整理,再出版發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真實的革命歷史。[4]
2.3 建立紅色旅游基地。革命歷史檔案中有井岡山、瑞金、紅安、延安、西柏坡等地方情況記錄,在這些地區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也出現過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和英雄人物。隨著檔案的解密,許多革命事跡都逐漸為人們所熟知。[5]當地也充分利用這些紅色資源,建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紅色旅游經典,不僅宣傳了革命歷史檔案中的紅色故事,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
3 革命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的拓展與延伸
第一,利用革命歷史檔案培養當代大學生愛國主義情懷。要將革命歷史帶進思政課堂,教育廣大的大學生。思政課是大學課堂的重要內容。大學階段是學生從學校踏入社會的過渡階段,同時也是人一生身體、精神所處的黃金時間段,更是人的價值觀、是非觀形成的最重要階段。[6]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大學生自身的價值觀和對祖國的情懷會直接影響社會主義事業。因此,高校的思政課堂承擔著重要的使命,需要從精神上改造他們,使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育他們愛國主義精神。但是,當前的高校思政課堂更多是講解理論,但這些理論知識又無法落地,所以學生在課堂上會覺得枯燥無味,思政課也沒有發揮實際作用,更無法從思想上改造當代大學生。[7]當前大學開設的思政課較多,而許多課程都與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相關聯。革命歷史檔案記錄的是革命發展歷程,其中有許多生動的事件和鮮活的個體,將其融入思政課堂則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8]
第二,將其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促進人民群眾思想的升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體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而革命歷史檔案則是圍繞這一體認展示給人們的最生動教材。[9]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規定的內容是對革命傳統的繼承與發展,可歌可泣的中國革命斗爭史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畫卷。人們通過接觸革命歷史檔案,實現更多的精神交流,使得精神境界得到升華。
革命歷史檔案的存在將現代人和中國近代革命斗爭史緊緊聯系在一起,為廣大民眾搭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的平臺,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建設的過程中表現出直接的效應性。[10]
第三,要為廣大民眾提供文化產品,實現對大眾消費傾向的正確引領。文化產品是表現出創意性的一種藝術產品,而文化產品表現出來的最好的狀態則是真、善、美的統一。在這三個要素之中,真是基礎,也就是用事實說話,客觀而真實。革命歷史檔案的真實性特性賦予當代文化產品創作者更強的自信心。隨著革命歷史檔案的進一步解封,越來越多的革命事件、革命人物被人們所熟知,而國家文化部門和檔案部門也經常聯合創作,充分利用革命歷史檔案資源,創作了一大批革命主題的影視作品,向廣大民眾推送了一大批精彩的文化產品。
*課題基金:本文系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新時代應用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班授課,小班研討 教學模式構建與實踐研究”的研究成果,(課題編號:2019SJGLX039)。
參考文獻:
[1]黃婷婷.文化旅游視角下廣西百色市紅色檔案開發利用研究[D].廣西民族大學,2019:2.
[2]葉麗群.紅色旅游背景下革命歷史檔案開發利用問題及對策[J].辦公室業務,2019(12): 85-86.
[3]夏琳芳,李鋼.關于挖掘和豐富紅色檔案資源的思考——黃岡市開展紅色檔案資源建設的做法[J].湖北檔案,2014(07): 26-28.
[4]黃明鰻.論口述類紅色檔案資源的傳承性保護——以百色起義紅色歌謠為例[J].山西檔案,2016(01): 85-87.
[5]陳昕燕.沂蒙紅色檔案資源的當代價值與利用研究[D].山東大學,2016:19-23.
[6]張清改.用紅色檔案資源激活黨員干部正能量芻議——基于信陽市紅色檔案資源的分析[J].延邊黨校學報,2017(01): 82-84.
[7]陳愚.從檔案文獻編纂看中國檔案文化的若干特點[J].廣西社會科學,2004(04): 194-195.
[8]孫曉形,薛梅.深入挖掘革命歷史檔案豐富愛國主義教育內涵[J].辦公室業務,2019(01): 53-54.
[9]陳洪誠.革命歷史檔案文化價值與民族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路徑研究——以百色館校合作為例[J].蘭臺內外,2019(06): 6-7.
[10]周建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角下地方特色檔案建設的重新思考[J].檔案學通訊,2014(03): 50-53.
(作者單位:平頂山學院 來稿日期:2020-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