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國企改革有何不同?
馬國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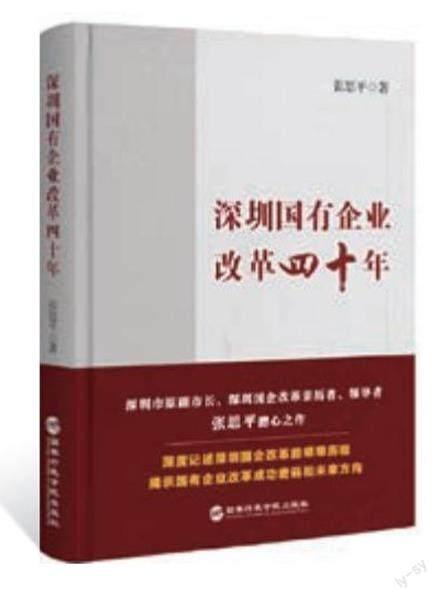
每次到深圳,我都喜歡登上蓮花山,俯瞰夜色中的鵬城。高樓林立、燈光璀璨,煥發著一座現代化城市的噴薄生命力。難以想象40多年前,這里竟然只是一座小漁村。可是,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這里就聳立起一座幾乎可以與香港媲美的國際大都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在《變革中國》一書里說,“中國的市場經濟道路是一個非凡的、動人的故事。”深圳篳路藍縷,砥礪前行,成為這個故事里最富有傳奇性的章節。隨著時光流逝,深圳的傳奇似乎也在漸漸淡去。但是,《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再次將那段歲月拉入人們視野,促使讀者在回顧中總結歷史,在反思中展望未來。
1981年8月,也就是特區建立第二年,深圳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機構改革,撤銷一批行業主管局,將它們改為獨立的公司。隨后,工業、商貿、建筑、城市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文化等領域,更多國有企業相繼建立。在20世紀80年代,除了工業領域,國有企業在深圳所有制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
不過,和國內其他地區的國有企業不同,深圳國有企業是適應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新型國企”,它們絕大多數處于競爭性領域,能夠獨立經營,具有適應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因此能夠迅速發展。不到十年時間,深圳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為200萬人口的現代化新城,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奇跡”。正如《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一書所說,“從整體上看,國有企業在特區初創時期起到了支撐和主體作用”。
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一起,共同支撐深圳的高速增長。深圳國有企業的一系列大膽探索,從股份制改革到現代企業制度建立,都為全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豐富經驗,起到了破冰的作用。
然而,從1995年開始,深圳的國有企業發展也出現了停滯,乃至陷入困境。要知道,20世紀90年代正是再次創造“深圳奇跡”的時期,為什么國有企業卻陷入困境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在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民營企業崛起,外資企業大量涌入,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在布局結構、體制機制、內部管理等方面的不足日益顯現。特別是處于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不但沒有“做大做強”,反而經營困難,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如果站在2000年的歷史時點上,俯視整個深圳就會發現,這個新興城市和20世紀80年代已經完全不同,呈現出嶄新的氣質。雖然遭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它卻頑強地保持著15%的高發展速度。可是,國有企業卻在風險集中爆發,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相當多國有企業處于破產關閉的邊緣,成為影響深圳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深圳的國有企業向何處去?
2003年,49歲的張思平擔任深圳市副市長,分管深圳的國有企業。壓在他肩頭的一大重任,就是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深圳以來,張思平已經在這里工作十多年,對于深圳國有企業非常熟悉。他看到了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也深知國有企業的弊端。在擔任深圳體改辦主任和廣東省體改委主任的八年間,他直接參與和組織了一系列國有企業改革實踐,積累了豐富的改革經驗。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確立,舊有的改革模式難以持續,國有企業改革迫切需要一次重大突破。
1999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為深圳國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圳市在此問題上也形成了共識,關鍵就在于如何實施。
作為這項重大改革的直接領導者,張思平精心組織實施了深圳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經過三年的艱難努力,克服了無數的困難,到2005年底基本完成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階段性任務。經過多年的艱難探索,深圳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也就是在經濟社會和城市發展中發揮保障作用。
從2003年起,深圳的經濟增速再度攀升到新的高位,崛起為全國領先的特大城市。
國有經濟布局調整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改革,也是政府職能的自我革命。因此,作為改革的操盤手之一,張思平在《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這本書里,用了近100頁的篇幅,記錄了這場影響深遠的改革過程。
在完成國有經濟布局調整之后,深圳又以市場化為導向,對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進行內部機制改造,實現了國有企業與市場機制的接軌,企業效率與活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自己具有優勢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里,深圳國有企業通過公平競爭,成長為大產業集團,效率、服務水平、競爭力等方面在全國都處于領先水平,乃至成為領軍企業。這些企業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市場為導向,發揮為高科技、現代物流業引導和服務的功能,促進了深圳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
在過去的40年里,深圳國有企業創造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功實踐案例,探索出一套改革發展的制度模式,不但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為全國國有企業提供了足資借鑒的改革發展路徑。
近年來,針對學者熱衷于 “熱點問題”的現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多次呼吁經濟學界“研究基本問題”。顯然,國有企業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大基本問題。
即使在深圳這樣的改革前沿,國有企業也在問題—改革—新問題—新改革中曲折前進,迄今未有窮期。作為見證者與參與者,張思平以60余萬字記錄了深圳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進程。《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的更大意義在于,為未來深圳乃至全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鏡鑒。

深圳福田區CBD城wFDQfUfY6MND89cnabanJyqjaLYjbX7qmtU08KP//Tc=市中軸線。圖/視覺中國
恩格斯曾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遺憾的是,中國學界的一大缺陷,就是輕視甚至蔑視理論思維,因此很難透過變動不居的現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四十年》這本書里,張思平作為一線的改革者,卻展現出驚人的理論水平,令人頗感意外。
其實不奇怪,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之時,張思平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實經濟系。當時他的老師們,特別是著名經濟學家馬洪、蔣一葦等人,已經開始探索放權讓利、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并對20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作出過重要貢獻。張思平深受這些老師的影響,幾十年來一直學習、追蹤、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因此他對國企改革的歷程有深刻的理解和系統的理論思考。難能可貴的是,張思平在深圳數十年的工作中,一直在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豐富理論,相得益彰,相互促進,既成就了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也成就了一位優秀的理論家。
在退休以后,張思平創辦民間研究機構“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繼續關注和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在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的兩年里,他回顧深圳國企改革的歷程,每日奮筆疾書,完成了皇皇巨著。在該書的后記里,張思平這樣寫道:“在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一個個人能夠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有幸的是,自己既能親歷這場歷史變革,又能在晚年為后人留下這場變革的一些記錄和歷史資料。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深圳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事業來講,我能夠做的事已經做完了。”
這段話樸實無華,卻令人感動。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為改革者,張思平守住了自己的“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我相信,他會繼續進行理論探索。
(作者為知名學者、資深媒體人;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