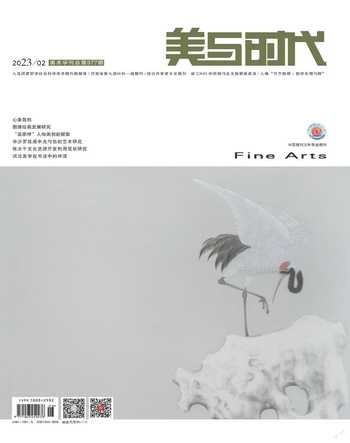朱熹書法的藝術特色研究

摘 要: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書法藝術的風格彰顯了時代的特點。南宋時期的書法進入了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期,朱熹作為南宋重要的書法家之一,在吸收前人書法藝術特色的基礎上融合理學思想,將內斂型的書風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關鍵詞:朱熹;書法;藝術特色;書風
朱熹作為南宋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一改北宋以來“尚意”的書風,其筆鋒沉著有力,渾然自成,頗有魏晉之意,目前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以墨跡和碑刻為主。其書法風格形意俱存,融合了自身對于理學的理解,將書風同“理”聯系起來,開創了以“理”為本的書論。其對于書法所著重的“追篆籀意”“自在書風”“不與法縛”的意境追求,對后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朱熹在書法上的建樹對于書法藝術的發展而言是一座里程碑,其特色鮮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書法的發展。
一、朱熹書法風格的形成
(一)對“二程”理論的繼承
朱熹被譽為理學的集大成者,“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是對于他的極高評價。在理學方面,朱熹自幼受其父朱松的影響,師從李侗,素好金石,在對于理學義理闡發的同時,也對前人的書學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朱熹十分推崇程顥、程頤對書法作品評價的相關思想,依托于其內在的理學路徑,構建出了一種以“理”為核心思想的書法特色。在朱熹書風形成的初期,當時大多書法家延續北宋之時的“意造書風”,蘇軾等人的書法備受推崇。而與蘇軾同處一時期的程顥、程頤等人認為蘇軾刻意求新及對于“奇”“險”等視覺效果的強烈追求,不但破壞了書法本身的自然構造與和諧美,而且也造成了書法家的審美觀與原義的背離。“二程”直接指出“意造書風”的方式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只側重于視覺上的美感而忽略了書法本身應該具有的教人向善的功能,不能夠發揮“其善惡是非勸誡有以起發其意”的作用[1]。
(二)對蘇軾書風的批判
朱熹對于“意造書風”批判思想的來源在于“二程”的觀點,他在繼承“二程”對蘇軾書風批判的同時,將其上升到了個人倫理認識的高度上。蘇軾在書法創作中強調以“意”為體,以“法”為用。蘇軾強調“自在無法”的重要性,認為要將個人才學及抱負施展于書法之中,打破“有法”對于個人的限制。蘇軾所追求的書法風格是一種向內而求的創作,也就是在書法創作中不應該單一地追尋千篇一律的格式,延續過往的書風,而應在書法創作的基礎上加以個人心性的發揮,貫穿變革之風與追求創新的精神,追求的視覺效果以極為“險”和極為“奇”為主。
在朱熹看來,一味追求書法風格上“狂”“怪”“奇”是一種不入流的創作。朱熹對于蘇軾與黃庭堅的批評是極為嚴厲的,他指出:“字被蘇、黃之流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2]在朱熹看來,蔡襄的書法是值得贊賞的,其對于“法度”的精準,如君子一般值得認可,從字中可以窺得人品。基于這種觀點,朱熹在其以“理”為核心的哲學觀下構建了在書法藝術中重視“守常”與遵循法度的理論。朱熹把書法的創作視為一種對“天理”的遵循,強調書法在書寫風格上秉持原有的特色,不能以夸張、執意做作的風格博人眼球,應該把書寫的重心放在字體的端正上,要起筆有力,似古法創作一般有所特點,以此才能正書法之道。朱熹曾言“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3],從中可以了解到,朱熹對書家書法作品的看法不僅繼承了“二程”之前對于“意造書風”流于媚世的批判,更把書法創作中的旨意上升到了與合乎理義相對應的高度上,將個人書寫藝術中真性情的流露視為逾越道德的體現,真正的書風應當有繩墨為則,一點一畫的書寫皆需要遵循法度,合乎“理”。
二、朱熹書法藝術特點
朱熹既是理學家,也兼具書法家和詩人的身份。朱熹在行書和草書方面較為擅長,其書法特色以大字最能顯現。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中曾評價道,“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也就是說,朱熹在吸收前人書法風格的基礎上,融合自身義理,在書法翰墨方面工筆極佳。朱熹將其理學思想融入書法創作,構建了以“理”為本的書法創作路徑,主張以古為鑒,在仿照古風書法的創作中凸顯自己的深意,整體以古淡和平的內斂之風為主,同當時的主流書法作品風格不大相同。
(一)追篆籀意
朱熹對于書法的見解同南宋時期“尚意”書風不同,與當時的主流書法作品不同的是他對于書寫意境的追求。朱熹認為,北宋所推崇的“尚意”從根本而言無視傳統古書風格的繼承,毫無法度。朱熹繼承了家族對于金石文字的研究,對金石情有獨鐘,這為他早期的書法風格埋下了伏筆。朱熹崇尚書寫中追篆籀意的境界,認為古書是最好的,對當時書法中追求“尚意”所不屑。朱熹早年書法風格直取魏晉之意,習得曹操與鐘繇之書,行文之字古樸有力又不失風韻,筆墨精妙,字法俊逸,頗有古書之味。
從目前的朱熹所保留的大字書法(圖1)中可以發現,朱熹的大字起筆雄厚有力,不拖泥帶水,自成一派,在結尾之處更是回鋒圓潤,與大篆行筆相同。尤其行筆處不是簡單的一筆帶過,而是一筆多次回頭,以循序漸進、不緊不慢的行筆方式造就了書寫上的佳績。在其行筆方式下,字體沉勁有力,不軟綿,也不過于鋒利,凸顯出了一種穩重古樸的實在之風,與古代鐘鼎文字有異曲同工之處,在字中特別注入了篆籀氣息。朱熹尊古學古,卻不一味沉浸在古書風的條條框框之下,他以古為新,遙接了古代篆籀的獨特眼光與厚重古樸的氣息,其書風有些大膽獨造,意境高遠,在整個唐宋的書法家中別具一格,自有風韻。
(二)自在書風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與磨煉,朱熹的書法爐火純青,其大字書法別具一格,自成一派,而再視其小字,更是婉約清麗,別有一番雅韻,然其成就最高者,莫過于他的擘窠大字。朱熹的大字筆意深遠,古樸端莊而不失其味,起筆飽滿,雄厚有力,以輕重交替的方法揮斥方遒,長短相宜,偶有飛白游絲,自在相承,末筆寬博有力,承載厚重。在圓轉之處,習得顏真卿書風的韌勁,在方折處,似松柏之挺秀,兼有篆隸的古樸之感。行草十分靈動,可以窺得其用筆食古而能化,一點一橫皆似魏晉書風的古韻,意境高遠,書體自然。結體部分大多平穩厚實,似泰山之巍峨,又如汪洋大海,渾然一體。其高拔處如秀木林立,直指云天;其疏曠處如遼源之廣,寂靜自在;其蜿蜒曲折處,似峰回路轉,悠悠蕩蕩,令人回味無窮。
品析朱熹大字的意境,好似龍盤虎踞,有威風凜凜之感。又或似南山永固,凝重厚實與古樸自成一體。品朱熹之字猶如閱書萬篇,能夠指教人之心相,仿圣學之所在,端正己心。在牌匾楹聯或摩崖石刻上留有朱熹的大字,尤其是其榜書《千字文》,整體可謂鴻篇巨制,堪稱奇偉之作,讓人望而喟嘆。歷代書家對朱熹的字評價甚高:“紫陽文公書法尤閎肆博大,其擘窠大書,浩逸之氣直可方駕鶴銘;即尋常著書草稿,縱橫浩蕩,擴大有尋丈之勢”,“神妙全在轉運藏鋒,若不用力而腕底竟有千斤之力,此種境界求元、明殊不可得……”[4]。
(三)不與法縛
朱熹書法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種有法卻又無法的境界,正如其所說的:“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從自己胸襟流出者。”[5]在朱熹看來,不論是書法還是任何畫作,都應當有一個法度準則,這個法度準則是貫通于“道”和“理”之間的。“道”與“理”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最高范疇,是一切事物之所以然的根本。“道”為“體”,“理”為用,只有在書寫的過程中秉持這一準則才能夠體現出形意俱佳的書風,遵循這一個規范,筆力到了,就不會有寫不好的字。朱熹對書寫中“不與法縛”的要求也體現了他“以理論書”的特色。
朱熹非常重視書法中的法度和功力,十分推崇蔡襄、朱鴻臚、喻工部等謹守法度的書家,曾言:“蔡忠惠公書跡遍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于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余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干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用筆之微意云。”[6]朱熹十分贊賞蔡襄的字畫筆力渾厚,是謹守法度的佳作,世人可以此書為對照,可以臨摹其下筆之勢,以此知曉書法中所流露的高深意境。
三、朱熹書法對后世的影響
書法不僅表現作者的精神風格,也會展現創作時的情景寓意,講究書法之氣與書法內容的統一。朱熹的書法行云流水,追求古意,卻在古風之中展現出勃勃生機的面貌。在有所規范的同時,顯現出渾厚之力,在整體感覺上呈現出了一種收放自如、蒼茫遼闊之意,觀如此性情,無不對其筆觸贊嘆。明代海瑞曾對此題曰:“是書風流韻逸,雅致超群,實乃天然妙品。”而朱熹的書法不僅為當時南宋書壇千篇一律的書風打開了新的局面,其筆觸的渾厚功力及自在的書風更對后世有深刻影響。
(一)對南宋、元的影響
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十分推崇“二程”之學,以“道”為體,重視在書法上的實踐,以書風為用。其書法遵循法度,有“書如其人”的主張,力求工筆端正,書風自然。同時又主張“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以超脫于工筆的格式追求深遠的意境,這些都深刻影響到了南宋以后書壇的發展。生活在南宋晚期的魏了翁就深受朱熹書學的影響,在繼承朱熹書學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發展。魏了翁在吸收朱熹書學的同時,對朱熹書學中偏激和片面的地方予以了修正,彌補了朱熹書論中的不足。魏了翁的書風在一方面繼承了朱熹所重視的“追篆籀意”和“不與法縛”的特點,將“法”與“逸”相結合,同時也強調凸顯“意”的外在表現。另外,魏了翁也主張“以書論人”的方式,即從個人書法的筆觸中窺探書家的人格品質,將書風本身同個人德行聯系在了一起。這種將道與藝相互結合辯證看待的方法,不僅使其理學構建體系更加完整,更促進了后世對于朱熹書風的研究。
在元代,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更推進了朱熹書學思想的盛行,朱熹書法中所強調的“義理”之要更被儒者接受,形成了以“理”承“法度”,尋求書法之意的風氣。元代崇尚朱熹學說,以趙孟頫為首的元代書法家實踐和發展了朱熹的書學思想。盡管元代早期理學思想在書論上的表現還是比較零散的,但是到了元代鄭杓新的理論的出現,進一步發展了朱熹的書學看法。與朱熹稍顯不同的是,鄭杓認為書寫不能刻意尋求規矩與法度,而應當在潛移默化中自成一體,在法度中尋求自在。鄭杓《衍極》的誕生,將書法理論系統化,從而完全體系化了朱熹的書學思想。
(二)對明清的影響
明清之時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主,朱熹所作的批注被視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與此同時,朱熹的書學迎來了發展的頂峰,適應科舉的“臺閣體”書法泛濫,遂成為這個時代書法審美的標準。朱熹反對以“狂”“怪”“奇”為視覺追求的書寫風格,認為這種書風是一種對書法自然美的破壞,因此他曾批評道,“字被蘇、黃胡亂指流寫壞了”。凡是姿媚多態、欹傾不正的書風,在朱熹看來都是媚于世俗、不符合傳統正道的。在明初之際,朱熹所遵循的書風逐漸被統治者重視,其所遵循的風格被視為標準,“臺閣體”書法便是以朱熹的書法觀為思想根源。這一時期的“臺閣體”書法代表人物為姜立綱,其筆觸恪守古法,每筆每畫必求來歷的精準便反映了這一時代的書寫風格。盡管“臺閣體”將唐宋至元末明初以來書法技巧予以明確的規范,卻在審美意識上呆板停滯。明中晚期書畫市場的興起,使書法功能發生了轉變,其欣賞功能被凸顯了出來。因此,書法用筆也由精細謹慎向恣肆欹側轉變。華亭派董其昌,其書法初宗米芾,遠師晉唐,行書溫婉恬淡,草書流利瀟灑,書風自成一派,尚有朱熹書風的影響。清初書壇,受浪漫主義思潮影響,雖有個性的書法家如王鐸、傅山等,但整體書風未出明人窠臼。清中葉以后,碑學的興起標志著書法的歷史變革,其社會審美向雄強渾厚轉變,朱熹書學的影響在此時已很微弱。
參考文獻:
[1]程頤,程顥.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236.
[2][3]黎靖德,朱子語類[M].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3 259,3 210.
[4]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5:43 136.
[5]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27.
[6]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 633.
作者簡介:
劉紫云,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學、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