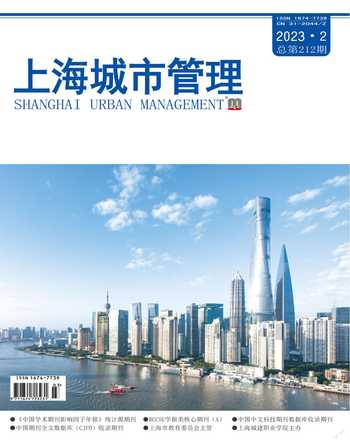社區參與:風險常態化背景下社區安全治理的分析視角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上升到“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高度,在風險常態化語境下,社區安全治理成為社會治理中極其重要的內容。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元,社區參與成為社區安全事件“源頭”治理的基礎。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是法律規定的基本職責,但在現實操作層面往往會被忽視。不同于政府職能部門以分級分類為依據,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后進行專業化應對,社區參與主要承擔預防及輔助職能,實際運作中存在的困境束縛了職能的發揮。作為解困之路,社區安全事件內在的全周期演變邏輯為社區參與提供了多維度的能力建設和多樣化的途徑選擇。
關鍵詞:風險常態化;風險治理;社區安全;社區參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3.02.011
2021年,我國出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針對“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作出了明確部署,提出要“健全黨組織領導、村(居)委會主導、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基層社會治理框架”。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將“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上升到“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高度,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共建共治的本質是公眾參與,在風險常態化語境下,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元,社區參與安全治理成為社會治理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對于預防和應對社區安全突發事件、建設安全社區十分關鍵。可以說,當前的社區安全治理是以安全風險常態化為場域特征的,如何提升社區參與效能,進而實現社區參與的常態化,成為能否適應安全風險常態化的重要環節。
一、社區參與是風險常態化背景下公共安全突發事件“源頭”治理的基礎
自烏爾里希·貝克1986年出版《風險社會》一書以來,三十多年的全球實踐已經將這一概念演變成了不可逆轉的現實,無論是2022年以來的全球極端高溫事件,還是不斷發生毒株變異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抑或是大型群眾性活動中發生的群體性踩踏事件等,諸多典型公共安全事件在全球范圍內多發頻發,凸顯了公共安全形勢的嚴峻性和復雜性。正如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當前“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不確定難預料”就是風險概念的核心內涵。事實表明,安全風險始終存在,“風險意味著危險”,[1]何時何地爆發公共安全事件看似未知,但一旦內外因具備,隨時可能轉變為突發事件,甚至產生災害性后果。一言以蔽之,“黑天鵝”漫天飛舞、“灰犀牛”橫沖直撞已經是公共安全面臨的常態,某種意義上正在以“嵌入”(embedding)的方式融進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階段。
公共安全突發事件一旦發生,社會公眾便成為最大的承災體,包括生命健康、公私財產、正常生產生活與學習工作秩序等在內的正當合法權益都可能遭受損害。傳統的安全維護和供給模式是政府包攬一切,在突發事件產生原因單一、衍生后果不明顯、耦合狀態不突出時,政府尚能憑借一己之力實施應急處置;但是,當前很多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產生及其演化都極其復雜,因果關系之間往往是多因多果,事件內在要素與外界環境相互之間有著強關聯度,而且應急處置所需的人力物力、設施設備等資源并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政府救援力量不足,則必然加大事件造成的災害性后果。由此,一方面需要由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協同應對取代政府“單打獨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當前社會的公共安全風險除了具有風險本身的不確定性,還具有極強的耦合性、系統性、整體性,這就客觀上使得安全風險的治理無可避免地與社會及社會公眾、社區及社區居民形成密切關聯,進而同社會治理、基層社區治理產生無法分割的交集。
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闡述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時就提出過“源頭治理”的重要思想,之后又明確要求“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①。公共安全的源頭治理,就是要在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爆發之前將事件的苗頭消減。“公眾參與對維護公共安全、應對和預防安全風險非常關鍵”②,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元,社區參與就是源頭治理的基礎,社會參與安全治理有利于充分發揮其居民的聚居地、事件的發生地等區位優勢,事發的源頭控制了,基礎扎實了,社區安全就形成了一道屏障、劃定了一條底線,由此也賦予了社區安全治理在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工程中重要支點和關鍵節點的地位。
二、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的法律規定及職責分析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0年11月轉發了《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辦發〔2000〕23號),開篇對社區做了如下界定:“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目前城市社區的范圍,一般是指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作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本文首先是在此地域意義上使用“社區”這一核心概念。
(一)社區參與的概念
當“社區”這一概念被賦予實踐內涵之后,則是“實現了社區的實體性與社區居委會的科層性的密切結合”。[2]這其中,除社區黨組織、政府行政組織之外,還包含社區自治組織、社區志愿者、企事業單位以及社區居民,共同構成了廣義上的多元化社區參與主體,也有學者將此格局描述為“一核多元”。[3]由此,社區參與是指“一核多元”的社區主體介入社區公共事務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包括行為的方式、手段、過程、結果等。具體到社區安全這一公共事務的治理,則是“針對突發事件所開展的風險防范、預防準備、響應處置和恢復善后等一系列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總稱。它既涉及行政組織(如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等)、自治組織(居委會、村委會),也包括大量社會組織、市場組織以及居民群眾等,是典型的跨域型應急系統”。[4]顯然,這一跨域性特征必然要求多元化社區參與主體的協同作用。
根據我國現行《突發事件應對法》對于突發事件的四種分類,當前對社區具有較大危害性影響的安全事件類型主要是自然災害類的地震、城市內澇、臺風,事故災難類的居民住宅及“三合一”場所的消防火災、天然氣爆炸③,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等傳染性疾病為典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個人極端事件等社會安全事件。以社區為中心開展突發事件應對是國際上和諧社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是將社區建設成有準備、有抵抗力和有恢復能力的社區。[5]
(二)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是法律規定的基本職責
《突發事件應對法》是我國現行應對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最高位綜合性法律,其中第6條、第9條、第55條分別規定,“國家建立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突發事件應對工作的行政領導機關”,“突發事件發生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和其他組織應當按照當地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進行宣傳動員,組織群眾開展自救和互救,協助維護社會秩序”。其他的專項法律法規,如《傳染病防治法》第9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40條更是明確了居民委員會應當履行“協助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報告”“人員的分散隔離”“公共衛生措施的落實”“宣傳防治知識”等具體職責。2006年5月1日,由原國家安全監管總局頒布的《安全社區建設基本要求》(AQ/T9001-2006)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對安全社區基本要素進行了明確描述,例如,“社區應建立事故和傷害預防的信息交流機制和全員參與機制”,要“建立群眾組織和志愿者組織并充分發揮其作用,提高全員參與率”。
諸如此類的法律條文、統一標準并不缺乏,這一方面表明社區參與安全治理是法治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應有之義,尤其是居民委員會的法定職責更為明確;但另一方面,這些法定職責在實際操作層面往往會被忽視,而且參與層次及路徑還存在極大的不明確性。
(三)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的預防性、輔助性職責
不同于政府職能部門以分級分類為依據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后所進行的專門化、專業化、系統性應對,如公安偵破案件、消防救火救災、衛生醫療救治等,社區作為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單元主要是承擔預防性、輔助性職責。具體包括:一是結合社區具體情況,組建突發事件先期應急隊伍;二是針對社區特點編制常發類型的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并定期開展具有一定參與度的預案演練;三是因地制宜,做好常態化公共安全防范宣傳教育和基本安全技能培訓;四是協助加強對社區應急物資、設施設備及應急避難場所的日常管理和巡查;[6]五是在公共安全事件爆發之初開展先期處置,以及在相持階段的社區總體動員;六是事件處置完畢之后,“協助專業機構做好硬件恢復和心理修復工作,盡快恢復社區韌性”。[7]可以說,社區究竟只是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主要承災體,還是降低災害損失的“前哨陣地”,與這些預防及輔助職責的履職程度及效度有著較大關聯。
從公共安全危機事件的全周期管理來看,社區參與的上述職責主要表現在管理全周期的三個階段。
其一是安全風險治理階段。南京大學童星、張海波教授率領研究團隊提出并發展了“風險—災害—危機”連續統(continuum)思想,[8][9]指出“突發事件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以風險的形式存在于先的”,從其過程性上講,這是一個“連續不斷的客觀演化過程”,[10]即突發事件發生之前是安全風險,只有首先對風險進行有效治理,才可能避免災害性后果。在此階段,社區參與重點就是要落實日常風險隱患排查化解。
其二是安全事件發生之初的先期處置階段。一旦前期常態化的安全風險治理缺失,導致安全事件仍舊在社區范圍內發生,這就需要遵照社區應急預案開展先期處置,為專業應急機構的系統處置贏得“黃金救援時間”。“生命至上”的底線思維強調盡量減少人員傷亡,尤其是減少遇難人數,時間則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變量。面對公共安全突發事件,自助自救、互助互救、公助公救作為階梯式的應急救援方式,三者的救援速度呈現出由快到慢的特點。一旦安全事件發生,職業救援人員客觀上無法提供“秒級”響應,或是由于事件波及面較廣,政府部門的應急救援力量不能面面俱到時,勢必需要社區參與,及時開展先期自救互救,盡量避免或減少人員傷亡。此時,居委、物業、志愿者組織、鄰里之間等就是第一波救援力量,他們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初的應對意識和救援技能直接影響著能否把握住救援的黃金時機。
其三是事件相持及處置完畢階段。如果說先期應急處置對于社區參與能力的檢驗是短暫的,那么事件一旦轉入相持階段,更需要有效的社區配合,這對于社區參與能力的檢驗則是持久的,而且更加具有挑戰性,此時的配合極可能需要“私權”讓渡于“公利”。此外,事件處置完畢之后,社區面臨的秩序恢復、硬件設施重建、居民心理恢復等重建任務的執行,都是社區參與安全治理極其重要的職責所在。
三、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引發的問題
從現實情況來看,社區多元化主體參與安全治理存在的困境束縛了上述預防性、輔助性職能的發揮。
結合上文社區概念的外延,在社區安全治理中,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為前提,社區參與的多元化力量具體包括:第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物業等社區力量;第二,社區范圍內的各類企業等市場力量;第三,各類志愿者團體等社會組織力量;第四,社區居民。其中,社區力量是骨干。[11]社區企業作為市場力量的參與主要表現為組織應急生產、捐錢捐物等,本文暫不將其納入社區層面的行動者予以討論。下文主要從居委會、志愿者團體、社區居民三個維度分析當前多元化主體參與社區安全治理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引發的問題。
(一)居委會職責不清,處于“看似有權,實則無權”的尷尬處境
居民委員會、業委會、物業作為社區力量,合稱為當前社區管理的“三駕馬車”,而且,由于居委會日常承擔著“宣傳憲法、調解糾紛、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任務④,易被視為“三駕馬車”之首。實際上,我國《憲法》第111條明確了居民委員會的性質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1989年頒布實施的《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細化居民委員會的運作模式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本質上屬于社會性組織,但是,對此也“只是做了定性表述,對自治范圍、內容及邊界等規定得并不清晰”。[12]作為一類社會組織,居委會的現實地位和實際功能卻超越了一般的社會組織,“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各城市居委會都是由街道辦領導和管理的”,“社區管理逐步行政化、科層化、目標政府化”,[13]行政功能越來越強,社會功能越來越弱,一旦社區發生公共安全突發事件,這一“行政管理職能遠大于自治作用”的模糊定位、錯位角色,[14]就只能導致“看似有權,實則無權”的尷尬處境,甚至“嚴重影響居民對居委會的認同和信任”。[15]
在此引發的問題,也是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是,如何為“社區居委會的性質定位與傳統操作模式之間的背離”尋找出路,[16]換言之,如何應對政府行政權與社會權在居民委員會這一社會性組織身上表現出的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沖突。
(二)社區志愿者組織有興起之勢,但專業性、持續性不足的現狀比較突出
嚴格意義上的志愿組織“具有法律注冊的合法地位,能對組織承諾承擔經濟責任,并具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資金來源”,[17]除了具有志愿服務性、公益性,還具有自治性,不受行政約束。隨著公共精神的弘揚與傳播,這類組織當前興起之勢比較旺盛,全國范圍內以“藍天救援隊”為典型品牌的志愿服務組織在災害應急救援、人道援助、災后恢復和減災等各個領域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社區層面的志愿者組織往往是由社區居民“因事因勢”自發組成,倉促上陣難免需要較長磨合,外加運行資金匱乏,直接導致突發事件應對所必需的應急救援物資嚴重缺乏。而且專業性不足,對于火災、地震、洪澇、傳染性疾病等公共安全事件如何預防,或者是發生之后如何減少損失,都缺乏常態化的專業培訓。
在此引發的問題,也是需要解決的緊迫性問題是,如何對常態化的社區志愿者組織進行專業培訓,如何獲得志愿服務基金,如何實現更加規范的可持續運作等。
(三)社區居民參與面不廣,參與能力較弱,參與渠道不豐富
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居民的社區參與現狀大體上呈現出參與領域不平衡、參與不深入、參與主體不平衡、參與率低以及參與運行機制行政化等特點。[18]這些特點在社區安全治理中亦有所表現。較多居民對社區安全治理基本觀念認識不到位,仍舊認為社區安全的維護是國家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或者是專業部門的專職,如社區治安秩序維護是公安機關的專職,傳染病防治是衛生健康及醫療部門的專職,火災事故搶險救援是消防部門的專職,等等。這種認識上的偏頗往往導致主觀上缺乏參與意識,協同治理積極性也不高,還有社區居民處于自身參與意識弱化但權利意識強化的矛盾狀態。而且,從參與行動來看,當前的社區參與層次較低,主要還是停留于被告知這一較低層次,較高層次的咨詢、協商、共同行動,以及更高層次的自組織行為仍舊非常缺乏。
在此引發的問題,也是需要解決的普遍性問題是,如何提升社區居民的公共安全素養、對社區安全風險的識別能力,以及面對公共安全突發事件時如何有效開展自救互救。
正是上述問題的存在,才會導致社區一旦面臨公共安全突發事件,就極易出現群體性慌、忙、亂,甚至因互不信任而導致沖突等不和諧現象。
四、社區參與社區安全治理的能力建設
“一部社區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培育居民社區意識、提高參與能力、擴大參與領域、提升參與質量的歷史。”[19]公共安全事件具有內在的全周期演變邏輯,作為這一邏輯起點的安全風險,其演化為安全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取決于風險本身的性質和風險治理能力的強弱,二者相比,后者更具有多變性,受主觀能動性的影響也更大,在風險性質不變的情況下,較強的風險治理能力是減少突發事件發生的重要前提,反之則會增加。安東尼·吉登斯曾指出,“能動作用不僅僅指人們做某事時所具有的意圖,而且首先指做這些事情的能力”,[20]通過能力建設提升社區參與安全治理效能是解決困境的現實需求。
(一)風險認知能力
準確的風險認知是有效應對風險、減少突發事件發生的前提。在社區層面,增強社區工作者和社區居民對于安全風險的識別能力,實現對安全隱患的早發現、早介入,這是消減公共安全突發事件苗頭的關鍵環節。如當前在一些小區較為普遍的隨意侵占消防通道、“三合一”場所漏管失管、管道煤氣泄漏、室內電瓶充電、樓上樓下“飛線充電”、群租現象屢禁不止等,對于小區公共安全而言都是極大的風險及隱患來源。無論是由于物業管理缺失,還是小區居民出于個人便捷、牟利,或者是無知無畏、心存僥幸而對此聽之任之,這些風險及隱患都是釀成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的苗頭。唯有先認知風險、識別隱患,才能打牢社區參與安全治理的基礎。
(二)自救互救技能
突發事件發生后,有效的自救與互救可以防止事態擴大,減少災害損失。這就需要社區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和災害結果,開展不同的自救互救技能專業培訓,如地震、洪水來臨的求生技能、火災初起時消防設施的使用、火場逃生營救、臺風預警響應等。防災減災,關鍵在日常,只有將應急處置培訓常態化、全民化,才能確保盡可能多的社區居民在接收到預警信息之后能迅速及時采取行動響應。自救互救技能的培訓應當由消防、公安、衛生等公共安全專業職能部門,以及專業的社會組織如紅十字會等向社區定期開展。
(三)信息收集能力
在公共安全突發事件應對中,社區是收集基礎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信息的重要來源。事件發生后,處于社區一線的社區工作者、樓組長、志愿者等人員,應當根據政府統一應急指揮的要求,依托微信群完成信息登記、電話詢問、登門查看等,及時、準確、盡可能全面地進行信息收集、匯總、上報,協助政府部門開展統籌決策與應對。
(四)危機溝通能力
突發事件的發生,除了引發直接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等后果,還會引發“無知之幕”狀態下社區公眾的心理恐慌,這種恐慌情緒在自媒體的驅動下會蔓延,甚至可能導致一些非理性行為,這是典型的由于缺乏溝通、溝通不暢而帶來的突發事件衍生后果。此時,社區針對事件所處的階段與狀態進行主動溝通、信息反饋尤為重要,居民知情權的適時滿足是提升居民安全感和信任度的關鍵,這也是危機溝通最大的作用。
(五)社區動員能力
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6條規定“國家建立有效的社會動員機制”,這是“突發事件發生之后啟動社會動員機制、推行社會動員具體措施最明確的法律依據”。這種動員本質上是應急動員,其“目的是調集全社會的力量,形成多元主體的有序、高效、合作、協同的參與模式”,既可以通過“人力、物力、財力的高效整合減輕政府的應急負擔”,也“有利于發揮社會凝聚功能,形成強大的社會積極心態”。[21]可以說,社區動員能力作為最基礎的社區安全治理能力,既是基層政府和社區工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更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應急處置效能的重要表現。無論是事件發生之初的先期應急響應,還是相持階段的配合行動,都需要社區動員才能更好達成目標。由此,社區動員能力的培訓應當在社區工作者隊伍能力培訓中居于重要位置,并落實長效機制。
五、社區參與視角下構建社區安全治理新格局的途徑
以上述社區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問題為導向,匹配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社區參與視角下構建社區安全治理新格局的途徑集中于以下四方面。
(一)制度途徑
此舉重在解決居委會作為“三駕馬車”之首的定位和職責問題。體制機制都屬于制度的范疇。“機制約束導致的居民與社區的制度性疏遠是當下我國城市的社區參與所面臨的主要問題。”[22]這一問題所需要的解困之路,一方面,在體制上理順區—街道—社區三級應急管理體系,建立以居民區黨組織為核心,居委會為主導,社區民警、網格員、業委會成員、物業服務人員、社區黨員、居民代表等共同參與的社區應急隊伍,為社區防范和應對突發事件提供常態化的人力保障。另一方面,從具體運作機制上擺正居委會與街道、居委工作者與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需要把包括人事權、財權、管理權等在內的社區權力下放給居委會,為其增權賦能,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居委會手中沒有社會權力,只能事事依賴于街道辦事處。
(二)社會途徑
此舉重在解決社區志愿者組織常態化、規范化建設問題。既需要在社區建立志愿者指導中心,實現志愿者組織的注冊管理,更需要把社區志愿者在社區安全治理中的初次培訓、階段性培訓和臨時性技能培訓結合起來,促進社區志愿者服務隊伍向管理正規化、技能專業化方向發展。同時,拓寬接受社區企業單位的捐贈渠道,建立志愿服務基金,“戰時”用于應急物資的購買與消耗,“平時”用于應急技能培訓及激勵,雙向發力,拓展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三)教育途徑
此舉重在解決社區居民參與不足問題。參與意識缺乏、參與渠道單一、參與技能有短板,這些參與不足問題的客觀存在一方面表明,由于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重大事件都屬于專業領域的范疇,公安、消防、衛生健康等專業職能部門在安全風險治理和危機事件處置中必然承擔著極其重要的專業主體職責。相對于此,社區參與的短板自然是明顯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對社區開展安全知識傳授、安全技能普及與安全文化教育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由此,教育途徑首先就是要求相應專業主體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告知社區組織、社區居民、企事業單位如何預防安全事件發生,以及一旦發生如何自救互救。同時,這些應對技能的習得還必須通過形式多樣的社區安全演練才能實現。從長遠來看,還需要建立社區安全風險治理文化教育體系,使社區居民接受系統全面的安全觀教育,實現安全教育的常態化、長效化。
(四)科技途徑
此舉重在依托科學技術手段提升社區安全治理成效。其一,運用信息化手段、大數據思維、高科技設施設備提高社區安全風險隱患排查化解效能,形成社區安全風險治理的技術支撐體系,這是適應信息化時代社區安全治理手段多元化的必然要求。其二,向公眾普及安全事件的科學知識,提高全社會對安全事件的科學認知,從根本上實現多元化主體對社區安全風險治理的科學態度和主動參與意識。其三,當然也包括在社會科學層面加強中國特色公共安全治理規律的研究,持續探索社區安全維護的機理,為社區安全治理實踐提供更具有時代特點、本土特色、社區特情的理論支撐。
說明:本文系2022年度上海公安智庫專項研究課題“大數據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研究”(22GAZK0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2016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上海基層取消了招商引資的職能,心無旁騖,也有了更多精力做好服務。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
②2015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③“三合一”場所是指住宿與生產、倉儲、經營一種或一種以上使用功能違章混合設置在同一空間內的建筑。
④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居民委員會的任務”。
參考文獻: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崔月琴,張譯文.雙重賦能:社區居委會治理轉型路徑研究[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175-184+217.
郝園園,雙傳學.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邏輯機理與實踐進路[J].江海學刊,2021(1):146-151+255.
容志.讓基層應急系統運轉起來:城市生命體視角下的融通型結構[J].中國行政管理,2021(6):136-144.
張永理.社區治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汪永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薛澤林,宋雪.超大城市應急管理中的社區參與[J].上海文化,2022(8):13-19.
童星,張海波.基于中國問題的災害管理分析框架[J].中國社會科學,2010(1):132-146+223-224.
張海波.應急管理的全過程均衡:一個新議題[J].中國行政管理,2020(3):123-130.
童星.兼具常態與非常態的應急管理[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5-15.
俞祖成.社區公共危機管理指導手冊[M].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孫莉莉,伍嘉冀.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居民自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童星.中國社會治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滕五曉,等.社區安全治理模式研究[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6):70-75.
吳開松.城市社區管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楊淑琴.社區沖突:理論研究與案例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4.
徐永祥.社區發展論[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21.
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M].李康,李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朱志萍.基于公共安全危機常態治理的公眾參與機制建設[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20(2):126-132.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alysis of Community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isk Normalization
Zhu? Zhiping
(Shanghai Police College, Shanghai 200137, China)
Abstract: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uplifted “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 to a level of “ promoting the modernize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 in the context of rish normalization, community secur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most basic uni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ulcrum and key node for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the source of community 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community subjects in community security governance is a basic obligation stipulated by law, but this legal obligation is often ignored in practic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ainly plays the role of prevention and assistance, different from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amd their professional responding action based on levels and types amid emergencies, and the dillemas in practice has constrained its role play. To ease the dillemas, the inherent whole-cycle evolution logic of community security incidents provide multi-dimensional ability construction and multiple route selection.
Key words: risk normalization ; risk governance; community secu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