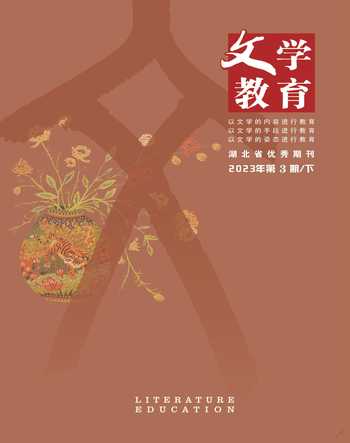殘雪《呂芳詩小姐》的空間敘事
羅寧凡 雷霖
內容摘要:《呂芳詩小姐》憑借豐富多維的空間結構、復雜多元的人物形象、詭譎多變的語言意象,建構了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文本,顯現出作家對于人性異化所產生的恐懼焦慮,對于人類生存困境的終極關懷。本文以殘雪小說創作中的空間敘事策略為出發點,挖掘人物在現實與非現實的災難沖擊之下,如何墮落、重構、救贖的全過程,最終指向的是我們應該如何反思當下的困境,展開對命運的抗爭,從而真正實現自我主體性的突破與超越,展望新的生命圖景。
關鍵詞:殘雪 《呂芳詩小姐》 空間敘事
在對當代文學的研究日趨多角度、多層面、多元化的今天,殘雪的寫作具有外露的鋒芒和內延的品格。作為中國先鋒小說的另類拓荒者,許多讀者將她的寫作定義為“施展巫術”,因為她總是有意地疏離傳統文學的形式,運用詭譎的意象、荒誕的情節、魔幻化的手法來建構一個非傳統的、甚至是極度異化的文學空間,創作了一個又一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作品。倘若我們對其作品進一步的梳理和概括,可以發現作品的結構、人物、語言逐漸走向豐富,凸顯了空間、角色、意象背后的深層意蘊和情感表達。這些轉變也體現了作家一種赤忱、真摯的美學努力。
于201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呂芳詩小姐》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通過描寫紅樓性工作者呂芳詩同眾多情人、友人、親人之間發生的系列故事,展現人的感性、理性、本我在欲望、死亡、永恒面前的不同呈現,證明了人是如何在災難性的生活中尋找圣潔的心靈故鄉,如何挖掘一種有價值的人生意義。在已有研究中,姜玉平的《心靈空間的開拓——論殘雪〈呂芳詩小姐〉中的三個空間意象》一文,以核心意象“紅樓”“貧民樓”和“鉆石城”來對文本進行剖析,以嚴謹的筆墨“書寫了主體突破重圍向本質自我挺進的艱難曲折的歷程。”①本文在吸收現有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挖掘文本尚未解答的深意,以期彌補現有研究在體量和方向上的不足。
一.“紅樓夜總會”:感性的墮落
“紅樓夜總會”作為文本的初始空間場景,承襲了中國古典文學當中最為經典的色彩,描繪了一幅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的畫卷。紅樓如夢悠揚,佳人、肉體、欲望在此間交織相伴。那里又是現代感的融合,就像一個大悶罐,彩色的激光四處亂舞。人的欲求被不斷喚醒,僅有的理智日益倒塌,也為故事中的人物帶來了復雜的矛盾體驗。
呂芳詩,高挑貌美,令所有的男人都為之傾倒,也直接指向了女性在異性關系中一直面臨的處境——一種被他者化、欲望化的存在。殘雪就是要讓讀者透過一個個男性的目光,去寫一位游走在眾人身邊的女性,進而揭示她從未消失的隱秘屈辱和內心傷痛。呂芳詩是聰慧的,她或主動或被動地為所有人物提供一種內心的幻想,借此換取她所想要的東西:童年缺失的疼愛、父輩真切的關照,擺脫貧窮的金錢、供以居住的處所亦或是重新開始人生的捷徑。很多傷痛和疑問,例如對女性的暴力,規訓、打壓,伴隨著呂芳詩的一生。那個幼時被父親鞭打的她,被“獨眼龍”扔在鐘乳石巖洞中,匍匐爬行的她,被“死去的T老翁”拋下的她……世俗規訓著她愿為情欲付出多少代價,要為情欲付出多少代價,她像一個賭徒,在兩性或者同性的博弈當中損耗自己,一旦變得習慣通過迎合一部分的主流敘事和男性審美來獲得一些東西,其自身主體性的部分就在慢慢地減弱、喪失。如果她想要突圍,想要逃離這種強者控制下的游戲,她就必須在既定的男權規則中學習、浸潤,最后往往發現自己舉步維艱。
殘雪在《追求邏各斯的文學》中提到:“欲望是我創作的核心,它也是我的想象力的黑暗的母親”②。她不僅寫欲望,也寫欲望對于人性的消磨和打壓,正是具有欲望這一本能訴求,文本中的每一個人才會在“紅樓”這個場域中盤桓、游蕩,在乏味生活中 尋找激情。當欲望在世俗場內不斷地彌散和擴張,變得永不滿足,人物內心的天平便會傾倒失衡。這也是為什么,在“京城紅樓”和“西部新疆”的隱形對照之間,呂芳詩一直在尋找自己靈魂的故土,對于她來說,京城繁華卻冰冷、虛無縹緲,陽光沒有一點真實的暖意,是一個肉體上暫居之地。而西部,是回想起來就讓人的靈魂為之痛苦顫抖的故鄉,那種痛苦是大海一般深廣而澎湃的激情,同過往不死不活的陰暗生活有著天壤之別,她叫嚷著:我們的稟性使我痛苦。她深知,在庸常和寂寞之間,那種無意義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為可怕。
二.“公墓社區”:理性的突圍
名叫“公墓”的貧民住宅小區,是作家殘雪創造的第二個空間場所,它的存在是如此的古怪而奇特,幽靈、鬼魂、守墓人都遍布其中,充斥著無名的陰影和噩夢。相較于“紅樓”這個意象而言,它更加具有殘雪創作風格中“魔幻象征化”的影子,是作家“側重于通過虛擬的形象群,用隱喻的方式表達對事物本質的一種抽象概括”③。在激情、曖昧的“紅樓”中起伏掙扎的曾老六和呂芳詩,深感痛苦和折磨。自我在墮落中逐步走向異化和分裂,從而誕生了主人公的第二個“分身”——理性自我。
呂芳詩來到“公墓社區”定居,在那個一室一廳的狹小單元房內,段珠用一場盛大的表演完成了呂芳詩對于死亡的認知。“段小姐躺在那張舒適的床上,一張臉縮得只有手掌那么大了。”④“她雖然已經半昏迷,說著胡話,一雙雞爪一樣的小手緊緊地抓著呂芳詩的手不放……她的指甲嵌進呂芳詩手掌的肉里頭……然后她的身體抽搐了兩下,漸漸變硬了。”⑤曾老六在“公墓社區”的經歷也充滿了奇幻、荒誕和虛幻的多重體驗。在首次進入“公墓社區”的過程中,他戰戰兢兢地走出電梯,被兩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帶入十五樓的玻璃房間,窺見不同樓層住戶的生活:紅棕色的母貓、爭吵的男女、臉上文著黑色蝴蝶的白浴巾女人、空中垂死的灰鴿。他被辱罵為草包、懦夫,被當作小偷、啞巴,又被兩個穿著黑衣的蒙面人痛打一番,推出了大門……
“公墓社區”在空間上是現實世界的映射,表達著世俗的欲望和生者的需求。在這個非現實的語境中,一切現實的意義和價值都被人為地擱置和抽空。呂芳詩、曾老六行走在這個如夢魘般的黑暗世界,或多或少迷失了方向,他們必須剝開世俗社會的偽裝外殼,以一個真誠的模樣面對自身。這也正是死亡和墓地之于人類的另一層意義,它使人變得更加理性,讓人有能力將無形的情感變得有形,從而脫身于欲望的泥沼。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更是一個裹挾著恐懼、傷感、委屈的過程。于是,當呂芳詩在段珠房間看見紛飛盤旋的海鷗,當她直面相似身份、相同性別的生命的離去,就必須正視她作為人的情感,認識到肉體生命的短暫,知曉只有真摯熱忱的靈魂才永遠不會消失。而當曾老六能和社區里的幽靈一樣,騎著自行車在空中飛翔那一刻,一種全然的欣喜和愉悅在他的身體里綻放。他混沌、孤獨地在世上活了三十多年。曾經竭力地想要看清世俗黑暗中的某一種輪廓,現在,這種輪廓已然悄悄地浮現了。
呂芳詩和曾老六就是這樣在理性自我的驅動和突圍下,實現了一場感性自我和理性自我的相遇和審判,從而有機會脫離肉體的枷鎖,站在更高的角度來審視曾經的自己與過去的生活。與此同時,人變得更為堅強、獨立,世俗欲望被消解,生活的牽絆被打破,從而轉向了更高的心靈需求。而“公墓社區”并不能為其滿足其渴望,理性自我的約束甚至會帶來心靈上的壓抑和欲望上的反彈。在理性自我的突圍和驅動下,他們更加向往一種全新的、自由的空間,以供心靈的遨游與探索,在這樣內心渴望的驅動下,他們開始奔赴新的遠方。
三.“鉆石城”:本我的重塑
“鉆石城”作為文本敘事發生的最后一個場域,對于呂芳詩來說,那是她的溫柔之鄉。當她被T老翁指引著來到鉆石城,試圖在這里尋找到一種心靈的滿足,卻不久聽聞他游河身死的噩耗,只留下對岸那盞在風中浮游的電石燈。她的另一位情人“獨眼龍”也在前往鉆石城的旅途中飛機失事,站在那個透亮、空靈的機場內,她的神經陷入了巨大的崩潰,死亡的陰影籠罩著她,使得“鉆石城”儼然成為了一個煩惱之地。
在“哭郎山”,呂芳詩望著藍紫色的天庭流淚,是對獨眼龍,也是對T老翁。小花說:“情人只能生活在悲傷之中”⑥。這種矛盾不失為殘雪的一種冷峻和幽默。她樂此不疲地為筆下的人物建造一座象征主義式的城堡,這座“城堡”不像作家卡夫卡那樣建在山坡之上,而淫浸在世俗里頭。T老爹、呂芳詩與曾老六,他們就像“土地測量員K”一樣,都在“鉆石城”這個場域內朝著更高的夢想邁進,卻又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掙扎終歸無用。這種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所謂的創造也許不過是自欺,理想中的目標也總是在遠處飄蕩,追求者找尋不到確鑿的證據,感受到的更多是寒冷、空虛與眩暈無力”⑦。在這種壓抑的生活里,人總是憑借一種內在的非公正與非理性來擺脫虛無,就如他們嘗試在黑夜里表達自己的憤怒,宣泄著對世界的困惑與不解,卻無法撼動現有的疾苦,也常常忘記這種苦痛,然后在混沌的生活里繼續行走。
在權力、欲望、金錢為中心的社會中,人類的幸福道路沒有既定的模板,也沒有恒定不變的可供參考或模仿的對象。呂芳詩這一類人要去實踐、突破些什么,必須要去朝著未知而不斷努力。這個過程也是掙扎、痛苦、充滿有代價的。必然伴隨著漫長的探索、掙扎、推翻、再重建的過程。從她們的身上,我們有機會看到人對于自由夢想的尋求,對重建生活秩序的渴盼。苦熬的人生不是一種純粹的悲觀主義,也不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有希望的壓抑,是在絕望的縫隙里依然向上生長的勇氣。或許,這就是他們表達內心希望的一種方式,以此來為她或他的生活帶來正確的方向感,產生一種屬于新生活的邏輯,引導他們向著不斷地超越本我的境界攀升。
如果說“紅樓”的存在是為了揭示欲望的本質和對人性的戕害,展現感性自我不斷淪落的過程,而“公墓社區”是以死亡為切入點,表現理性自我在精神上的層層突圍,那么“鉆石城”則比“紅樓夜總會”和“公墓社區”的內核更為復雜深邃。正如小花的父親所說的:“沙漠里頭有一種定力,因為它,我們的城市才被稱為鉆石城的”⑧。這種所謂的定力或許跟鉆石的品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澄澈、透亮、清明,純潔。這也是為什么“鉆石城”能不斷地接納和吸收眾多來自“紅樓”與“公墓社區”的遷移者——那些內心燃燒著熊熊烈火的人、那些不滿足于世俗現狀尋求突圍的人,那些渴望實現內在自我超越的人。“鉆石城”以它的外在和內核表達著一種持久性的精神追求,關乎人的尊嚴,關于人生邊界的探索,關于主流生活之外的想象,它教導人如何過一種有道德的生活、如何追求自由、尋求真理,也只有這樣的“鉆石城”才能有動力將過往的糜爛生活拋卻,將人的世俗欲望抽離、打磨、升華為具有質感的精神力量,去叩響永恒之門,從世俗人生躍入到真正的、藝術的、故鄉式的生活。
殘雪作為先鋒派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小說和文字,建立在背離傳統的文學閱讀感受和日常經驗世界的基礎之上,以一種個人化的言說方式,打造了一座獨具“殘雪式”風格的文學王國。她被眾多的呼聲推向贊揚與追捧的漩渦中心,又主動地隱退到關注的人群之外,始終將深沉而遼遠的目光投向人的精神領域。從結構布局到人物塑造,從主題蘊含到語言風格,行走在殘雪的文字之間,我們似乎很難看到那些充滿動感、歡樂、溫暖的言語,在那些看似晦澀、奇絕、灰暗的意象背后,在那些躍動、多彩的“呂芳詩”式的靈魂身上,能夠看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影子,它們的形態各異,內含著智性和詩意。就像文本中所說的那樣,呂芳詩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內心的誘惑、潛在的情感,足以引發內心的傷痛。在某種意義上,當我們望向他人而遺忘了自我的時刻,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呂芳詩。她的倩影融化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給每個人帶來某種新的意義。
也正如文章所描繪的那個心靈的歸宿——“鉆石城”,那個純潔的、熱情、一目了然的不夜城。它是屬于女性的心靈城堡,更是屬于人類的心靈家園。這座神秘、動人、充滿希望的城堡,是像呂芳詩一樣的女性,通過自我精神的搏斗,靈魂的淪落與重構才能接近它、觸摸它。即便距離我們當下的生活是那么隔絕而遙遠,殘雪就是通過這樣一種寫作范式的構建,帶我們進入那座城堡。在那個如夢魘般幽深、奇異和反傳統的文學圖景內部,殘雪以一種決絕的勇氣,不斷地叩問人類應該如何尋找本真的自我與意義,促使人們直面自己的生存處境,展現了她對于世俗人生的另類反思,從而抵達了被傳統觀念所遮蔽的精神真實,使得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我們尚且存在,這種心靈的探索和靈魂的挺進就永遠不會停止。
參考文獻
[1]殘雪.呂芳詩小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2][美]喬恩·格里菲思,殘雪.追求邏各斯的文學[J].作家,2010(3):110~120.
[3]徐寶鋒.宇文所安中國詩學研究的“情”“欲”視角[J].閱江學刊,2015(2):108~113.
[4]姜玉平.心靈空間的開拓——論殘雪《呂芳詩小姐》中的三個空間意象[J].宜賓學院學報,2015,15(8):49~55.
[5]姬志海.新千年殘雪長篇小說“魔幻象征化”的創作考量[J].南方文壇,2018(5):148~153.
注 釋
①姜玉平.心靈空間的開拓——論殘雪《呂芳詩小姐》中的三個空間意象[J].宜賓學院學報,2015,15(8):53.
②[美]喬恩·格里菲思,殘雪.追求邏各斯的文學[J].作家,2010(3):115.
③姬志海.新千年殘雪長篇小說“魔幻象征化”的創作考量[J].南方文壇,2018(5):148.
④殘雪.呂芳詩小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90.
⑤殘雪.呂芳詩小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91.
⑥殘雪.呂芳詩小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162.
⑦姜玉平.心靈空間的開拓——論殘雪《呂芳詩小姐》中的三個空間意象[J].宜賓學院學報,2015,15(8):53.
⑧殘雪.呂芳詩小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176.
基金資助:2021年湖南省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平臺國家級立項項目“新世紀以來湖南長篇小說中的災難敘事研究”(202110548023)結題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