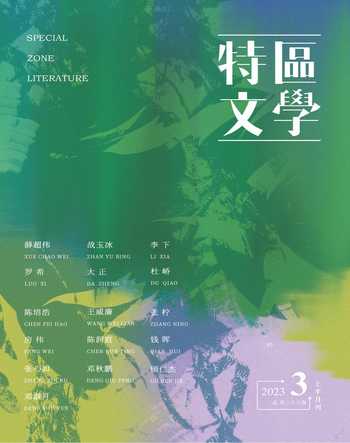回鄉,喚醒小時候的自己
一
“大巴從國道拐進鄉村公路,我看見了小時候的自己。”薛超偉小說《青梅》開頭的這句話,清楚地點出了整篇小說中的“回鄉結構”。這種小說敘事結構我們并不陌生,魯迅的經典名篇《故鄉》《祝福》都是采用了“回鄉結構”,知識分子“我”通過回鄉的旅程進而對傳統鄉土社會進行重新觀察、反思和批判,改造國民性議題與啟蒙主義觀念等皆由此得以舒張。在小說《青梅》中,這種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性隱喻也是無處不在,比如國道和村里彎彎繞繞的道路,以及城里公寓房“筆直的走廊”和村里土樓的“環廊結構”等。
進一步來說,《青梅》中“回鄉結構”的匠心之處更在于,“回鄉”由“今日之我”引出“昨日之我”,由“現在的自己”引出“小時候的自己”,從而牽引出兩條故事線交替推進、并駕齊驅。而作者薛超偉又通過敘事人稱上的巧妙變化,將“小時候的自己”充分他者化。由此,小說里“我”此次回鄉與過去回憶這兩條敘事線索,就變成了“我”與“她”或者“我”與“曉念”的兩條故事線。一方面,“我”此次回鄉的短暫旅程與所見所聞,每一個細節都勾連著“她”/“曉念”十幾年漫長的童年經歷。小說的筆觸在兩個不同的時段里自由穿梭,慢慢繪制出了昨日的“她”/“曉念”是如何變成今日之“我”的完整成長路徑。另一方面,“過去的我”的故事在第三人稱的約束下,即使講述童年創傷也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一份客觀、冷靜與不動聲色,而對感情表達的充分節制正是小說《青梅》另一個突出的優點。“曉念”童年的經歷是充滿扭曲與痛苦的,但小說對這段經歷的回憶卻并不沉溺于哀傷,相反,其中更多透露出一種時間的沖淡與理性的清明,而這種表達效果的達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說中對過去自我的他者化處理。
二
借魯迅的《故鄉》《祝福》來談薛超偉的《青梅》可能并不算太過僭越。除了三篇小說都采用了明顯的“回鄉結構”之外,《故鄉》里中年閏土與少年閏土之間的今昔對比、楊二嫂“細腳伶仃的圓規”形象與曾經“豆腐西施”的明顯變化……共同匯聚成了小說的開頭之問:“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同樣地,小說《青梅》中也充滿了這種今昔之間的細節對比,比如過去土樓里滿滿地住著一整個家族的人與現在大量親屬搬離、整個土樓顯得空落落的;又如過去“被長輩們稱為瘋子”的小姑與現在生意上做得風生水起的小姑,以及一直生活在土樓二十多年的蕙心。
不同的是,《青梅》中并沒有簡單流露出現在優于過去、城里優于鄉下的啟蒙主義或進步主義觀念,而是如小說在字里行間所暗示的那樣,“我”闊別多年,剛回到土樓時:“到了三樓,一眼望去,環廊結構讓我感到短暫的暈眩。當初在土樓住久了,搬進城里的公寓房,看著筆直的走廊,也有一段時間不適應。”即在小說中,鄉下土樓的風俗習慣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和城里公寓房里的生活經驗平等的存在。“我”的“回鄉”之旅也并不是停留在簡單揭示出傳統鄉土社會在男女性別方面的落后與陋習,而是盡力克制住主觀的情緒,冷靜勾畫出一幅鄉土生活的圖景與面貌。當然,作者在其中自有其鮮明的批判立場和態度,只不過小說并沒有因為這種作者的立場而過度干擾到敘事本身的冷靜風格。
和《祝福》相類似,《青梅》也把“我”回鄉的時間節點設置在傳統年關節日,這固然有現實生活的合理性作為依托(過年回老家是比較自然常見的現象),同時也構成了一種氛圍上的渲染和反襯。小說《祝福》里,在“遠處的爆竹聲”與“祝福的空氣”映襯下祥林嫂的悲慘命運更顯凄惶,甚至令整個“祝福”都給人以一種陰森森的鬼氣之感。而在《青梅》中,在“附近幾個村輪流‘做熱鬧”的背景下,供奉、上香、祭祖、聚會、敬酒等一系列原本代表著歡樂祥和的風俗行為,卻無一不關聯著“我”不堪忍受的童年記憶。由此,小說寫的雖然是當下的“熱鬧”場景,用的最多的形容詞卻是“冷清”/“冰冷”。
三
如果說《青梅》中多少存在著某種現在與過去、現實與回憶、城里與鄉下的對應性(而非對立性)二元結構的話,那么“過去”“回憶”與“鄉下”則顯然處于相應的結構位置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小說對鄉下空間環境的描寫,則可以更好地打開“我”的回憶世界。比如“鄉村的路不總是筆直的,它們的走向要順著山、顧著河”“村里的路二十年沒怎么變過,彎彎繞繞,石子路和土路,上坡和下坡”,這種被反復凸顯的鄉村道路的彎彎曲曲,同樣也暗示著過去與回憶的曲折、復雜、難以名狀。在這種過去與回憶中,“曉念”憎惡“冠林伯”不斷的性騷擾,卻不敢把這種羞辱經歷講述給自己最親近的表姐蕙心以及自己的父母;“曉念”似乎抓住了母親出軌的隱秘罪惡,卻又沒有真正看清這種隱秘背后的真相(即父親的無能與母親的苦悶);“曉念”曾經想要通過毒死徐公樹來殺死所有人,卻不知蕙心竟然曾經和“她”有過同樣的想法,后來又阻止了“她”的行動……過去與回憶中的點滴細節,在“我”此次回鄉的旅途中,以及物閃回的方式一一鋪展開來,通過不同片段的連接,形成了一幅生動、完整的生活畫卷。而這些引發過去與回憶的及物點,可能是土樓里“半腐的樓梯踩一下就吱呀一聲,木頭會嘆氣”,也可能是對面“屋頂上坐著兩個小女孩,看不清模樣”,還可能是“廚房里傳來菜香,很熟悉的氣味”……聲音、場景、氣味,都隨時能夠作為連通現在與過去的關節點。小說《青梅》中的兩條敘事線索的交叉與閃回,也由此產生了一種沉浸式的閱讀感受,讓讀者仿佛也置身于當下正在“做熱鬧”的土樓之中,并隨時在任何一個可能的感覺契機下,回到過去的歲月與童年回憶之中。
四
與“我”曾經離開土樓,后來又“回鄉”相對應的是蕙心一直“守在我們出生的地方”。如果說小說中“我”對于故鄉土樓的態度還相對比較明確——“村里人叫它圓寨,但我更愿意跟著外人叫它土樓。很早開始,它就不是我的家了”,那么蕙心這些年的成長經歷和對待故鄉的態度或許要顯得更為曲折、曖昧一些。一方面,相比于出走的解脫和輕快,留在原地顯然更加沉重,且需要更多的隱忍態度,“時間好像重一些,因為往事層疊在此處,會以數倍的分量壓在人身上”;另一方面,留守鄉下的生活也并不完全是一種單純的苦難敘事,正如小說中描寫大伯母和小姑時所說的,“她們都是熱熱鬧鬧、認真生活的人,我為她們高興”。蕙心也顯然屬于這群“熱熱鬧鬧、認真生活的人”之中的一個。
在這個意義上,與“我”整個回鄉過程中,無所顧及地冷嘲熱諷,甚至多次想要故意激起“冠林伯”的怒氣相比,蕙心最后的爆發竟然比“我”更為激烈且直白得多。小說在這里完全拋開了“回鄉敘事”中經常相伴而生的啟蒙主義敘事期待,即它并不是要講述一個從城里“回鄉”的“我”,用更豐富的知識和更進步的觀念來喚醒一直生活在鄉村的蕙心的俗套故事,而是讓多年來承擔了更多、隱忍了更多的蕙心最終獲得了一場更具破壞力的爆發。
進一步來說,小說中這種對啟蒙主義敘事俗套采取“反寫”策略所牽扯出的更為復雜的情況在于,“我”或者蕙心,對于故鄉土樓及其所象征的傳統鄉土社會的態度,并不是單純的否定與批判,其中更帶有一份“殘忍的留戀”,即“我躺在這里,躺在過去的殘余里,發現自己無論經歷過什么,依然會對這里生出留戀。這種留戀很殘忍”。換句話說,小說中的“我”固然通過離開土樓、進入城市、“故意學很硬的知識”、選擇了“女孩子學了,別人就覺得你很難嫁的東西”,已經相當程度地擺脫了“曉念”童年創傷經歷所帶來的心理陰影。即使“往事會出現在我眼前,出現在夢里。但我已經不害怕了”,甚至“我”對肉體的疼痛也感覺麻木,以至于同事“說我這人很可怕,鎮靜得像個沒有痛覺神經的動物”。“我”在經歷了這種種后續的成長之后,已經完全不同于當年無知、弱小、任人凌辱的“曉念”,“現在,當我看到從前的自己,很想告訴她,不要害怕,沒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她會聽見嗎”?但與此同時,“曉念”之于“我”,又不僅僅是童年創傷與痛苦記憶,其中也有“小時候我跟蕙心、揚波三個人經常會趁著這份熱鬧溜出去玩”的快樂、有對家人親情的眷戀和故鄉風土的懷念。至此,小說中“我”、蕙心與土樓所代表的故鄉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難解:“我”與蕙心,似乎既構成了離開與留守的一體兩面,同時又都作為女性內心覺醒的發聲者;而我們之于故鄉土樓的關系,則包含有生養之地、血脈之親、痛苦之源與生活經驗實感等多個豐富面相。
五
毋庸諱言,對傳統鄉土社會中男女性別地位不平等的批判,是小說《青梅》最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觀,在小說克制、冷靜的主要敘事風格之外,凡是作者忍不住直接表露自家立場與態度的地方,無一例外都是關乎性別議題的內容。在小說“創作談”中,作者薛超偉也明確指出這篇小說的創作緣起就是因為他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和不吐不快,為此他甚至選擇了使用“女性角色為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扮演”式表達策略。
回到小說文本中,土樓世界的男女不平等隨處可見:從“女人是不凈的,女人不能處在比男人高的位置,如果一個男人不小心從女人的胯下經過,會給家里招來不幸,那么,女人騎在最高的屋頂,就是對家里所有男性的不敬”,到“女孩的內褲不能掛在外面,只能在自己的房間陰干”;從男孩們可以肆無忌憚地聊“與身體有關的話題”,而“那對女人來說是禁忌”,到“女人是不能太開心的……從此她要學著盡量不讓開心露出來,把它當作自己的一條尾巴”……土樓世界里各種有形無形、或顯或隱的對女性的束縛和壓迫可謂無處不在,更何況還有“曉念”和蕙心童年時所經歷的既不敢拒絕、又無法對別人傾吐的長久的被侵犯。而因為身材矮小而處于男性隊伍末位、被其他男人瞧不起的“冠林伯”對“曉念”的凌駕和侵犯,其實更突出表現了土樓世界里男女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在這種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性別顯然是小說《青梅》的核心議題。而這種性別不平等,其實更加關乎到一種自由的問題,一種指向僭越倫理束縛的邊界、可能和勇氣。比如土樓里男孩可以站在屋頂,可以肆意談論與身體有關的話題,這就是一種女性所沒有的自由。小說對此也有著明確的認識和表達,“我體會到年幼時在揚波哥哥身上見到的那種自由。那種叫自由的東西,男人生下來就有,女人卻需要變成蕩婦才能得到”。
當然,如果我們就此把性別議題作為理解小說《青梅》的唯一價值維度,又顯然是大大減損了小說本身的豐富性。比如,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輩分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維度,這在類似于“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等民間俗語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樣是傳統家庭中的女性,隨著輩分的躍升,就會出現從被壓迫者轉化為壓迫者的變化。在小說《青梅》對家族關系的描摹過程中,輩分也是一個被多次提到或暗示的重要因素:“我逐漸知道,輩分決定了很多東西。如果是我們跟爺爺這樣吵,長輩會一起來教訓我們,但如果換作小姑,他們卻只是勸架而已。這也給了我一點啟示,時間會賦予人力量,他們只不過是被時間充了很多氣的氣球而已。”
另外一個重要的維度則在于經濟能力或者說物質基礎,借用下戴錦華老師的說法,就叫作被性別議題掩蓋的階級問題。比如小說里小姑的行為處事方式一直與土樓世界顯得格格不入,小姑也因此“被長輩們稱為瘋子”,而后來隨著“她懂得了隱藏,也獲得了世俗意義的成功,所以再沒有人說她了”。小姑在家族中地位的變化,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個人經濟條件也是形塑其家庭地位、形象,乃至話語權的重要因素。類似的角度也可以用來理解“我”與蕙心之間的差別,“我”與蕙心之間的對應性關系不僅僅是前文所分析過的離鄉與留守、現代與傳統、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其中還包含有“我”在城市里通過專業知識成為了一名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在經濟條件上遠勝于蕙心,因此家族父老也相應給予“我”更多的寬容和自由。
六
當然,不管從主觀意愿還是客觀效果哪一個方面來說,性別議題仍然無疑是小說《青梅》最重要的話題內容。其中,或者像“我”通過離開而漸漸忘卻曾經的痛苦,并以一個外來者的姿態重新挑戰各種傳統倫理的教條;或者像蕙心因留守而只能繼續隱忍這種性別上的不平等,最終因長久的壓抑而獲得一種更為激烈的爆發;或者像作者借助表妹這一戲份并不多的人物形象所表達出的美好祝愿:“我捏她的臉,她躲我。她會感到驚奇,說明她沒有類似我和蕙心的經歷,我真心希望她們都有這樣的驚奇。”
這種驚奇其實是一種未經社會摧殘的童真與純凈,愿這樣的驚奇永遠存在下去。
戰玉冰,文學博士、博士后,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