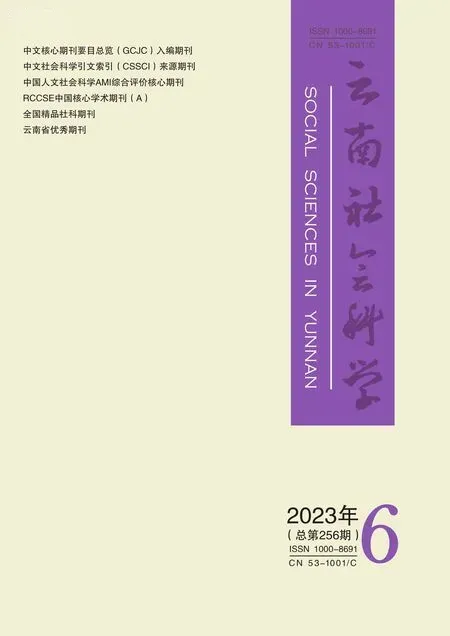邊民“國民化”:現代邊境建構的題中之義
孫保全 胡興梅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邊境在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相關議題也被列入國家決策性文件之中。與此同時,作為生活于邊境地區的居民,邊民及其相關問題也開始得到社會各界前所未有的關注。黨的二十大提出要“推進興邊富民、穩邊固邊”,進一步通過“興邊”和“富民”的正式表述,把邊境和邊民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重要的知識性問題被凸顯出來:邊境和邊民之間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或者說,邊境和邊民是通過怎樣的機制而發生關系的?反觀當前的相關研究,尚未非常清晰地提出并闡釋上述問題。這主要與兩種研究偏好有關:一是以往研究多從跨界民族、跨境貿易、跨國婚姻、跨境犯罪等具體領域出發,而沒有在整體層面、本質層面上分析邊民與邊境間的耦合性;二是在既定的時間斷面上,相對靜態地看待邊境、邊民及其關系,而非將其置于歷史演變的動態過程中加以考察。這樣一來,邊境僅被看作邊民生產生活的空間場域,而邊民則被視為邊境治理的對象,或被視為守邊固邊的社會力量,邊境與邊民的關系被簡單化。
作為一國國土的邊緣性部分,邊境具有突出的國家建構性特征。《國語》中記載的“夫邊境者,國之尾也”①(春秋)左丘明:《國語》,尚學鋒、夏德靠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303 頁。,就是對中國傳統邊境形態的一種描述。近代以后,與國家主權體制相伴而生的線性邊界的出現,對于邊境建構范式的現代化產生了根本性影響。自此,邊界之“邊”和表示縱深性區域的“境”,成為現代邊境的兩大構成要件。而現代邊境形成以后,仍處于不斷建構的過程當中。其一,國家可以選擇以何種空間口徑來劃分邊境向內延伸的范圍。其二,邊境與內地之間的異質性程度,會隨著邊境治理的持續開展而逐漸削弱。其三,邊境既是拱衛國家安全的屏障,也是國家對外開放的前沿,而“安全”和“開放”雙重功能的發揮,離不開國家對邊境空間的布局和整治。
邊民即邊境地區的常住居民,同邊境概念一樣,也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如《史記?匈奴列傳》曾記載:“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①司馬遷:《史記?卷110》,甘宏偉、江俊偉評注,武漢:崇文書局,2010 年,第633 頁。當然,彼時邊民與今日邊民的涵義大不一樣。當代中國的邊民身份,不僅意味著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還蘊含著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在國家沿邊開發開放政策中,將邊界線3 公里范圍內的居民,列入享受邊民補助政策的對象;在9 個邊疆省區各自出臺的邊境管理條例中,通常把邊民認定為邊境縣域內的有常住戶口的公民;而“在具體的邊境縣治理實踐中,通常又是以上級政府實施的邊民補助政策為導向和規約,由此形成的邊民范疇是指沿邊行政村范圍內的居民”②夏文貴:《論邊境治理中邊民角色的轉換與重塑》,《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
邊民“國民化”主要是指,邊境常住人口擺脫傳統社會政治身份并不斷獲得“國民”屬性的過程,包括取得國民身份、形成國民意識、享受國民權利、履行國民義務等諸方面。而邊民“國民化”問題,是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宏大背景下,伴隨現代邊境的建構進程而不斷被凸顯出來的。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而言,建構起與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相適應的邊境形態,并在此基礎上開展現代化的邊境治理活動,都無法回避邊民“國民化”問題。就此意義而言,通過歷史梳理來揭示邊境內涵、邊民屬性及二者之間的互構關系,對于理解“興邊”和“富民”的深刻內涵,進而推動邊境治理現代化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二、“有邊陲而無邊界”時代的邊民屬性
對于中國來說,邊境和邊民皆為古已有之的詞匯。但無論是古代的邊境還是邊民,都與今天二者的含義相去甚遠。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把前主權時代的國家描述為“有邊陲而無邊界”③[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第4 頁。。在缺少穩定邊界作為參照的條件下,古代中國的邊境與邊疆幾乎是一對同義詞,是由內而外地進行界定和劃分的,地處核心區的周遭、外圍,且被視為王朝中央控制的末端。在缺乏主權體制規約的疆域架構之中,核心區是王朝存續的根本,中原地區的淪喪往往意味著一個王朝統治的終結;而邊境則處于附屬性的次要地位,在必要之時曾被認為是可以舍棄的。因此相對于核心區域,邊境的存廢盈縮顯得非常頻繁。
邊境本身呈現出結構性或層次性的特征,即不同邊境地區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由于地理環境對于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結群形式的深刻影響,歷史上中國的邊緣性區域可分為形態各異的幾大文明板塊,包括東北漁獵耕牧文明板塊、大漠游牧文明板塊、雪域牧耕文明板塊、山地文明板塊、海洋文明板塊等。④于逢春:《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類型及其統合模式序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3 期。以同中原王朝的親疏關系、受華夏文明影響的深淺程度為標準,可以進一步把這些邊境地區劃分為若干層次。先秦時期“五服”“九服”的“服事觀”就帶有疆土分層的意味;秦漢之際,開始有意識地把南部邊地作“蠻夷”和“半蠻夷”⑤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711 頁。之分;唐代則以“海內”和“海外”來分別指代夷狄之地及更為疏遠的屬國;宋代區分邊境的方式較此前更為細化,出現了“外邊”“內邊”“次邊”等具有軍事防衛和文化分野內涵的邊境概念⑥杜芝明、黎小龍:《“極邊”、“次邊”與宋朝邊疆思想探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2 期。;而明清以后大量使用的“內藩”“外藩”和“生番”“熟番”,可視為對歷代諸朝邊境觀念的繼承和發展。
在這樣的疆域格局中,王朝國家邊境地區的人口形態也表現出鮮明的異質性特點。秦漢以后,隨著中央集權體制下編戶齊民制度的確立,中原地區的居民始漸成為皇帝的臣民和子民。而在王朝的邊境,邊民的身份屬性和分布狀況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漢代班固曾對此有過描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①(東漢)班固:《漢書?卷94?下》,陳煥良、曾憲禮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第1669 頁。當然,這樣的記述帶有想象性和歧視性的色彩,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邊境居民與內地居民之間深刻的二元性區隔。此外,對于生活在不同文明板塊中的邊民來說,彼此差異性也非常突出,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正是對邊民區域性差異的一種表達方式。
邊民本質上是國家人口的一部分,因此僅僅從核心區視角、邊境視角來看待古代邊民是不夠的。若要在人口形態上對邊民身份作出準確而深刻的判斷,就離不開國家視角,特別是國家與邊民關系的認知角度。歷史上,有些邊境地區的居民受王朝政權和中原文化的影響較深,有些同中原勢力的關系相對松散,還有些則生活于與世隔絕的封閉性的社會場域之中。如此一來,邊民的分布態勢就形成了一個以王朝中央為內核的同心圓結構,或者說是構成了一個國家性的差序格局,處于不同圈層中的邊民具有不同的身份屬性。按照這樣的關系邏輯,古代邊民可大致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準臣民”,即雖與內地居民有異,但也受到中原王朝較為緊密控制的邊民。在秦王朝剛剛統一六國的時候,中國的版圖還比較有限。此后經過歷代的開拓和經營,周邊的土地和人口逐漸納入統一的版籍之中,最終在清朝中期完成了國家疆域的底定。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原本社會異質性非常突出的邊境地區,經過中原王朝長期持續的統治和治理,發生了內地化和同質化的轉變,該地居民也逐漸成為王朝的臣民。比較典型的就是清雍正年間,先后在西南多個地區實施了改土歸流,繼而在這些地區設置府縣、增設軍事機構、清查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賦稅。原土司地區的廣大居民,由此納入王朝直接管轄的人口范疇。但從改土歸流后陸續發生的叛亂來看,這樣的邊民還不是完全忠于朝廷的臣民,而是一種向背不定的“準臣民”。
第二種“化外之民”,即受王朝力量影響極小,對王朝國家缺乏基本感知的邊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交通通信不便的傳統社會中,自然地理環境對人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對于一些生活在封閉空間內的邊民來說,雖然置身于王朝國家的版圖之中,但同來自中原的政治勢力和文化勢力長期保持著兩不相知、兩不相擾的隔絕關系。“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是這類邊民國家意識的生動寫照。如居住于今天中緬邊境獨龍江鄉的獨龍族,到了清初期才開始被外界所知并粗略地記錄于史冊,直到20 世紀50 年代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發展階段。實際上,在遙相羈縻、因俗而治的治邊方略下,中原王朝與普通邊民之間通常沒有建立起直接而緊密的聯系。他們只知頭人、領主而不知皇帝,以及只知村寨、族群而不知國家,是邊境地區一種普遍性的文化現象。
第三種“交互型居民”,即處于上述兩種人口類型的中間狀態,受到中原王朝和周邊政權交叉性管理的邊民。作為西方學者里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先驅和佼佼者,拉鐵摩爾提出,在亞洲內陸和中國(中原)之間存在著一個“邊境世界”。由于同時受到農耕文明、游牧文明的交互影響,這個“邊境世界”具有“過渡地帶”“混合文化”“混合經濟”的人文地理特征。而生活于過渡性地區和混合性社會中的邊民,也就具有了中原農民和草原牧民的雙重身份。②[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322,324,376 頁。另有研究發現,漢代某些邊郡居民雖屬編戶齊民,卻與“蠻夷”雜處,雖來自中原,卻漸染“夷風”,從而形成了介于華、夷之間的族群身份。③朱圣明:《漢代“邊民”的族群身份與身份焦慮》,《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 年第3 期。這種邊民類型可稱之為“交互型居民”,他們同中原王朝的關系比“準臣民”更疏遠,但又遠比“化外之民”更密切。
這樣一種邊民社會政治身份,是在王朝國家時代形成的,同“有邊陲無邊界”的傳統邊境及其治理相適應。或者說,此時的王朝、邊境、邊民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強化。從更大的空間視野來看,王朝、邊境、邊民之間的互動邏輯是在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文明系統(經常被稱為“天下體系”)中產生的。但到了王朝國家末期,當古老的中華文明因受到西方勢力挑戰而無法獨善其身之時,中國的政權、疆域、人口都被推向了現代化轉型的軌道之中,建構現代化的邊境空間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邊民身份,也就成為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
三、邊境形態轉型與邊民的“去地域化”
晚清以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蹣跚開啟,推動邊境形態由碎片化向整體化、領土化轉變,邊民屬性由地域性、離散性向國家化、向心性轉變,成為一種大勢所趨。不過,近現代的邊境觀念與今天大不一樣,是以省級單位進行界定的,因此基本上與“邊疆”是同義詞。1931 年國民政府內務部頒發的《提倡國人考察邊境辦法》就明確規定:“本辦法所指邊境暫以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西康、云南、廣西為范圍。”①《提倡國人考察邊境辦法》,《現代法學》1931 年第8 期。而邊民當然也不是狹義的沿邊居民概念,而是邊疆居民的意思。究其緣故,大抵是因為此時整個邊緣性區域的異質性都非常突出,沒有將邊境和邊疆進行明確區分的必要,另外這也延續了古代邊疆和邊境概念的同義性傳統。
在中國國家形態由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轉變的過程中,晚清及后來的民國政府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展開邊境重構的。一是邊界與領土的構建。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季的疆域外圍出現了斷斷續續的邊界,并在一定限度內獲得了主權領土的外部承認。在此基礎上,民初政府通過廢約、修約活動,推動了邊境空間的領土化。二戰以后,中國的國際地位大為提升,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也獲得了更具實質性的內涵。二是邊境地方政治制度的變革。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晚清時期的邊疆建省、北京政府設置熱河、綏遠、察哈爾特別行政區,南京國民政府在邊境地區推行省制、縣制等等。經過一系列變革,邊境不同于內地的政治地理屬性愈發淡化,而作為統一行政區劃的“地方”性質變得越來越突出了。三是邊境治理的加強。從清末邊疆新政、邊疆開禁,到民國初年的開墾蒙荒,再到國民政府時期的“西北開發”“西南開發”,邊境地區的開發建設日漸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上述過程中,圍繞邊民“國民化”改造的活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從而在上述“空間”建構的基礎上,為現代邊境增添了“人口”內涵。作為一個舶來概念,“國民”是指具有國家意識、享有公民權利和公民利益的居民身份。然而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下,近現代中國國民塑造的重心在于“國”而不在于“民”,尤為強調在國家主義取向下對國內人口進行重新凝聚,這一點對于“山高皇帝遠”的邊民來說顯得尤為突出。如何使廣大邊民從邊緣性、封閉性的地理空間與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成為具有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效忠感的國民,就成為現代邊境建構乃至國家建構的重要任務。就此而言,近現代的邊民改造是沿著“去地域化”和“國家化”的路徑漸次展開的。
在列強環伺的國防壓力之下,清廷一改此前實施的邊境封禁政策,開始逐步開放邊境并大力推動邊境的內地化。此后,加強邊境整合、邊境與內地的一體化,成為中國邊境建構的基本取向,這就為邊民的國民化轉變提供了前提性條件。晚清政府在邊境地區的“造國民”活動大體包括了三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在新疆、臺灣、東北地區設置行省、府縣,改變過去統而不治的局面,在此基礎上對當地居民實施直接管理和征繳賦稅,推動邊民從“藩部之民”向“國家之民”②王珂:《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238 頁。發生轉變。其次是繼承和發展了歷史上的移民實邊之策,隨著大量的內地居民涌入沿邊地區,邊民的規模和結構都發生了明顯改變。最后是對于邊地文化的態度由“因俗而治”轉變為“化彼殊俗,同我華風”③袁大化:《新疆圖志》(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11 頁。,對邊民施以“國語、國史、中國地理等方面的教育”,以此增進其“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意識”④阿地力?艾尼:《清末邊疆建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217 頁。。
辛亥革命以后,擺在民國政府面前的一大任務就是,“把清朝統轄下的各族民眾轉化為‘中國國民’,并在這樣一個地域和人口范圍內建立一個完整的‘中華國族’(a Chinese nation)”⑤馬戎:《民國時期的造“國民”與造“民族”》,《開放時代》2020 年第1 期。。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孫中山就表示:“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辦公廳:《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 年,第24 頁。,這種國民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在此后的歷部憲法中不斷得以確認和鞏固。邊民自然也屬于國民的范疇,時人對此也有明確的認知:“邊疆為我版圖之邊疆,邊民亦即我國民之一部”②陶云逵:《開化邊民問題》,《西南邊疆》1940 年第10 期。;“蓋邊地人民,漢人少而土著多,同生長于本國領土內之人民,均是中華民國國民,在理論上,實不必有民族之區分,此為整個國家政治與國民義務關系而言”③楊成志:《西南邊疆文化建設之三個建議》,《青年中國季刊》1939 年第1 期。。
在這樣的整體形勢之下,邊民身份的“國民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第一,確認邊民作為“國民”的政治法律地位。中華民國成立以后,歷屆政府無一不將邊境視為國家的領土,將邊民視為國家的國民。尤其是通過憲法性文件的規定,逐漸明晰了邊民“由何種途徑,來表達他們對國事的意見,來參加國家的政治”,以及在國家憲政體制中“是怎樣的地位”的國民權利問題。④芮逸夫:《行憲與邊民》,《邊政公論》1947 年第3 期。第二,邊民及邊民社會的調查。開展普遍性的人口調查,是顯示國家能力的一大指標,也是確定和落實國民權利的前提。⑤陳玉瑤:《國民團結:法國的理念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第114 頁。在國民政府時期,由官方主導的邊民調查活動陸續展開,如20 世紀40 年代云南省民政廳就曾主持編印了《全省邊民分布冊》,對各類邊民人口數量做了比較精確的統計⑥民政廳統計室:《云南全省各種邊民人數統計表》,《云南民政月刊》1947 年第1—3 期。。第三,邊境地區的國民教育。民國學者楊成志在著名的《邊政研究導論》一文中,曾把“邊民開化問題”列為當時“千頭萬緒百端待舉”的邊政問題之首。⑦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廣東政治》1941 年第1 期。在實踐層面上,以推動“‘蠻夷’向‘國民’轉化”⑧陳征平:《近代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內地化進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96—110 頁。為基本取向和內容的教育活動,也開始在邊境地區展開,并取得了一些值得稱道的成效。第四,國民改造運動。這一時期,由政府聯合知識分子開展的多種社會運動,也涵蓋很大一部分的邊境地區。這些運動包括國民外交運動、鄉村建設運動、邊疆社會服務運動、國語運動、新生活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等。
抗日戰爭爆發對于邊民的國民身份塑造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亡國滅種的巨大壓力之下,包括邊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被喚醒。來自邊遠地區的廣大邊民開始紛紛公開聲明自己“與全國同胞責任平等,休戚與共”的“國民”身份⑨《蒙藏回族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致全國同胞電》,《西北論衡》1938 年第8 期。,并以實際行動履行國民義務。地處西南邊陲的瀘水設治局(今瀘水市),就曾在滇西抗戰中“前后捐獻糧食共12.5 萬公斤,出動民夫50 萬人次,民夫負傷56 人,死亡208 人”⑩瀘水縣志編纂委員會:《瀘水縣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376 頁。。同仇敵愾的抗戰經歷,使得一種國家主義的政治文化在邊境社會傳播開來,并內化為廣大民眾的國家認同和國民意識,邊民的國民化進程由此被大大推進。
四、邊境鞏固發展與邊民身份的根本性改造
在近現代中國的主權國家建構的時代背景下,邊境形態、邊民身份都發生了重大轉變。然而在風雨飄搖的時局之下,囿于有限的國家能力,無論是晚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都始終未能實現對邊境領土的全面整合,也未能實現對邊遠人口的徹底改造。中國的國民塑造,還主要局限于“居于中國政治空間核心及社會上層之主流知識分子”?王明珂:《民族與國民在邊疆:以歷史語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為例的探討》,《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2 期。,而對于底層民眾和邊境居民的影響還十分有限。這從民國學人凌民復的描述中也可略窺一斑:邊民“既缺乏國家觀念,又無民族意識。散處邊地,易受外人誘惑,今日為中國人,明日亦可為外國人。……對于國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險殊甚”?凌民復:《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西南邊疆》1938 年第2 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家發展步入新的歷史紀元。執政黨和國家力量不僅“下了鄉”而且“到了邊”,現代邊境的建構進程由量的積累變為了質的飛躍。一是領土性邊境空間的構筑。對于新生的國家政權來說,“我們同周邊國家都有邊界糾葛,解決好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335 頁。。自20 世紀50 年代起,中國政府便著手勘界和劃界活動,到了60 年代中期,近一半的陸地邊界線得以標定,“有邊無界”的邊境樣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二是邊境地方建制的統一安排。自上而下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在省區層面設置“省”和自治區,在縣域層面廢除了“設治局”等過渡性的地方政權,統一設立縣、自治縣和自治旗。三是建立現代化的邊防體系。建立以軍事防衛為重心的人民邊防制度,組建軍、警、民聯防的武裝防衛力量,解決了“有邊無防”的問題。四是凈化邊境地區的政治生態。主要表現為驅除影響邊境安全穩定的境外勢力,以軍事手段清除邊境匪患和國民黨殘余勢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邊境空間的整體性改造,為邊民國民身份的進一步塑造創造了必要條件。但邊境建構和國民塑造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錯位性,或者說“人”的改變要相對滯后于“地”的改變。這一時期,在中蘇邊境地區,由于“當地居民對國家、祖國認識的模糊”,“祖國觀念的混亂,國界觀念也極為淡薄”,“邊防概念模糊,邊境管理不善”,出現了大量邊民非法遷居國外的“伊塔事件”②李丹慧:《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歷史考察》,《黨史研究資料》1999 年第4 期。;而在已經劃界的中緬邊境上,因缺乏國別和領土觀念而導致的過境放牧、過境耕種,以及改變邊界走向、移動邊界標志物的現象仍時有發生。③瑞麗市志編纂委員會:《瑞麗市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第227—228 頁。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沒有邊民的國民化,就沒有邊境及邊境治理的現代化。這種邊境與邊民之間的失衡關系,經過一系列的國民塑造舉措而逐步得到了協調和平衡。
一是政治法律地位的“人民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國內人口性質的改造是按照階級理論指導下的“人民化”路徑展開的。④周恩來曾專門對此做過說明:“‘人民’與‘國民’是有分別的。‘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反動階級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分子。而對官僚資產階級在其財產被沒收和地主階級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極的是要嚴厲鎮壓他們中間的反動活動,積極的是更多地要強迫他們勞動,使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人民范圍,但仍然是中國的一個國民,暫時不給他們享受人民的權利,卻需要使他們遵守國民的義務。”參見《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68—369 頁。而在邊境地區,這樣的邊民“人民化”又大致經過了三個環節:統一性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為廣大邊民獲得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創造了基本條件;通過階級劃分和社會政治地位重構,消解上層勢力與底層民眾的不平等關系;突出邊民的民族身份,開展民族識別和民族工作,構建新型民族關系,從而經由各族人民之間的平等來實現國民平等。
二是經濟生產關系的“去依附性”。歷史上,在各邊境地區傳統性的經濟基礎之上,邊民社會存在著多樣性的人身依附關系。對此,在邊境的農業區、牧業區開展的以“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改造,從根本上改變了既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廢除了封建制度、奴隸制度、政教合一制度,逐漸將整個邊境地區引向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廣大邊民“從過去‘人身依附’的被壓迫地位,成為國家政權和土地的主人”⑤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年,第681 頁。。
三是社會文化形態的“去孤立化”。即把邊民從過去狹隘的空間場域和認知視野中解放出來,推動社會文化從家族性、村落性、部落性向國家化、國民化發生轉變。這樣一種打破“孤立化”枷鎖的國民塑造機制,是從由外而內的“嵌入式”路徑開始的,具體包括:人員的嵌入,通過知青支邊、部隊成建制轉業的屯墾戍邊等方式,改變了邊境地區的人口構成和社會文化;教育嵌入,按照當時的話語來說,就是通過多重性的文化教育機制來“改造舊的社會、舊的思想、舊的人,建立新的社會,新的思想,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⑥張養吾:《十年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偉大成就》,《民族研究》1959 年第10 期。;符號的嵌入,通過國旗、國徽、黨旗、領導人畫像、宣傳標語、政治口號等文化政治符號的展示和傳播,繼國家政權的“硬在場”之后,實現了國家認同的“軟在場”。
經過上述環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及此后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現代化的邊境空間和國民化的邊民形態在整體上被建構起來。改革開放后,這樣的建構過程得到了全面升級和發展。在邊境建構層面上,除個別地區外全面勘定了邊界,并專門出臺了沿邊開發開放、邊境轉移支付、支持邊境經濟貿易等政策,設立了一大批陸地邊境口岸,成立了若干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進而在以往“安全”“穩定”邊境治理取向的基礎上,大大強化了“發展”“開放”的邊境空間定位。與此相適應的是,邊民的國民化內涵也不斷得到豐富。尤其是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興邊富民”行動、沿邊居民生活補助、邊民互市優惠等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增進了邊民的國民權利和國民利益,增強了邊民的個體發展能力和家庭發展能力,為邊民居邊生息、守土固邊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邊民群體在整體層面上實現了從傳統社會身份向現代國民身份的轉變,但這并不意味著邊民國民化的完全終結。特別是在不同區位的邊境空間內,邊民的國民化程度還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如在一些邊境地區,還有大量的居民不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有些地區的邊民保持著日常性的跨界流動習慣,而很多時候這種跨界活動是有悖于國家出入境管理規定的;在部分邊境地區,還居留著由于各種原因產生的無國籍人口;等等。這樣的區域性差異表明,邊民的“國民化”問題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有可能制約“加強邊疆地區建設,推進興邊富民、穩邊固邊”戰略目標的有效實現。
五、邊境再建構與邊民“國民化”的新議題
邊境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邊民是國家人口中的特定群體,二者皆以國家為存在載體,離開了國家就無所謂邊境和邊民了。因此,國家本體的演變發展必然會引發邊境空間、邊民身份的深刻變化。近代以后,隨著中國國家形態由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轉型,以及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邊境和邊民的屬性及其建構都發生了范式性的變遷。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現代化的邊境空間和國民化的邊民身份被逐漸塑造出來。時至今日,中國的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又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以國家為本質內涵,同時又服務于國家治理與發展的邊境,面臨著“再建構”的課題。其一,中國已然由此前強調重點區域開發建設的非均衡發展階段,轉向了整個國土空間總體布局的均衡化和整體性發展階段。而作為“老少邊窮”的代名詞,邊境社會總體上處于相對落后狀態,推動邊境地區的振興是補齊國家發展戰略短板的必然要求。其二,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國家利益逐漸溢出領土空間之外,國家發展對外依存度與日俱增。在此形勢之下,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外向型國家發展戰略陸續實施,從而對邊境在國土空間格局中發揮通道、門戶、前沿的開放性功能提出了全新期待。其三,經過改革開放40 多年的快速發展,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大幅提升,從而為調配更多資源用于邊境地區開發建設提供了基礎性條件。
在全新的歷史定位上建構一個更具安全、穩定、和諧、發展、開放特性的現代邊境,就變得勢在必行了。以往的經驗一再表明,現代邊境建構離不開邊民和邊民社會的基礎性支撐,邊民的分布形態和身份屬性直接攸關邊境空間功能的發揮和邊境治理的成效。就此來看,打造升級版的邊境,就意味著要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繼續推進邊民的國民化進程。從目前的情形來看,有五個議題顯得尤為突出。
首先,邊民權益和國民義務的平衡。與內地居民相比,邊民除了履行基本的國民義務之外,還承擔著守土固邊的職責。而在資源稟賦相對匱乏的邊境地區,邊民的抵邊居住、靠邊發展卻經常陷入“一方水土不能養一方人”的困境。近年來,各級政府在邊民生活補助、邊民抵邊就業、邊民互市貿易等方面給予了特殊照顧。但總體來看,邊民的國民權益保障仍顯得不足。一是邊民福利不足以支持邊民義務。對于產業結構比較單一的邊境地區來說,僅靠農業產出和沿邊補助,并不足以實現居邊致富,自然也就無法安心固邊。二是“邊民”的劃定范圍偏小。目前各地多以抵邊村來劃分邊民,并據此來實施各類優惠政策。這樣一來,享受相關政策待遇的“邊民”,遠小于國家以縣域為單位劃分的“邊境”范圍。三是邊民政策的內容較為單一。如作為中國的鄰國,越南實施惠邊實邊政策的力度非常大,而且涉及邊民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在農業畜牧業生產、小額信貸、教育、衛生、扶貧、住房補貼、征兵等方面,都出臺了專門的扶助性政策。相比之下,中國邊民政策并未全面覆蓋上述諸多領域。①相關材料來自筆者在中越邊境地區的實地調研。
其次,“邊民意識”的重塑與強化。在現代邊境的再建構過程中,廣大邊民守邊固邊基礎性功能的充分發揮,除了與邊民享有的權益有關,還同其所秉持的“邊民意識”直接相關,即“沿邊居民基于邊境場域而形成的對于國民身份的確認,對于國家利益的認同,以及對于守邊固邊職責的自覺”②孫保全:《邊民意識:一種重要的邊境治理資源》,《廣西民族研究》2019 年第2 期。。邊民意識建立在一般性的國民意識基礎之上,并且強調這樣一種觀念:作為特定類型的國民,邊民擔負著特殊性的國民責任和義務。這對邊民國民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單是領土認同和國籍認知問題,還包含著致力于邊境治理的責任感、能力感和效能感。并且,隨著邊境治理由傳統的邊防內涵,拓展為安全、穩定、和諧、發展、開放的綜合性內涵,邊民意識也不再僅僅指向“保家衛國”“守土固邊”,而是要適應整體性的國家發展和邊境治理形勢。這對邊民國民化的目標和路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再次,邊民“個性”與國民“共性”的統合。邊民是一類具有獨特習性的社會群體。其中,以跨境交往、跨境謀生、“用腳投票”來進行國別選擇等為主要表征的“流動性”,是邊民不同于內地居民最典型的群體特性。曾經中國邊民外流到鄰國,以及今天他國邊民流入中國,就是這種“流動性”的集中表現。這種習俗是在千百年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同時也受到邊境地區特有的地緣、族緣、文緣、業緣環境根深蒂固的影響,所以只能因循、規約,而不能斷絕、取締。以“一刀切”標準來規定和限制邊民的跨境活動,表面上維護了邊境的安全和秩序,實際上并不利于“興邊”和“富民”。在強調邊民同質性國民身份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邊民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形成邊民習性和國民塑造的有機統合。
復次,無國籍人口國民身份的確認。在中國邊境地區長期居住的,除了本國居民之外,還有一些身份尷尬、難以界定的無國籍人口。其中一部分來自非法的跨國婚姻。許多嫁入中國的鄰國婦女,由于無法按照《中國邊民與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辦法》等法律法規辦理相關手續,因此未能取得中國國籍,自然也就無法享受相應的國民待遇。另外一部分來自外流邊民的回遷。20 世紀90 年代以前,曾有大批邊民遷出中國并流向鄰國,因此喪失了中國國籍。而隨著中國社會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外流邊民又紛紛返回故土,但無法重新獲得國民身份。對于這些無國籍人口,各地方政府采取了登記造冊、簽發《境外邊民居留證》《臨時居留證》等方式進行管理。但這畢竟只是權宜之策,尚未在根本上解決無國籍人口的國民化問題。
最后,邊民國民化的區域性差異問題。受到內外環境的疊加性影響,不同邊境區域的邊民國民化往往存在著顯著差異。有些地區的邊民國民化程度較高,而有些地區則相對偏低。另外,在現代邊民身份的建構過程中,有的區域側重于守邊固邊的安全導向,有的區域則趨向于開發開放的邊境發展內涵。為適應新的時代形勢,一方面要全面提升整個邊民群體的國民化水平,另一方面還應從“安全”和“發展”這對現代邊境建構的雙重目標出發,塑造更具完整性和現代性的邊民身份和邊民意識。
六、結論
第一,邊境與邊民皆為變動的存在,尤其受到國家發展階段的決定性影響。在傳統王朝時代,國家有邊陲而無邊界,邊境呈現出碎片化的空間格局,邊民的身份屬性則迥異于內地的臣民。隨著主權國家的構建,邊境與邊民均被納入國家一體化的整體進程中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邊境和邊民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徹底改變了邊境和邊民的性質與面貌。近年來,國家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由此對現代邊境建構和邊民國民化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邊民國民化是現代邊境建構的基礎性環節。邊民構成了邊境的人口維度,也是邊境在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中發揮其地理空間功能的基本條件。中國在領土空間內開啟現代邊境建構的同時,也開啟了邊民的國民化歷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邊境建構目標的轉換都伴隨著與之相適應的邊民身份的形塑。離開了邊民國民化的基礎性支撐,所謂的現代邊境便徒有其表、形同虛設。立足今天的時代背景,建構一種安全、穩定、和諧、發展、開放的新型邊境,同樣需要在更高層次上持續推進邊民的國民化。
第三,邊民國民化不是簡單地確認國籍的問題,而是具有綜合性的意涵。作為現代國家普遍性的人口形態,國民身份是由國民意識、國民權利、國民利益、國民文化等多個維度有機構成的。而邊民國民化則意味著傳統身份屬性的逐漸減弱,以及現代國民屬性的不斷增強。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廣大邊民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已然非常明確,邊民國民化的突出議題在于,維護和提升同守邊固邊義務相匹配的“額外的”邊民權益。
第四,邊民國民化過程體現了“因邊造民”的差別化邏輯。邊界或邊境是界定邊民的空間依據,居邊生息、跨境交往是邊民不同于內地居民的基本特性。因此,中國在對邊民進行國民化改造的過程中,除了參照現代國民的普遍性標準之外,還遵循了“因邊造民”的獨特邏輯:根據邊民之“邊”的固有特性,采取差別化措施來實施國民塑造。這一點對于理解邊民所具有的不同于內地居民的國民意識、國民權益、國民責任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