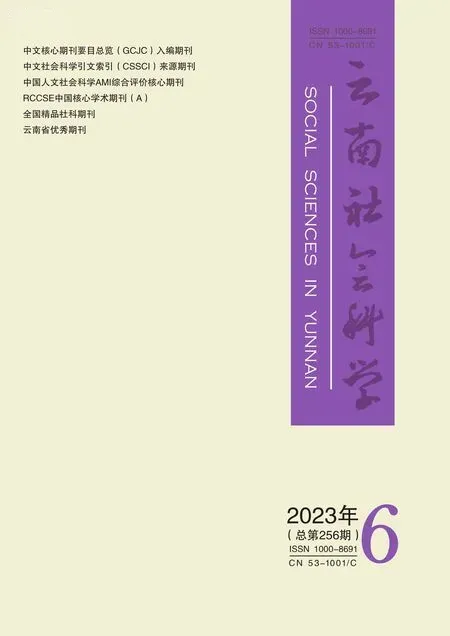西周對西北邊疆的統(tǒng)御與多族群融合
張星德 張瑞強
西周時期,西北邊疆①拙作所指的西周西北邊疆主要以鎬京西北方位的隴山東西兩側(cè)以及涇水上游地區(qū)為主,大致包括今固原市、慶陽市、平?jīng)鍪小⑻焖小氹u市等地區(qū)。共存有周人、商人、姜人、戎人等族群,周室如何控制西北邊疆是一項重要的學術(shù)課題,學界對該課題有一定的研究②代表性研究包括:周書燦先生認為周初西周曾遷徙殷遺民于西土,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孝王通過對秦的封建來加強對西方戎族的防御,西周晚期,周室對西北各族繼續(xù)戍守防御(參見周書燦:《西周王朝經(jīng)營四土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44—69 頁);楊寬先生認為西周統(tǒng)治西北邊境少數(shù)部族采取荒服制,少數(shù)部族首領(lǐng)接受分封低下爵位,并承擔“歲貢”和“終王”的職責(參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53—460 頁);李峰先生認為至晚在西周早期,涇河上游地區(qū)已經(jīng)被納入王室行政管理的地域之內(nèi),并且與王畿地區(qū)結(jié)為一體(參見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62 頁);劉旭先生認為西周統(tǒng)治方略有分封諸侯國、遷徙殷遺民、懷柔政策(參見劉旭:《西周疆至的考古學考察——兼及周王朝的統(tǒng)治方略》,《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268—273 頁);王坤鵬先生認為西周管控西北的主要策略是以貴族宗族防守關(guān)鍵據(jù)點并與土著族邦聯(lián)姻(參見王坤鵬:《由近出伯碩父鼎銘論西周王朝西北邊域之管控》,《中國邊疆學》(第十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第133—147 頁)。,但是,關(guān)于姬姜聯(lián)姻、申駱聯(lián)姻、西申、密國、殷商貴族等在周室管控西北邊疆中所起到的作用,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并且,隨著近年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尤其是固原彭陽姚河塬遺址的發(fā)現(xiàn),對于探討西周管控西北邊疆提供了新的考古資料。姚河塬遺址屬于文獻失載的獲國遺存,獲侯為殷遺民①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考古》2021 年第8 期。,加之,靈臺發(fā)現(xiàn)的同屬殷遺民的潶伯、伯之墓②甘肅省博物館工作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第2 期。,這些考古材料有利于研究周室通過遷徙歸順的殷商貴族來加強對西北邊疆的管控。另外,姚河塬遺址發(fā)現(xiàn)有周文化、商文化、寺洼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多種考古學文化并存,這表明多族群共同生活于獲國境內(nèi),多族群長期的共同生活對于探討當時民族交融提供了便利,而且,獲侯、申侯、潶伯等封君侯伯對周天子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以及戎人對周室的臣服等,都有助于推動西北邊疆多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總之,筆者嘗試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chǔ)上,綜合運用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擬探討西周如何統(tǒng)御西北邊疆以及西北邊疆多族群之間的互動交融。論述不當之處,祈請專家斧正。
一、族群聯(lián)姻穩(wěn)固西北邊疆
(一)姬姜聯(lián)姻、控制西戎
周人的興起與周邊的戎族具有密切的關(guān)系,姬姜聯(lián)姻更是周人崛起重要的政治基礎(chǔ)。據(jù)《史記?周本紀》載:“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說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周棄外家。”③(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第145 頁。由此可知周人祖先乃姜原所生,姜原,姓姜,是有邰氏之女,屬于炎帝之后,所以,周人有姜姓的血統(tǒng),周姜兩家是姻親關(guān)系。又據(jù)《國語?周語》載:“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憑神也。”④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卷3?周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138 頁。文中“皇妣大姜”即周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可見周人與姜族在西周建立前已經(jīng)形成較為穩(wěn)固的姻親關(guān)系。西周建立后,姬姜姻親關(guān)系更加密切,兩者逐步形成世代聯(lián)姻的同盟關(guān)系。據(jù)《史記?晉世家》載:“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⑤(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9?晉世家第九》,第1977 頁。據(jù)此可知周武王之妻為邑姜,她是重臣呂尚之女,也是周成王和晉國始封之君叔虞的母親;呂氏,姜姓,故而稱武王之后為邑姜,所以,西周建國后第一代王后即為姜姓之人。武王之妻應(yīng)為文王所選,周文王之所以選擇呂尚之女為兒媳,背后當有諸多考量。首先,周人興起于戎狄之間,其與周邊戎族關(guān)系密切,姜族作為西土重要的政治勢力,與其聯(lián)姻無疑會極大增強周族的實力,況且當時正是密謀滅商之際,為武王擇娶姜女是十分明智的選擇;其次,呂尚作為周文王的重要謀士,選擇與其結(jié)親,無疑對自己及以后武王穩(wěn)固統(tǒng)治、東進伐商有利;最后,周人本就有姜姓血統(tǒng),且文王的老祖母為太姜,文王為兒子擇娶姜姓兒媳,合乎傳統(tǒng)。所以,武王娶姜女,是上合傳統(tǒng)、下合周人根本利益的選擇。正是武王和邑姜的結(jié)合,奠定了太姜以來周姜二族聯(lián)姻的基礎(chǔ)。
20 世紀80 年代陜西眉縣出土了一件青銅器,其銘文為“王乍(作)仲姜寶鼎”,有學者指出這是周穆王為妻子仲姜所做的一件青銅器。⑥劉懷君:《西周申國初封地淺談》,《陜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匯報會論文集》,西安:陜西省文物事業(yè)管理局,1981 年,第160 頁。由此可知穆王所娶之妻亦為姜姓女。又《詩?大雅?崧高》載:“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⑦(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8?大雅?崧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1427 頁。周宣王在冊封申伯時稱其為“王舅”,可見宣王之母和申伯應(yīng)為兄妹或姐弟關(guān)系,而“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后,太姜之家”⑧(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50 頁。。故而,申伯也姓姜,和齊、許、呂同屬周太王之妻太姜的本家,所以,宣王之母即周厲王的王后也姓姜。除此以外,據(jù)《史記?周本紀》載:“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⑨(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86 頁。可知幽王之妻也是申氏女,即姜姓之人。厲王、幽王王后皆為姜姓,據(jù)此推測宣王之妻也應(yīng)為姜女。由此可知武王、穆王、厲王、宣王、幽王五代王后皆為姜女,其他諸王由于史料匱乏難以明辨,但是,根據(jù)上述史料可推測出西周王后似乎大部分出自姜姓。姬姜極有可能是世代聯(lián)姻的兩個族群,這或許是史前時期兩個氏族世代通婚的遺風。
周姜聯(lián)姻本質(zhì)上是一種政治聯(lián)盟關(guān)系,它肇始于周太王,從武王時開始逐步系統(tǒng)化,武王娶邑姜標志著兩族政治結(jié)盟關(guān)系的確立。有學者指出:“申呂同屬姜姓,申或為呂的別支。姜與羌本屬同源,皆是西方著名的氏族。”①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122—123 頁。姜姓不僅僅是西北邊疆重要的部族,其同源的還有羌人,所以,姜姓代表的是西北邊疆的姜羌勢力集團,姬姜聯(lián)姻結(jié)盟,對西周控制西北邊疆、穩(wěn)定統(tǒng)治極為有利。《詩經(jīng)》言:“維申及甫,為周之翰。”②(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8?大雅?崧高》,第1419 頁。這就表明申甫(呂)即為西周的屏障。據(jù)《竹書紀年》載:“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五年,西戎來獻馬。”③(梁)沈約:《竹書紀年集解?孝王》,上海:廣益書局,1936 年,第107 頁。申侯聽從孝王號令,率師討伐西戎、護衛(wèi)邊疆,后西戎賓服,向周朝獻馬,據(jù)此可見姬姜聯(lián)姻確實有利于西周鎮(zhèn)撫西戎。
總之,周姜聯(lián)姻既是族群結(jié)合,更是政治聯(lián)盟,西周通過與姜人聯(lián)姻,將西北邊疆的重要政治勢力——姜羌集團拉攏為己用,姜羌同源,這使得姜人成為西周控制西北邊疆的重要輔助力量。同時,姜人也是西周籠絡(luò)羌人、聯(lián)系西戎的重要橋梁,故而,文獻直言同屬姜姓的申、呂為西周之屏障,并且,申侯遵從周王命令,討伐不服從的西戎,這些史實皆表明姜人在西周控制西北邊疆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西周除了通過姬姜聯(lián)姻來穩(wěn)定西北邊疆外,還利用親家申侯和大駱(秦人先祖)聯(lián)姻來控制西戎。據(jù)《史記?周本紀》載: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fù)與大駱妻,生嫡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邑之秦,使復(fù)續(xù)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嫡者,以和西戎。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卷5?秦本紀第五》,第228 頁。
大駱,嬴姓。申侯,姜姓。申嬴早期就聯(lián)姻,到了周孝王時,申侯之女又嫁給大駱,生嫡長子成。因為大駱另一個兒子非子善于養(yǎng)馬,得到孝王賞識,孝王欲使非子成為大駱繼承人。此時,申侯為外甥說話,其重要理由就是申駱重婚、西戎皆服,從而保護周的西北邊疆。孝王聽從了申侯的建議,保持成的嫡子身份,同時,又冊封非子于秦亭,號秦嬴,成為西周的附庸。這段史料表明在周孝王以前,申侯就和大駱族聯(lián)姻,而申侯又是周朝諸侯和盟友,申駱聯(lián)姻實際上是在保護周的西部邊疆,從西戎皆服的記載看,也確實達到了穩(wěn)定西北邊疆的效果,正因為此,周孝王才未因個人好惡選擇大駱繼承人,而是聽從申侯的意見。申侯既和姜羌等戎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又和西周有著姻親關(guān)系,所以,申在周與戎人之間起著緩沖調(diào)和的作用,他是西周控制西部戎人的重要力量,而申駱聯(lián)姻,對于周室控制西戎更是錦上添花。此外,周孝王之所以賞識非子,不僅僅是因其善于養(yǎng)馬,更重要的是非子在犬丘人中間具有威信。孝王想要非子繼承大駱之位,以便他能團結(jié)大駱族,成為周控制西戎的重要幫手。在申侯的勸說下,孝王一方面穩(wěn)定申駱聯(lián)姻,另一方面,冊封非子,使其成為周管控西戎的另一個重要支點。總之,姬姜聯(lián)姻、申駱聯(lián)姻對于周鎮(zhèn)撫西戎、控制西北邊疆具有重要意義。
二、政治分封與遷徙殷商軍事貴族
(一)推行分封建立軍事?lián)c
1.分封密國。周人崛起于關(guān)中一帶,周文王之時,就開始對周邊不服從方國進行征伐,據(jù)《史記?周本紀》載:“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應(yīng)劭曰:密須氏,姞姓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①(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53 頁。由此可知密須國在商代就已存在,為姞姓之國,地處涇州靈臺,即今甘肅靈臺縣,周文王時滅掉姞姓密須國,周文王此舉明顯是為了穩(wěn)定后方,翦除商人同盟,為以后伐商做準備。據(jù)《國語?周語》載:“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②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卷1?周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8 頁。由此可知密國為姬姓封國,到周恭王時,密康公因為得罪周王,被周恭王滅掉。由密康公陪恭王游于涇上,可知密國當在涇水上游一帶,周文王滅姞姓密須國之后,又改封同姓宗親于密須,此為西周時期的姬姓密國,兩者地域應(yīng)當重合,即密國位于今甘肅靈臺縣一帶。周室分封同宗于靈臺,應(yīng)該有多重考量,第一,該地地處涇水上游,是防范西北戎人入侵的戰(zhàn)略要地,靈臺位于涇水河谷要道咽喉,而且,沿著長武—彬縣一線可直抵關(guān)中平原,封姬姓宗親于靈臺,可控制該線路,進而確保宗周安全;第二,靈臺也是周人進出西北的軍事?lián)c,占據(jù)此地,一方面,可以解除后顧之憂,另一方面,也可以進討西北戎人,該地進可攻、退可守,故而,周室冊封宗親于此,意在將戰(zhàn)略要地牢牢掌控在自己人手中。
2.分封獲國。經(jīng)考古發(fā)掘,寧夏固原市彭陽縣發(fā)現(xiàn)有姚河塬遺址,該遺址發(fā)現(xiàn)有西周時期封國都邑性質(zhì)的城址,其年代由西周早期持續(xù)到西周晚期,城址面積達92 萬平方米,還發(fā)現(xiàn)有高等級大墓、墻體、護城河、車馬坑、道路,并出土有青銅器、玉器、原始瓷、甲骨刻辭等珍貴文物,其中甲骨刻辭有“入戎于獲侯”文字。③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考古》2021 年第8 期。由出土遺跡、遺物可知姚河塬遺址為西周時期封國所在地,根據(jù)甲骨卜辭內(nèi)容可知其很可能是文獻失載的獲國,根據(jù)遺址發(fā)現(xiàn)的“甲”字形大墓有腰坑、殉狗等典型商人葬俗,可知獲侯為殷遺民。姚河塬遺址發(fā)現(xiàn)的大型建筑基址、“甲”字形大墓、青銅器、玉器、原始瓷等表明該封國級別很高。另外,該遺址發(fā)現(xiàn)有寺洼文化、劉家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遺存④馬強:《周王朝西北邊疆的新發(fā)現(xiàn)——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大眾考古》2020 年第2 期。,這表明獲侯所在的封國是多種文化共存,而寺洼文化族屬為犬戎⑤尹盛平:《寺洼文化族屬探索》,《文博》2020 年第5 期。,劉家文化族屬為姜戎⑥尹盛平:《姜氏之戎與寶雞》,《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2 期。,這說明獲國境內(nèi)存在商人、姜戎、犬戎等多族群勢力。此外,大量馬匹隨葬,也表明固原一帶是畜牧馬匹的地方,這與夷王命虢公討伐大原之戎獲馬千匹⑦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30 頁。的記載相符合。
由姚河塬遺址存續(xù)時間,可知獲侯是在西周早期被分封于固原彭陽一帶。作為殷商后裔,獲侯明顯是歸順西周并被周室冊封于此地的。獲侯由殷墟千里徙封于彭陽,一方面,此舉是周王為了分散殷商貴族勢力,通過遷徙、分封手段,達到分化控制殷商貴族的目的,殷商貴族脫離其舊有領(lǐng)地,遠徙西北,這既體現(xiàn)了周王權(quán)力的威嚴,也表明殷商貴族的臣服,殷商貴族遷徙新地,對新地的政治秩序、族群構(gòu)成是一種新的建構(gòu),遷往彭陽,面臨復(fù)雜的族群關(guān)系,殷商貴族只能牢牢聽命于周王,融入整個西周政治體系之中,成為周王控制西北邊疆的重要力量,這樣他才能背靠西周王朝的強大勢力以及自身的軍事力量,站穩(wěn)腳跟;另一方面,這也是為了通過殷商貴族來控制西北要地,防范戎人入侵,拱衛(wèi)關(guān)中,兩者的相互需求,使得西周與分封的殷商貴族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即身為殷商貴族的獲侯從周王手里獲得合法性和政治地位,受封領(lǐng)命,同時,也作為西周統(tǒng)治機器延伸的一部分,存在于彭陽地區(qū),其為周王室控制西北邊疆、防范戎人,從而成為周室的軍事屏障。
(二)遷徙殷人軍事貴族為輔助
20 世紀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靈臺縣白草坡發(fā)現(xiàn)了西周時期墓群,這些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并伴有隨葬車馬坑,出土器物有青銅器、兵器、車馬器和各種工具等,其中三件青銅尊銘文有“潶伯作寶尊彝”“伯作寶尊彝”,由此可知帶銘文的青銅尊所屬的M1、M2 為潶伯、伯之墓,根據(jù)墓葬隨葬習俗可知兩者為殷人貴族,發(fā)掘者認為二者作為軍事首領(lǐng)率領(lǐng)殷人戍守西北要沖。①甘肅省博物館工作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 年第2 期。由兩座墓葬中出土多達三百余件的兵器(如青銅戈、鉞、戟、箭矢、盾飾)可知潶伯、伯是掌管軍隊的軍事首領(lǐng),青銅鉞是典型的象征軍權(quán)的器物,墓中隨葬該物,彰顯了墓主的尊崇軍事地位,靈臺靠近戎人分布區(qū),將二者遷于此地,顯然是為了軍事鎮(zhèn)壓、控制周邊戎人。作為歸順殷人的軍事貴族,潶伯、伯封地接近密國,密國作為姬姓封國,地位顯赫,故兩位殷人首領(lǐng)應(yīng)受密國節(jié)制,這類似于唐叔受封于晉,被賜懷姓九宗一樣,而潶伯、伯也應(yīng)是被周室冊封于靈臺,與密國共同扼守西北邊疆。總之,潶伯等作為殷商貴族,歸順西周后,成為受姬姓密國節(jié)制的軍事首領(lǐng),以密國、潶伯為代表的周朝封國侯伯正是西周為扼守西北邊疆而設(shè)立的軍事?lián)c。
西周在西北邊疆推行分封,將密國、獲國嵌于宗周與戎人之間。兩個封國地理位置重要,是控制西北戎人的軍事?lián)c。密、獲二國作為西周封國,一方面,將西周勢力拓展于此,通過封國政治實體,重構(gòu)了靈臺、彭陽等地的政治秩序,而該秩序的確立,使得西周進一步控制了上述地區(qū),不管是當?shù)氐耐林⑦€是臨近的戎人勢力,都處于西周封國的管控、監(jiān)視范圍之內(nèi),西周通過控制上述封國,進而控制了西北邊疆,最終確保宗周的安全;另一方面,密國、獲國的長期存在,也使得上述地區(qū)族群長期與周人、商人共存,在新的統(tǒng)治秩序下,多族群的長期互動、文化交流,必然會促進族群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獲國多種考古學文化共存,就是很好的例證。而遷徙潶伯、伯等殷商軍事貴族,也確保了密國軍事實力的強大,姬姓密國和殷商貴族成為西周統(tǒng)治涇河上游的政治、軍事力量,二者的存在確保了西周對上述地區(qū)的有效統(tǒng)治。
三、軍事鎮(zhèn)撫:懷柔壓制并重
西周初年戎人是周的盟國,并參與伐商之戰(zhàn)。《史記?周本紀》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②(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58 頁。由此可知西北的戎人、羌人參與了武王伐商之戰(zhàn),而呂尚作為武王的重臣,更是伐商的積極參與者,呂尚背后代表的是姜羌等族勢力,所以,西北的戎人是武王的盟國,也是西周建國的功臣,故而武王優(yōu)待西北戎人,周戎關(guān)系比較融洽。成王時,周人致力于平定東方,戎人仍臣服于周,據(jù)《逸周書》載:“天子南面立……方二千里之內(nèi)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nèi)為荒服,是皆朝于內(nèi)者……犬戎文馬。”③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卷7?王會解第五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810、858、885 頁。可見成周之會,諸侯、戎狄蠻夷皆來朝覲,犬戎還獻文馬于周,所以,成王之時周戎關(guān)系亦較融洽。康王之時“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71 頁。。社會安定,周戎之間也保持和平狀態(tài)。⑤康王時對鬼方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征伐,據(jù)小盂鼎記載“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可見戰(zhàn)果頗豐。(詳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55 頁)據(jù)學者考證,允姓之戎、犬戎、玁狁屬于一系,即后來的氐族,鬼方和赤狄為一系,且鬼方主要分布在陜西山西北部一帶(詳見尹盛平:《獫狁、鬼方的族屬及其與周族的關(guān)系》,《人文雜志》1985 年第1 期)可見鬼方和犬戎等不同,所以,本文未將鬼方納入宗周西北的戎人范疇之內(nèi)。昭王時,周朝主要對南方的楚國用兵,《左傳?僖公四年》載:“昭王南征而不復(fù)”⑥(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12?僖公四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379 頁。,即昭王溺死于漢水,故而周朝也無暇西顧,周戎之間大體保持著和平狀態(tài)。
到了穆王時,周戎關(guān)系日益緊張。據(jù)《史記?周本紀》載:“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xiāng),以文修之,使之務(wù)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⑦(西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第四》,第173 頁。祭公謀父闡述了先王對戎人的政策“懷德而畏威”,即修文務(wù)德,以德為主,以兵為輔,這種政策確保了西北邊疆戎人對周朝的臣服,然而,穆王卻依仗兵威,以軍事手段壓服戎人,所以,他征伐犬戎雖取勝,但導(dǎo)致“自是荒服者不至”,戎人對西周離心離德。周孝王時,他曾從兩個方面著手處理西戎問題:第一,仍是延續(xù)穆王以來軍事打擊政策,命申侯率軍討伐西戎,此次戰(zhàn)斗使得西戎賓服;第二,孝王尊重、支持申駱聯(lián)姻,使其兩族成為周管控西北邊疆的輔助力量,同時,分封非子于秦,使其成為周的附庸。此時,申侯、大駱、秦嬴成為周控制西戎的三個支點,孝王通過以上措施加強對西北戎人的控制。夷王時,“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大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①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第30 頁。夷王延續(xù)了穆王以來軍事征伐的政策,命虢公帥周六師討伐犬戎,此次周師獲勝,俘馬千匹。據(jù)多友鼎銘文記載:“唯十月用玁狁放(方)興,廣伐京師,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自(師)。葵未,戎伐筍,衣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辰,搏于邾,多友右(有)折首執(zhí)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口又五人,執(zhí)訊廿又三人,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②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65 頁。據(jù)學者考證多友鼎年代為厲王時期。③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志》1981 年第6 期。所以,根據(jù)鼎上銘文可知厲王曾命武公伐玁狁(即犬戎),武公命多友追擊玁狁,多友與之多次交戰(zhàn)并取得勝利,其中一次消滅敵人二百多人,俘虜二十多人及一百多乘戰(zhàn)車。至宣王時,周戎之間戰(zhàn)爭更趨頻繁。據(jù)《詩?小雅?出車》載:“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④(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9?小雅?出車》,第698—701 頁。宣王命南仲討伐玁狁,并在北方筑城防守,可見玁狁對西周威脅日甚。又據(jù)《詩?小雅?六月》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⑤(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0?小雅?六月》,第748 頁。可見宣王曾命尹吉甫率軍征伐玁狁。又據(jù)宣王時期青銅器兮甲盤載:“唯五年三月既死霸,王初各(格)伐玁狁,……兮甲從王,折首執(zhí)訊,休亡(無)敃,王易(錫)兮甲馬四匹。”⑥陳連慶:《兮甲盤考釋》,《吉林師大學報》1978 年第4 期。據(jù)此可知周宣王曾親征玁狁。
由上述史料可知武王至昭王時,周朝保持著對西北邊疆戎人的懷柔政策,這一方面是因為周先人與戎人關(guān)系密切,且戎人曾參與武王伐商之戰(zhàn),是周的盟國;另一方面是由于西周前期用兵主要方向為東、南兩方,因此為了穩(wěn)定宗周的西土后方,周也必須保持與西戎的和平狀態(tài),所以,武王至昭王時,周戎關(guān)系較為融洽,西戎也保持了對周的臣服。但是,到了穆王時,其逐漸摒棄先王對西戎的懷柔政策,轉(zhuǎn)而以軍事打擊為主,這導(dǎo)致犬戎等對周室的離心傾向越發(fā)嚴重。這一方面刺激了犬戎等族,以至于不斷和周朝發(fā)生沖突,另一方面也促使以后周王不得不繼續(xù)穆王的軍事打壓政策,從而形成一個死循環(huán),西周越軍事打壓,犬戎等反抗越激烈,后者的反抗又促使西周進一步軍事征伐。總之,西周為了控制西北邊疆戎人,早期以懷柔為主,通過和平方式處理西北戎人,到了穆王時轉(zhuǎn)向于軍事手段,穆王至夷王時,周朝整體而言占據(jù)軍事優(yōu)勢,其大致處于主動進攻地位,而犬戎等戎人基本上處于防守狀態(tài)。到了厲王、宣王時,玁狁(即犬戎)勢力膨脹,不斷進攻周朝,周朝雖取得不少勝利,但是,攻防之勢已經(jīng)發(fā)生轉(zhuǎn)換,其對玁狁只能處于戰(zhàn)略防守狀態(tài),以至于在北方筑城防御。以犬戎為代表的戎人勢力對西周的沖擊,既是他們本身實力增強的體現(xiàn),也是穆王以來軍事打擊政策的惡果,周朝與犬戎的對立,使后者成為西周晚期最主要的邊患。
四、政治文化認同與多族群融合
西周早中期國力強盛,周天子是天下一統(tǒng)的共主。周文化作為主導(dǎo)的文化,此時,各個諸侯國必然會受周文化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使得諸侯對西周產(chǎn)生多重認同。這種認同表現(xiàn)為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等多個方面。
(一)政治認同
對內(nèi),通過推行分封制,西北邊疆確立了周天子—封國統(tǒng)治秩序。西周確立的分封制度,使得廣域王權(quán)國家得以形成,在如此廣袤的領(lǐng)土內(nèi),分封制確保了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周王在戰(zhàn)略要地冊封密國、獲國、西申等封國,進而形成了西北邊疆的封國統(tǒng)治秩序,而接受分封則代表地方認同周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封封君從周王手里獲得權(quán)力與地位,在封國內(nèi)行使周王賦予的權(quán)力,同時,也盡藩屏周室等義務(wù)。如此,周王和諸侯在政治上確立了共主與封臣的關(guān)系,這無疑加深了受封侯伯對周王的政治認同。所以,封君從周王手里獲取政治地位與政治、軍事等權(quán)利,這表明封君對周天子的臣服,兩者形成政治范疇內(nèi)的君臣關(guān)系,封君既為周王錫封之臣,那么,封國亦為周土,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①(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第13?小雅?北山》,第931 頁。。所以,諸侯無疑會對周室產(chǎn)生廣泛的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周人政治集團的融入,這種認同能將封國與周王統(tǒng)治集團牢牢捆綁在一起,加深雙方的利益融合。對外,西周確立了內(nèi)外服制度,戎人朝覲貢獻方物,對周天子表示臣服,兩者形成寬松的政治關(guān)系。例如,犬戎在成周之會時曾朝覲周天子,并貢獻方物②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卷7?王會解第五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885 頁。,這表明以犬戎為代表的西北戎人對周天子的政治認同。一方面,西周將其納入外服管理體系之內(nèi),另一方面,犬戎等戎人也接受了西周的羈縻并以朝覲、貢獻方物的形式表示對周的臣服,這種行為說明了西北戎人對西周的政治認同。當然,隨著西周政策的調(diào)整和雙方關(guān)系的變化,這種政治認同也在逐步變化。總之,西周通過推行分封制,控制了廣闊的疆土,以密國、獲國、西申為代表的西北邊疆封國從周天子手里獲封到土地、民眾,并取得政治軍事等權(quán)利,這使得上述封君對周天子產(chǎn)生政治上的認同,而西北戎人也以朝覲等形式表達對西周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歸附。
(二)文化認同
周公制周禮,受封侯伯自然要遵從周禮,不管是同為姬姓的密國國君,還是歸順的殷商侯伯,他們在日常生活、政治交往中,必然會遵守周禮,規(guī)范行為,此為文化認同。強勢的周文化深入諸侯的日常生活,這既是政治上的約束,也是文化上的浸染。一系列的禮樂制度增強了諸侯對周天子的向心力和歸屬感,長期的文化熏陶,使得諸侯對華夏禮制文化產(chǎn)生了認同。例如,姚河塬遺址高等級墓地發(fā)現(xiàn)有2 座“甲”字形大墓,馬坑6 座,車馬坑4 座,祭祀坑2 座。③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I 象限北墓地M4 西周組墓葬發(fā)掘報告》(上),《考古學報》2021 年第4 期。“甲”字形大墓是西周時期比較典型的高等級墓葬,陪葬車馬坑也是周文化比較有代表性的高等級陪葬葬俗。比如,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就發(fā)現(xiàn)有“甲”字形晉侯大墓、陪葬的車馬坑、祭祀坑。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86—87 頁。該墓地屬于西周時期的晉侯墓地,晉國是姬姓封國,始封之君叔虞是周成王之胞弟,故其喪葬習俗代表了周人的文化傳統(tǒng)。而遠在寧夏的獲侯墓地也同樣發(fā)現(xiàn)有“甲”字形墓葬、車馬坑等遺跡,并且,潶伯墓葬也發(fā)現(xiàn)有陪葬的車馬坑,這表明獲侯、潶伯等受到了西周喪葬文化的影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依照周文化禮制埋葬。所以,以獲侯為代表的西北侯伯埋葬習俗受到西周禮制文化的影響,這表明上述侯伯對周文化的認同,而這加速了他們對西周集團的融入。
(三)族群聯(lián)姻
上層貴族聯(lián)姻既是政治利益的結(jié)合,也促進了族群融合。西周時期,同姓不婚,獲侯、密公、潶伯等必然和異姓通婚,不論是哪一族姓,雙方的聯(lián)姻無疑會推動當?shù)氐淖迦喝诤稀@纾拔奶岬降闹芡鹾蜕旰畹穆?lián)姻,申侯和大駱的聯(lián)姻,姬姜聯(lián)姻促進了周姜二族的融合,申駱聯(lián)姻也促進了申侯與秦人之間的聯(lián)系;此外,慶陽合水縣發(fā)現(xiàn)一座西周晚期墓葬,出土1 件青銅鼎,其銘文載:“唯王三月初吉辛丑,伯碩父作尊鼎,……伯碩父、申姜其受萬年無疆,蔑天子歷,其子子孫孫永寶用。”⑤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67—268 頁。該青銅器銘文表明器主伯碩父司職戎人事務(wù),他的妻子為申姜,而申姜應(yīng)為西申女子,這表明伯碩父和申姜聯(lián)姻;另外,考古發(fā)現(xiàn)有王尊,該尊年代為西周早期前段,其內(nèi)有銘文“王乍(作)夨姬寶尊彝”,考古學者指出王和伯應(yīng)屬同一部族,其妻為夨國女子,姬姓,由此可知和夨兩族通婚。①吳鎮(zhèn)烽:《近年新出現(xiàn)的銅器銘文》,《文博》2008 年第2 期。根據(jù)出土青銅器銘文可知西周西北族群之間存在聯(lián)姻現(xiàn)象,這種多族群之間的聯(lián)姻互動,無疑會推動民族交流與融合,族群聯(lián)姻對于早期華夏族的形成具有積極意義。
姚河塬遺址發(fā)現(xiàn)多種考古學文化共存的現(xiàn)象。例如,發(fā)現(xiàn)有殷遺民、劉家文化、寺洼文化、周人、土著雜居的情況②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I 象限北墓地M4 西周組墓葬發(fā)掘報告》(下),《考古學報》2022 年第1 期。,這表明屬于殷商貴族的獲侯與屬于劉家文化的姜戎、屬于寺洼文化的犬戎、北方草原族群同處一地。一方面,這說明獲國所在的彭陽地區(qū)族群構(gòu)成復(fù)雜;另一方面,這也暗示多族群在獲侯統(tǒng)治之下的和平共處。多族群同居一地,顯然有利于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與融合。而密國境內(nèi),姬姓貴族與潶伯等殷商貴族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文化交流,以及普通周人、殷遺民、當?shù)赝林g的混居同處、族群聯(lián)姻,也會促進周人、商人與土著人之間的族群融合。
(四)地緣實體促進族群互動與融合
分封于彭陽的獲國,由于其地處涇水上游,他與戎人靠近,故而其封國內(nèi)存在姜戎、犬戎、北方草原等族群。這些戎人遺物留存于獲國遺址內(nèi),表明戎人與獲國居民交流互動較多,所以,獲國這樣的地緣封國實體為多族群交流互動提供了平臺,不論是雙方交換貿(mào)易,還是人員流動,無疑會促進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同樣,作為分封的姬姓密國,以及徙封而來的潶伯等,也推動了多族群互動融合。密國統(tǒng)治階層為周人,隨遷而來的潶伯等殷商貴族及其家族成員,共存于密國境內(nèi),周人、商人、當?shù)赝林仍诿車餐幼∩睿L期的交流及婚聘無疑會推動封國內(nèi)族群融合,而與臨近的戎人貿(mào)易、交往也會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合。因此,周人、商人、土著人、戎人等族群在上述封國之內(nèi)長期共存并處,封國的政治實體為多族群交流互動提供了平臺,而且地域?qū)嶓w之內(nèi)的聯(lián)系無疑會促進族群之間的交流融合。
總之,周天子通過錫封諸侯,加強了對西北邊疆的管控,而分封制的推行也增強了諸侯對周天子的政治認同。諸侯從周天子手里獲取管轄土地、統(tǒng)御人民等權(quán)利,也對周王盡藩屏周室、朝覲等義務(wù),雙方結(jié)成君臣關(guān)系。作為周天子所分封的密國、獲國,其無疑會對周天子產(chǎn)生政治認同。而周禮的推行,以及鎬京作為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其先進的文化中心地位,也會促使諸侯國對西周產(chǎn)生文化認同。廣闊西北邊疆內(nèi)的多族群,不單是某個族群之人,也是封國之人,更是周天子的臣民,長期的文化浸染和政治規(guī)訓,有利于推動由血緣群體到地緣政治實體的文化認同,這為今后華夏族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此外,周室與諸侯之間的聯(lián)姻、諸侯與他族之間的聯(lián)姻等,都推動了族群之間的融合,而作為政治實體的封國也使得周人、商人、土著、戎人等共存并處。長期的生活、交流、貿(mào)易等加深了各族群之間的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進了族群之間的交流融合。
五、結(jié)語
西周建立后,疆域得到極大的擴展。為了有效鞏固統(tǒng)治,西周采取分封制,同時,周在西北邊疆采取了姬姜聯(lián)姻的手段。姜羌本屬同源,姜羌是西部的強大政治軍事勢力集團,周室通過與姜族聯(lián)姻,得到了姜羌集團的支持,這既穩(wěn)固了周人后方,也便于控制西北邊疆。而作為周室親家的申侯又和大駱聯(lián)姻,申駱聯(lián)姻、西戎皆服,這有利于周室控制西戎。除了聯(lián)姻之外,周室還在戰(zhàn)略要地分封同姓的密國、歸順的殷遺民所建的獲國、作為姻親的西申等封國,并安置潶伯等殷商軍事貴族。通過分封諸侯國與遷徙安置殷商軍事貴族,一方面,便于西周控制上述戰(zhàn)略要地,保障鎬京安全;另一方面,也使得上述封君侯伯以周天子代理人的身份統(tǒng)治這些地區(qū),并使他們成為周與西部戎人之間的屏障,進而藩屏周室,最終確保周天子在西北邊疆的統(tǒng)治地位。另外,周天子還派遣周師討伐不服從的戎人,通過軍事征伐來加強對西部戎人的管控。總之,周室通過族群聯(lián)姻、分封諸侯、遷徙殷商軍事貴族、軍事征伐等多重手段確保了西周對西北邊疆的統(tǒng)治,而上述措施推動了周人、商人與戎人之間的交流互動。不論是諸侯對周室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還是封國實體內(nèi)族群的交流、貿(mào)易、互動等都促進了多族群之間的聯(lián)系和融合,這逐漸打破了族群以血緣為標準的觀念,推動了地緣實體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觀念,進而為以后華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