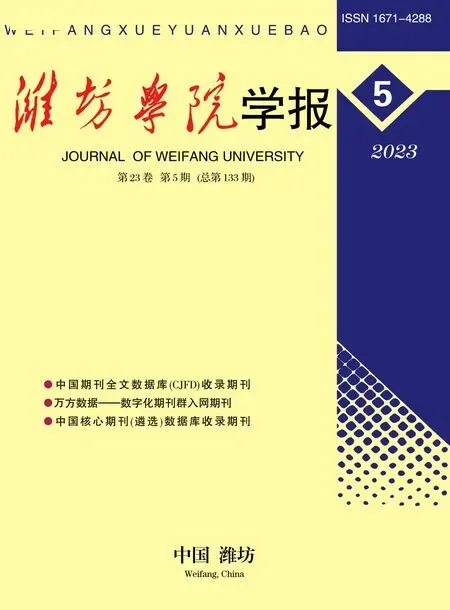圖書館建設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的融合思考
閆格寧,高 橋
(1.青島酒店管理職業(yè)技術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2.青島工程職業(yè)學院,山東 青島 266112)
1 引言
1960 年代,隨著信息化概念的提出,以及由信息化而及的后工業(yè)時代的來臨,催生了終身教育理念。后續(xù),終身教育由理念思潮,到教育實踐應用,演變與流變促進了傳統(tǒng)教育類型的跨代與迭代。隨著后工業(yè)時代的來臨、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終身教育實為社會責任,用以滿足社會個體乃至群體終身學習的實際需求,對于個體提升,社會進步,意義非凡,無需贅言。但其中挑戰(zhàn)在于“終身學習有一定的劣勢,由于缺乏相應的場地支持和資源支持,并且由于其自發(fā)性、自助性等特點,個體缺乏全面系統(tǒng)的知識儲備,導致其在學習的過程中不能有效地利用現(xiàn)有資源”[1]。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性至關重要,其中也包括圖書館在內的社會文化場館,在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中,作用不可或缺;進而,從終身學習角度探討圖書館建設及功能拓展,成為值得細致梳理、聚焦討論的問題。
2 圖書館的教育功能與社會服務屬性
古今中外圖書館的發(fā)展歷程深刻揭示著圖書館職能和角色的轉變,其中顯著的特征是圖書館的教育功能,以及逐漸深化的社會教育屬性。公元前4000 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就有了大量以泥板文書形式的文獻收藏;公元前290 年,亞歷山大圖書館就開始注重學術研究等等,同時“有教人識字、提供學習讀物之職”[2]。在我國圖書館一詞出現(xiàn)之前,先后出現(xiàn)過“書院、書樓、書庫、書藏、書籍館、大書堂、義書堂、公書林、典籍院、藏書處、藏書樓、藏書院、圖書樓、圖書院、圖書館”[3]等稱謂,其主要職能除了文獻保存、服務政治和學術研究外,也包括人才培養(yǎng)。但在我國,皇家藏書,服務皇族貴胄;官府藏書,旨在學術官守;私家藏書,多僅限一族,開明之士鮮矣;書院藏書,源于唐,達于宋,直至明清……圖書館教育屬性得以體現(xiàn)的同時,也應看到社會教育屬性的局限性,服務對象范圍仍具有相當的局限性。
無獨有偶,西方在文藝復興及資本主義啟蒙思想影響下,較早產生了具有公共服務特征的圖書館。世界上首座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是1852 年建立的英國曼徹斯特公共圖書館。其后,英國率先頒布公共圖書館法和相應制度,歐美各國受其影響,公共圖書館快速增加,自由平等與免費服務的主旨思想廣泛波及,開啟了真正意義的現(xiàn)代化圖書館發(fā)展時期。西學東漸,晚清改良派積極倡導圖書館建設,其社會化服務功能逐步確立彰顯。新中國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20 世紀末21 世紀初,我國圖書館事業(yè)蓬勃發(fā)展,與國際進一步接軌。特別是1996 年國際圖聯(lián)第62 屆大會在北京召開后,《公共圖書館宣言》在國內廣為傳播[4];2008 年中國圖書館協(xié)會發(fā)布《圖書館服務宣言》,又進一步標志著我國圖書館事業(yè)步入現(xiàn)代化快速發(fā)展道路。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以及社會服務的廣度與深度得到進一步夯實,預示著圖書館未來發(fā)展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之間的關聯(lián)契合。
3 終身學習思潮與學習觀的時代變遷
終身教育思潮誕生標志是1965 年法國學者保羅·朗格朗在第三屆世界成人教育大會所做的《終身教育報告》。隨后,1968 年,美國教育思想家羅伯特·赫欽斯進一步提出了“學習化社會”的概念[5]。歐美學者在同一時間階段,聚焦同一教育范疇,又具有接續(xù)延展性,主要體現(xiàn)在從教育責任向學習主體、從教育供給向學習需求、從教育范疇向社會意義構建拓展提升等維度,深刻體現(xiàn)了教育順應社會發(fā)展,做出的積極努力,也同時引發(fā)了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1976 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羅畢召開會議,提出了“終身學習”的概念,促進了學習化社會實為學習型社會,依托終身教育的進一步融合。1995 年,我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確立了終身教育在我國的法律地位,同時強調“為公民接受終身教育創(chuàng)造條件”[6]。
由此,從教育內涵意義,到社會發(fā)展轉型,再之于個體學習方式,都體現(xiàn)了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與終身學習三位一體的系統(tǒng)性。要實現(xiàn)終身學習型社會的良性互動,需要具備“兩個要件:作為公共品的終身學習社會平臺和個人的終身學習意愿。公共圖書館,已經成為全民終身學習的重要基礎設施之一。”[7]其中,學習型社會教育供給與終身學習個性化需求兩者互為條件,相互關聯(lián),在支撐學習型社會內涵構建同時,也深層次變革著社會成員的學習觀,即知識獲得、技能養(yǎng)成、學術素養(yǎng)、職場素質等等。而與此同時,圖書館的獨特作用和重要性凸顯出來。
4 圖書館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的契合與挑戰(zhàn)
“古今中外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與實踐表明公共圖書館具有天然的教育使命”[8],且社會化服務屬性呈現(xiàn)出進一步增強的歷史發(fā)展脈絡,公共圖書館更成為“促進終身學習的社會大學”[9],終身學習思潮的興起與終身學習觀的深入人心,也為圖書館參與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帶來可能,同樣也存在挑戰(zhàn)。
4.1 圖書館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的契合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信息技術革命、互聯(lián)網快速發(fā)展和全球教育改革的推進,圖書館的現(xiàn)代化成為時代命題,推動圖書館走出傳統(tǒng)模式,順應社會、經濟和科技發(fā)展,圖書館的現(xiàn)代化進程成為焦點和重點。“現(xiàn)代化圖書館”指在傳統(tǒng)圖書館的基礎上,運用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系統(tǒng)管理技術等各種高科技手段,實現(xiàn)圖書館所有功能“數字化”管理,所有文獻信息資源一體化、共享化的新型全能圖書館[10]。由此,“數字圖書館”“復合型圖書館”“智能圖書館”等圖書館形態(tài),在圖書館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應運而生,并在快速發(fā)展變化的知識經濟時代,強調信息資源的開放共享、以人為本、服務讀者的社會職責,發(fā)揮著重要的學術研究、文化交流作用和社會教育功能。足見,在現(xiàn)代技術的加持影響下,契合于終身學習的時代大脈絡,實現(xiàn)圖書館功能的躍升,其最主要的職能正在從傳統(tǒng)信息收集整理和公共閱覽服務,向提供更為廣泛多維且迅捷方便的教育服務轉型。
4.2 終身學習體系建設對圖書館的挑戰(zhàn)
2019 年頒布的《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2035》明確提出,我國教育發(fā)展主要目標之一是建成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xiàn)代教育體系[11]。目標于服務終身教育體系構建,圖書館又迎來了新的發(fā)展契機,且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
4.2.1 讀者變化之挑戰(zhàn)
圖書館服務目標群體構成多樣性進一步趨強。Prensky 于2001 年就提出“數字土著”的概念[12]。“數字土著”一代來臨,使得圖書館面臨的服務對象發(fā)生著重大變化;再加之,包括數字移民,甚至還包括數字遺民,使得圖書館的服務對象差異性增強。曹培杰等認為數字土著“在豐富的信息技術環(huán)境中成長,對新技術的習得更具優(yōu)勢,并善于利用技術促進學習”[13]。此外,數字移民,可以順應數字化變革;數字遺民,亦并非貶義,實則是熱衷或堅持傳統(tǒng)閱讀和信息接收習慣的讀者群,譬如部分樂齡人士。以上三者,基于技術素養(yǎng)而言、閱讀習慣,特別是閱讀媒介,差異顯著,且難于統(tǒng)合。因此,差異性終身學習需求和偏好,客觀存在;圖書館的挑戰(zhàn)性也因應而生。且同時面向三類數字素養(yǎng)的讀者提供信息及閱讀服務,其難度挑戰(zhàn)、成本精力,不容低估。
4.2.2 知識激增之挑戰(zhàn)
知識信息爆炸背景下,信息時代的知識焦慮表現(xiàn)為“面對如潮水般向我們涌來的信息與資訊,人們常常會感到無所適從。想要專心閱讀,面對琳瑯滿目的圖書,卻不知從何入手……”[14]針對于此,孫赫男認為“尤其是數字化環(huán)境中,讀者所面對的海量信息,讓有效的閱讀引導服務更加重要”[15]。但問題還在于,隨著終身學習參與度提升,“信息需求與信息供給兩端的矛盾:需求和供給的數量都很大,但是卻達不到相互匹配的狀態(tài)”[16]。由此,在知識激增的時代背景下,有效引導與供求匹配,雙重作用下,挑戰(zhàn)不容小覷。作為社會化信息知識服務的重要陣地,圖書館責無旁貸,但又需要突破性提升服務功能,特別是供給的有效性。
4.2.3 知識認知之挑戰(zhàn)
隨著知識信息爆炸時代的來臨,人們對于知識的認知也呈現(xiàn)出劇烈變化。信息技術的普及,知識檢索的迅捷,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知識內化的重要性,使得對知識的傳統(tǒng)理解認知產生動搖,甚至顛覆。“知識內化是將有用的顯性知識轉化為用戶自身隱性知識的過程,能夠反映出用戶在社會化問答情境下進行知識采納、轉移和學習的效果”,換言之知識“要通過知識內化過程才能將它們轉化為學習、工作或生活中的能力”[17]。圖書館作為傳播知識的重要社會化服務機構,如何引導終身學習參與者樹立正確的知識觀,也成為了當下的挑戰(zhàn)之一。此外,碎片化知識習得與知識系統(tǒng)性學習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也需要在終身學習中進一步加強引導。作為知識傳播主陣地之一,圖書館也肩負著重塑或者賡續(xù)知識認知態(tài)度及信念的社會責任。
4.2.4 現(xiàn)代技術之挑戰(zhàn)
現(xiàn)代技術,特別是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等的應用,都挑戰(zhàn)著圖書館舊有服務方式,深刻變革并催生著圖書館新的服務模式及體系。傳統(tǒng)借閱與數字閱讀;大數據信息的存儲與檢索;大眾虛擬在線服務與物理空間閱讀服務;個體靈活閱讀服務與實時、非實時的讀者互動閱讀活動,等等新舊形式的對立并存,衍生接續(xù),都為圖書館的功能延伸提供了種種可能,奠定了廣泛的發(fā)展空間。圖書館技術投入與整合,工作人員的技術素養(yǎng)及技術應用能力等等,都面臨巨大挑戰(zhàn),但依托技術革命性推動圖書館建設發(fā)展又勢在必行。
5 討論建議
“圖書館社會教育作為終身學習‘立交橋’中的重要一環(huán),在幫助讀者打通學習渠道,為市民提供終身學習的場所和相應支持的作用日益凸顯”[18],但同時在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不斷深刻變革社會,信息技術革命如火如荼,在此歷史背景下,圖書館服務學習型社會建設和終身學習體系構建,又顯得格外必要。結合先前述圖書館建設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的契合與挑戰(zhàn)機遇,綜合各相互關聯(lián)要因情境,討論建議如下:
其一,圖書館傳統(tǒng)服務業(yè)態(tài)既需要保護加強,又需要推陳出新,積極引導服務社會學習者,支撐終身學習。圖書館作為傳統(tǒng)閱讀公共服務的主體機構,肩負著普及閱讀、營造閱讀氛圍的社會責任。其中,紙媒閱讀又具有電子閱讀無法比擬的獨特體驗,對于閱讀習慣、閱讀方法、系統(tǒng)性閱讀培養(yǎng)又至關重要,因此在新媒介碎片化閱讀的時代,傳統(tǒng)紙媒閱讀公共服務不可或缺,需進一步加強。同時,對于知識激增與信息冗余,還包括“知識過載”“虛假知識”“知識迷航”等[19]問題,應進一步發(fā)揮社會服務功能,加強引導,提升公眾認知能力,服務終身學習發(fā)展進程。
其二,圖書館建設應與信息技術緊密融合,凸顯技術賦能,在降低成本與服務拓展之間,尋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甚至,通過技術賦能,深刻改變傳統(tǒng)圖書館業(yè)態(tài),服務終身學習,并以此為契機加快建設圖書館。針對各項具體功能,凸顯技術融合,提升預約流轉、便利借閱、知識交流、分享互動等等服務,并大力依托技術組織學習共同體、促進形成學習自組織,切實推動終身學習。此外,技術賦能也是降低服務成本、拓展服務維度、深度、廣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挖掘內生動力的途徑所在。技術賦能,成本與功能再次匹配優(yōu)化,必將使得圖書館服務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潛力進一步加強。
其三,圖書館深入發(fā)揮教育場館職能,增強信息部、社群部、學術部等職能,延伸知識交互,增加學習互動,特別是為專題講座、讀書分線等線下互動和面對面交流,提供場地及組織服務,使圖書館成為終身學習的樞紐。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構筑圖書館在終身學習體系構建中的重要作用,構建廣域的城市終身學習空間、具象化學習環(huán)境,增強臨場感, 并積極宣傳,營造終身學習氛圍,擴展社會學習參與度。喜聞樂見的學習內容,靈活多變的學習方式,輕松愉悅的學習互動等等,圖書館大有可為。
其四,圖書館打破舊有館界壁壘,形成圖書館互借互通服務體系。可進一步貫通市區(qū)縣三級圖書館,打通廠礦企業(yè)以及中小學圖書館,匯聚館藏服務終身學習;設立車站、地鐵、CBD 寫字樓、養(yǎng)老院等圖書驛站,支撐處處可學;積極倡導高等院校圖書館服務駐地周邊,特別是服務對口行業(yè)企業(yè),提供專業(yè)化信息情報服務的功能等等。不拘一格,打破陳規(guī),創(chuàng)新方式,支撐建設城市終身學習體系建設。
其五,圖書館需進一步橫向聯(lián)合社會教育機構、社會場館,形成更廣義的終身教育供給體系并鑄就終身學習自持生態(tài),發(fā)揮綜合性復合化終身教育功能。圖書館通過內部優(yōu)化組合,重在功能創(chuàng)新;外部功能聯(lián)合,旨在系統(tǒng)構建。雙管齊下,在提升發(fā)展自身的同時,勢必深度參與優(yōu)化重構社會公共教育服務構架,整合資源,輸出服務,使學習者始終沉浸在泛在終身學習支撐服務環(huán)境下,浸濡在終身學習的氛圍中,成為切實推動終身學習變革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