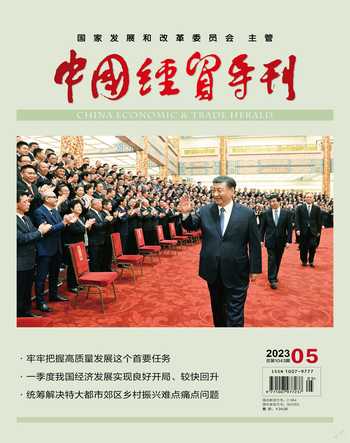以新型城鎮化建設擴大內需的五大方向
王利偉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和促進我國長遠發展的戰略決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是擴大內需最大潛力所在。當前,我國城鎮化邁入“五期疊加”的新發展階段,準確把握新型城鎮化建設方向和趨勢對于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呈現“五期疊加”新特征
邁向新發展階段,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在基本特征、演化趨勢、內在邏輯等方面都將呈現出新變化,造成這些新變化的原因既有規律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準確把握這些新特點是以新型城鎮化建設擴大內需的重要前提。
(一)步入“速降質升”并行的城鎮化發展中后期
從城鎮化發展階段來看,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5.22%,已經邁入了城鎮化發展的中后期,呈現出典型的速度下降、質量提升的趨勢性特征。一方面,城鎮化速度呈現緩慢下降趨勢。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基本保持在年均1.2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在2018年我國城鎮化率突破60%后,城鎮化速度呈現逐年下降的基本趨勢,到2022年增速已經下降到0.5個百分點,從未來來看,我國城鎮化率也將步入增速下滑的軌道,但整體處于城鎮化中期階段的中西部地區仍將保持較快的城鎮化增速。另一方面,城鎮化質量將不斷提升。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有20個點左右的差距,近3億農民工仍然長期徘徊于城鎮和鄉村,未來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將是促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農民工進城落戶,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這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動力來源。
(二)步入“極化分化”交織的城鎮結構體系變動期
受城鎮化步入中后期發展階段、人口出現“負增長”拐點、城鎮經濟轉型分化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我國城鎮基本告別以往“普漲”的發展階段,開始步入極化和分化交織的城鎮結構體系變動期。一方面,城鎮結構出現明顯“極化”現象。以省會城市和發達地區核心城市為主的“極化”效應突出,2010—2020年,北京、上海、廣州等九大國家中心城市GDP占比由18.8%提升至19.1%,省會城市GDP由20.7%提升至21.5%。“十三五”時期,深圳、廣州、杭州、長沙等中心城市年均人口凈流入超過20萬人。未來隨著我國產業結構服務化轉型和新型城鎮化戶籍制度改革等政策調整,中心城市及以其為核心的都市圈對優質要素的吸納能力將更加突出,城鎮“極化效應”更加凸顯。另一方面,城鎮結構出現明顯“分化”現象。發展水平高、行政等級高的高等級城市由于具有眾多就業崗位、優良公共服務設施等將持續吸引人口流入,而欠發達地區城鎮、資源枯竭城鎮、規模較小城鎮等將呈現人口流入放緩甚至人口凈流出狀態,部分城市呈現明顯的“城市收縮”現象,以縣城為載體的就地城鎮化趨勢也將更加明顯。由此,從城鎮結構體系變化趨勢看,人口凈流入的中心城市和縣城地區將成為擴大內需的重點關注區域。
(三)步入“存量增量”轉換的城鎮空間調整期
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后,特別是隨著城鎮化階段和人口結構的深刻調整,我國大部分城市已經接近或基本完成大規模向外擴張建設的過程,未來將呈現由城市大規模“增量”建設為主轉向城市“存量”改造升級為主的階段。一方面,“增量”擴張空間不足。隨著我國人口邁過“負增長”的拐點、城鎮化步入中后期、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等結構性變化,城鎮人口對建設空間需求增速下降,生態空間和農業空間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我國城市大規模向外擴張的紅線約束越來越明顯,“增量”擴展速度和規模都將呈現下行態勢。另一方面,“存量”挖潛潛力巨大。隨著我國新型城市建設的推進,在快速城鎮化階段形成或積累的城市內部舊城鎮、舊廠房、舊小區等“存量”空間的更新改造,將成為城市空間調整的重點。這一趨勢必將引導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從城市“增量”擴展為主轉向“增量”擴展和“存量”更新相輔相成的階段。
(四)步入“硬件軟件”互促的城鎮品質提升期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快速建設發展造成的“重建設、輕管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具體表現為重規模擴張輕品質提升、重“形象工程”輕民生工程、重經濟效益輕其他效益,不僅造成一系列“城市病”,也造成城市整體品質不高的問題,不符合我國新型城市的政策導向,未來我國城鎮建設將步入“硬件軟件”互促發展的品質提升期。一方面,城鎮“硬件”更加完善。隨著信息化、綠色化等浪潮推進,城鎮發展對信息基礎設施、綠色基礎設施的需求將呈現快速增長趨勢,伴隨智能交通設施和能源設施、高品質公共服務設施等建設加快,我國城鎮“硬件”支撐能力將顯著提升。另一方面,城鎮“軟件”更加健全。我國城鎮參與國際競爭更加激烈和少子化、老齡化等人口結構變化,對城市高水平治理要求越來越迫切,特別是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地區的智慧化管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城鎮對老齡化適應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一趨勢為擴大內需在智慧基礎設施、優質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提供了很大需求,需要在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中重點關注。
(五)步入“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鄉結構交融期
隨著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和一系列重大城鄉改革舉措加速落地,我國城鄉差距呈現逐步縮小的基本趨勢,城鄉融合發展態勢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城鄉要素交換更加頻繁。在我國邁入人均10000美元發展階段后,城鎮居民對鄉村優質農產品、傳統鄉土文化產品和鄉野生態產品的需求上升,鄉村振興對城市農業科技、工商資本、各類人才的需求上升,在信息技術支持下,城鄉之間的產品、人口、資金、科技等要素流動將呈現更加頻繁的態勢。另一方面,城鄉改革進程更加活躍。長期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和政策障礙將逐步破除,農民工進城落戶限制加快破除,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加快探索,城市現代工商資本下鄉趨勢增強,城鄉融合發展改革試驗加快推進,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建設提速,城鄉融合發展將成為主要趨勢。這一趨勢為擴大內需增添了城鄉互為提供優質產品消費需求、城鄉統一大市場建設等增長點。
二、以新型城鎮化建設擴大內需的五大方向
新型城鎮化對擴大內需的帶動作用和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必須充分考慮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和增長潛力,從強化精準投資、擴大優質消費、實施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管治、暢通城鄉循環等五大方向制定擴大內需戰略舉措。
(一)強化精準投資,全面提升城鎮綜合承載能力
以中心城市及以其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縣城等人口凈流入區域為重點,強化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綠色智慧設施等領域的補短板強弱項,適度超前布局建設城鎮設施,全面提升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當前,我國人均基礎設施存量水平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20%—30%,在社會民生領域也存在不少短板弱項,在我國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綠色智慧設施等投資空間仍然具有很大潛力,尤其是要著力加強城市群都市圈之間和城市群都市圈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城際軌道交通和高速公路建設、加強城市群都市圈以及人口大縣縣城等重點區域的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加強城市綠色和智慧基礎設施投資等,提升城鎮對人口和產業的綜合承載能力和水平。
(二)擴大優質消費,全面增強城鄉居民高品質消費供給
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高品質消費需求為出發點,著力聚焦擴大優質消費供給,強化城鄉居民消費對擴大內需的基礎支撐作用。一是大力培育城鄉居民新型消費,大力培育網絡消費、定制消費、體驗消費和信息產品消費等新業態,拓展新型消費增長空間。二是大力發展服務型消費,順應城鄉居民消費由商品消費為主轉向服務消費的基本趨勢,積極發展城鄉育幼、養老、健康、文化、體育等服務業,推動生活服務業向高品質和多樣化方向升級。三是大力發展城鄉公共服務消費,聚焦城鎮化人口凈流入較快地區,超前增加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公共消費投入,提升城鄉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據有關研究機構測算,“十四五”期末,我國城鄉居民消費規模將達到55.93萬億元,釋放內需潛力達約17萬億元。
(三)實施城市更新,打造高品質宜居城市
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是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路徑,有利于充分釋放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為抓手,以老舊小區、老舊城區、老舊街區、城中村等“三區一村”為重點,加大城市更新改造投資,持續解決突出民生問題,創造高品質宜居城市生活。加快推進老舊小區改造,有條件的地區可加快開展建筑節能改造,到“十四五”期末,爭取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鎮老舊小區改造任務。在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等發達區域,率先推進老舊廠區和老舊街區改造,因地制宜將一批城中村改造為城市社區或其他空間。相關機構預測,城市更新將撬動10萬億級的內需空間,對于擴大內需具有重要意義。
(四)提升城市管治,建設新型智慧城市
以建設新型智慧城市為目標,充分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完善城市信息基礎設施,推進市政公用設施智能化升級,整合公共數據資源,建設“城市大腦”。綜合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傳統基礎設施升級改造,推進智慧交通、智慧水務、智慧能源等基礎設施布局,提升城市管治效率,尤其針對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防疫防汛防災中暴露出的問題和風險隱患,加快補短板強弱項,切實提高特大城市的風險防控能力。據有關研究機構估算,我國新基建投資規模將持續擴大,在基建投資中的占比將逐步提高至15%—20%左右,到“十四五”期末將帶動累計投資規模達到20萬億元。
(五)暢通城鄉循環,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以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為重點,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農村居民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推動城鄉治理資源向鄉村地區傾斜配置,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城鄉聯動改革、雙向開放,堅持城鄉改革一體設計、一體實施。下大力氣深化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改革,提高城鄉要素流動的效率。加快完善城市科技、人才、資本等優質資源下鄉的政策保障和激勵機制,促進各類要素有序向鄉村流動,實現城鄉之間人才、土地、資金、技術、信息良性互動,提升城鄉要素循環水平,激發城鄉間互相需求潛力。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