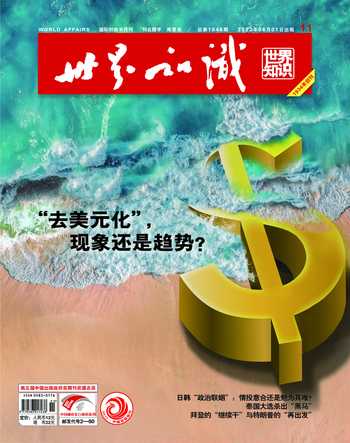巴基斯坦外長訪印,“破冰”易“融冰”難
林一鳴
5月5日,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成員國外長會在印度果阿邦舉行。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正式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后,印度首次作為輪值主席國舉行這一會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議也是巴基斯坦外長12年來首次訪問印度。一些國際輿論期待此訪成為印巴關系的“破冰之旅”,但由于內外環境限制,印巴關系的“凍結”狀態恐怕還將延續。
被“恐怖主義陰影”籠罩
巴外交部門負責人已有12年未赴印開展雙邊外交活動。2016年12月,巴總理外交事務顧問薩爾塔吉·阿齊茲赴印參加“亞洲之心”阿富汗問題多邊會議。而此前的2011年7月,巴首位女外長希娜·拉巴尼訪印并舉行雙邊會談。作為本屆巴政府外交國務部長,希娜·拉巴尼向印媒明確指出巴外長比拉瓦爾此行“不是一場雙邊之旅,而是上合之行”。果然,會議期間印巴外長未舉行雙邊會晤。
印巴關系在波動中下行的趨勢延續已久,2019年降至冰點。2019年2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發生自殺性爆炸襲擊,造成40多名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官兵死亡。印媒稱,這是數十年來發生在印控克區傷亡最嚴重的一次沖突,印方宣稱該襲擊背后“存在巴基斯坦因素”。局勢緊張期間,印巴兩軍還發生了空中對抗。同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廢除憲法“370條款”,取消印控克區的“特殊地位”,這被巴方視作是單方面改變兩國主權領土爭議地區現狀、打壓克什米爾地區民眾政治權利的舉措。此后,兩國宣布將外交關系降至代辦級。
印巴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的主權和領土爭端有著復雜的歷史成因。巴方認為應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實行公投來決定其歸屬,而印方則宣稱該問題屬于印度內政。進而,印度將印控克區的安全問題歸咎于“巴支持恐怖主義活動”,企圖將克什米爾問題轉化為反恐問題。2014年,印度人民黨(印人黨)政府上臺后,對巴采取孤立和打壓政策,極力渲染巴國家“支恐”。巴方亦針鋒相對,指出印度情報部門煽動巴境內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分離主義。
由此,相互指責“支恐”成為近年來印巴兩國外交戰、輿論戰的一大重點。在本次上合組織外長會上,印巴外長繼續就反恐問題打起“口水仗”。印度外長蘇杰生在發言時強調印度面臨“跨境恐怖主義威脅”,宣稱“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不會與加害者討論該問題”。巴外長比拉瓦爾則表示,“反恐需要合作,不應被用作外交工具”,“印方有責任為談判創造有利環境”。
關系轉圜缺乏內在動力
印巴關系近年來的“凍結”狀態也與兩國國內局勢相關。在2019年4~5月印度舉行全國大選前,印人黨及印度總理莫迪為謀求連任,將“國家安全”擺在競選綱領的首要位置,極力塑造自身“國家安全捍衛者”形象。很大程度上,這是促使當年2月莫迪政府悍然出動戰機進入巴空域的政治動因,也引發兩軍的空中對抗。同樣作為其國家安全政策內容,印人黨也將取消印控克區“特殊地位”作為競選承諾,并在成功連任數月后兌現。
不僅如此,由于印人黨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近十年來,印人黨政府極力強化其治國理政的“印度教色彩”。許多觀察者注意到,針對穆斯林的立場,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巴敵意和對克什米爾問題現狀的強烈不滿,內嵌在印人黨“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所宣揚的意識形態之中。因此,不少分析人士強調印人黨政府對巴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不容忽視。比拉瓦爾自印返程后表示,“印度宣揚所有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但我此行打破了印度制造的這種‘神話”。由此可見,改善對巴關系在印人黨的政治議程中即便存在,恐怕也是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2023年5月5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外長會在印度果阿邦首府帕納吉市舉行。圖為印度外長蘇杰生與巴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合影。
雖然近年來巴尋求緩和對印關系,甚至在中東國家的斡旋下對印開展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接觸,但這些接觸都無果而終。雙方在克什米爾等問題上立場過于懸殊,巴方以克什米爾問題為中心尋求緩和對印關系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巴先后在本國經濟金融穩定、阿富汗問題、反恐等領域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這沖淡了其緩和對印關系的外交努力。此外,2023年巴將舉行全國大選,當前其國內各方政治勢力正加緊博弈,如何處理對印關系更是“燙手山芋”。
當下,轉圜關系對印巴兩國而言都缺乏內在契機,但并不意味著雙方可以承受危機升級帶來的風險。2021年2月,印巴兩軍作戰局長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在克區“控制線”兩側實施停火,這一舉措使克區緊張局勢降溫。時至今日,雙方都維持了“控制線”兩側的整體穩定。不過,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兩國進一步加強接觸的迫切性,把印巴關系“凍結”在了低水平穩定線上。
美國是最大外部阻礙
2017年,印巴兩國正式加入后,上合組織實現地緣覆蓋面的“跨越式發展”。雖然有觀點擔憂這兩國的加入會增加上合組織內部的協調難度,但同樣不應忽視印巴借重上合組織開展地區合作與多邊外交的客觀需求。此番上合組織外長會促成巴外長時隔多年赴印,反映出上合組織的影響力,體現出其勸和促談的獨特作用。事實上,勸和促談、加強合作也是中方以“親誠惠容”開展周邊外交的重要內容。作為中國與陸上周邊國家合作的重要平臺,上合組織對中國周邊外交的作用更加凸顯。
盡管如此,印巴關系轉圜的外部環境仍難言樂觀。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大搞所謂“對華競爭”,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極力拉抬印度的國際戰略地位,這已成為制約印巴關系緩和的最大外部障礙。軍事上,美國在裝備研發、技術轉移、戰術協作等方面加快與印“合作”“融合”,這在客觀上加劇印巴軍事力量失衡。政治上,美國高調宣揚對“印度崛起”和“印度在地區領導地位”的支持,以“四方安全對話”等系列機制誘印方入局,這掩蓋了南亞域內政治和解的重要性。經濟上,美國企圖聯手印度在地區搞“‘一帶一路替代方案”與“排華供應鏈”,這進一步加劇了南亞域內國家經濟合作的鴻溝。倘若美方繼續把所謂“對華競爭”在南亞鋪開,甚至一廂情愿地按地區各國“對華親疏”程度推行其南亞政策,勢將給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帶來更嚴峻的挑戰。事實上,美國戰略界已有觀點注意到這一趨勢,并警告這將導致南亞危機管控難度加大。考慮到這一前景存在的可能性,印巴關系甚至是更大范圍的南亞國家間關系依然欠缺良性互動的有利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