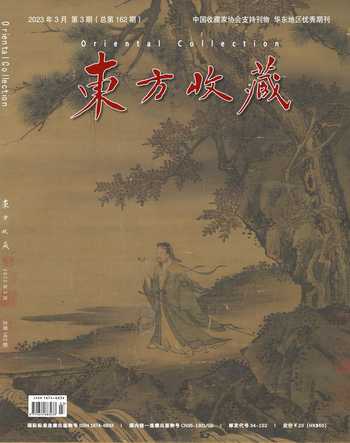陌生化的藝術語言
周昕雨
摘要:文章從何多苓帶有詩意的陌生化的藝術語言出發,論述懷斯寫實主義繪畫以及文學詩歌對何多苓的影響。同時以何多苓作品為例,論述其朦朧性的視覺效果和抽離性的感官體驗中表現形式陌生化的意象美,以及從現代化的精神維度和跨越性的時間維度兩方面論述何多苓繪畫語義下陌生化的意象美。
關鍵詞:何多苓;陌生化的藝術語言;意象美
20世紀中國繪畫的發展也隨著時代在不停變革著,從20世紀70年代典型概括的繪畫模式到之后具有“懷舊”情結的“傷痕美術”,似乎畫家的繪畫作品都反映著現實。但何多苓并沒有過多關注社會中的現實,而是運用他帶有詩意般的畫筆,通過“陌生化”的語言把人們從共性繪畫中解放出來,找尋自己的本真。其藝術雖然學習西方繪畫的表現形式,卻帶有中國傳統繪畫的意象,他的畫面是其心靈世界的一種真實。何多苓以新穎的手法改變了傳統的寫實主義面貌,這種陌生的視覺刺激讓讀者能夠走進何多苓的內心世界。
一、陌生化語言中的意象美
(一)陌生化的概念
陌生化這個釋義,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使用過“驚奇”“奇異”等說法,“陌生化”這一概念就是和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所相悖的。什克洛夫斯基在《藝術作為手法》一文中對“陌生化”學派的審美哲學進行闡釋:“藝術是一種體驗事物之創造的方式,而被創造物在藝術中已無足輕重。”我們往往會忽略那些習以為常的事情,我們延遲這個藝術的領悟過程,實際上也是將平常的事物加以“陌生化”,從而吸引讀者的眼球。
所以當藝術作品使用陌生化的藝術語言時,更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使讀者在欣賞作品時增加閱讀和感受的難度,就如同“距離產生美”一般。讀者和作品要保持好一個恰如其分的心理距離,如果距離太近,就容易忽視這件作品,或者說這件藝術品消弭于大眾的視線之中,從而無法進行審美。
(二)意象美的起源和由來
“意象”這個詞語早就存在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之中,《周易》提出“立象盡意”,這里的“意”指的就是思想、情意;“象”指的是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最早將“意”與“象”連著來用的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說:“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意思是說,正如同有自己獨特見解的工匠,憑借頭腦中審美表象的組合進行藝術創造活動。這篇文章所運用到的“意象”,所代表的就是藝術構思中外物形象和藝術家情感互相結合所構成的審美表象。“意象”,也是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一種體現。
意象美的產生,不僅僅是主體對客體的簡單反映,它往往還包含了主體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的情感可能來源于主體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抑或是主體的人生經歷所導致的喜怒哀樂。所以在藝術作品中,畫面構成的意象是經過藝術家主觀處理的“真實”而又“抽象”的意象。這種“真實”體現在藝術作品的內容,并不是胡亂捏造的,而是真實存在過的物體。
(三)藝術陌生化與意象美的關系
意象美的誕生,是藝術作品的物象承載著藝術作品的靈魂和生命,通俗來說,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在反映藝術家的內心世界。宗白華曾說:“美感的養成在于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這種“距離感”使物象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從而產生意象美。
意象美的誕生,本身就是區別于具象美的非自動化語言。當一件藝術作品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它可能不是具象地描繪外部世界,而是將具體物象加以提煉、概括、重組,以不尋常的視角來表現尋常的事物,使作品成為更高級的美的形態,觀眾在面對這種藝術作品時,往往會伴隨著“驚奇”的表情,因為這種作品并不是隨處可見的,而是“陌生化”的。在何多苓的繪畫作品中,他用帶有詩意的眼光去發現生活中的美,用有“距離感”的陌生化語言來詮釋意象美。
二、何多苓“陌生化”意象美的由來
無論是何多苓早期繪畫中寫實具體的女孩形象,還是后來繪畫中朦朧隱晦的女性形象,我們都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其作品中詩意神秘的特質,唯美中帶著一絲感傷。他擺脫刻板單一的創作模式,將自己觀察、體驗過的或者內心平靜的生活表現在畫作當中,創造出具有真情實感的繪畫作品,努力探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我們可以從何多苓繪畫作品中,看到懷斯鄉土主義寫實繪畫和中國傳統詩歌的影響。
(一)西方繪畫對何多苓的影響
安德魯·懷斯是美國現當代寫實主義畫家,他以逼真的繪畫手法、銳利的眼光、敏銳的洞察力捕捉和描繪美國鄉間的風土。在懷斯的作品畫面中,簡樸的房間、孤寂的老人、優柔的花草等意象,常常給人一種寂靜哀怨之感,同時也讓人感受到懷斯對鄉土深深的熱愛。
何多苓曾坦承懷斯對他的影響,他說:“我喜歡懷斯那嚴峻的思索,他那孤獨的地平線使我神往。”我們似乎可以從何多苓的成名作《春風已經蘇醒》中隱約看到懷斯那哀愁的影子:畫面中一個農村小女孩伸直雙腿坐在草地上,一只手自然地向下垂落在一條腿膝蓋上,另一只手則放在嘴唇上,似乎在啃咬著,神情專注,若有所思,仿佛是在渴望春風帶來新的生活和希望。小女孩的身旁是一只仰天抬頭張望遠方的小狗,身后是一只趴著的黑牛。整幅作品描繪精細,栩栩如生。這幅作品是何多苓在看到懷斯《克里斯蒂娜》后創作的,畫面的感覺同樣是悲傷寂寥的,同時,也對未來充滿了渴望。何多苓被懷斯的作品所深深感動著,這種孤寂卻又充滿著自然主義情調的詩意和他個人情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何多苓的繪畫作品帶有現實主義的傾向。
與此同時,何多苓并不滿足于只表現現實主義。在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下,何多苓更沉浸于西方藝術中的神秘感,所以在其繪畫中能夠看出他始終在尋找一個平衡,那種超越寫實主義之上的朦朧美感。“比如畫面保持寫實主義的外表,在簡潔到抽象的構圖中利用不是常態下的光線、色彩、環境、動作等‘錯位,造成畫面的緊張感和陌生感。”何多苓在吸收懷斯和達利畫面優點的同時,也在打破當時藝術的既有框架,尋求自己心中的那一片桃花源。
(二)文學詩歌對何多苓繪畫的影響
中國傳統繪畫講究以詩入畫,語言藝術的文學與視覺藝術的繪畫相交融,必然會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何多苓坦言自己醉心于詩歌,所以他的繪畫其實也帶有文學元素。
何多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段在四川涼山的知青生活。對于年輕的何多苓來說,盡管只能勉強填飽肚子,但是他卻很熱愛那里的生活。他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大家在閑暇之余,閱讀了許多經典名著,像巴爾扎克、雨果等文豪的著作。他曾如此回憶那時的生活:“在我四年的插隊生活中,始終處于一種審美的樂趣和狀態之中,那是一種非常激動和特別興奮的狀態。”很顯然,何多苓是享受那里的生活的,他將自己閱讀的詩歌融入對生活的感受中去,在繪畫中表達,迸發出別樣的藝術靈感。
三、何多苓“陌生化”手法中的意象美
何多苓曾赴美講學,當時的美國藝術創作商品化,部分藝術作品為了迎合消費者的審美變得程式化和淺薄化,使得一些后現代藝術作品沒有任何的闡述空間。那段時間,何多苓也曾賣出過一些藝術作品,但是他感覺到很迷茫,好像畫面少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后來他意識到這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便尋求屬于自己的內容。他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宋代的一些繪畫作品,宋畫的意境美給了何多苓以啟示,他同時開始吸收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寫意精神。在他晚年的兔子系列繪畫作品中,會用一些“陌生化”的手法來表現他自己帶有朦朧美以及淡淡哀傷的精神世界。
(一)表現形式陌生化的意象美
1.朦朧性的視覺效果
在何多苓后期的繪畫作品中,作品的表現形式出現“陌生化”的改變,他描摹的不是真實存在的具體空間或物象,而是一種精神空間的象征。他晚年創作了兔子系列作品,以其作品《兔子的誕生》為例,畫面中描繪的是一名裸體女子,長著一對兔耳朵,用手擋住下半身,站在一個巨大的白色盤子上,身后是一片汪洋大海。這幅作品整體以綠色為基調,畫面中采用“陌生化”的手法來表現女子形象,打破了固有觀念帶來的藝術限制。女子的形象和我們平常看見的并不一致,藝術家將本不屬于一體的元素加以拼湊,使我們關注點聚焦于畫面中心,同時將背景虛化,主體融入到背景之中,從而對這件藝術作品感到驚奇。它采用具象和抽象的手法相結合,使作品“陌生化”。他自己亦曾說道:“在具象和抽象之間尋求和解,賦予我根深蒂固的浪漫意識與對優雅的渴求,和一個新的、站得住腳的物質框架。”很顯然,何多苓的繪畫也是在具象和抽象化的藝術語言中尋找一個平衡基點,而這個基點就是他畫面中朦朧的意象美。
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件作品里看到中西方藝術碰撞中極具個人風格特色的獨特魅力:畫面與構圖均借鑒、采用了文藝復興時期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但是與之不同的是采用了中國傳統“寫意”的表達方式,將物體的邊緣線模糊淡化,讓女子的客觀外形消融在背景中,并沒有很強的線條感,筆觸不再具象。畫面構圖也趨向于平面化,體積感和空間感的削弱,抒情式的創作使表達的意象更加含蓄內斂。作者將整體色彩控制在統一的綠灰色調中,注重營造色彩感覺,給人一種清冷、悠遠、若隱若現的朦朧詩意美,讓人心中產生無限奇妙的聯想,產生一種社會現實世界與自我內心世界交織起來的意味。
2.抽離性的感官體驗
在何多苓的繪畫作品中,很少有鮮亮的色彩和強烈的明暗對比。以作品《小翟》為例,畫面中沒有高純度的色彩,畫面的顏色如同被抽離了一般,運用這種低純度、低飽和的色彩表現,營造出褪色了一般不同尋常的色彩表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置身于一個虛曠的空間中,眼神直視著觀者,好像在述說著什么,卻又緊閉著雙唇。
這種單一灰色調的表現形式,在單純的繪畫形式語言中又能看見其復雜的心理,使作品顯得孤寂、憂傷,帶有濃濃的詩意。
藝術家運用色彩抽離化這種陌生化的表現形式,以一種詩意的意象美形式表現了自己內心淡淡的憂桑。畫面整體的灰色調使人感覺到壓抑、無奈,卻又渴望在這種時代找到屬于自己內心的一絲慰藉。
(二)繪畫語義陌生化的意象美
1.現代化的精神維度
作為我國現當代畫家“傷痕美術”的代表藝術家之一,何多苓的繪畫風格是十分具有現代性特點的,我們從他的繪畫作品可以窺探出20世紀人們的內心情感。《兔子的誕生》這幅藝術作品也讓我們腦海里不禁聯想到文藝復興時期波提切利的作品《維納斯的誕生》和現代表現主義蒙克的作品《青春》,何多苓巧妙地將《維納斯的誕生》中大致的構圖以及《青春》中女孩子的姿勢,通過自己的表現手法巧妙地結合起來。這種“戲仿式”的表現手法,將原作的神話意義剔除,而賦予了現代語境。
《維納斯的誕生》寓意女神的誕生,也是美的誕生,而在《兔子的誕生中》,卻變成了一個赤身裸體的長著兔子耳朵的女子,運用“兔子”這種符號來使女性形象變得更加立體化,好像女性就如同兔子般柔弱。
在何多苓的兔子系列繪畫作品中,都運用藍色調。作品中除了共同的女性人物主體以外,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水”這一意象的存在。在《維納斯的誕生》中,水是生命之源,是大自然的象征;而在何多苓《兔子的誕生》中,背景模糊朦朧,大面積的藍色似水非水,背景中的水被時間溶解,只剩淡淡的哀傷。
2.跨越性的時間維度
何多苓對作品的“陌生化”處理,甚至打破了時間的維度。在《兔子的誕生》中,他將不同時間維度的作品與自己現當代藝術語境有機結合在一起,表現同一女性題材在不同時空維度下的不同含義。他將《青春》的女孩子形象挪用到《維納斯的誕生》的古典美之中,暗含兩個不同的時間線索:從文藝復興到現代,再從現代到當代,這種手法使觀者注意到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女性形象的異同。女性題材貫穿于何多苓的創作中,其對女性的描繪,恰巧也是不同時空人們對于女性的態度。
何多苓晚年的繪畫似乎有一種層疊錯綜的復雜性,在作品中好像運用陌生化的語言將常見的物象符號化,卻運用帶有詩意的筆觸和朦朦朧朧的意象美,向我們述說著現當代的故事。
在時代的洪波中,何多苓始終邁著他找尋自己個性的步伐,順應卻又不屈服于潮流,而是用自己獨特的眼光去發現生活的美。他能夠在高歌猛進的時代停下自己的步伐,細細品味這個世界,也能夠運用包容的眼光學習各種不同的文化進行藝術創作,不斷突破自己。
參考文獻:
[1]張毅.陌生化手法與格列柯神秘氛圍的營造[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0(05):88-94+210.
[2]曹利華.解答美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209.
[3]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
[4]黃道賓.懷斯的鄉土寫實主義與中國“傷痕美術”[J].藝術探索,2006(03):81+83.
[5]劉淳.藝術 人生 新潮:與四十一位中國當代藝術家對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0.
[6]趙歡.何多苓文獻集[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9.
[7]張藝文,荊蕊蕊,梁韻,李巖巖.時代的反潮與引導——淺析“傷痕美術”[J].明日風尚,2018(03):134.
[8]劉明玉.小議“傷痕美術”的歷史意義和審美價值[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04):104-105.
[9]許晟.何多苓[J].當代油畫,2018(03):78-81.
[10]丁妮.何多苓與他的“傷痕美術”[J].大眾文藝,2015(17):64.
作者簡介:
周昕雨(1999—),女,漢族,江西南昌人。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術學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