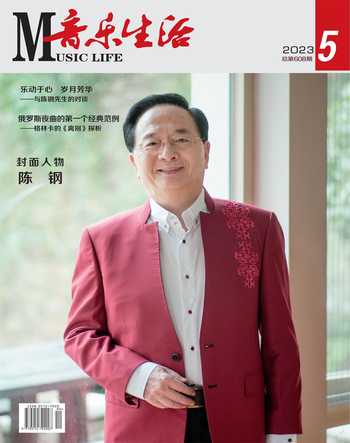傳統(tǒng)曲藝的當(dāng)代融創(chuàng)
在中國(guó)文藝蓬勃發(fā)展的今天,蘇州評(píng)彈作為曲藝界的一朵奇葩,面臨著文化快速消費(fèi)時(shí)代的新形勢(shì),挑戰(zhàn)與機(jī)遇并存。傳統(tǒng)曲藝的傳承同樣需要有新鮮血液的注入,而承載體最強(qiáng)大的則是廣大的學(xué)生群體。在我國(guó)各大高校幾乎都開設(shè)了聲樂(lè)表演或聲樂(lè)演唱的專業(yè)課程,以及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聲樂(lè)作品賞析等選修課程的今天,筆者認(rèn)為,開展民族傳統(tǒng)曲藝藝術(shù)在聲樂(lè)課程中的學(xué)習(xí),是非常有必要的。傳統(tǒng)曲藝的表演形式,能兼容聲樂(lè)演唱技巧,拓寬聲樂(lè)教學(xué)思路,使教學(xué)內(nèi)容的質(zhì)量得到提高,從而吸引學(xué)生的興趣學(xué)習(xí),造就音樂(lè)人才的全面性。因此,構(gòu)建和諧并行、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文化生態(tài)與教育事業(yè)的優(yōu)化路徑,就是傳統(tǒng)曲藝與聲樂(lè)教學(xué)的融合發(fā)展。
一、歷史與當(dāng)下:蘇州評(píng)彈的古今概況
無(wú)論哪種文化,都形成于特定的時(shí)間和空間中,人們根據(jù)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因而創(chuàng)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體現(xiàn)的精神、表現(xiàn)的特點(diǎn)和發(fā)展的態(tài)勢(shì)各不相同[1]。清中葉以來(lái),評(píng)彈文化逐漸“盛于江南”,這些江南市鎮(zhèn)既是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評(píng)彈藝人演出的“書碼頭”。[2]地處蘇東南地區(qū)的蘇州,獨(dú)特的地理?xiàng)l件使其農(nóng)產(chǎn)品豐富,歷史上就有“魚米之鄉(xiāng)”的美譽(yù)。蘇州是吳文化和江南文化傳播的中心地帶,曾有“才子佳人出江南”之譽(yù)。蘇州在清代的“康乾盛世”中,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經(jīng)濟(jì)文化。“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人文積淀,才有了“昆曲”“評(píng)彈”等藝術(shù)珍品的孕育。蘇州評(píng)彈憑借“小橋流水人家”“文人墨客吟詩(shī)作賦”這一蘇州特有的人文空間,逐漸加深了蘇州評(píng)彈的影響力。蘇州評(píng)彈是由評(píng)話和彈詞組合而成,用蘇州地域方言演繹,是濃縮了蘇州地方文化的精華,也是當(dāng)代吳文化的一種呈現(xiàn)。評(píng)彈分布的地方主要在江南一帶,也是因?yàn)槠湔Z(yǔ)言的行通范圍所致:“過(guò)遠(yuǎn)之處聽不懂蘇白,去亦徒然”。[3]
蘇州評(píng)彈最早發(fā)源于明朝,后來(lái)流傳于清代。清代早、中期,政府政權(quán)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繁榮,社會(huì)大眾在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逐漸豐富起來(lái),為了滿足社會(huì)不同層次人群的需求,蘇州評(píng)彈既貼合大眾,又具有文藝氣息的說(shuō)唱藝術(shù)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上至達(dá)官貴人,下至市井居民,都對(duì)評(píng)彈這種表演形式樂(lè)此不疲。于是,從清乾隆到嘉慶、道光年間,蘇州評(píng)彈迎來(lái)了發(fā)展的第一個(gè)高峰。有群眾基礎(chǔ)的評(píng)彈,這時(shí)候發(fā)展的余地就更大了。這一時(shí)期,“陳”“俞”“茂”“陸”四大流派的聲名鵲起。“陳”是陳遇乾,“毛”是指毛營(yíng)佩,“俞”是指俞秀山,“陸”是指陸瑞庭,被大家稱作評(píng)彈“四大名家”。四人的表演方式各成一派,各成體系,深刻影響了評(píng)彈事業(yè)在后世的發(fā)展。蘇州評(píng)彈繼續(xù)發(fā)展到清咸豐、清同治年間,此時(shí)評(píng)彈藝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說(shuō)唱內(nèi)容上,并在原有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增補(bǔ),由以往的篇幅較短,增加到了篇幅較長(zhǎng)的評(píng)彈作品;評(píng)彈藝人在“說(shuō)”的比例上更加講究,縮減了演唱段落,“板腔體”在這個(gè)時(shí)候也更加成熟地發(fā)展起來(lái)。[4]此時(shí)評(píng)彈界除了之前的陳遇乾、俞秀山等人形成的“陳派”“俞派”,”又產(chǎn)生了新的風(fēng)格流派,以評(píng)彈藝人馬如飛所代表的“馬調(diào)”獨(dú)當(dāng)一面。他吸收當(dāng)時(shí)流行的花鼓調(diào)、東鄉(xiāng)調(diào)、灘簧調(diào)、吟詩(shī)聲調(diào)而創(chuàng)造質(zhì)樸明快的“馬腔”,是基本唱腔之一,與“俞調(diào)”齊名,“馬調(diào)”的曲風(fēng)較為豪放,但豪放中見功力細(xì)膩,深得人們的喜愛。[5]蘇州評(píng)彈發(fā)展到清代末期,發(fā)展速度比較緩慢。而馬如飛為此時(shí)的評(píng)彈發(fā)展做了許多貢獻(xiàn),如評(píng)彈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社團(tuán)組織“光裕社”在戰(zhàn)爭(zhēng)中被毀,許多評(píng)彈藝人推舉馬如飛重建光裕社。[6]直到民國(guó)時(shí)期,評(píng)彈在上海迎來(lái)了“黃金期”。彼時(shí)的上海經(jīng)濟(jì)文化繁榮,作為全國(guó)文化娛樂(lè)中心,曲藝界為滿足大眾娛樂(lè)需求,評(píng)彈藝人開設(shè)了多家書場(chǎng),在競(jìng)爭(zhēng)激烈的市場(chǎng)中,評(píng)彈依靠其活躍多變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脫穎而出。
蘇州評(píng)彈自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在面臨新挑戰(zhàn)的同時(shí),也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發(fā)展階段。此時(shí)的演出場(chǎng)地——書場(chǎng),已經(jīng)發(fā)生了改變,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影響評(píng)彈的生存空間,書場(chǎng)的經(jīng)營(yíng)維系十分艱難,蘇州評(píng)彈進(jìn)入了遲滯的發(fā)展時(shí)期。到20世紀(jì)六十年代中期,評(píng)彈藝術(shù)在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發(fā)展的情況下重新興盛起來(lái),更多的聽眾也帶動(dòng)了書場(chǎng)的開辦。蘇州評(píng)彈中有極具時(shí)代特色的曲目,如《刺繡女工心向太陽(yáng)》。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文化環(huán)境在改革開放的新時(shí)期受到外來(lái)文化的沖擊,蘇州評(píng)彈也遇到了和很多傳統(tǒng)藝術(shù)一樣的困境,評(píng)彈藝人頭上縈繞不去的問(wèn)題就是如何傳承和發(fā)展。隨著我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的推進(jìn),蘇州評(píng)彈2006年被國(guó)務(wù)院授予首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蘇州評(píng)彈成功入選“非遺”名錄是對(duì)蘇州評(píng)彈較為有力的保護(hù)。
二、觀念與探討:蘇州評(píng)彈融入聲樂(lè)教學(xué)的可能性
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蘇州評(píng)彈無(wú)論從評(píng)彈的曲藝本體,還是從評(píng)彈的生存空間來(lái)看,都是以活態(tài)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在筆者看來(lái),通過(guò)各種形式實(shí)現(xiàn)其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目前對(duì)傳統(tǒng)曲藝最直觀的保護(hù)方式。當(dāng)然,評(píng)彈的發(fā)展與保護(hù)不可孤立來(lái)看,如果失去了保護(hù)就沒(méi)有發(fā)展了,如果沒(méi)有保護(hù)約束就“發(fā)展”了,那對(duì)傳統(tǒng)藝術(shù)來(lái)說(shuō),就可能是一種摧殘。將評(píng)彈藝術(shù)融入到現(xiàn)今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中,是結(jié)合高校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的角度考慮而形成的一種有效的保護(hù)和發(fā)展機(jī)制。現(xiàn)在國(guó)內(nèi)很多高校都在教學(xué)規(guī)劃中融入了當(dāng)?shù)氐膫鹘y(tǒng)文化,比如北京地區(qū)在教學(xué)中融入了京劇,廣西地區(qū)在教學(xué)中融入了少數(shù)民族歌曲,這些都為把評(píng)彈融入江浙滬地區(qū)的聲樂(lè)教學(xué)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yàn)。現(xiàn)在中國(guó)的聲樂(lè)教學(xué)主要是西方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教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也大都圍繞著這幾個(gè)內(nèi)容來(lái)進(jìn)行。但中國(guó)幾乎每個(gè)地區(qū)都有許多民間音樂(lè)或曲藝、戲劇等豐富多彩、文化價(jià)值極高的民間音樂(lè),具有很高的文化價(jià)值。然而流傳幾百上千年的傳統(tǒng)曲藝卻在今天漸漸式微。就像蘇州評(píng)彈一樣,蘇州評(píng)彈所面臨的傳承問(wèn)題,也在這個(gè)文化快速消費(fèi)的時(shí)代接踵而至。基于這樣的現(xiàn)象,身為高校教育從業(yè)者不禁思考:傳統(tǒng)曲藝的保護(hù)與傳承,能否讓學(xué)校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
從蘇州評(píng)彈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來(lái)看,非常契合聲樂(lè)教學(xué)的內(nèi)容和目標(biāo)。蘇州評(píng)彈的表現(xiàn)手法主要有“說(shuō)、噱、彈、唱、演”。[7]在評(píng)彈發(fā)展中,“說(shuō)”是藝人所說(shuō)的故事和內(nèi)容,通常是藝人表達(dá)文字和唱本中人物所說(shuō)的內(nèi)容組成,評(píng)話是只說(shuō)不唱,彈詞是又說(shuō)又唱,評(píng)彈有“敘述、代言、說(shuō)明、議論,采用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襯白、托白[8]”等不同的手法與技巧。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通過(guò)“說(shuō)”的技巧學(xué)習(xí),可以鍛煉學(xué)生吐字、咬字等表述能力,對(duì)一些歌劇選段中念白演繹的能力提升有很大作用。蘇州評(píng)彈中的“彈”是指樂(lè)器的演奏,蘇州評(píng)彈的主奏樂(lè)器是三弦和琵琶,二胡還會(huì)根據(jù)作品的不同而加入其中。琵琶和三弦都屬于彈撥樂(lè)器,所以用“彈”,評(píng)彈藝人可以單獨(dú)一人邊彈邊唱,兩人時(shí)可相互伴奏進(jìn)行演出。通過(guò)樂(lè)器的學(xué)習(xí)或鑒賞,可以讓學(xué)生對(duì)傳統(tǒng)樂(lè)器有一個(gè)深入的了解,對(duì)基本的音樂(lè)知識(shí)和審美能力有一個(gè)加強(qiáng)。“唱”指的是評(píng)彈者將故事內(nèi)容以“唱”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與我們大眾意義的唱略有出入。通過(guò)學(xué)習(xí)評(píng)彈的演唱,使學(xué)生加深對(duì)聲音的控制,對(duì)氣息的運(yùn)用有很大幫助。“噱”,是評(píng)彈中非常特色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在評(píng)彈中有“放噱”一說(shuō),通過(guò)藝人的前期鋪墊,在一瞬間將笑料釋放出來(lái),從而增強(qiáng)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張力。“‘說(shuō)是說(shuō)書的根本,而‘噱則是書中的潤(rùn)滑劑,就像燒菜的調(diào)味品一樣,沒(méi)有了它,書聽起來(lái)就干巴巴、讓人覺得枯燥乏味。” [9]通過(guò)對(duì)“噱”的學(xué)習(xí),在舞臺(tái)表演的實(shí)踐中得到鍛煉,在情感上逐漸實(shí)現(xiàn)個(gè)體的收放自如。“演”是指具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審美價(jià)值與美學(xué)要求的評(píng)彈表演。藝人們?cè)谖枧_(tái)上的神態(tài)動(dòng)作、言語(yǔ)腔調(diào)都是表演的成分,是塑造藝術(shù)形象的必要手段,從中吸取表演經(jīng)驗(yàn),特別是評(píng)彈藝人與觀眾互動(dòng)的技巧。從表演層面來(lái)說(shuō),這與歌劇、音樂(lè)劇的舞臺(tái)表現(xiàn)是相通的。蘇州評(píng)彈作為說(shuō)我國(guó)曲藝界唱藝術(shù)的精華,可以從創(chuàng)作、表演、欣賞等多個(gè)角度反映中國(guó)傳統(tǒng)唱腔的藝術(shù)內(nèi)涵,可以說(shuō)蘇州評(píng)彈與聲樂(lè)演唱是相互貫通的,既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又有教學(xué)價(jià)值的體現(xiàn)。
三、融合與實(shí)踐:蘇州評(píng)彈與聲樂(lè)教學(xué)的互視互鑒
對(duì)于進(jìn)入現(xiàn)代化、信息化社會(huì)的眾多傳統(tǒng)文化來(lái)說(shuō),因?yàn)槿狈Α皠?chuàng)新點(diǎn)”而逐漸式微的態(tài)勢(shì)成為必然的結(jié)果。在傳統(tǒng)藝人和非遺傳承人的吶喊呼吁之外,面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的困境,筆者從文藝工作者的角度出發(fā),將蘇州評(píng)彈融入聲樂(lè)教育,對(duì)二者都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國(guó)正在積極打造文化大國(guó),為文化實(shí)力的積聚儲(chǔ)備能量,讓國(guó)家和社會(huì)不斷向前邁進(jìn)。把傳統(tǒng)文化輸入現(xiàn)代教育事業(yè),落實(shí)到教育一線陣地,功效才能發(fā)揮到極致,這也就成了我們傳統(tǒng)文化傳承和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文化實(shí)力的功效才能得到最大的發(fā)揮。此外,蘇州評(píng)彈融入聲樂(lè)教學(xué)推動(dòng)教育改革的現(xiàn)階段,為聲樂(lè)教學(xué)體系的“特色化”建設(shè)再添磚加瓦。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在校園里播種傳統(tǒng)曲藝文化,其發(fā)展模式的有效性也被教學(xué)實(shí)踐所證明。北京地區(qū)多所高校在聲樂(lè)教學(xué)實(shí)踐中都融入了戲曲的聲腔唱法,戲曲作為一種綜合性藝術(shù)的呈現(xiàn)方式,具有很強(qiáng)的辨識(shí)力,靈活多變的腔調(diào),別具一格的藝術(shù)形式使教學(xué)多樣化。所以,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融入代表江浙滬的傳統(tǒng)曲藝文化,讓評(píng)彈的傳承命脈延伸到校園,不僅可以讓傳承和保育之路更加寬廣,對(duì)于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的綜合能力,也是一種促進(jìn)。
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shí)的蘇州評(píng)彈,歷經(jīng)數(shù)百年的傳承。歷史上的江蘇,正是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吳地文化的發(fā)源地,而蘇州評(píng)彈則是濃縮了吳地文化的精品曲藝,其中不乏直接取材于歷史事件的故事性情節(jié),如陳潔的文章里就談到了:……評(píng)話《二國(guó)·甘露寺》關(guān)于宮廷婚嫁禮俗的內(nèi)容,《自蛇傳·游湖》可以管窺吳地清明踏青、郊游、賞景、掃墓、祭祖等民俗活動(dòng),聽《楊乃武》的《屈打成招》《賓主反目》《二堂會(huì)審》就會(huì)了解清末官場(chǎng)政治的黑暗。[10]我們可以了解到,藝人在評(píng)彈說(shuō)唱的過(guò)程中,往往會(huì)加入一些歷史典故,其中既有民間百姓的生活片段、禮俗文化,也有宮廷官場(chǎng)的風(fēng)波軼事,幾乎涵蓋了社會(huì)中的各個(gè)方面。蘇州評(píng)彈像是蘇州地區(qū)吳文化的教科書,而學(xué)生鑒賞評(píng)彈的過(guò)程,也是獲得新鮮知識(shí)的過(guò)程。高校的聲樂(lè)教學(xué)對(duì)其傳承與保護(hù)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將蘇州評(píng)彈融入當(dāng)前的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中,是新時(shí)期下探索多元化聲樂(lè)教學(xué)的一種選擇,是當(dāng)代民族聲樂(lè)教學(xué)實(shí)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模式的一項(xiàng)重要實(shí)踐,是為打造具有中國(guó)特色化教育而實(shí)施的一項(xiàng)政策方針。
四、契機(jī)與展望:評(píng)彈融入聲樂(lè)教學(xué)的多重意義
作為江浙滬地區(qū)的文藝“名片”,曲藝評(píng)彈傳承至今,已經(jīng)走過(guò)了400年的風(fēng)雨歷程。它在當(dāng)下遇到了和很多傳統(tǒng)藝術(shù)一樣的困境,“傳承”和“發(fā)展”是每個(gè)評(píng)彈人都不得不思考的問(wèn)題。將評(píng)彈引入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體現(xiàn)多重意義,是基于評(píng)彈本身的發(fā)展和聲樂(lè)教學(xué)的全面多元化提升。
(一)探索評(píng)彈藝術(shù)傳承與傳播的新路徑。傳統(tǒng)評(píng)彈的繼承和發(fā)展是有比較穩(wěn)定的空間的,它的繼承方式、表演場(chǎng)合包括在這個(gè)空間里,它的繼承是固定的,表演場(chǎng)合也是比較固定的。然而,在傳統(tǒng)文化往往難以適應(yīng)快速發(fā)展的文化消費(fèi)市場(chǎng)的今天,主動(dòng)去學(xué)習(xí)評(píng)彈表演藝術(shù)、主動(dòng)進(jìn)入評(píng)彈表演場(chǎng)合觀看評(píng)彈的人卻寥寥無(wú)幾,大眾的消費(fèi)熱情下降,致使評(píng)彈表演團(tuán)體的出團(tuán)率越來(lái)越低。人們的消遣方式已經(jīng)不再拘泥于傳統(tǒng)曲藝,許多年輕人對(duì)評(píng)彈的了解已經(jīng)不多了。面對(duì)這種令人擔(dān)憂的現(xiàn)狀,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引入評(píng)彈不失為一種延續(xù)傳統(tǒng)文化的做法。作為文化學(xué)習(xí)和傳播的集中地,學(xué)校對(duì)于文化的反哺能力具有先天的優(yōu)勢(shì)。特別是在評(píng)彈盛行的江浙滬地區(qū),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引入“非遺”評(píng)彈,不僅能使聲樂(lè)教學(xué)的過(guò)程富有特色,使之強(qiáng)化地域文化色彩,而且能將傳統(tǒng)曲藝文化傳播出去,形成蘇州新時(shí)期教學(xué)改革的大背景下的文化自覺,提升蘇州文化自信。蘇州評(píng)彈以中國(guó)七大方言之一的吳語(yǔ)來(lái)演繹,其特點(diǎn)是如行云流水般的細(xì)膩感,評(píng)彈會(huì)藝術(shù)地表現(xiàn)出吳語(yǔ)的腔調(diào)。筆者認(rèn)為在江浙滬地區(qū)聲樂(lè)教學(xué)中引入評(píng)彈,對(duì)吳語(yǔ)文化的保護(hù)和傳承、對(duì)本土文化強(qiáng)化歸屬感都是有好處的。保護(hù)傳承蘇州評(píng)彈,發(fā)揮地域文化優(yōu)勢(shì),在教學(xué)中引進(jìn)這一蘇州文化濃郁的曲藝,更好地保護(hù)傳承這一國(guó)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我們作為高校教育實(shí)踐者的責(zé)任和義務(wù)。
(二)構(gòu)建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體系的多模式。在第二十九個(gè)教師節(jié)慰問(wèn)信中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教育發(fā)展的理想、方向和目標(biāo)就是“發(fā)展具有中國(guó)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現(xiàn)代教育”。因此,中國(guó)特色教育的中心思想應(yīng)該由高校教學(xué)工作者來(lái)實(shí)踐。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在我國(guó)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在豐富教學(xué)內(nèi)容的同時(shí),也不斷思考新的教學(xué)模式和教學(xué)內(nèi)容,以確保教學(xué)質(zhì)量。在教學(xué)中融入傳統(tǒng)曲藝文化,不失為一種新的嘗試。通過(guò)融入富有特色的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在豐富教學(xué)過(guò)程的同時(shí),拓展學(xué)生的視野,開拓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思路。現(xiàn)在高校聲樂(lè)課堂教學(xué)模式比較單一,聲樂(lè)老師往往以硬性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要求和教授每一位學(xué)生,如此“科學(xué)”“規(guī)范”的教學(xué),缺少了音樂(lè)家靈動(dòng)的個(gè)性,與倡導(dǎo)的多元化發(fā)展有一定的差距,應(yīng)該讓傳統(tǒng)藝術(shù)進(jìn)入現(xiàn)代聲樂(lè)教學(xué)中,多種模式共同探索,構(gòu)建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聲樂(lè)教學(xué)體系,讓傳統(tǒng)藝術(shù)走入現(xiàn)代聲樂(lè)教學(xué)的軌道。而蘇州評(píng)彈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強(qiáng)調(diào)的是“說(shuō)”“噱”“彈”“唱”“演”,故事內(nèi)涵通過(guò)“說(shuō)”與“唱”相結(jié)合的方式表達(dá)出來(lái),是貼近大眾生活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shù)形式,在評(píng)彈藝術(shù)的五大要訣中,每一點(diǎn)都是表演藝術(shù)的精髓所在。因此,將評(píng)彈融于聲樂(lè)教學(xué)中,對(duì)提高學(xué)生的演唱能力、加強(qiáng)呼吸的掌控力等都是有益的,也能使學(xué)生在演唱時(shí)加深情感的表達(dá)和他們的表演才能。
作為現(xiàn)今蘇州地方文化的呈現(xiàn),評(píng)彈的體裁也是五花八門。結(jié)合當(dāng)今社會(huì)大環(huán)境,運(yùn)用現(xiàn)代教學(xué)優(yōu)勢(shì),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融入蘇州評(píng)彈鑒賞教學(xué)的形式,讓傳統(tǒng)曲藝披上新的“外衣”,應(yīng)該在歲月的流逝中給予“老藝術(shù)”足夠的尊重。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在實(shí)踐中貫徹落實(shí)國(guó)家教育改革、實(shí)施文化興國(guó)戰(zhàn)略。在國(guó)家倡導(dǎo)保護(hù)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倡議中,特別是在評(píng)彈普及的江浙滬地區(qū),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與現(xiàn)代聲樂(lè)教學(xué)的融合,是隨著中國(guó)特色化教育的不斷推進(jìn)而進(jìn)行的有效嘗試,尤其是作為典型而需要實(shí)踐探索的地區(qū)。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其內(nèi)在的藝術(shù)規(guī)律,從實(shí)際出發(fā)挖掘內(nèi)在的文化內(nèi)涵。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蘇州評(píng)彈的發(fā)展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站在傳統(tǒng)文化的高點(diǎn),尋求與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巔峰對(duì)話,努力實(shí)現(xiàn)對(duì)歷史和民族的多重超越。多模式化構(gòu)建中國(guó)高校聲樂(lè)教學(xué)體系,是由實(shí)踐積累而成。教育者在實(shí)踐教學(xué)中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在尊重科學(xué)教學(xué)規(guī)律的指導(dǎo)下,選擇合適的蘇州評(píng)彈作品進(jìn)行教學(xué),在思考傳統(tǒng)文化與當(dāng)代專業(yè)音樂(lè)教學(xué)融合發(fā)展的有效路徑和模式的同時(shí),對(duì)高校教學(xué)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對(duì)評(píng)彈藝術(shù)進(jìn)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路徑探索。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2018年度高校訪問(wèn)工程師“校企合作項(xiàng)目”,“蘇州評(píng)彈的演唱研究及在聲樂(lè)教學(xué)中的運(yùn)用”(FG2018098)的研究成果。
注釋:
[1]夏日云、張二勛:《文化地理學(xué)》,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頁(yè)。
[2]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zhèn)探微》,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
[3]該處引自1948年的《蘇州日?qǐng)?bào)》。
[4] 周勝南:《蘇州評(píng)彈現(xiàn)代書創(chuàng)作的敘事選擇》,《四川戲劇》2021年第7期,第120-123頁(yè)。
[5]劉曉海:《晚清以來(lái)蘇州評(píng)彈傳承研究》,《上海師范大學(xué)》2018年第8期,第184頁(yè)。
[6] 周良:《蘇州評(píng)話彈詞史》,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yè)。
[7]戴蔚:《 論蘇州評(píng)彈學(xué)校的音樂(lè)教學(xué)》,《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2021年第9期,第77頁(yè)。
[8] 陳潔:《 蘇州評(píng)彈藝術(shù)生存狀態(tài)初探》,《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2008年第8期,第45頁(yè)。
[9]秦建國(guó)主編:《評(píng)彈》,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版。
[10]陳潔:《蘇州評(píng)彈藝術(shù)生存狀態(tài)初探》,《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200年第8期,第45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朱夢(mèng)婷:《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研究——以評(píng)彈為例》,《西南大學(xué)》2015年第12期。
[2]陳潔:《 蘇州彈詞藝術(shù)發(fā)展史研究:原樣保護(hù)與能動(dòng)傳承的有機(jī)統(tǒng)一》,《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2013年第2期。
[3]龐政梁:《蘇州評(píng)彈的傳承、創(chuàng)新與普及》,《蘇州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年第3期。
[4]潘訊:《論蘇州評(píng)彈的文化特征》,《常熟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年第5期。
[5]吳琛瑜:《 晚清以來(lái)蘇州評(píng)彈與蘇州社會(huì)——以書場(chǎng)為中心的研究》,《上海師范大學(xué)》2009年第9期。
[6]周學(xué)文.:《評(píng)彈與近世蘇州社會(huì)生活》,《蘇州大學(xué)》2008年第11期。
[7]申浩:《社會(huì)史視野下的評(píng)彈文化變遷》,《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5期。
[8]陳潔:《蘇州評(píng)彈藝術(shù)生存狀態(tài)初探》,《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2008年第8期。
章蔓麗 浙江藝術(shù)職業(yè)學(xué)院副教授
(責(zé)任編輯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