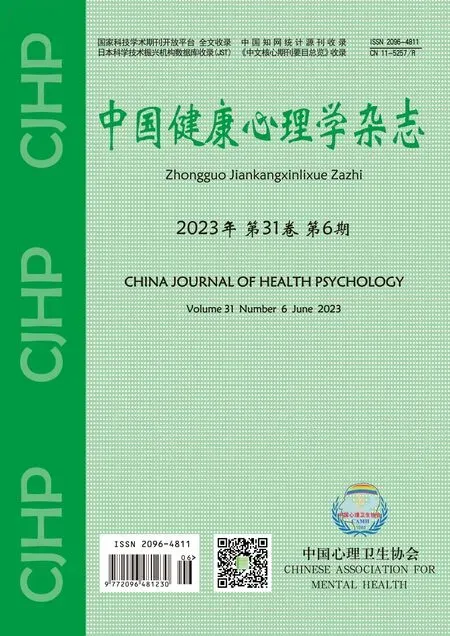父母低頭行為與中職生社會排斥的交叉滯后分析*
馬芳芳 梁維林 向祖強△
①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心理系 510006 ②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
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統計顯示,手機上網者數量為10.29億,且30~39歲與40~49歲占比最多,分別是19.9%、18.4%[1]。國外研究發現73%的父母在與孩子共餐時會低頭玩手機,35%的父母在陪伴孩子過程中每5分鐘就有1分鐘花在手機上[2]。同樣,國內父母低頭玩手機現狀也不容樂觀。44%的中國父母在與孩子共處時會使用手機[3],且《2014年國民家庭親子關系報告》顯示在親子互動中,父母低頭玩手機行為較以往增長至51.8%[4]。可見,父母因使用手機而忽略孩子已成為常態,這種現象稱為父母低頭行為。父母低頭行為(Parental Phubbing)指在與孩子共處時,父母沉浸于低頭看手機,因而沒有時間精力照顧與陪伴孩子或忽視孩子的家庭現象[5]。研究發現,父母低頭行為會誘發孩子消極情緒[6]、增加孩子攻擊性行為[7-8]、網絡成癮行為等[9]。
父母低頭行為是一種關系阻撓、情感決絕行為。父母與孩子溝通時,將注意力集中于手機會阻礙親子間的眼神與肢體交流,從而降低親子互動質量與減少親子溝通,使孩子感受到被排斥[10]。父母因玩手機而分心使得其對孩子的情感與需求不能給與及時反饋[2],即使能夠及時觀察到孩子的需求與情緒,也有可能因沉迷于手機而給與孩子敷衍的反應[11]。這種反饋有效性很低,會讓孩子覺得父母冷落、忽視自己,從而產生被排斥感。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指個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被社會群體排斥,導致無法建立正常人際關系、缺乏歸屬感的一種社會現象,其內涵包括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12]。親子互動實驗研究發現在父母玩手機時,孩子向其表露親近行為,父母會用手推開孩子[13],這是一種社會排斥行為。也有自然觀察研究發現父母與孩子玩耍時,父母因關注手機而不理會孩子[11],這是一種社會忽視行為。
自2004年至今,我國大力促進職業教育,以協助國家發展與經濟結構調整,但職業教育社會污名仍存在。中職生作為職業教育的關鍵群體,他們被社會定義為中考的“失敗者”[14]。可見,與高中生相比,中職生遭遇更多的社會排斥。且中職生處于青少年進入成人階段前的特殊時期,身心發展并未成熟,社會排斥對其殺傷力更大。據認知情感個性系統理論指出,在拒絕情境中長大的個體往往知覺到不被接受與忽視,長期以往,個體對拒絕行為會表現出過度恐懼與焦慮,甚至泛化拒絕情境,對拒絕信號敏感性上升[15]。中職生長期處于拒絕情境,他們對拒絕信號變得更為敏感[16]。那么,父母低頭行為會使中職生體驗到更強烈的社會排斥。同樣,被排斥的恐懼是與生俱來的,當人們受到社會排斥威脅時,大腦中旨在檢測與調節疼痛的區域被激活,此時大腦主要目標是停止社會排斥造成的痛苦,因此會出現退縮、反社會行為[17]。經歷社會排斥的青少年往往表現出更多內外化問題,如引發抑郁[18]、成癮行為等[17]。社會化理論與代際傳遞觀點認為家庭是社會化的單位之一[19-20],即社會排斥存在代際傳遞,孩子遭遇社會排斥使其父母也感同身受。研究表明經歷社會排斥的個體更渴望得到關注,而使用社會媒體會釋放其更多多巴胺[21],以至于他們更加依戀手機。因此,孩子經歷社會排斥會加劇其父母低頭行為。
以往研究已提供充足證據證明伴侶低頭癥的負面影響,但較少研究探討孩子被父母“低頭”后的心理狀態[22],且以往關于低頭行為更多是橫向研究,較缺乏縱向研究[5]。在家庭系統中,親子關系對青少年發展至關重要[19]。父母低頭行為會給親子互動制造一種“冷氛圍”,是社會排斥的特殊現象[9]。目前社會排斥相關研究更多聚焦于實驗情境下的狀態社會排斥及成年人群體研究[7],忽視在自然觀察下的持續性社會排斥與中職生群體研究。中職生心理尚未成熟,且被貼上較多社會污名[14],由此可以推斷他們經歷更多的排斥與歧視,且社會排斥對該群體的消極影響更大。鑒于此,本研究采用縱向研究設計,基于中職生群體,探討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的因果關系。為響應國家關注中職生心理狀況政策,為改善親子互動與親子溝通質量提供實證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整群抽樣于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中職生,剔除漏填、不填及僅有一期數據被試,保留有效被試951名,進行間隔半年共兩期的追蹤調查。其中女生315人(33.12%),男生636人(66.88%);職一280人(29.44%),職二398人(41.85%),職三273人(28.71%)。
1.2 方法
1.2.1 父母低頭行為 采用由Roberts和David[6]編制,丁倩等[5]翻譯修訂的父母低頭行為量表,共9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1表示“一點也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總分越高表示父母低頭行為越嚴重。在本研究中,量表兩時間點的Cronbach's α均為0.92。
1.2.2 社會排斥 采用張登浩等[23]編制的青少年社會排斥量表,共11個項目,包括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兩個分量表。采用5點計分,1表示“一點也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總分越高表示被排斥感越強烈。在本研究中,社會拒絕分量表兩時間點的Cronbach's α為0.89、0.90;社會忽視分量表兩時間點的Cronbach's α均為0.92。
1.2.3 施測程序 兩次施測分別在春季與秋季開學后進行,施測前對班主任及班長進行培訓。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施測,由經過培訓的班主任及班長擔任主試,施測結束后當場收回問卷。
1.3 統計處理
采用Epidata進行數據錄入,SPSS 23.0進行相關分析與方差分析,Mplus 8.0進行交叉滯后分析。
2 結 果
2.1 描述性分析
兩時間點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社會忽視均呈正相關。其中T1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社會忽視繼時性正相關,T2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社會忽視同時性正相關。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呈繼時性與同時性正相關。T1的社會拒絕、社會忽視與T2父母低頭行為呈正相關,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平均、標準差和相關分析(r)
2.2 發展變化趨勢分析
父母低頭行為、社會拒絕、社會忽視的性別主效應均不顯著,表明父母低頭行為、社會拒絕、社會忽視對男女生影響不存在差異;父母低頭行為、社會拒絕、社會忽視的時間主效應均顯著,且均呈線性增長趨勢,見表2。

表2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
2.3 交叉滯后分析
對整個中職生與職一、職二、職三中職生群體而言,在控制了前測的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后,前測父母低頭行為顯著正向預測后測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在控制了前測的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忽視后,前測社會拒絕顯著正向預測后測父母低頭行為;在控制了前測的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后,前測社會忽視對后測父母低頭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結果見圖1、圖2、圖3、圖4。結果表明,在全體中職生及不同年級中職生樣本中,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是相互預測關系,與社會忽視是單向預測關系。

圖1 中職生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的交叉滯后分析圖

圖2 職一學生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的交叉滯后分析圖

圖3 職二學生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的交叉滯后分析圖

圖4 職三學生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的交叉滯后分析圖
3 討 論
前測橫向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社會忽視相關不顯著,而前后測縱向及后測橫向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拒絕、社會忽視呈顯著正相關。縱向及后測橫向研究結果與以往橫向研究結果一致[7],該結果說明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既有同時性正相關也有繼時性正相關。可見,父母低頭行為是一種與手機使用相關的社會排斥行為。
據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父母低頭行為的時間主效應顯著,相關分析結果也表明前后測父母低頭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說明前測父母低頭行為可以正向預測后測父母低頭行為,這與以往縱向設計結果一致[5]。低頭行為隨處可見,使得該行為變得可以接受與成為習俗。據從眾效應也可推測隨著低頭行為普遍化,父母低頭玩手機頻率會上升。俗語“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可知習慣力量的強大,父母一旦形成低頭玩手機習慣后,去習慣化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后測父母低頭行為顯著高于前測父母低頭行為。父母低頭行為的性別主效應不顯著,即男女生受父母低頭行為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與張永欣等研究結果相似[8]。社會化理論指出男女性均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如價值觀、行為規范等[19],且中職生心智仍未發展成熟,男女生在神經心理上不存在顯著差異[24]。因此,父母低頭行為作為一種風險性因素對中職生的影響不存在顯著性別差異。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揭示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的性別主效應均不顯著,前人研究也發現性別與社會排斥不存在顯著相關[25]。需要-威脅時間框架提供可能的解釋,該框架指出經歷社會拒絕的個體會表現出一系列自動化反應,如反射、反思、退避[26]。基本心理需要理論也指出被認可、與群體建立聯結是個體最強烈的需求,社會排斥是此需求最大阻礙[27]。因此,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的性別效應具有一致性。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的時間主效應均顯著,且后測社會拒絕、社會忽視均顯著高于前測社會拒絕、社會忽視,與以往縱向研究結果相近[28]。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可知,個體在遭遇某一群體排斥后,他們會產生悲傷與憤怒等情緒[18],敵視排斥者從而更難得到社會認可[29],進一步加劇他人對自己的社會排斥。
交叉滯后分析結果顯示:在整個中職生及不同年級中職生群體中,父母低頭行為均正向預測中職生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期望違背理論及實證研究均證實父母低頭行為與社會排斥存在密切聯系[10,30]。期望違背理論指出青少年希望他們父母在親子互動中表現出高度參與,即當父母的注意力被手機打斷時,子女的期望就會受到負面影響,他們會產生負面情緒,比如社會排斥。研究也發現父母低頭玩手機是一種親子交流中斷行為,互動頻率較低,使孩子產生被排斥感[10]。中職生處于青春期,家庭是他們健康發展的保護因素之一,父母是社會化的重要來源。父母因關注手機而忽視孩子,處于青春期的中職生容易產生消極自我評價,如:父母不愛自己、自己是不好的、父母不歡迎自己等[10]。因此,該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了父母低頭行為是一種由手機引起的社會排斥行為。
此外,研究還發現中職生社會拒絕正向預測父母低頭行為,中職生社會忽視對父母低頭行為預測不顯著。社會排斥包括兩種體驗,分別是社會拒絕與社會忽視,社會拒絕是更直接與更明確的,而社會忽視是更含蓄與更微妙的[31]。根據代際傳遞的觀點,社會排斥存在代際間的傳遞,即中職生經歷社會拒絕后,其父母也同樣遭遇社會拒絕[20]。當個體經歷社會拒絕后,他們的存在感、歸屬感均受到威脅[31]。當個體缺乏歸屬感時,他們在生理和心理上均遭受痛苦。那經歷社會拒絕的個體如何重新獲得歸屬感呢?為什么他們會轉向手機,而不是參與面對面互動以獲得關注與歸屬感呢?人們會評估他們目前的排斥性地位,不是通過檢查他們與目前接觸的群體排斥性地位,而是通過評估他們在各種情況下的排斥性[32]。據此可知,被排斥者會認為其不僅在與排斥者共處時會產生被拒絕的感覺,而且與其他群體也會產生類似結果。最優流動理論認為在被拒絕后,個體會感到被排斥,渴望得到關注與被接納,而使用社交媒體會令人愉快,以至于個體與手機建立非常密切聯系[33]。研究也發現在Facebook上發布一張照片獲得“贊”與評論、熟悉的通知鈴聲,會釋放多巴胺,這與人們從面對面擁抱或微笑中獲得滿足等同[21]。因此,孩子經歷社會拒絕會將排斥感傳遞給其父母,從而使其父母同樣遭遇社會拒絕,經歷社會拒絕的個體,更渴望與他人保持聯系,以至于他們在手機上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希望重新獲得包容性,從而形成低頭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