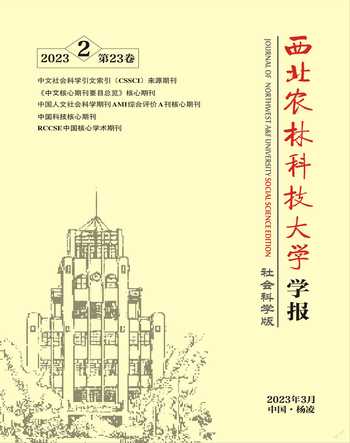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共同富裕效應(yīng)
匡遠(yuǎn)配 彭凌鳳
摘 要:伴隨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持續(xù)推進(jìn),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不斷發(fā)展壯大,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作用愈加凸顯。在闡述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與帶動農(nóng)民共富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的基礎(chǔ)上,總結(jié)了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帶動農(nóng)民共富的主要途徑。基于全國總量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我國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面臨著集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集體資產(chǎn)分布不均衡、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能力弱、經(jīng)營管理型人才匱乏、集體資產(chǎn)管理相關(guān)制度與法律不完善等問題,因此應(yīng)通過拓寬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路徑、發(fā)展多種形式股份合作制、加強(qiáng)人才隊伍建設(shè)、強(qiáng)化政府財政政策扶持、加快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立法進(jìn)程等途徑來促進(jìn)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
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323.89;F306.4?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3)02-0016-07
收稿日期:2022-06-09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2.03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面上項目(71973042);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2022年委托課題(2022NYB01)
作者簡介:匡遠(yuǎn)配,男,湖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理論與政策。
2020年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了全面建設(shè)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步入了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新階段。實現(xiàn)共同富裕關(guān)鍵要解決區(qū)域、城鄉(xiāng)、居民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問題,但我國目前經(jīng)濟(jì)發(fā)展存在諸多問題,實現(xiàn)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任務(wù),需分階段推進(jìn)。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在促進(jìn)農(nóng)民增收、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不斷深化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探索農(nóng)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xiàn)形式,發(fā)展壯大集體經(jīng)濟(jì),是引領(lǐng)農(nóng)民走向共同富裕與實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的必由之路。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推動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農(nóng)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權(quán)力,發(fā)展壯大集體經(jīng)濟(jì)[1]。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jìn)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提到,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是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善農(nóng)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的必然要求,是維護(hù)農(nóng)民合法權(quán)益、增強(qiáng)農(nóng)民財產(chǎn)性收入的重大舉措,對于增強(qiáng)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活力,引領(lǐng)農(nóng)民實現(xiàn)共同富裕具有深遠(yuǎn)歷史意義[2]。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2018-2022年)》提出要積極“發(fā)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夯實鄉(xiāng)村振興的基礎(chǔ)[3]。
近幾年,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對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作用方面。郭曉鳴等從動力機(jī)制、傳導(dǎo)機(jī)制、響應(yīng)機(jī)制、保障機(jī)制解構(gòu)了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緩解相對貧困的作用機(jī)制。同時,基于治理主體面臨的約束,從明確治貧賦權(quán)、強(qiáng)化要素流動、創(chuàng)新支持政策等層面提出相應(yīng)的基本框架[4]。李韜、耿羽等提到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是縮小城鄉(xiāng)發(fā)展差距、提高農(nóng)民生活水平、改善農(nóng)村基本公共服務(wù),推動“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走向 “強(qiáng)、美、富”,促進(jìn)實現(xiàn)共同富裕目標(biāo)的重要經(jīng)濟(jì)形態(tài)[5-6]。王曙光等檢驗了集體經(jīng)濟(jì)促進(jìn)農(nóng)村居民增收和減貧的制度優(yōu)勢,主要體現(xiàn)在供給農(nóng)村公共品、形成民主決策、提升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倫理規(guī)范以及產(chǎn)業(yè)發(fā)展等方面[7]。崔超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壯大有利于盤活農(nóng)村集體資產(chǎn),促進(jìn)人才、技術(shù)、資本等生產(chǎn)要素在城鄉(xiāng)之間流動互補(bǔ),從而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縮小城鄉(xiāng)之間的發(fā)展差距[8]。趙春雨研究發(fā)現(xiàn),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可以調(diào)動村支“兩委”、鄉(xiāng)村精英、農(nóng)戶等多方積極性,推動農(nóng)村社會治理變革,激發(fā)共同脫貧致富的內(nèi)生動力,此外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很好地實現(xiàn)了共同富裕效果[9]。楊博文等認(rèn)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通過規(guī)模化生產(chǎn)、推動城鎮(zhèn)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優(yōu)化分配關(guān)系、勞資關(guān)系革命等路徑促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帶動農(nóng)戶增收[10]。陳錫文認(rèn)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內(nèi)部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的局面尚未普遍形成,并出現(xiàn)了質(zhì)疑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作用的聲音,但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有效避免了農(nóng)村的兩極分化,在歷史上體現(xiàn)出極其重要的作用[11]。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進(jìn)程中,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將起到托底作用。總體來看,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讓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在促進(jìn)城鄉(xiāng)共富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是需要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但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如何拓展發(fā)展空間,形成穩(wěn)健發(fā)展路徑、健全激勵和約束機(jī)制、完善制度環(huán)境等問題,實踐探索和研究總結(jié)都還不夠。本文基于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全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各地的實踐總結(jié),梳理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帶動農(nóng)民共富的途徑,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發(fā)展當(dāng)前面臨的突出困難和制約進(jìn)行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相關(guān)對策建議。
一、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與帶動農(nóng)民共富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共同富裕以“富裕”為基礎(chǔ)、“共同”為特征,是一種更加強(qiáng)調(diào)共享、共商、共建,尋求社會效率與公平平衡的富裕。實現(xiàn)共同富裕是動態(tài)的漸進(jìn)的過程,同時也是各領(lǐng)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相互促進(jìn)的過程,要在高質(zhì)量發(fā)展中去推進(jìn),堅持全面發(fā)展的理念。《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關(guān)于支持浙江高質(zhì)量發(fā)展建設(shè)共同富裕示范區(qū)的意見》明確指出,共同富裕要求“普遍達(dá)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qiáng)、環(huán)境宜居宜業(yè)、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wù)普及普惠”[12]。
實現(xiàn)“高質(zhì)量”共同富裕,至少要求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1)以全民共富為首要任務(wù)。以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壯大中產(chǎn)群體,提高全民收入水平,縮小貧富差距,促進(jìn)社會和諧。(2)以全民共享為內(nèi)在要求。共同富裕具有“普惠性”特征,全體人民都有享受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成果的權(quán)利[13],這不僅包括財富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不斷提升,還應(yīng)包括公平的享有教育、醫(yī)療、文化、福利等基礎(chǔ)設(shè)施與社會公共服務(wù)。(3)共同富裕以全民共治為重要手段。全民參與社會治理是社會和睦的基礎(chǔ),也是治理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共同富裕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只有人民當(dāng)家作主,才能保證“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wěn)步前進(jìn)”[14]。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jīng)過農(nóng)業(y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土地私有制被土地公有制取代。隨著剩余索取權(quán)的轉(zhuǎn)換,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的組織經(jīng)營與管理權(quán)能從農(nóng)戶轉(zhuǎn)入各級各類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經(jīng)由改革開放、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確立,農(nóng)地經(jīng)營權(quán)能重新回到農(nóng)戶手中。長期以來,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依然承擔(dān)著較多的行政和社會職能,發(fā)揮著公共品供給和保障農(nóng)民基本福利(如平地權(quán))的功能。2016年12月,《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jìn)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lián)合實現(xiàn)共同發(fā)展的一種經(jīng)濟(jì)形態(tài)。”[2]2020年11月4日,《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示范章程(試行)》規(guī)定,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具有管理集體資產(chǎn)、開發(fā)集體資源、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jì)、服務(wù)集體成員等職能,部分還承擔(dān)社區(qū)公共品供給、社區(qū)治理和文化傳承服務(wù)等公共職責(zé)[15]。2020年“一號文件”提出,要全面開展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試點,有序開展集體成員身份確認(rèn)、集體資產(chǎn)折股量化、股份合作制改革、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登記賦碼等工作[16]。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是具有市場性與社區(qū)性雙重屬性的特殊組織,兼容成員權(quán)益保護(hù)和集體增效增收的功能。
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是一種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jì)的要求,順應(yī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發(fā)展,以壯大集體利益為基本原則,通過財產(chǎn)聯(lián)合或勞動聯(lián)合,實行共同經(jīng)營、管理民主、共享利益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組織和經(jīng)營方式,是促進(jìn)農(nóng)民增收、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而形成的重要經(jīng)濟(jì)形態(tài)[17]。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變化主要為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治理化、生產(chǎn)經(jīng)營市場化、分配制度股份化、退出權(quán)力自由化等。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是勞動聯(lián)合或者財產(chǎn)聯(lián)合,也是要素與技術(shù)、管理、制度等聯(lián)合經(jīng)營。從要素配置和利益聯(lián)結(jié)的角度看,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實行“雙元分配方式”,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兼顧要素分配的方式。在新時代新階段,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承擔(dān)著共同富裕的底線任務(wù)。
二、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帶動農(nóng)民共富的主要途徑
內(nèi)生發(fā)展動力和能力是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根本力量。作為一種組織化和內(nèi)生性的發(fā)展方式,只要把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在經(jīng)濟(jì)性質(zhì)、組織理念、組織形態(tài)、組織功能、運營機(jī)制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特殊性把握和運用好了,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特殊重要性也將日益彰顯。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帶動農(nóng)民共同富裕,主要從農(nóng)民增收、公共產(chǎn)品供給、鄉(xiāng)村治理三個方面體現(xiàn)。
(一)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帶動農(nóng)民增收致富成效迅速凸顯
產(chǎn)權(quán)制度是市場經(jīng)濟(jì)的基石,發(fā)展壯大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必須構(gòu)建完善的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2015年以來,我國共先后開展了5批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試點,范圍覆蓋了全國所有涉農(nóng)縣、市、區(qū)。目前,試點改革任務(wù)已全部完成,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此次改革共核實集體資產(chǎn)7.7萬億元,其中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3.5萬億元,集體土地資源65.5億畝,確認(rèn)集體成員9億人,共建立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約96萬個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官方網(wǎng)站。。基本構(gòu)建了歸屬清晰、權(quán)能完整、流轉(zhuǎn)順暢、保護(hù)嚴(yán)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為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經(jīng)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后,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效明顯。2020年完成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村共530 874個,村級確認(rèn)成員數(shù)突破8億人,當(dāng)年村集體分紅435.6億元,人均分紅54元數(shù)據(jù)來源于“2020年中國農(nóng)村政策與改革統(tǒng)計年報”。。
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初步具備帶動農(nóng)民共同富裕的能力。在上海市閔行區(qū),村級經(jīng)濟(jì)抱團(tuán)發(fā)展的局面已經(jīng)形成。全區(qū)入股農(nóng)民30余萬人,農(nóng)村集體年收入已超過百億元,超過50%的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實現(xiàn)收益分配,僅農(nóng)村集體人均分紅一項就為村民增收超過4 000元[18]。浙江省嘉興市以統(tǒng)籌實施“飛地抱團(tuán)”項目為抓手,扎實推進(jìn)“強(qiáng)村富民”計劃,不僅富裕村莊繼續(xù)得到發(fā)展,相對薄弱村莊“造血”質(zhì)量也迅速提升,形成了先富帶后富,穩(wěn)步共同富裕的局面。2021年,全市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總收入達(dá)到50.6億元,其中經(jīng)營性收入達(dá)到19.4億元,村均經(jīng)常性收入達(dá)到300萬元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已經(jīng)實施的6個“飛地抱團(tuán)+”項目吸納了8 151戶低收入農(nóng)戶,占低收入農(nóng)戶的56.93%,初步建立起所有農(nóng)村人口逐步共同富裕的機(jī)制[19]。江蘇省蘇州市通過實施“萬企聯(lián)萬村、共走振興路”行動,2020年聯(lián)建企業(yè)283個、聯(lián)建村居784個、村企對接聯(lián)建項目725個,實際投資23.59億元。2018-2020年,蘇州市對100個相對薄弱村實施了一輪幫扶,到2020年底,這些村的集體經(jīng)濟(jì)平均收入達(dá)到444萬元,村民人均達(dá)到1 379元。2020年,全市村均集體可支配收入達(dá)到1 054萬元[20]。在中西部地區(qū),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近年帶動農(nóng)民增收的效應(yīng)顯著增強(qiáng)。據(jù)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廳數(shù)據(jù),通過探索發(fā)展資源開發(fā)型、資產(chǎn)經(jīng)營型、產(chǎn)業(yè)配套型、為農(nóng)服務(wù)型、電商創(chuàng)業(yè)型、聯(lián)合經(jīng)營型、能人領(lǐng)辦型等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2020年廣西全區(qū)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24.3億元,與2016年改革前的6億元相比,實現(xiàn)了5年翻兩番數(shù)據(jù)來源于廣西新聞官方網(wǎng)站。。梧州市全市941個行政村(社區(qū))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平均達(dá)到11.7萬元,比2017年增長3.28倍數(shù)據(jù)來源于梧州市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局官方網(wǎng)站。。陜西省延安市支持村集體統(tǒng)籌整合農(nóng)村土地、人力和資金等要素資源,因地制宜發(fā)展蘋果、棚栽、畜牧等“3+X”特色優(yōu)勢產(chǎn)業(yè),村集體累計發(fā)展蘋果、核桃、葡萄等產(chǎn)業(yè)園8.1萬畝,種植蔬菜、中草藥等1.8萬畝,帶動全市624個村實現(xiàn)集體經(jīng)濟(jì)收入3.7億元。
(二)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公共產(chǎn)品供給能力明顯提升
“大河有水小河滿”。基于區(qū)域性、公共性、綜合性特點,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在內(nèi)部一方面實行按勞分配,另一方面在提升農(nóng)村醫(yī)療救助、養(yǎng)老救濟(jì)、教育補(bǔ)助、基礎(chǔ)設(shè)施管護(hù)等方面發(fā)揮普惠性作用。
1.補(bǔ)充供給數(shù)量。在財政支持有限的約束下,通過村集體積累和內(nèi)部動員,擴(kuò)張公共積累規(guī)模,內(nèi)生性供給生產(chǎn)生活公共品,有效提升公共品供給水平,直接促進(jìn)減貧[21]。2020年,全國村集體組織用于公共服務(wù)和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費用約1 200億元數(shù)據(jù)來源同腳注②。。隨著集體投入能力的增強(qiáng),各地農(nóng)村集體的公共投入水平呈現(xiàn)出快速增長的態(tài)勢。推行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以來,梧州市長洲區(qū)從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總收入中累計提取公益金1 000多萬元,用于解決農(nóng)村水、電、路、垃圾處理等問題,農(nóng)村人居環(huán)境加快改善。
2.優(yōu)化供給結(jié)構(gòu)。基于當(dāng)?shù)匦枰霭l(fā),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針對性更強(qiáng),效率更高,農(nóng)民的滿意度更高。以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為單位,規(guī)范化提取用于公共福利的公積金和公益金,定制公益性福利項目、文娛活動等,多元化拓展供給渠道,實現(xiàn)供需匹配和公平再分配。
3.加強(qiáng)運維管理。自己建設(shè)的成果,農(nóng)民也更加珍惜。公共品移交后,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利用內(nèi)部積累或者發(fā)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參與公共品的運營、維修、管護(hù)等,可持續(xù)地發(fā)揮公共品的功能。
(三)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日益促進(jìn)鄉(xiāng)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和鄉(xiāng)村治理相互交融,在提升鄉(xiāng)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水平中愈加發(fā)揮重要作用。一方面,村干部領(lǐng)導(dǎo)力集中體現(xiàn)在鄉(xiāng)村治理能力方面,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有助于提高村干部的素質(zhì)水平、權(quán)威和聲望,進(jìn)而提升鄉(xiāng)村治理能力。2020年,我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干部報酬支出共計451.5億元,占集體總支出的10.8%,對比上年增長0.6%數(shù)據(jù)來源于“2020年中國農(nóng)村政策與改革統(tǒng)計年報”。。隨著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提高,干部報酬不斷增加。集體經(jīng)濟(jì)水平的提高會加大干部報酬的支出,不僅激發(fā)村干部參與鄉(xiāng)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22],而且可以吸引具有領(lǐng)導(dǎo)力的村莊精英進(jìn)入村干部隊伍[23],村干部整體素質(zhì)和領(lǐng)導(dǎo)力的提升又進(jìn)一步地促進(jìn)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另一方面,隨著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村民的“主人翁”意識和集體意識不斷加強(qiáng),也更注重行使自己的成員權(quán)。在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成效顯著的村莊,成員權(quán)效果出來了,村民參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鄉(xiāng)村治理的內(nèi)在動力顯著增強(qiáng),人心普遍渙散的狀態(tài)變成了主動積極參加共享共治。村民參與性增強(qiáng)后,出主意的人多了,各種要素聚集了,發(fā)展路子寬了,農(nóng)民增收渠道多了。特別是在成員權(quán)明確、股權(quán)量化、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收益分配等方面,不公平、不穩(wěn)定的問題得到極大化解,大大減少了社會糾紛。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民主治理機(jī)制建立起來以后,村民參與政治建設(shè)、社會建設(shè)、文化建設(shè)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普遍增強(qiáng),鄉(xiāng)村有效治理的社會基礎(chǔ)不斷得到夯實。
三、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共富帶動能力亟待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
自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以來,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進(jìn)入了發(fā)展快車道。但總體來看還處于起步階段,與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促進(jìn)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比,改革發(fā)展任務(wù)還相當(dāng)艱巨。當(dāng)前,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發(fā)展還面臨大量困難和問題,突出地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總體薄弱
2020年,我國村集體資產(chǎn)總計59 818.63億元。其中村集體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共計25 196.97億元,占村集體總資產(chǎn)的42.1%。村均資產(chǎn)1 068.8萬元、村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450萬元、人均資產(chǎn)5 892元、人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2 481元。從集體收益分配看,2020年村集體總收益2137.8億元,村均收益38.2萬元,人均收益210元,其中分配給農(nóng)戶的收益為772.27億元,村均13.8萬元,人均76元。根據(jù)國家2020年統(tǒng)計的539 890個村中,經(jīng)營收益在5萬元以下的村占總村數(shù)的45.6%,其中無經(jīng)營收益的村占比為22.5%,而當(dāng)年收益在50萬元以上的村占比不超過10%。總體來看,我國目前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資產(chǎn)較少,收益較低,空殼村數(shù)量較大,大部分資產(chǎn)集中在少數(shù)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如廣東、山東、江蘇、浙江、北京、上海6省(市)村級資產(chǎn)共計31 897.36億元,占全國村級總資產(chǎn)的53.3%,村均2 122萬元,人均13 220萬元,其余25省(區(qū)、市)共占據(jù)不到一半的村級總資產(chǎn)。因此,我國絕大多數(shù)的村集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集體發(fā)展水平較低,帶動農(nóng)民共富能力較弱數(shù)據(jù)來源同腳注①。。
(二)不同地區(qū)集體經(jīng)濟(jì)帶動共富能力不平衡
2020年東、中、西部村級資產(chǎn)分別為39 000.89億元、12 414.96億元 和8 402.77億元,分別占全國村級總資產(chǎn)的65%、21%和14%,村均資產(chǎn)分別為1 667.4萬元、696.2萬元和569.8萬元,人均資產(chǎn)分別為10 800元、3 520元和2 788元。從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看,東、中、西部村均資產(chǎn)為847萬元、182.4萬元和144.6萬元,人均資產(chǎn)為5 486元、922元和708元數(shù)據(jù)來源同腳注①。。從各地區(qū)資產(chǎn)分布的數(shù)據(jù)看,我國集體資產(chǎn)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的集體資產(chǎn)集中在東部,中西部地區(qū)資產(chǎn)相差不大。東部地區(qū)的村均資產(chǎn)、村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人均資產(chǎn)、人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遠(yuǎn)高于我國村集體資產(chǎn)的平均數(shù)。尤其是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幾近村級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平均數(shù)的2倍,而中、西部地區(qū),尤其是西部,村均資產(chǎn)、村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人均資產(chǎn)與人均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均遠(yuǎn)低于全國平均數(shù)。
2020年,東、中、西部集體收益分別為1 602.14億元、298.86億元和236.8億元,分別占總收益的74.9%、14%和11.1%。東部地區(qū)村均收益68.5萬元、人均收益443元,其村均收益、人均收益分別約為中、西部的4倍和5倍。東部地區(qū)可分配給成員的人均收益為195元,中、西部集體成員人均可分配到的收益在10元左右,與東部相差數(shù)十倍數(shù)據(jù)來源于“2020年中國農(nóng)村政策與改革統(tǒng)計年報”。。集體資產(chǎn)分布的不平衡直接影響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不平衡,集體資產(chǎn)較多的東部地區(qū),集體發(fā)展水平總體較高,帶動農(nóng)民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能力較強(qiáng),而中、西部地區(qū)集體資產(chǎn)總量較少,集體發(fā)展水平低,分配給集體成員的收益有限,帶動農(nóng)民增收致富的能力非常薄弱。
(三)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能力不強(qiáng)
從收入結(jié)構(gòu)看,2020年集體總收入為6 320.2億元,其中與經(jīng)營管理活動有關(guān)的收入,如經(jīng)營收入、發(fā)包及上交收入、投資收益、補(bǔ)助收入占比分別為30.6%、15%、4.1%和27.4%數(shù)據(jù)來源同腳注①。。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主要依靠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獲取穩(wěn)定收入,比如土地承包金、集體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用地出租收入,以及政府資金投入,真正參與市場經(jīng)濟(jì)活動,發(fā)展集體產(chǎn)業(yè)所獲收益較少。地處偏遠(yuǎn)的村集體的土地、山林和公房等資產(chǎn)價值低,開發(fā)成本高,難以帶來直接效益,因此村集體收入主要來源于政府投入。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空間小,渠道單一、發(fā)展模式有限,很難通過長效增收產(chǎn)業(yè)增加經(jīng)濟(jì)收入,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不夠。
(四)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需要深化
我國農(nóng)村集體資產(chǎn)總量龐大,截至2020年共核查集體資產(chǎn)7.7萬億元,其中固定資產(chǎn)3.7萬億元,占總資產(chǎn)的48%,資產(chǎn)高度集中在村級。目前集體資產(chǎn)清產(chǎn)核資工作已經(jīng)完成,但仍有401.9億元資產(chǎn)待界定數(shù)據(jù)來源同腳注①。。由政府下?lián)艿姆鲐氋Y金和鄉(xiāng)村建設(shè)資金所形成的大量資產(chǎn),在資產(chǎn)量化確權(quán)過程中存在確權(quán)難、移交難的問題。廣西約有一半的農(nóng)村集體資源資產(chǎn)為村民小組一級所有,但目前組級的改革還集中在城中村、城郊村等少數(shù)集體資產(chǎn)比較多的村民小組開展,尚未普遍推開。農(nóng)村集體資產(chǎn)確權(quán)尚未完全到位,部分村、組的集體資產(chǎn)尚未明晰產(chǎn)權(quán),一些地方的扶貧資產(chǎn)尚未劃歸農(nóng)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管理。由于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成員身份確認(rèn)缺乏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一部分特殊群體的成員權(quán)得不到確認(rèn),對保持農(nóng)村社會安定有序形成了一些隱患。一些地方村集體資產(chǎn)臺賬管理、經(jīng)營合同管理不規(guī)范,民主程序履行不到位,集體資產(chǎn)存在一定的流失風(fēng)險。對于歷史遺留債務(wù),大多數(shù)地方未能有效化解。
(五)經(jīng)營管理型人才匱乏
目前,我國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與村“兩委”實行“一套班子”,村干部在管理村級政務(wù)的同時還需兼顧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發(fā)展,但村干部人數(shù)有限,無法同時兼顧二者,對于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關(guān)注不夠。大部分的村干部受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思維束縛,對新產(chǎn)業(yè)新產(chǎn)品的了解少,接受能力不夠,不懂市場,不善于經(jīng)營管理,無法有效運用集體資產(chǎn)、資源優(yōu)勢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jì)。此外,部分村干部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jì)的積極性不高,一方面村干部認(rèn)為農(nóng)村無資金、無技術(shù)、無人才、無資源優(yōu)勢,缺乏政策支持,發(fā)展難度大,不愿發(fā)展;另一方面,部分村干部認(rèn)為發(fā)展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存在一定的風(fēng)險,不敢發(fā)展,只想依靠物業(yè)出租等方式獲得穩(wěn)定收入來源。
四、發(fā)展壯大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措施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xiàn)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要求。我國已經(jīng)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把實現(xiàn)共同富裕作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重要目標(biāo)。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決不能落下農(nóng)民。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承擔(dān)著確保農(nóng)民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底線任務(wù),要切實深化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加大扶持力度、拓展發(fā)展空間,推動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加快發(fā)展,在帶動農(nóng)民共同富裕上發(fā)揮更大作用。
(一)拓寬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路徑
依據(jù)村集體的區(qū)位優(yōu)勢,資源優(yōu)勢,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情況,因地制宜探索新型集體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路徑。土地資源、礦產(chǎn)資源或生態(tài)資源豐富的地方,可通過開發(fā)當(dāng)?shù)刭Y源,發(fā)展種植業(yè)或旅游業(yè),帶動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于城郊村和城中村等區(qū)域優(yōu)勢明顯的村集體,可通過發(fā)展物業(yè)經(jīng)濟(jì)獲取穩(wěn)定收入;對于農(nóng)業(yè)發(fā)達(dá)或產(chǎn)業(yè)發(fā)展較好的村集體,可通過提供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性服務(wù)或勞務(wù)輸出、技術(shù)指導(dǎo)等中介服務(wù)發(fā)展服務(wù)經(jīng)濟(j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較好,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管理能力強(qiáng),有一定市場經(jīng)驗的村集體可探索自主對外股權(quán)投資的方式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jì),這種方式收益高,但風(fēng)險大。
(二)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發(fā)展多種形式股份合作制
根據(jù)集體資產(chǎn)情況分類施策發(fā)展股份合作制。有集體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的村,通過資產(chǎn)量化,成立股份合作社,農(nóng)民實現(xiàn)“資產(chǎn)變股金”,按股分紅。有土地等集體資源性資產(chǎn)的,積極發(fā)展土地股份合作社,農(nóng)民實現(xiàn)“資源變股權(quán)”,這樣可以有效解決因勞動力進(jìn)城務(wù)工導(dǎo)致土地撂荒等問題,農(nóng)民還可以獲得穩(wěn)定的土地流轉(zhuǎn)收入和分紅。無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和資源性資產(chǎn)的村,要建立統(tǒng)一運行管護(hù)機(jī)制,為集體成員提供公益性服務(wù)。
(三)強(qiáng)化政府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財政政策扶持
農(nóng)村每年的公共服務(wù)事業(yè)與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支出總額較大,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無法完全承擔(dān),應(yīng)增加政府對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的公共財政投入,優(yōu)化對農(nóng)村道路、電力、網(wǎng)絡(luò)等基礎(chǔ)設(shè)施以及農(nóng)村科技、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公共服務(wù)的投入,提高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對于無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或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的村組,政府應(yīng)強(qiáng)化精準(zhǔn)幫扶政策。依據(jù)村集體經(jīng)濟(jì)狀況,每年投入一定的財政資金,幫助村集體經(jīng)濟(jì)實現(xiàn)初期的資金資本積累。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要用好政府投入的各項財政扶貧資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項目資金以及其他涉農(nóng)資金。政府投入資金目的是要增強(qiáng)村集體的“造血”能力和內(nèi)生動力,促進(jìn)集體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村集體要將錢用活,用于發(fā)展村集體產(chǎn)業(yè)項目,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實現(xiàn)集體資產(chǎn)的保值增值,保障集體經(jīng)濟(jì)的長遠(yuǎn)發(fā)展。積極出臺農(nóng)村土地使用權(quán)、林權(quán)、股權(quán)等產(chǎn)權(quán)抵押、質(zhì)押等政策,強(qiáng)化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金融支持,拓展農(nóng)民共富空間。
(四)加強(qiáng)人才隊伍建設(shè)
發(fā)展和壯大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村級班子建設(shè)至關(guān)重要。一要配好村“兩委”班子,選好帶頭人,將懂經(jīng)營、善管理、有技術(shù)、愛奉獻(xiàn)的高素質(zhì)人才配置到村委領(lǐng)導(dǎo)人的崗位上,強(qiáng)化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人才支撐。二要加強(qiáng)人才培養(yǎng)。以薪資、福利待遇為突破點,發(fā)揮剩余索取權(quán)的激勵作用,培養(yǎng)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致富帶頭人,吸引優(yōu)秀人才返鄉(xiāng)入鄉(xiāng)領(lǐng)辦創(chuàng)辦村集體經(jīng)營實體,發(fā)揮能人帶動效應(yīng);加強(qiáng)對村委班子的培訓(xùn)力度,著重提高其發(fā)展壯大集體經(jīng)濟(jì)、帶領(lǐng)群眾脫貧致富的能力。三要加強(qiáng)基層黨建,激活領(lǐng)導(dǎo)班子的動力。強(qiáng)化黨建引領(lǐng),把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干部業(yè)績考核直接關(guān)聯(lián)。選拔一批年輕化、能力強(qiáng)的黨支部書記,注重后備干部培養(yǎng)儲備。培養(yǎng)造就一批熟悉市場經(jīng)濟(jì)規(guī)則、有專業(yè)經(jīng)營管理能力的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管理人才干部隊伍。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較好的村集體可以考慮聘請專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團(tuán)隊,負(fù)責(zé)集體經(jīng)濟(jì)的運行和管理。
(五)加快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立法進(jìn)程
目前,只有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少數(shù)省(市)出臺了農(nóng)村集體資產(chǎn)管理條例等地方性法規(guī)。國家層面缺乏規(guī)范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及其資產(chǎn)經(jīng)營管理的專門法律,關(guān)于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稅收、金融、土地等政策支持明顯滯后。要加快制定“農(nóng)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法”,對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法人屬性、組織架構(gòu)、成員身份、權(quán)責(zé)關(guān)系、運營、國家扶持等作出明確規(guī)定。
參考文獻(xiàn):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wǎng).關(guān)于全面深化農(nóng)村改革加快推進(jìn)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若干意見[EB/OL].(2014-01-19)[2021-01-19].http://www.gov.cn/zhengce/2014-01/19/content_2640103.htm.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wǎng).關(guān)于穩(wěn)步推進(jìn)農(nóng)村集體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的意見[EB/OL].(2016-12-29)[2021-12-29].http://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wǎng).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2018-2022年)[EB/OL].(2018-09-26)[2021-09-26].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4] 郭曉鳴,王薔.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特征、優(yōu)勢與作用機(jī)制[J].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20(12):67-73.
[5] 李韜,陳麗紅,杜晨瑋,等.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壯大的障礙、成因與建議——以陜西省為例[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21,42(02):54-64.
[6] 耿羽.壯大集體經(jīng)濟(jì),助推鄉(xiāng)村振興——習(xí)近平關(guān)于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重要論述研究[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02):14-19.
[7] 王曙光,郭凱.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減貧效應(yīng)與內(nèi)在機(jī)理研究[J].農(nóng)村金融研究,2019(11):3-9.
[8] 崔超.發(fā)展新型集體經(jīng)濟(jì):全面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的路徑選擇[J].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02):89-98.
[9] 趙春雨.貧困地區(qū)土地流轉(zhuǎn)與扶貧中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發(fā)展——山西省余化鄉(xiāng)扶貧實踐探索[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7,38(08):11-16.
[10] 楊博文,牟欣欣.新時代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鄉(xiāng)村振興研究:理論機(jī)制、現(xiàn)實困境與突破路徑[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與管理,2020(06):5-14.
[11] 陳錫文.充分發(fā)揮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22,43(05):4-9.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wǎng).關(guān)于支持浙江高質(zhì)量發(fā)展建設(shè)共同富裕示范區(qū)的意見[EB/OL].(2021-06-10)[2021-10-10].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3.htm.
[13] 唐鑫.正確理解共同富裕理論內(nèi)涵的四維審視[J].社會主義研究,2022(02):1-8.
[14] 衛(wèi)興華.論社會主義共同富裕[J].經(jīng)濟(jì)縱橫,2013(01):1-7.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示范章程(試行)[EB/OL].(2020-12-20)[2021-02-01].http://www.moa.gov.cn/nybgb/2020/202012/202102/t20210201_6360834.htm.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wǎng).關(guān)于抓好“三農(nóng)”領(lǐng)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xiàn)小康的意見[EB/OL].(2020-02-05)[2021-02-05].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5/content_5474884.htm.
[17] 高鳴,魏佳朔,宋洪遠(yuǎn).新型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戰(zhàn)略構(gòu)想與政策優(yōu)化[J].改革,2021(09):121-133.
[18] 王磊.閔行做強(qiáng)集體經(jīng)濟(jì)讓農(nóng)民“業(yè)主”收入持續(xù)增長[EB/OL].(2020-02-07)[2021-02-07].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002/07/321722.htm.
[19] 吳濤.浙江鄉(xiāng)村觀“共富”:嘉興村集體經(jīng)濟(jì)何以突破300萬大關(guān)[EB/OL].(2022-03-19)[2022-03-20].http://www.chinanews.com.cn/sh/2022/03-20/9706859.shtml.
[20] 蘇州市人民政府網(wǎng).蘇州市提升壯大村級集體經(jīng)濟(jì)助推鄉(xiāng)村振興[EB/OL].(2020-02-05)[2021-02-05].http://www.suzh.gov.cn/szsrmzf/bmdt/202102/aa5cc2ba48484723995db7e9bc7b399b.shtml.
[21] 王曙光.中國扶貧[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0.
[22] 徐朝衛(wèi),董江愛.資源型村莊治理中集體經(jīng)濟(jì)的多重效應(yīng)——基于山西H村的經(jīng)驗分析[J].貴州社會科學(xué),2018(07):163-168.
[23] 付明衛(wèi),葉靜怡.集體資源、宗族分化與村干部監(jiān)督制度缺失[J].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7(03):2-15.
The Effec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UANG Yuanpei,PENG Lingfeng
(School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and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driving farmers to get rich together,and summarizes the main ways to drive farmers to get rich togeth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total data,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facing problems,such as the weak founda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assets,the weak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the lack of management talents,and the imperfection of collective asset management related to systems and laws.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ways to develop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1)broaden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2)developing various forms of joint-stock cooperation system;(3)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4)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policy support;(5)accelerat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Key words: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common prosperity
(責(zé)任編輯:董應(yīng)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