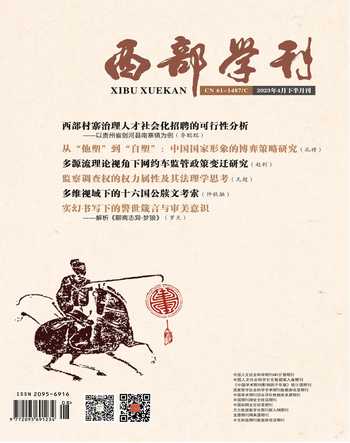先秦儒家道德認識論中言象意的關系
周子琳 劉正平
摘要:中國傳統認識論以道德為主要認識對象,先秦儒家的道德認識論存在兩個階段,即道德理論認識以及道德實踐。先秦儒家道德認識中言象意的關系:言不盡意。由于“道”的先驗性決定了在道德原理認知階段,道德之“言”與道德之“意”之間呈現的是言不盡意的關系。以象表意。教育的過程是接受典范人格耳濡目染的熏陶。從而觸發內在道德心象的顯現,激發出如不忍、惻隱、悲憫、憐愛等道德情感。先秦儒家道德實踐中言象意的關系:(一)孔子“學思并行”;(二)孟子“擴充本心”;(三)荀子“聞見知行”。獲得完善的道德認識需要言、象、意的貫通,即只有從道德心出發,依據道德原理指導,規范道德行為。
關鍵詞:先秦;道德認識論;言象意;道德實踐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3)08-0165-04
“言意之辯”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專題,它興盛于魏晉時期,當時眾多名士都熱衷于討論儒家經典文字與圣人之意之間的關系問題,希望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以把握至真之理,玄學家對此問題的論述成為魏晉玄學大多哲學理論的思想基礎。“言意之辯”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前人對此專題的研究成果可謂浩如煙海。目前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將“言意之辯”視為方法論來研究。自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論稿》中將“言意之辯”視為玄學家建構魏晉玄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以來,前人研究多集中在以“言意之辯”為方法對魏晉時期的解經、建構形上學、會通儒道二家之學等方面的作用與意義。其二,將“言意之辯”視為認識論來研究,主要在道家哲學思想體系中分析言意關系,將玄妙的道視為最高認識對象并強調以“黜聰明”“心齋”“坐忘”等方式才能把握道。其三,分析總結“言意之辯”對美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中國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的影響。雖然從認識論領域來研究“言意之辯”的成果已非常豐富,但大多將研究對象的歷史限定在魏晉時期且側重于在語言哲學和邏輯學視域下來分析認知問題。本文從言象意辯證關系分析先秦儒家道德認識論,有助于呈現先秦儒家在德性認知與道德活動之間的辯證關系。
一、儒家道德認識論
認識論非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概念,近代西方哲學傳入中國以來,為了滿足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需要,出現“以西釋中”的詮釋潮流,“認識論”一詞從而被廣泛使用。雖然中國傳統哲學中沒有認識論的概念,但卻不乏對認識對象、認識主體的理論反思。早在《尚書》中就記載有古人關于“知”的思考,如“知人則哲”“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1]“知人”即能鑒識人的品行才能。“知之”指通曉事理。中國古代追求的知識內容不僅有認識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也有認識主體自身德性品性。不同于以科學知識論為主流的西方傳統認識論,中國傳統認識論以道德為主要認識對象,這是自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對性與天道、認識自我與認識世界的探索過程中劃定的中國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內容。
先秦儒家的道德認識論在邏輯上存在先后兩個階段,即道德理論認識以及道德實踐。道德理論認識指明的是認識主體所知的對象,在先秦儒家道德認識論中,認識的終極對象就是超越經驗世界的“道”。超越性的“道”,我們應如何學?“曰于文。圣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2]243圣人體道之后,通過文章言辭將道德認知表達出來或者以身作則使“道”在行為舉止中顯著,如此我們可以通過圣人言傳身教來認識道。但是,識得道德本體只是道德認識的一個前提條件,并不意味著道德認識過程的完成。因為對主體而言,言辭所表達的“道”本質上還是屬于概念認知,這與超越經驗世界的道德本體根本屬性不同。同時,先秦儒家認為體“道”完全是個體自覺的行為,正如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2]367孔子對人性與天道的覺知是一種自我內在覺解,這種體悟離不開當時的境遇,具有鮮活性、時效性、切己性,不可能通過重復或者模仿孔子來獲得其證道的體驗,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947道德認知主體只有自己參與到道德實踐中才能獲得對“道”的真切感知并使自己成為“道”的載體將“道”落實在事事物物中,如此才算是道德認知的完整過程。
二、先秦儒家道德認識中言象意的關系
(一)言不盡意
孔子創造性地將“仁”納入“禮”的范疇,使得作為一種制度設計和秩序安排的周公之禮轉化為以“仁”為最高道德準則,引導個體修養和道德實踐的禮儀規范。仁與禮既是孔子道德認識論中的兩大支柱,也是主要認識對象。仁是禮的實質內涵,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禮如果沒有仁的內涵,無法發揮指導人的道德修養的作用,人不知禮就無法在在處處指點為仁。孔子安仁、學禮的目的是“達道”。孔子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2]282“聞道”在孔子看來,是終極意義的追求,是生命意義的證成,“孔子的一生就是‘志道’‘學道’‘行道’的一生。”[3]道德認識的實踐要求以及“道”的先驗性決定了在道德原理認知階段,道德之“言”與道德之“意”之間呈現的是言不盡意的關系。孔子對仁與道的證悟,是在其努力好學并持續不斷地自證自知的過程中實現的。在旁人看來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4]106,就連顏回也感嘆:“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685但是,顏回接著說道:“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2]686道德之“言”是道德倫理的載體和直接反映,孔子在教化弟子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通過言辭來說明仁,并強調禮的學習,在經驗世界中,按照禮所規定的有序行為模式獲取仁的內在品質。荀子也重視禮的學習,他將禮作為道德認識論建構的邏輯起點,禮既是最高道德認識層次道的體現,又是引導落實道德實踐行為的道德規范。“君子處仁以義,然后仁也;行義以禮,然后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后禮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5]492《顏淵》篇記載了樊遲向孔子問仁,孔子的回答概括出了仁的基本含義:“樊遲問仁,子曰:‘愛人’。”[2]1005仁是人之為人的本質,但僅有仁愛之情并不足以促使人格的完善,孔子強調“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2]1387人在孝敬父母關愛他人的過程中要使自己的“親親”之情恰當地表達出來,需要學禮、知禮、行禮,所以在顏淵問仁時,孔子又說“克己復禮為仁”[2]942,此處孔子十分強調行仁的為學修己工夫。另外,還有仲弓問仁、子貢兩次問仁,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孔子主要是從個體修養、與人相待、執事這幾個方面來釋仁[6]。這體現出仁具有豐富內涵,但也說明語言表述“仁”的局限性,孔子釋“仁”多是自己道德情感體驗的抽象概括總結,語言消解了許多促使孔子當時道德情感發動的情景和語言無法表述的感受,所以道德教化同時還需要以象表意的方式來進一步清晰地顯明“意”。
(二)以象表意
孔子通過以身作則,彰顯人格感召力的方式來深化弟子們對“道”的認知。孔子曾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2]1037“教育的過程就在于接受典范人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熏陶。”[7]孔子常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禮節態度、容貌言辭、飲食衣著等表達他對禮、仁、道的認知。如《鄉黨》中就詳細記載了孔子如何具體行仁:孔子在朝和在野時不同的言行態度表現在“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2]733-734,孔子對長者的尊敬表現在“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2]812,孔子在生活飲食方面的講究表現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2]794。孔子就是通過這樣春風細雨、潤物無聲的方式為弟子們樹立楷模,加深弟子們的道德認知。
孟子以內在的道德心象為道德認知提供論證依據,在《孟子·公孫丑》中,孟子以“孺子入井”來舉例說明人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4]221。他設定“孺子入井”的危急場景,人運用回憶、聯想、想象的能力去感知危難者所處境況,從而觸發內在道德心象的顯現,激發出如不忍、惻隱、悲憫、憐愛等道德情感,即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將此惻隱之心擴展開來則包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四心”是仁義禮智的發端。孟子以人人能親身所見、所感、所知的道德之象來證明人人本有的道德屬性,為主體的道德修養提供堅實基礎。
三、先秦儒家道德實踐中言象意的關系
在道德認知實踐階段,對主體來說言象意之間又存在著由明了道德之“意”向道德之“象”以及道德之“言”落實于經驗世界的趨向,即立象以明意。“象”具有與“道”相似的特性,首先“象”具有原發性,“象”總是跟隨著事物的動態生成過程,因此把握“象”的思維方式也是前語言、前邏輯的思維,而語言、邏輯的概念思維是事后的反思,是在事物發展歷程結束之后生成的。其次“象”是非對象性的,“象”的顯現總是發生在事物生成過程中,總是處于未完成的狀態[8]。最后“象”具有整體性,從人與自然的原始親和關系而言,“象”與實在的自然世界和人的百感、生命、精神境界緊密相關。所以以“象”作為跨越言、意之間認知隔閡的中介,通過意象思維和道德實踐中直觀體認“象”以及能動地創造“象”“言”的方式達到對“道”的把握和彰顯,進而貫通言與意。
(一)孔子“學思并行”
道德實踐過程中,具體如何“以象盡意”實現向善工夫的完成呢?在孔子看來,這不僅要“博學多聞”,更要“慎思篤行”。孔子曾評價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555孔子強調:“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2]566在積累經驗認知的過程中,孔子還非常重視“思”的功能,“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2]1327思可以幫助認識主體在日常生活中言行舉止恰當適宜,增強認識主體在道德實踐中的決斷力和執行力[9]。如果說“學”在道德意識活動過程中指向“去蔽”的話,那么“思”就是道德實踐活動中趨向“通明”,也即《大學》中所說的“明明德”。“明明德”一方面指向個體修身,修身最關鍵的是躬行實踐,“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2]362孔子以是否身體力行作為檢驗道德修養的標準。另一方面指向“修己以安百姓”[2]1196的道德教化事業,孔子塑造的理想人格不僅具有崇高道德操守還能成就一番事業,達到“博施于民而能濟眾”[2]493的境地。
(二)孟子“擴充本心”
孟子在孔子“學思并進”的認知徑路上開啟了儒家擴充本心的工夫論。他認為人天生就具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4]331但這并不意味著孟子否定人的認識實踐活動,“良知”“良能”更確切地來說是人先天具有的認識能力,是為人達至超越性的認知目標提供的根據,要切實體貼、領悟“道”還必須在日常學習生活中不斷擴充、充實“良知”“良能”。要從日常道德認知實踐向完善的人格境界超越,孟子提出“盡心—知性—知天”的修習路徑。“盡心”在道德認知實踐中包含三層意思:首先是從道理上知道如何實施道德行為,使得認知不斷擴充、豐富,這要求主體依習俗、禮法、圣人教誨來認知。其次是“敬以直內”,即通過心之總象來認知心,在主體認知官能“心”與外界交互過程中會產生內在的心象,這包括道德性的心象與情緒性心象,是主體在當下狀態立即能感知的。如見孺子入井,主體不僅能認知到當下危險狀況,還能立即感知道德心發動產生惻隱之情的情動狀態。最后是禮、敬合一,單純學習禮主要是認知心起作用,不足以促使道德認知主體堅定地實施道德行為,而只有道德心發動也無法保證行動的恰當適宜,只有“敬”“禮”合一才能保證道德心象不失并產生有效的行為結果。
(三)荀子“聞見知行”
荀子將人的認識活動分為聞、見、知、行四個階段。他在《荀子·儒效》中說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5]142在荀子看來行是認識的最終目的,也是認識的完成,是認識最重要的階段。雖然荀子認為聞、見、知都不如行,但并不意味著他否認一般經驗知識。他主張學習《詩》《書》《禮》并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價值標準。人之所以能學,在荀子看來,是因為人“心”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5]406“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5]395-396心是普遍性、抽象性、超越性的“道”之主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5]423心為認識道提供了依據,如何依心來認識道?從內在修身而言,荀子提出“虛一而靜”的認識方法,“虛一而靜”要求人排除外界和內心的一切干擾,使精力高度集中達到對事物透徹無偏弊的“大清明”認識境界。從外在經驗積累而言,荀子提出“所積而致”的成圣之道。荀子認為圣人與普通人的才性是相同的,后天的修習才造成圣人與凡人在德性上的差別,“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后備者也。”[5]63后天修為既包括荀子所說的知識積累,也包括道德修養,即向內去除雜染妄念,向外實施道德實踐行為。
道德認知的完整過程并非僅是主體自身內在人格境界的提升,“道”的證成也會通過認知主體的身體以可見的、有形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孟子所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4]332從道德修養來看,認識主體道德實踐行為的效果以認識主體的身體為載體顯現出來,這種象表現為主體實施道德行為過程中的語言、行為,還表現為主體“成德”后身形的轉變。
結語
在先秦儒家道德認識論中,“言不盡意”與“立象以盡意”是主體道德認知過程中運用不同認知方式呈現出的兩種不同結果,它們區分出了道德認知過程中思維方式和認識領域的不同,在單純的道德觀念輸入和道德原理教育過程中,主要是主體的認知心起作用,認知心能知善惡但不能發動實際行動以成就善,所以由思辨所得的認識并非真正的、完善的道德認知。另外,單純依靠道德心的發動而實施的道德行為如果不是通過道德原理和禮儀規范的學習而來就只有通過模仿別人的行為習得,在這一過程中,主體對外在的善惡判斷標準沒有準確的認識,其行為就容易受外物干擾,正如荀子所說:“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5]404獲得完善的道德認識需要言象意的貫通,即只有從道德心出發,依據道德原理指導,規范道德行為。主體須努力奮進,不斷在道德實踐中擴充仁心,使其由內發乎外,最終上達于天道。言象意的貫通是概念思維和意象思維的統一,是認知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統一,也是經驗知識領域與超越性的最高層次道德認識“道”的統一。先秦儒家的道德認識過程不僅是認識主體下學上達的修習過程,也是認識主體“居敬存誠”“成己成物”擴充自心,旁通物則的過程。
參考文獻:
[1]吳瑾菁.道德認識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
[2]劉寶楠.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王雅,楊義.論孔子之道的現實性與形上性[J].孔子研究,2017(6).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王先謙.荀子集解[M].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6]車載.孔子論仁[J].文史哲,1961(3).
[7]宗超.論孔子的“人格之教”[J].孔子研究,2016(5).
[8]張祥龍.概念化思維與象思維[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9]孫齊魯.孔、孟、荀學思觀辨略[J].孔子研究,2009(6).
作者簡介:周子琳(1996—),女,漢族,四川廣安人,單位為昆明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
劉正平(1972—),男,漢族,山東招遠人,博士,昆明理工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佛教哲學。
(責任編輯:趙良)